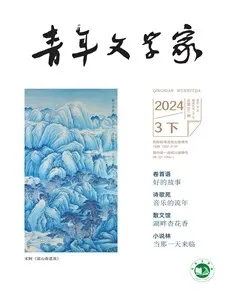南方的春天
熊佳林
驚覺春天的到來,是騎單車路過一樹繁花的時候,聞到了那彌漫在空氣中清新的花香。坐在車上,春天于我只是窗外的浮光掠影,但騎單車就不一樣了,穿行在一樹樹花枝下,雨絲中飄落了一地細碎的花與葉,抬頭一看,那密密的新葉不知什么時候冒了出來,這城市里見縫插針的春天呀,它還是來了。
風鈴木的春天是短暫的,它就像一場盛大的煙花,讓人又驚喜又憂愁。在藍天映襯下,一團團如火焰般肆意而濃烈的金黃的焰火,好像要把天幕點燃。沒有風鈴木肆意燃燒過的春天,好像一個人沒有經(jīng)過快意恩仇的青春,終是不完整的。它是天地間最調(diào)皮的那個精靈,不經(jīng)意地來,匆匆又溜走。一不留神兒就錯過了街口的黃色風鈴木盛開,等我看到的時候,枝頭只擎著零星幾朵,那沉寂的背后,只有飄零的豆莢和新葉,好像煙花過后余下的灰燼,只能在空氣里作甜蜜的回想。風鈴木,多好的名字呀!曾經(jīng)有多少串風鈴在我們的春天里叮叮當當?shù)負u過呢?它去了哪里呢?是不是變成街頭騎著單車搖著鈴鐺擦肩而過的少年?曾經(jīng)錯過的一場又一場風鈴木,會不會在以后加倍還回來呢?
木棉花的春天是孤傲的,它在高高的枝頭,仰望天空吹響春天的號角。那一朵朵質(zhì)地堅硬的五瓣花,像一只只對著藍天鳴放的小喇叭。在鄉(xiāng)下,春天是布谷鳥叫來的,那悠長婉轉的布谷聲,在寂靜的村莊里回蕩,然后才是田野一夜之間鋪上了一層新綠。你能聽見鳥兒的叫聲,你卻不曾聽見城里這高架橋下、高樓大廈之間小喇叭嘟著小嘴的一聲聲號響。先是枝頭的舊葉掉光,騰出了營地,然后光禿禿的粗枝上,綻放了第一朵,它陸續(xù)叫醒了其他的花苞,好像清晨營地里的哨兵。它們鉚足了勁兒,把整個枝頭都染紅了,有一天你突然抬頭看,才發(fā)現(xiàn)它遠遠地停在那里,轟轟烈烈的一片紅云。木棉的謝幕也是剛烈的。一朵木棉花,從高高的枝頭突然掉下,啪的一聲,好像突然被暗地一道寒光冷劍刺中的俠客,帶著幾分墜入塵泥的決絕,跌倒在地,卻依然保持著高傲且倔強的姿勢。一朵接一朵,漸漸滿地都是,長劍跌落在地,飄飄衣袂被漸漸滲透的血跡染紅。分外醒目的木棉花,立在那舊日的街道,俯視著人群潮來潮往。布吉,那舊世界里的輝煌已歸于沉寂,如今又舊又堵。人群也是灰蒙蒙的,與提著行李箱、塑料桶的人們擦肩而過,他們好似遷徙途中沉默的鳥。出了地鐵站,路旁就停留著三三兩兩拉客的摩托車,他們低聲地吆喝,對每一個走出地鐵口的人滿懷期待。摩托輕松地跨越一排排擁堵的汽車,像飛翔在水面的燕子,滿滿的優(yōu)越感,雖有點兒冒險,但是又能在風里自由穿梭。付了款之后,聽到身后載客的大叔在盛開的木棉樹底下夸張地大聲對我說:“妹子,你是個好人,祝你一生都平安!”這樣的祝福已經(jīng)意味著人海中的偶遇今生不會再相見,也不會再相識,因而顯得特別真摯而有趣。
三角梅的春天是熱烈的,霸道且鋪張。它藏在尋常巷陌,在舊時的房子陽臺上,在磚瓦縫隙之間,出其不意地闖入你的眼簾,讓人暗暗心驚。最神奇的是園博園的那一株三角梅,好像一個人要從頭到尾霸占整個春天。那是一整株的老樁三角梅,藤蔓交織,曲折迂回,一院子都是它。而馬路兩旁的三角梅像鮮紅的地毯,一路鋪向天邊,鋪向那花海的深處。深一腳淺一腳,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踏進了它為你鋪好的夏天。
在黃昏的春天里靜坐,也能感受到涌動的春的氣息:暮色將遠處的海灣卷起浪潮,將近處的層層樓宇淹沒,等那星星點點的萬家燈火亮起,照亮那一樹樹的繁花。即使是燈影闌珊、人聲鼎沸處,空氣里也彌漫了荔枝樹濃郁的花香。街頭紫荊花瓣的飄落是無聲的,隨風而散,好像那不經(jīng)意回眸的淡淡一瞥。而木棉凋謝后,不久就會在枝頭掛起一團團的木棉絮,被風吹得滿地拉拉扯扯,像絲絲縷縷的離愁。那個時候,夏天的風已經(jīng)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