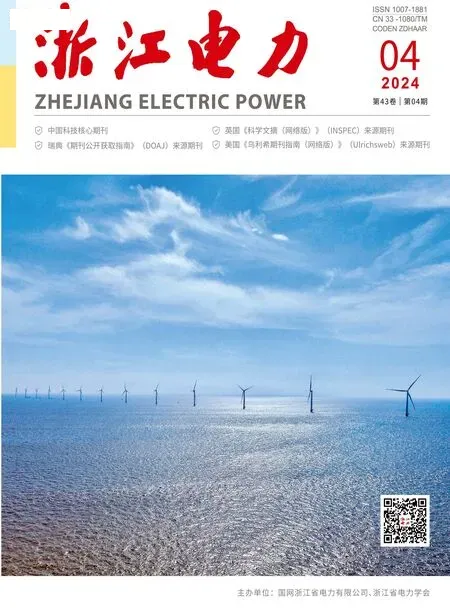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優化調度方法
朱丹丹,賈勇勇,周前
(國網江蘇省電力有限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南京 210000)
0 引言
我國風電發展迅速,但由于電網調峰能力不足,大規模風電消納形勢不容樂觀,江蘇等省份面臨調峰資源緊張的問題。研究表明,將負荷側可調節資源[1]納入電力系統調度范圍以提高風電消納水平[2-6]是拓展調峰資源、緩解棄風問題的有效途徑。
然而負荷側可調節資源包括海量的分布式可控負荷[7]。針對全部負荷個體進行直接調度對電網而言成本太高,控制過于復雜[8],負荷聚合商[8-9]作為大量中小規模可調節負荷資源與電網調度中心的中間協調機構,在負荷側可調節資源參與電網調節實踐中可發揮重要作用[10]。
對于負荷聚合商參與下的荷源協調調度,前人已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在調度方法方面,文獻[11]在綜述發達國家負荷聚合商實際應用的基礎上,提出了結合國內實際情況的實施方法及途徑,為我國的負荷側資源通過負荷聚合商參與電網調節提供了參考。文獻[12]建立了空調聚合商參與的配電網溫控負荷控制與運行重構策略模型。文獻[13]提出了考慮公平性的多負荷聚合商參與的動態需求響應方法。但以上文獻側重于以削減負荷為出發點的調度模型建立,無法直接應用于受阻風電消納過程。在負荷參與調節相應的價格機制方面,目前主要分為兩種類型[14],直接電價引導和補償機制。由于直接電價引導對于部分負荷作用有限[14],因此本文采取補償機制。文獻[15]根據負荷調節意愿和負荷的性質將負荷劃分為3個等級后,不同等級給予不同的補償價格,但未給出具體的等級劃分方法以及從等級到獎勵價格的計算方法。文獻[16]根據用戶合同違約百分比,對負荷聚合商實行等級化補償。文獻[17]在計算負荷聚合商違約率的基礎上,利用分段線性函數建立了各負荷聚合商的補償價格與其違約率之間的關系。但將負荷聚合商的補償價格與其違約率相關聯,反而會使得違約率高的負荷聚合商因其補償價格低而在最小化調度成本目標下具有調節容量優先分配權,可能導致系統中出現大量的違約電量。
此外,目前的荷源協調調度[16-17]僅考慮了用戶側由于意愿等產生的概率性違約行為,而忽略了僅以調節能力上下限表征負荷聚合商調節特性[8-9,13,17]的情形下,受其所聚合終端的調節特性限制將導致的必然違約。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了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并通過算例分析驗證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1 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
1.1 負荷聚合商的必然違約電量
負荷側可參與受阻風電消納的調節資源眾多,本文主要考慮離散可調節負荷終端[18]。離散可調節負荷除了調節上下限外,還受到功率穩定運行時長的限制,調節曲線表現為矩形波。具體調節特性曲線可參見文獻[18]。
調度在進行電網調節需求分配時,通常將負荷聚合商向上報的意愿調節功率作為其調節上限[17],繼而制定各負荷聚合商的調節任務。但由于離散可調節負荷終端的存在,負荷聚合商的總體調節特性無法以調節上下限表征,即調度下達的某些調節任務雖然處于負荷聚合商的調節上下限內,負荷聚合商卻無法完成。由此產生的違約電量,本文稱之為必然違約電量。必然違約電量與負荷終端的調節意愿無關,需要與負荷終端調節意愿導致的概率性違約相區別,以下稱概率性違約產生的違約電量為可能違約電量。
以某一僅聚合了一個離散可調節負荷終端的負荷聚合商為例,對調節過程的必然違約電量進行說明,如圖1所示。需要說明的是,負荷聚合商上報調節功率時,必然會考慮其負荷終端的調節能力,因此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上限曲線(圖1 中的橙色曲線)是一條可執行的調節功率曲線。

圖1 負荷聚合商參與調節過程中的必然違約電量Fig.1 Inevitable default energy of load aggrega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gulation
由圖1可以看出,調節任務曲線雖然在負荷聚合商的調節上下限(本文的下限為0)范圍內,負荷聚合商卻受限于負荷終端的離散特性,無法完成調節任務,產生必然違約電量。
1.2 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
為了降低在荷源協調過程中產生的違約電量,需要在荷源調度過程中考慮負荷聚合商的必然違約行為。此外,根據違約率確定補償價格[16-17]會使違約率高的負荷聚合商因其補償價格低而在最小化調度成本目標下具有調節容量優先分配權,從而使得可能違約電量較高,因此,需要尋找新的補償價格確定依據。為此,本文定義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為:負荷聚合商完成調節上下限內調節任務的能力。定義負荷聚合商i資源靈活度βi為:
當負荷聚合商i能完全完成調節任務時,其資源靈活度為βi=1。
1.3 基于資源靈活度的負荷聚合商補償價格
本文將負荷聚合商的補償價格與其資源靈活度相關聯。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越高,可以更好地響應電網的調節需求,補償價格越高;相反,負荷聚合商的靈活度較低,則適應電網調節需求能力越低,補償價格越低。設對電網而言,負荷聚合商的理想靈活度為β0,對應補償價格為R0,靈活度βi相對應補償價格Ri為:
通常,電網理想中的負荷聚合商能完全執行調度下達的分配任務,即理想靈活度β0=1。理想靈活度對應補償價格可結合本地標桿價格及調節成本等綜合確定。
2 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模式
本文主要設計負荷聚合商與調度中心之間的協調調度模式,具體如圖2所示。在該模式下:

圖2 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模式Fig.2 The load-source coordinated scheduling model considering resource flexibility of load aggregators
1)風電場將風電預測數據上報調度中心。
2)調度中心進行常規調度(不考慮負荷調節能力)后,將受阻風電功率下發給各負荷聚合商。常規調度及受阻風電功率下發過程中,調度中心可將當地風電功率的預測水平考慮在內。
3)負荷聚合商根據意愿調節功率上報模型,上報意愿調節功率曲線。
4)調度中心根據各負荷聚合商的資源靈活度,確定各聚合商補償價格。結合受阻風電功率及意愿調節功率,建立調度中心容量分配模型,計算各負荷聚合商的初分配調節功率,并下發至各負荷聚合商。
5)負荷聚合商根據調節功率確認模型,對調度初分配的調節功率進行調整確認,將確認調節曲線上報至調度中心。將確認調節曲線作為負荷聚合商可完成調節功率,將調度中心初分配調節功率作為調節任務,根據式(1)、式(2)進行負荷聚合商的資源靈活度計算。
6)調度中心將最終調節曲線、受阻風電消納曲線分別下發給各負荷聚合商及風電場。需要說明的是,調度中心將負荷聚合商調整確認后的調節曲線作為最終調節曲線。
相較于文獻[17]中的調度模式,增加了負荷聚合商對調度中心分配調節曲線進行調整確認的環節,可避免調度優化分配后的調節曲線與各負荷聚合商調節特性不匹配而產生違約電量。此外,通過負荷聚合商的補償價格與其資源靈活度相關聯,使得資源靈活度低的負荷聚合商具有低價優勢,一方面可在調度分配調節容量時,最大程度保持靈活度低的負荷聚合商上報調節曲線的波形,最終降低負荷聚合商必然違約電量;另一方面可避免根據違約率分配調節容量[16-17],將調節容量優先分配給違約率高的負荷聚合商,從而產生大量可能違約電量(概率性違約)。本文采用文獻[16-17]中違約率的概念,即本文所提到的違約率僅表征概率性違約行為而不包括必然違約行為。
3 負荷聚合商決策模型
在本文提出的荷源協調調度模式下,負荷聚合商需進行兩次決策,分別為意愿調節功率上報及調節功率確認。
3.1 負荷聚合商意愿調節功率上報模型
負荷聚合商根據調度中心下發的受阻風電功率信息,結合自身調節特性,進行意愿調節功率上報[17]。
意愿調節功率上報過程中,負荷聚合商以上報的調節電量最大為目標:
式中:E0為負荷聚合商上報的意愿調節電量;為負荷聚合商上報的意愿調節功率;T為控制期內時段數,Δt為每一時段的持續時間,本文取T=24,Δt=1 h。
式中:j為負荷聚合商i下的第j個負荷終端;為負荷終端j的調節功率;NT為負荷聚合商下負荷終端個數。
負荷聚合商上報意愿調節功率時,一方面需要考慮調度下發的調節需求約束,見式(6);另一方面需要考慮其代理的各負荷終端的調節特性約束,主要包括調節上下限約束,調節次數約束,功率穩定運行時長約束等,具體參見文獻[18]。需要指出的是,功率穩定運行時長約束針對有功率穩定運行時長約束的負荷終端,如部分工業負荷等,對于其他負荷則略去該約束。
3.2 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確認模型
負荷聚合商根據調度中心初分配的調節功率,結合自身調節特性,進行調節功率確認。
調節功率確認模型與3.1節中所述的意愿調節功率上報模型基本相同。不同之處僅在于,決策變量由意愿調節功率變為確認調節功率,調度調節需求約束變為:
由確認調節功率與調度中心初分配調節功率可計算負荷聚合商i的調整電量Ei,J。
4 調度中心容量分配模型
調度分配調節容量過程中,希望在盡量多消納受阻風電的同時,調度成本最小。因此以消納受阻風電最大及調度成本最小為目標,建立多目標容量分配模型如下:
1)目標函數
式中:EWc,stuck為控制期內消納的受阻風電電量;C為控制期內的調度成本;為消納的受阻風電功率;NA為參與容量分配的負荷聚合商個數;Ri為電網對負荷聚合商i的補償價格。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促進受阻風電消納,因此,將受阻風電電量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求解時采用加權系數法[19]將上述多目標化為單目標,如式(11)所示。
式中:α1和α2為權重系數,α1+α2=1,α1?α2;為了統一單位,設置EWc,stuck和C對應的標幺化基準EB和CB。
2)約束條件
(1)調度中心為負荷聚合商分配的調節功率不大于負荷聚合商上報的意愿調節功率。
(2)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之和等于消納受阻風電功率。
(3)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之和不大于受阻風電功率。
5 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
本文提出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如圖3所示。

圖3 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Fig.3 The load-source coordinated scheduling method considering resource flexibility of load aggregators
1)調度中心將風電受阻情況下發至各負荷聚合商。
2)負荷聚合商根據受阻風電功率及其下各負荷終端調節能力,建立負荷聚合商意愿調節功率上報模型,上報負荷聚合商意愿調節功率。
3)調度中心根據各負荷聚合商上報的意愿調節功率和資源靈活度,建立調度中心容量分配模型,形成初分配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并下發。
4)負荷聚合商根據初分配調節功率及自身調節能力,建立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確認模型,形成最終調節功率曲線,并上報。該過程中由于負荷調節特性限制無法完成調度下發調節曲線的負荷聚合商,可對調度下發曲線進行調整,調整前后曲線差別將被系統用于對各負荷聚合商進行資源靈活度評估。
5)電網調度中心根據各負荷聚合商返回的確認調節功率,確定受阻風電消納功率,見式(13),形成最終荷源協調調度方案。
6 算例分析
6.1 算例介紹
某地電網由于電網調節能力不足產生受阻風電,設該電網中的負荷聚合商A、B、C共同參與受阻風電消納調節,各聚合商下的負荷終端調節特性如表1所示,仿真日當天負荷聚合商最大調節能力及受阻風電預測功率曲線如圖4所示。采用文獻[16]中的概率模型對違約率進行估計,取聚合商A、B、C 的特性系數分別為0.1、0.16、0.15,得違約率估計值分別為8%、13%、12%。

表1 各負荷聚合商下負荷終端特性Table 1 Load term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ad aggregators

圖4 計算日受阻風電及負荷聚合商數據Fig.4 The calculated daily curtailed wind power and load aggregator data
6.2 負荷商資源靈活度及補償價格計算
將各負荷聚合商的資源靈活度初始值均設為1,以連續120 d 的受阻風電為基礎,根據本文提出的資源靈活度計算方法,逐天計算聚合商資源靈活度。計算結果如圖5所示。

圖5 連續120 d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Fig.5 The resource flexibility of load aggregators over 120 days
由圖5 可以看出,聚合商C 的資源靈活度最高,一直維持在1,說明所計算的120 d 期間,聚合商C對調度中心初分配的調節功率未進行調整,即負荷聚合商C 無法完成的調節功率為0,見式(1)、式(2);聚合商B 的總體靈活度高于聚合商A,與負荷終端特性呈現的直觀感受一致。此外,從圖5的波動可以看出,聚合商A的靈活度經歷一定程度的上升之后,會出現一次相對較大幅度的下降。這是由于靈活度計算值上升到與實際靈活度不匹配的時候,相應補償價格上升,調度中心不再優先為其分配調節容量,初分配的調節功率波形將偏離其上報的意愿調節功率波形,使得在負荷終端調節特性約束下負荷聚合商A 無法完成的調節功率較大。根據式(1)和式(2)對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定義,在下一輪資源靈活度評估時,聚合商A 的靈活度計算值出現大幅下降。可見,在本文提出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下,計算出的資源靈活度可自然被約束在合理范圍內。
在以上資源靈活度計算結果的基礎上,由式(3)計算負荷聚合商補償價格。負荷聚合商的資源靈活度及補償價格如表2所示,理想資源靈活度對應補償價格取60美元/MWh。

表2 負荷聚合商參數Table 2 Parameters of load aggregators
6.3 計算結果
考慮表3所示的4種不同調度方法,分析荷源協調調度的計算結果。

表3 調度方法說明Table 3 Description of scheduling methods
6.3.1 違約電量分析
各負荷聚合商上報的意愿調節電量、調度中心初分配的調節電量及各負荷聚合商確認調節電量如表4所示。從表4中可以看出,由于調度中心無法獲知負荷聚合商所有負荷終端的具體調節特性,負荷聚合商可能無法完成調度中心初分配的調節任務。方法2及方法4下的聚合商調節確認環節,聚合商對于終端特性限制無法完成的調節任務進行了調整,調整電量分別為1 049.7 MWh 和110 MWh。不同調度方法下的違約電量分析如表5所示,其中可能違約電量的估算方式為:(最終分配調節電量-必然違約電量)×違約率。

表4 負荷聚合商參與下的荷源協調調度結果Table 4 Results of the load-source coordinated scheduling with load aggregators involved MWh

表5 不同調度方法下的違約電量分析Table 5 Default energy analysis under different scheduling methods MWh
從表5可以看出:
1)在方法2及方法4下,產生的必然違約電量均為0 MWh,設置負荷聚合商調節量確認環節可避免由于負荷終端特性與調度中心下發的調節任務不匹配而產生必然違約電量。
2)本文提出的根據資源靈活度確定補償價格的方式,一方面可降低必然違約電量,方法3的必然違約電量遠低于方法1,是由于調度中心在容量分配過程中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靈活度低負荷聚合商上報的調節功率波形,因而相應產生的必然違約電量較小;另一方面,根據資源靈活度確定補償價格的方式還可降低可能違約電量,方法3及4比方法1 及2 的可能違約電量減少了87.9 MWh,這是由于方法1及2根據違約率確定補償價格,調度中心將調節電量優先分配給了違約率高的聚合商B,而方法3及4則將調節電量優先分配給了靈活度低的聚合商A。
由上可知,必然違約電量:方法4=方法2<方法3<方法1;可能違約電量:方法4=方法3<方法2=方法1;合計違約電量:方法4<方法2<方法3<方法1。
因此,本文提出的方法4在降低違約電量方面的表現優于其他方法,相比方法1,方法4下的合計違約電量降幅達1 137.6 MWh。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將負荷聚合商按照資源靈活度從低向高排序的結果與按照違約率從高向低排序的結果完全相同,則采用資源靈活度確定補償價格與采用違約率確定補償價格的調節容量分配結果將完全相同。即只要違約率排序與資源靈活度排序不完全一致,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將優于目前已有文獻中的按照違約率確定補償價格的方法。
6.3.2 受阻風電消納分析
將調度中心最終分配的調節量減去必然違約量作為受阻風電消納的估計值,則不同方法下的風電消納情況如圖6所示。

圖6 受阻風電消納情況Fig.6 Consumption of the curtailed wind power
計算日受阻風電19 477.5 MWh,方法1、2下預計消納受阻風電16 472.8 MWh,受阻風電電量降低84.6%;方法3、4 下預計消納受阻風電17 412.5 MWh,受阻風電電量降低了89.4%。方法3和4比方法1和2多消納受阻風電939.7 MWh。
由上可知,受阻風電消納量:方法4=方法3>方法2=方法1。因此本文提出的方法4 可有效消納受阻風電。
綜上可知,本文提出的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可有效消納受阻風電。同時,通過增加聚合商調節功率確認環節及根據負荷資源靈活度確定補償價格,可有效降低荷源協調控制中產生的違約電量,為調度方案的可靠實施提供一定保障。
7 結語
本文提出了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模式及該模式下的負荷聚合商側及電網側決策模型。提出了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通過負荷聚合商整合負荷側可調節資源進行受阻風電消納。
1)提出了考慮負荷聚合商資源靈活度的荷源協調調度方法,可有效利用負荷側可調節資源進行受阻風電消納,提高風電消納水平。
2)提出了資源靈活度指標,在調度中心進行調節容量優化分配時,將負荷聚合商的補償價格與負荷聚合商的資源靈活度相關聯,可避免補償價格與違約率關聯時出現的違約率高的聚合商優先獲得調節容量,從而增大違約電量的情況出現;同時,可在調節容量分配過程中最大程度保持靈活度低的負荷聚合商上報的調節功率波形,從而降低負荷聚合商的調整電量。
3)提出荷源協調調度模式,考慮不同負荷聚合商的資源靈活度對完成調度中心初分配調節容量的影響,設置了負荷聚合商調節功率確認環節,并在負荷聚合商調節容量上報及確認模型中考慮了不同負荷終端的調節特性,從調度方法層面降低了負荷側的違約電量,可為調度方案的可靠實施提供一定的保障。
本文提出新的負荷聚合商特征指標并將其引入荷源協調調度方法中,配合調度模式的設計,在有效消納受阻風電的同時,降低荷源調度方案實施過程中的違約電量。但本文側重于技術實現,負荷聚合商在參與荷源協調控制過程中的合約機制、經濟收益問題,以及在調節容量上報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耦合關系及虛報行為在本文中未有涉及,將作為下一階段的研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