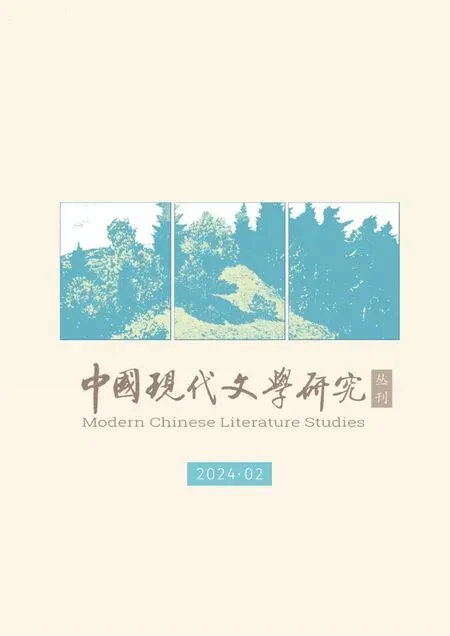從新見檔案看國民黨對“文協”的管控機制和矛盾態度
張智勇
內容提要:筆者新近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中發現了一批有關“文協”的檔案材料,其中包括“文協”與政府機關的關系機制及其演變,“文協”擬在各地成立分會的申報材料及各地黨政部門的反饋電文,以及“文協”向國民黨中央社會部申請經費補助的相關材料等。在結合相關報刊材料等既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這批此前大多未曾公開的檔案文獻對于了解“文協”成立初期的活動計劃和國民黨不同時期對于“文協”的管理部門、方式及效果,有著重要的補遺作用。一直以來,對于“文協”的“左”“右”屬性或者說“文協”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都存在爭論。而這批官方檔案文獻的特殊意義在于,其自身的政府視角可以直觀反映出抗戰時期國民黨官方對待“文協”的態度,尤其是其對“文協”管控有余而支持不足的矛盾心理,這也是“文協”此后對國民黨政府逐漸疏離、失望繼而轉向的原因之一。
一 國民黨對于“文協”的管控及其隸屬機制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對于“文協”的管控部門及其隸屬機制曾發生過多次變化,這影響了不同階段“文協”與國民黨政府關系的演變。
1938年3月27日,“文協”在武漢正式成立。“文協”最初由左翼作家陽翰笙提議建立,但在當時抗日合作的整體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中的部分成員幾乎全程參與了“文協”的策劃、籌備和成立過程,包括身居高位的邵力子、馮玉祥、張道藩,尤其是在國民黨中雖地位不高但在“文協”成立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王平陵及其下屬的華林等中國文藝社成員。對此,段從學曾有過詳細的專論。1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7頁。由于這些國民黨人本身多為文藝界人士,和相關作家較為熟稔,因而能夠在抗戰大局面前同包括部分左翼文人在內的民間文藝界進行合作,使得“文協”在成立之初的武漢階段能夠較為順利地開展工作。在國民黨的黨政機關中,當時參與組織“文協”成立的主要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時任部長邵力子對于“文協”的成立幫助很大,而王平陵等在“文協”成立過程中承擔事務執行工作的中國文藝社成員實際上也隸屬該部。此外,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和教育部也在經費等方面給予了“文協”支持,它們當中的部分領導如周恩來(時任政治部副部長)和陳立夫(時任教育部部長)作為“文協”成立大會的名譽主席團和主席團成員見證了“文協”的成立。但由于“文協”的救國團體屬性,根據《社會部工作計劃大綱草案》和《抗戰時期文化團體指導工作綱要》等相關章程辦法,其主管政府部門卻是稍晚于“文協”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本部對于民眾團體內部工作之策進與指導,凡與各種社會事業有關者,概由主管社會運動之處科負責辦理之,不屬于各項社會事業范圍者,應暫由主管民眾組織之處科辦理之。”2《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工作計劃大綱草案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317,第7頁。社會部由前身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改編而來,主要負責民眾團體的組織訓練事宜,以及對相關抗日救亡團體的組織、監督工作。自1938年4月成立至1940年11月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改隸行政院期間,該部一直是負責直接管轄“文協”的上級部門。也正因如此,在1938年底,盡管已經在事實上成立并且被政府有關部門見證、許可和支持,但“文協”依舊要按照要求向社會部補辦登記注冊立案手續。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時的社會部屬于黨務而非政府部門,其工作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本部工作,依據中央所賦予之職權,在秉承抗戰建國之最高原則,指導各級黨部及黨員,協助民眾團體之組織,一面求其本身工作之策進,一面力謀各種社會事業之發展。基此原則,關于民眾組織之指導及社會運動之推行,應盡力策動黨員,運用黨團,以取得黨的領導權,務使本黨政策,透過民眾團體,以普及于社會,而成為全國之廣大運動,以期增強抗戰力量,完成建國使命。”1《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工作計劃大綱草案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317,第4頁。與此同時,社會部還奉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積極加強并統一本黨之民眾運動,使各階層民眾,皆在本黨領導之下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以杜絕共黨活動之機會”2《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及實施方案(內有社會部簽擬關于“異黨”問題處理方法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4091,第89、95頁。的指令,會同政治部戰地黨政委員會專門制定了“民眾運動中‘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其中包括 :“一、普遍嚴密各民眾團體之組織,使異黨無法混入”,“三、黨團之組織應普遍于各民眾團體中,切實運用,以發生各團體之核心作用”。3《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及實施方案(內有社會部簽擬關于“異黨”問題處理方法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4091,第89、95頁。而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要求“文協”等相關民眾團體要及時上報其組織章程、人員構成、工作計劃等手續,就是要實時掌控這些民眾部門的最新動態,以實現其控制意圖。
正因如此,一方面,以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這一“文協”主管部門為代表的政府機關對于成立初期的“文協”給予了認可和支持:“該會工作頗為努力,所擬計劃亦均切要。前經本部派員視查認為組織尚稱健全并已批令準予備案。”4《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82頁。另一方面,該部又十分重視在組織層面上對于“文協”的參與、指導乃至控制。因而,他們十分重視王平陵在“文協”所擔任的部主任的位置和角色,社會部還試圖通過令王平陵在“文協”建立秘密黨團的方式對“文協”予以滲透和控制,但基層具體辦事人員對此事卻頗為謹慎:
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系屬救國團體。其會員均系國內較已成熟之文藝作者,惟其思想素不一致,份子頗為復雜,亦屬事實。嗣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經本部張副部長及邵力子先生等之號召,多方聯絡,煞費苦心,始獲共同組織斯會,受本黨之領導,從事抗敵宣傳。關于該會黨團之組織,依據吳云峰同志所簽有云:“……王平陵君亦謂,如約集某某等商談組織黨團問題,恐易引起誤解而發生相反作用。……”(王平陵系本黨同志,從事文藝工作有年,現任中宣部指導員,及該會組織部主任。)足見該會內部之復雜,黨團之組織,人選之抉擇尤須慎審,以免引起誤解而發生相反作用。根據以上情由,該會黨團之組織及人選之抉擇,擬由主管處科請示張副部長后再行依照黨團組織及活動通則辦理。當否?請核!
孟建民 鄭燊畬十二、七 發表 十二、八1《社會部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各理事政治態度之分析及擬控制該會的有關函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4008,第7~10頁。
某種意義上,“文協”組織部實際由王平陵及其代表的中國文藝社實際運行,其副手和干事也多為與該社關系密切之人:“組織部大忙,已請徐霞村和沙雁二君為該部干事。”2老舍:《一月二十日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頁。但由于王平陵和中國文藝社屬于國民黨宣傳部而非社會部統轄,其與社會部的聯系并不甚多,也很難完全按照規劃幫助社會部在組織層面對“文協”進行滲透和控制,反而經常會出現各部門間因缺乏有效溝通而造成的烏龍事件。比如,1939年6月22日,“文協”將最新的會務報告及第二屆理事名冊呈報社會部備案,社會部在6月26日對此的批示卻指出“文協”召開年會并改選理事事前并未向社會部報告并請求派員參加指導,認為這不符合《文化團體組織大綱實施細則》中第十條和第十一條之相關規定,要求對此予以糾正,并與“文協”理事王平陵接洽以核實此次會議情況。3《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88、96頁。對此,社會部干事楊琪、處長李中襄等人在7月10日呈報了對此事的調查回復:“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行年會及改選理事情形,因王平陵同志鄉居,經詢明中國文藝社編輯沙雁,當日舉行年會由邵力子先生主持,中宣部葉部長、本部張副部長均親自出席領導,所有推選理事情形尚無不合。除依前簽指正外,擬準備案。”4《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88、96頁。吊詭的是,包括時任社會部副部長張道藩、中宣部部長葉楚傖、軍委會政治部戰地黨政委員會秘書長邵力子等人在內的國民黨高官均參加了“文協”的年會和第二屆理事改選工作,但社會部具體辦事人卻對“文協”的呈報顯得毫不知情,這說明業務范圍和管理較為混亂的社會部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于“文協”等民眾救國文化團體的實時控制,更難談具體的監督和指導。盡管社會部在7月15日的批示中仍認為“文協”此舉不符合程序并予以糾正,但最終仍然核準了“文協”呈報的理事和候補理事名冊及會務報告。1《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97~98頁。但這不意味著“文協”同社會部已然割裂了關系。恰恰相反,“文協”此后經過向社會部協調、申請,最終在1940年春促成了以保障戰時生活和創作為主旨的“文獎會”的成立,并在救濟作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盡管社會部對于“文協”組織和會務等方面的實時掌控意圖并未實現,但在“文協”方面看來,其在相關規定下向社會部等有關部門補辦注冊立案手續和呈報會務動態等事務性工作大大增加了自身尤其是老舍所主持的總務部的工作負擔,更阻礙了“文協”工作計劃的展開:“最繁重之工作,為向各機關請求立案備案;全部規章及名冊俱須鈔呈。本會已在社會部立案,并在中宣部,內政部,教育部備案。”2老舍:《總務部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89、290頁。“由上邊這點記錄看來,可知文牘工作的繁重,可是會中并沒有聘設專人司管。函電公文的稿子是由大家擬制,交由總務部繕發。”3老舍:《總務部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89、290頁。其中已不乏“文協”對于國民黨相關主管部門的怨言。在團結一致抗戰救國的原則下,“文協”原意接受國民黨政府有關部門的管理和統轄,但這些繁重又對于抗戰救國毫無實際意義的案牘工作只會引起人手和經費本就不足的“文協”的反感。但在工作熱情較為高漲的抗戰初期,“文協”在有所不滿的同時仍然在總體上對于政府的相關要求進行遵守。
1940年底,社會部從國民黨中央黨務系統改隸行政院,遂將原來所屬的關乎意識形態的黨團事項移歸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將文化運動事項劃歸中宣部負責。如此一來,原屬于社會部對“文協”等團體的監督、指導權被轉移分散至組織部和宣傳部等部門,社會部只有一般意義上的組織注冊權限。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實際上并沒有完全接過原屬于社會部的監督管理之責。且由于社會部的改隸使得國民黨各部門對于“文協”等團體的控制權限不再明確,反而在客觀上放松了管控。1941年5月9日,行政院還專門發布指令以避免社會部改隸后與其他各部門在民眾團體和社會救濟等方面的權責不明確:“該部職掌在該部組織法中原已明白規定,惟關于民眾組訓與社會福利兩項與其他各部會職掌,每多牽涉,自應特予指明,以免混淆之弊。”1《社會部為改隸行政院并劃分各部會職權與振濟委員會、行政院、中央黨部秘書處的來往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175,第5頁。另外,由于“文協”的上級主管部門不再明確,也使之部分失去了國民黨原有對于“文協”經濟和各項工作上支持的可能,比如“文獎會”機制的式微。2參見張智勇《老舍在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的工作——新見老舍八封佚信及“審稿意見”》,《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2期。這一得一失實際上都減弱了國民黨政府與“文協”之間的聯系。“文協”對于政府不再如抗戰之初那樣支持和信賴。
二 國民黨社會部與各地黨部對于“文協”組織成立分會的批復及反應
“文協”成立之后遂著手在各地成立分會。而各地分會籌備成立并取得注冊立案手續的過程中所面對國民黨中央和各地方黨政機關的態度和反應,又暴露出了抗戰初期國民黨對于“文協”的矛盾心理。新見檔案則將這一過程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在為“文協”總會進行立案注冊的同時,老舍還向社會部提交了題為“為呈請準予成立各地分會并發給許可證由”的另一公函,匯報了“文協”準備在各地成立分會的組織情況并呈請批準:
查本會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會務進行,自應不遺余力,竊以欲發展全國文藝宣傳工作,必須策動各地文藝界共同努力,始能收分工合作之效;俾中央抗戰建國之國策得以深入而普遍,茲經本會第三次理事會議決,先成立桂林、成都、昆明、貴陽等地分會;并推派歐陽予倩、豐子愷、封禾子、孫毓棠等為桂林分會籌備委員,朱光潛、沙汀、馬宗融、周文、羅念生等為成都分會籌備委員,楊振聲、朱自清、沈從文、穆木天、彭慧等為昆明分會籌備委員,謝六逸、高滔、蹇先艾等為貴陽分會籌備委員,事關抗敵宣傳,理合備文呈請大部發給許可證,準予成立,俾便知照各地分會籌備分會,迅予成立而利進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謹呈
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總務部主任舒舍予
會址:本市公園路青年會一〇四號
二十七年九月三日1《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57~58、10~13、68、70頁。
“文協”試圖同時向社會部為總會和各地分會進行立案注冊,以為其早日爭取合法身份并開展工作。社會部在擬定批復草稿時基本同意了這一請求:“該會為普遍發展文藝抗敵工作,計劃在各省市設立分會,尚屬可行,擬予批準。惟設立時仍須依照人民團體組織方案辦理。”2《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57~58、10~13、68、70頁。為此,“文協”召開理事會通過決議:“各地分會宜積極成立,由本會通知各分會籌備會呈請地方最高黨政機關準予備案。”3老舍:《十一月二十六日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79頁。但是,“文協”此后在各地成立分會時卻因與各地主管黨政部門對于各地分會立案流程的理解差異而遭遇阻礙:“地方政府以為總會既在中央備案,則分會自當通過總會,得到中宣部的許可;中央允準,地方政府自然準予備案。”“總會順利的在社會部立了案,便趕快辦理分會登記的事。可是,社會部指示總會:分會成立,須呈報地方政府,無須部中許可。總會于是又急將此意通知分會,促其進行。分會急將呈文遞上,而黨部聲明,民眾團體登記尚無確定機關管理;成立會就又開不成了。”4老舍:《一月二十八日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81頁。有些省市黨部還專門致電詢問社會部是否批準了“文協”各地分會的成立,并向其部報告了“文協”分會在各地組織成立時的情形。現存的社會部檔案留存了包括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湖北省黨部、四川省黨部、“中統”等各地黨政部門的有關報告和商討函件。
1938年8月23日,李宗黃以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名義向社會部匯報姚雪垠等人擬在河南南陽組織“文協”分會一事,并詢問“文協”總會對此是否已備案,“文協”可否在該地組織分會?5《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57~58、10~13、68、70頁。對此,社會部在同年9月函復河南省黨部說明目前正在辦理“文協”登記注冊事宜。11月4日又函復表示,“文協”已經由社會部核準備案,“并準設立分會。惟組織分會仍需依照修正人民團體組織方案之規定辦理”6《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57~58、10~13、68、70頁。。1938年12月,四川省黨部也就“文協”成都分會擬成立事項上報社會部:“據朱光潛等呈稱,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指定為成都分會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分會。經查該會會員多系前經勒令解散之成都文化界救亡協會分子,可否準予組織?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曾否經貴部備案?請查核迅賜電復為荷。四川省執行委員會。”1《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105、106、87頁。四川省黨部的電文中特別之處在于,其對“文協”成都分會的會員分子問題進行了政治成分分析及針對性請示。對此,社會部回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業經本部核準備案,成都準設立分會,會員分子問題可于指導組織時注意并多派研究文藝之黨員加入。”2《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105、106、87頁。1939年1月11日,湖北省黨部也就“文協”宜昌分會成立事項向社會部詢問,社會部回復已核準“文協”成立并在各地成立分會,并希望地方黨部“派黨員參加,設法積極領導為荷”3《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105、106、87頁。。
而有關“文協”昆明分會的匯報更是直接來源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特務機關“中統”。其在1939年11月將《文抗協會云南分會之組織情形報告》一份抄送社會部,內容涉及對于“文協”云南分會(昆明分會)成員政治傾向的分析,落款署名為“中統”局長朱家驊和副局長徐恩曾:(以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茲有關于文抗協會云南分會之組織情形報告一件,相應抄同原報告,函請查照參考為荷!
此致中央社會部陳部長
附抄原報告一件
局 長 朱家驊
副局長 徐恩曾
文抗協會云南分會之組織情形
昆明十一月廿二日訊
文化界抗敵協會云南分會設昆市民教館,于廿七年二月成立,業經備案。該會產生原因初系滇黨部宣傳科鑒于文化界有組織領導之必要,乃派查宗藩、馬夢良等同志參加,初名云南文藝界座談會。后因全國文抗協會成立,乃改為文化界抗敵協會云南分會,其組織為理事七人,常務理事三人,下設文藝、時事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等三組。會員大會為該會最高組織,原為本黨同志領導,繼而本黨同志逐漸減少,逐為左派及共黨份子所操縱。目前擔任該會理事者為楚圖南與馮素濤(現任云大教授)、楊亞寧(文藝界左傾份子)、楊濟生(云南日報副刊編輯)、張克誠(云南日報編輯主任)(均系左傾份子)、甘汝棠(滇黨部宣傳科長)、張友仁(滇黨部總務科長)等七人。甘汝棠、張友仁二人雖加入但未實際領導,開會亦少出席。該會成立后之經費來源除教廳每月補助少數外,每會員按月繳納國幣三角,其不足者則向外募捐。該會工作進行頗為努力,除按期出有《文化崗位》月刊一種外,并隨時尋機召開會議或小組會,不時又到郊外旅行或舉行游藝,均有宣傳作用云。1《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102~103、99~100頁。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統”致社會部關于“文協”昆明分會調查公函首頁
對此,社會部函詢“文協”組織部主任王平陵后認為上述報告所指“文化界抗敵協會云南分會”應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誤指,并希望云南省黨部對此事進行核查。2《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章理事會員名冊及各地分會組織成立等事項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2229,第102~103、99~100頁。“中統”的此份報告尤其強調了國民黨對于“文協”昆明分會控制力的衰微,并強調了該會部分成員的左傾性及其宣傳意圖,這種分析是比上述其他地方黨部的相關報告更為細致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文協”總會同樣注意到了昆明分會會員成分的復雜性,其通過理事會決議:“關于昆明分會之會員中有非文藝工作者,應在其他(如音樂、繪畫)抗敵協會未成立前,暫在支協會工作,一俟各協會成立,即請其自動轉入。”1老舍:《十一月二十六日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79頁。這種策略一方面符合“文協”作為文藝作家協會的性質,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客觀上借此將云南省黨部在該會中的成員逐漸排除在外,以減少該會所受的外在政治性困擾。
無論如何,從“會員分子問題可于指導組織時注意并多派研究文藝之黨員加入”到“派黨員參加,設法積極領導為荷”,再到特務機關“中統”的直接參與,可看出國民黨黨政機關對于“文協”及其分會的控制和領導意圖。國民黨中央社會部較為重視“文協”及各地分會的會員成分問題,其防范辦法是要求各地有關部門在“文協”及其分會成立備案、會員上報、理事改選時加以留意和“指導”,同時令各地黨部盡量委派、鼓動研究文藝的國民黨黨員加入“文協”,以期達到參與、了解乃至控制“文協”的目的。正因如此,社會部十分看重王平陵在“文協”中所擔任的組織部主任的身份,認為這是實時掌控“文協”及其成員的關鍵位置。但實際上,無論“文協”是否有意為之,其對于會員作家身份的資格設定使得政府官方很難直接派員滲入。而王平陵也并未對“文協”有實際的策動和監督行為,比如上述提及的通過在“文協”內部建立黨團以逐漸控制該會的意圖就難以落實。
三 國民黨政府對于資助“文協”的猶豫態度和影響
如上所述,在各方的籌劃與溝通下,“文協”的成立得到了國民黨官方的準許和支持,其中也包括各黨政有關部門對于“文協”的經費資助。但是,礙于對“文協”組成成分與功能定位的矛盾態度,國民黨對于“文協”的資助是有限度的,且并未隨通貨膨脹的加劇而實時增加。這直接限制了“文協”的工作計劃和積極性,最終導致了抗戰后期“文協”直接向社會民眾進行募捐活動,并逐漸擺脫了對于政府的依賴關系。
“文協”最初的每月補助經費來源于國民黨教育部、中宣部和軍委會政治部,這在各時段的“文協”總務部報告中有著較為清晰的記錄:“補助: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教育部補助本會每月二百元;中宣部每月五百元——于六月間始行領到。九月起,政治部批準每月補助本會五百元,于本年一月領到。本會舉辦通俗文藝講習會,教育部特予補助三百元。”1老舍:《總務部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86、287頁。扣除教育部給予通俗文藝講習會的一次性補助外,“文協”此時每月所獲政府補助總額為一千二百元。在1938—1939年通貨膨脹尚未十分惡劣之時,這一數額雖基本可以維持日常所需,但卻難以進一步擴展業務:“結至今日,稍有存余,若刊行前線增刊,及舉辦講習會等,即無余裕。”2老舍:《總務部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86、287頁。隨著社會部的成立并成為自己的主管單位,“文協”原本認為又有了一個可以請撥經費之地。1938年11月25日,“文協”向社會部呈送公文《為發展會務廣作文藝抗戰宣傳請發給經常補助費由》,請求該部每月補貼“文協”經費五百元:
本會成立,已歷八月,已往工作,業經呈報在案,并蒙貴部嘉許,以后會務推展,當更努力以副厚望。唯本會經常費除會員納費外,只有教育部中宣部每月發給補助費計共七百元。會費為數甚微,補助亦嫌過儉。即以刊行會報抗戰文藝而言,紙價印工既數倍于昔,而推銷發行復日見困難,每月需賠墊三四百元。其他工作因物價其漲,入款有限,致多未能按照預定計劃進行。近中社會上熱心抗戰宣傳人士紛函本會,請求開辦文藝講習會,以增進文藝知識及寫作技能。本會困于經費,雖有立刻創辦之決議,而乏設立之款項,故尚遲遲未開辦。舉此一例,足證其他,急待辦理之件甚多,固不僅文藝講習會一事。素仰貴部愛護輔導民眾團體,不遺余力,懇祈惠予經常補助費每月五百元,以便積極發展會務,廣作文藝抗戰之宣傳。實為公便。謹呈
中央社會部部長陳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3《社會部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各理事政治態度之分析及擬控制該會的有關函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4008,第12~13頁。
從此時起,經過了雙方長達幾個月的對話磋商,“文協”為此還專門呈報了開辦文藝講習會和《前線特刊》的計劃及所需經費明細。但到了1939年4月下旬,社會部副部長張道藩對于上述“文協”所請經費的最終回復卻仍是:“呈件均悉。本部因經費困難,礙難照準,已函請教育部酌情予補助矣。”1《社會部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各理事政治態度之分析及擬控制該會的有關函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4008,第22、2頁。“文協”試圖通過政府增加經濟支持以開展和擴大業務的希望遂成泡影。
更為重要的是,國民黨官方之所以拒絕“文協”的相關經費請求并非全部緣于財政經費緊張。就在“文協”向社會部申請經費的同時,該部文化事業科科長吳云峰的一份秘密報告顯示,社會部在不愿將經費直接撥給“文協”用于其開展文藝講習會和《前線特刊》等業務的同時,卻愿意撥發專款給擬由王平陵等人在“文協”中成立的國民黨秘密黨團,以實現由該黨團逐步控制“文協”的企圖:“……旋又奉論:‘指定該會理事中之黨員組織黨團,然后補助之。’”2《社會部對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各理事政治態度之分析及擬控制該會的有關函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十一(2),案卷號:4008,第22、2頁。盡管社會部通過建立秘密黨團以滲透和控制“文協”的計劃后來并沒有真正落實,但此處仍能看出其對于所屬民眾抗戰團體“文協”的態度并不是助其發展,而是對其加以羈縻、規訓和控制。
根據“文協”的會務報告,直到1940年下半年左右,社會部才正式撥給“文協”每月經費300元:“關于經費者:在春天,我們的收入是仰仗著中宣部、政治部,與教育部的補助。可是,政治部的補助因手續的關系,往往不能按月領到。……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努力向政治部懇請,得蒙請發未領之款,且允以后按月發給補助。我們又向社會部申請予以補助,亦蒙批準每月補助三百元。這樣,我們每月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三百元。可是物價的高漲和開支的增多,還使我們不能不十分的節儉。”3老舍:《總務部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300~301頁。從1940年春開始,大后方物價陡增并逐年加劇,然而“文協”的經常費卻在經由向社會部的多次請求下僅僅增加了每月三百元,這極大地限制了“文協”的活動和工作計劃。由于申請經費的不被批準,原定的文藝講習會沒能開辦,《前線特刊》(后在成都分會合作下一度改為《通俗文藝》)以及與香港分會合辦的《抗戰文藝》英文版4“由華林先生到中宣部接洽,撥給經費,舉辦會刊英文版。這原是香港的同志們的提議,要每月出八開本十二至十六頁的英文版會刊一期,經費約四百元,與中宣部接洽,尚無立時得到經費的可能,現正向其他方面進行。向國外介紹抗戰文藝是件極要緊的事,理應有專刊,同人等都非常注意此事,期能于最近解決了經費問題。” 老舍:《八月十日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292頁。也沒能持續下去。這很難不影響“文協”對于政府的態度。
由于國民黨黨政機關缺乏對“文協”等抗戰民眾團體在經費和政策上的足夠支持,使得這些機構的工作開展在抗戰中后期逐漸趨于停滯,對于團結抗戰所發揮的作用也不再明顯。對此,甚至一些政府官員自身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1943年10月,中宣部“文運會”主任委員張道藩在向中宣部報備的《動員計劃大綱文化動員具體辦法》中表示,如果要推進文化動員及包括“文協”在內的各文藝機構團體在其中的作用,則“非充實其經費不可。此舉擬應由中央宣傳部會同國家總動員會議統籌辦理,徹底加強各機構以免徒具虛名”1《中宣部文化運動委員會一九四三年度工作計劃、工作報告、三民主義研究會一九四五年度工作計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一八,案卷號:104,第4頁。。但實際上,在抗戰后期面對內政外交一團亂麻而又深陷財政困境的國民黨政府,難以也不愿將有限的財政大規模運用在文化事業特別是并非作為政府機構的“文協”等民間文化團體上,這就意味著張道藩的此種建議只能停留在紙面上。而“文協”也只能繼續沉溺在因缺乏經費導致的工作停滯中:“慢慢的,物價越來越高,會中越來越窮,而在團體的活動上又不能抱著一動不如一靜的態度,‘文協’就每每打個小盹了。”2老舍:《“文協”七歲》,《老舍全集》第18卷,第256頁。更重要的是,由于國民黨官方上述對于“文協”的種種態度和處理方式,最終斷裂了政府官方與文藝界進行有效關聯的可能,并加速了“文協”及其所代表的民間文藝界在抗戰后期的日漸民主化和左轉。“文協”在1944年下半年向社會各界發起的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并取得的巨大成功,更加改變了其與社會民眾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系屬性和相關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