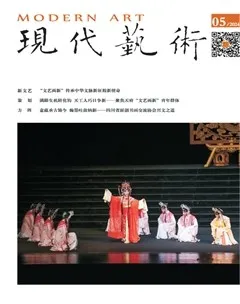行走在科幻與現實之間
羅明金
《白色陷阱》以“隱喻”告訴我們,科學是在人們不斷的探索和痛苦的追求中產生,是在“陷阱”中掙扎與獲得,甚至是要以生命為代價。人類不應一味以功利的眼光來看待科學探索的得失,更應該看到科學進步背后的艱辛。作者把一個追求理想、勤于探索、不達目的不休的科學工作者血淚交織的悲劇展示給人們看,把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們看,就是要給人們以告誡、以警醒。
她,無疑是一匹黑馬,一匹顏值高而實力強的黑馬。當她以接二連三的作品一躍進入文壇,就以踏驚飛燕的英姿引人矚目。這匹黑馬,她的名字叫“賈煜”。
賈煜先是以科幻系列小說亮相《中國校園文學》《科幻世界》等知名刊物,隨后,長篇科幻小說《時空迷陣》《幻海》等相繼出版,她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具有時代特色的語言把粉絲們帶進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夢幻世界,多篇作品相繼獲得第五屆中國(成都)國際科幻大會“100年后的成都”全球科幻作品征集二等獎等。當這位30多歲的才女以新的題材華麗轉身之際,她聚焦現實的《溫暖的涼山》 《暗疾》等佳作又被 《青年作家》 《四川文學》等刊發。不同凡響的創作力成就她成長為巴金文學院2021年度最年輕的簽約作家。2023年12月,把夢幻與現實巧妙結合的中篇小說《白色陷阱》更上層樓,被《中國作家》隆重推出。筆者想要重點評說的,正是這一部2萬多字的非常之作。
獨特的題材,“秘境”的探究
病毒,是永遠纏繞人類的夢魘,是不斷以惡毒因子危害人類并與人類斗智、斗狠的怪物。我們的醫學專家剛剛要降服它,它卻以另一種面目和更加兇悍的姿態和詭異陷阱侵害著我們。而賈煜在《白色陷阱》,正是把筆觸伸向了這一片“秘境”:作為研究病毒的專家“我”,窮盡精力研究對付病毒的疫苗,三個學生也各懷心思地跟隨進修與研究。兩年后,趕在其他機構前面把“伊卡埃疫苗”研制成功。但在第二年,疫苗出現了狀況,接種的兒童因嚴重感染伊卡埃被收治入院的概率比未接種疫苗的兒童高了五倍,“我”和主研的高足弟子桂素月只得立即叫停疫苗接種項目。當桂素月和“我”的團隊分道揚鑣后,不甘失敗的她進入了新一輪研發。此后,作者的筆下出現的病毒隱蔽運行、自我復制、獨立生存、惡意設計等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的陷阱和桂素月等提出的解決病毒脫靶問題的“基因編輯”“共生疫苗”“四維支架”“終極疫苗”等的一系列只有醫學專家能夠明白理解的專業術語,對于常人來說,則是極其陌生、晦澀的世界,而作者把這一切寫得如此行云流水。我想,這或許就是這位青年作家頭腦中的科幻因子產生的效應,抑或是她善于學習、善于研究的成果!而這個題材,又是在這個時代人們極想知曉的、極想破解的密碼。面對疫情,選擇“秘境”題材,本身就是小說吸引讀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小說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們不少作家在寫這類題材時,往往只看到醫務工作不能盡快破解的表象,卻未能探究深層的原因。常以指責現實為操守,以批判現實為快事,見不得疫情害人而生出悲憫情懷,在筆端怨天尤人,殊不知埋沒了多少人的艱辛與努力,從而陷入主觀與偏激。還有許多作家對某一些病毒是“文盲”,當然對這類題材就不敢涉及。而賈煜敢于選擇別人不敢寫或不能寫的“秘境”題材,足以證明作者具有獨具的智慧與思維,善于獨辟蹊徑,敢于闖入題材的“禁區”,而且能把許多不為大眾知曉的東西展示得那么清晰可見,那么引人入勝,足以證明作者駕馭“生猛”題材的非凡能力。究其原因,正是源于作者對科幻的興趣與探究,獨具的想象力、思維發散力于此得到充分發揮,成為其小說創作特有的優勢和不同尋常的風格。
交織的矛盾,驚心的布局
小說要吸引讀者,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小說中故事情節的矛盾沖突激烈。在《白色陷阱》中,作者對故事情節的布局可謂匠心獨運,布局巧妙。使矛盾沖突錯綜交織,把故事逐步帶入悲劇氛圍,從而使作品漸入佳境,給人以驚心動魄之感。
作者首先描寫了自己走進一座廢品堆積、房屋破敗、被雜物掩蓋、四周沒有任何活物跡象的村莊。聽到這個“垃圾村”里的哭聲,看到感染病毒的男孩奄奄一息,見到了一個叫做“桂素月”的女孩,然而這個女孩“扭頭就跑。我快步追上去,但在越來越濃的雨霧中,我漸漸失去了方向”,作者把讀者帶入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夢幻境界,給我們如墜五里霧中的感覺。讀了小說開頭,我們就產生了好奇心: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垃圾村”?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作者設計這個情節是為了什么?直到讀到小說最后一部分,讀者才明白,原來小說開頭這一段中的“我”,是進入了一個剛死去不久的女人的記憶看到的碎片,而這個女人,就是小說塑造的主要人物之一——“桂素月”。這種情景代入避免了常見的平鋪直敘,避免了陷入常規式倒敘的“脫臼”。這正是作者情節布局的精心和高明之處。
隨后,故事一下子跳到二十年前,寫到了“我”和三個學生之間的故事。學生桂素月讀博,是“為了救人”,想從源頭上就去抑制疾病的發生;余凝讀博,目標是“繼承家族企業”,因為她的家族是疫苗制造商;而學霸小柒壓根就沒目標,拼命讀書只因懼怕涉入社會,便要繼續留在“象牙塔”。“我”詢問學生學習目的這個情節的設計,暴露了三個學生不同的求學觀,由此為后文“我”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矛盾埋下了伏筆。
對于三個學生之間的矛盾沖突,作者并沒有立即花費筆墨正面去寫,而是一下子跳到“我”被調到南方某研究所研究疫苗,及兩年后接到博士畢業的桂素月想來研究所工作的電話后的系列情節。此時,通過“我”的片段性回憶,表述出桂素月與余凝之間的矛盾——她和余凝對一篇論文的觀點發生過爭執,此后好幾次兩人都因觀點不合而爭吵,相互耿耿于懷。而這些小小的矛盾,卻成為后文矛盾高潮的誘因之一。余凝對于“我”帶桂素月出入各種研討會顯然嫉妒,作者寫道,會中,“有幾次她專程來給我打招呼,完全無視站在一旁的桂素月,兩人的那種暗潮涌動,讓所有熟悉她倆的人都能感到空氣中的緊張。”這種暗中的較勁,終于在桂素月在得知伊卡埃疫苗被余凝的公司承接生產后爆發:“那天,她(桂素月)氣勢洶洶地闖進我的辦公室,質問我:‘為什么把我們的疫苗交給她!”當“我”解釋:“這不是我能決定的”,桂素月毫不讓步,“但你至少有建議權吧!”隨后憤憤離開。桂素月在老師面前出現如此沒有控制的狀態,足見她與余凝的矛盾加劇的程度。之后,作者又把故事情節的矛盾推向另一高潮——疫苗生產出來后,效果非常顯著,但在第二年,伊卡埃疫苗出現了狀況:“從接種的兒童來看,接種后因嚴重感染伊卡埃被收治入院的概率,比未接種疫苗的兒童高了五倍,我們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立即叫停了疫苗接種項目。然而媒體已經發酵,輿論瞬間就把我們和康龍公司推到了風口浪尖。”“我”終于認可了桂素月的“病毒陷阱”理論的正確。“但桂素月早已辭職去了國外公司。‘我把疫苗問題找到了,帶領團隊沒日沒夜地加班,就在快出成果的時候,一款進口疫苗卻搶先占領了市場。”可以說,“我”的團隊和科研成果掉入了“病毒陷阱”,已經被自己學生“置于死地”。“我”只好回高校教書,而桂素月卻在后來繼續與人合作,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成立了公司,以一種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心態繼續從“白色陷阱”中掙扎而出研制疫苗。然而最終,桂素月將疫苗用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再次掉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再也沒有醒來。讀到這里,故事強烈的悲劇色彩讓人驚心而感嘆不已。
就這樣,《白色陷阱》把故事置于不同的矛盾沖突中,這些矛盾交錯演繹,層層推進,在一個又一個旋渦中釀成高潮,釀出“桂素月成為疫苗研發的犧牲品”這個悲劇性結局!把美麗與勤奮撕成破布,讓理想破滅而魂歸“陷阱”,達到了撼人心魄的藝術效果。由此可見作者在小說情節布局上的非凡功力。
細膩的描寫,人性的解構
小說中的細膩描寫,或許是女性作家的天生本能。作品中,桂素月是一個有追求、質樸、勤奮、執著、好強、激進的人,是作者重點塑造的人物。
對人物的動態細節描寫,是作者用功較深、著力較多刻畫人物的方法之一。“我”初見桂素月時,“她一只手捏著衣角,一只手背在身后……我注意到她左手腕上,有一塊燒傷的疤痕。”一個“捏”字,一個“背”字,把桂素月這個從鄉村走出來的孩子的那種質樸、靦腆刻畫得活靈活現,而寫到她手上的傷疤,隱示著桂素月一定有著不凡的經歷,為后文寫她做事不怕困難、敢闖敢干和不服輸的性格留下伏筆。“只要穿上工作服,進入實驗室,整個狀態就是一種癡迷。她可以為了等待一個實驗結果,守在那里不吃不喝,通宵達旦地連續工作七八十個小時,專注到不知疲倦。”人物置身事件的精短描述把桂素月的勤奮、做事專注、不怕吃苦的特征表現了出來。又如,“我”再次見到桂素月時,“與三年前相比,她從外貌到氣質都發生了變化,手腕上的疤痕,也用一個動物文身遮掩了。這晚,我請她吃飯,暖色調的燈光下,略施粉黛的她有種嬌媚般的青澀,令我不免走神。”“疤痕被動物文身遮掩”,這一個小小的變化,顯示出女孩子心理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單純,她已經愛美和希望掩飾自己的缺點了;而“略施粉黛”與“嬌羞般的青澀”,則進一步地證實其性情的變化。這一切,很符合女孩子的成長規律,很符合人性的變化邏輯。再如,寫桂素月科研成果未能獲獎后的失落神態:“我去房間找她,推開門,看見一地狼藉,她仰面坐在沙發上,蓬頭垢面,閉著眼睛”,那種渴望成功、難以接受失敗的打擊、面對失敗的痛苦,都從這細致的描述中得以展露。疫苗出現問題,她竟然在遭受多次挫折、失敗,甚至被人們打斷了胳臂的情況下,仍然癡心不改,執著于“終極疫苗”的研發。通過多種細節描寫,作者把一個有激情、有追求、勤于工作、不達目的誓不休的人物活脫脫呈現在人們面前。在描寫人物典型語言方面,賈煜也善于抓住富有個性化色彩的話語:“余凝能做的,我也能做,而且會比她做得更好!”桂素月在與“我”談到余凝時,語調變得尖銳,“是的,她的目標不是我的目標,卻是我目標的動力之一。”話語間明顯透出桂素月倔強、自信的性格,透出女性與女性之間不服氣和明顯較勁的心理。再看,當她研發的疫苗不被世人認可,老師勸給其改換一個名字時,她忽而提高聲音,賭氣地回應,“我不換!”“這是我的心血。它沒有錯,我也沒有錯,憑什么我要給它換名,像它見不得人似的?”堅定的語言,把那種倔強、堅持的性格展露無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既是小說刻畫人物的需要,更是深化人性解構的方法。
在解構“我”這樣一名男性博導的人性時,作者也寫得很到位,很真實可信。“說實話,在她與余凝之間,假如我有私心,那一定是偏向于她,可能因為我們曾經共事,也可能因為她曾經的擁抱,讓我持有了男人對女人的那種幻想。我不是偽君子,也算不了真君子。”又如,當桂素月希望“我”能幫助她研究新的疫苗時——“賈老師,別猶豫。”她伏在我肩頭,一副深不可測的神情,“她的唇離我的耳垂很近,她的呼吸讓我產生了某種錯覺。如此氛圍里,我幾乎喪失了方向感,任由自己被溫情、歡愉和強烈的情欲所俘虜。”這一段描寫,把師生兩人在長期的學習、共事、生活中的友情、親情甚至是曖昧之情生動展示了出來,把“我”面對一位美麗的學生差點意志崩潰寫得非常形象生動。這樣寫來,就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真實、更接地氣,同時為后文敘述桂素月安裝仿生手臂住院那段時間的表現作了鋪墊,“我給她喂食,她就伸長脖子,喂什么吃什么,像只小狗,有時還把勺子舔凈;我訓練她的假肢,向她投球,她接住了就得意地大笑,沒接住就噘著嘴發怒;她做身體檢查,我幫她揭衣,她就笑盈盈看著我,任由我輔助醫生檢查,絲毫沒有不適表情。”這樣的情節,則順理成章,人性的光輝也彰顯得更加自然而無可挑剔。從這一點來看,賈煜構思小說情節的細心、精心、用心,可謂達到較高境界。
現實的反照,科幻的隱喻
一部小說究竟想要表達什么,究竟要讓人們明白什么?這是一個長期被爭論的問題,“虛無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等各執一詞。但筆者以為,不告訴讀者什么、不讓讀者明白什么,作品還有什么意義?對于這一點,作家們常常在小說中以“隱喻”的方式來體現,村上春樹如此,莫言如此,賈煜也如此。《白色陷阱》以“隱喻”告訴我們,科學是在人們不斷的探索和痛苦的追求中產生,是在“陷阱”中掙扎與獲得,甚至是要以生命為代價。人類不應一味以功利的眼光來看待科學探索的得失,更應該看到科學進步背后的艱辛。作者把一個追求理想、勤于探索、不達目的不休的科學工作者血淚交織的悲劇展示給人們看,把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們看,就是要給人們以告誡、以警醒。《白色陷阱》憤懣地揭露了人性丑惡的一面。人們往往看到利于自己的一面而忽視其他存在,當疫苗有效時,人們則奉之為神明,“一夜之間,桂素月似乎也成了英雄,關于她研發疫苗的成功事跡,被媒體反復渲染,變得神乎其神。如此看來,不需要我的指引或幫助,她就已經成為生物醫學領域最閃亮的那顆星。”而當病毒變異,藥物不能控制時,必然成為攻擊和泄憤的對象,研究疫苗的桂素月只得離鄉背井另求出路。人性之功利、之兇惡何其厲害,而輿論之利刃更是無可抵御。不僅如此,故事還揭露了資本競爭的殘酷,以及道德、權利、資本綁架科學工作者的現實。在這個物欲橫流、功利遍地的世界,別人不僅可以“把你的基因疫苗悄悄換了名,交給了其他人負責”,在資本運作上,作為同學的余凝以公益事業的幌子把桂素月的疫苗踢出局后,再重新開啟商業模式,從而壟斷市場。在這個功利的世界,一個科學工作者也會因此如浮萍不能自主,“我”的學生可以通過運作調動“我”違背意愿地去為他們服務,這一段描寫生動呈現掌握資本者的任性與囂張:余凝“輕笑兩聲,眼睛再次逼視過來:‘今天,我來找你,只是出于尊重,事先告知一聲,讓你有個心理準備而已。”掌握資本者是何其囂張,隨后還居高臨下地說,“賈老師,現在不是我們需要你,而是更多的人需要你。這種時候,我覺得你應該站在更高的道德層面考慮一下問題。”余凝丟下這話,就踩著高跟鞋,以傲視群雄的姿態走了——請看,憑借經濟實力,學生竟然反過來威逼老師,還以道德綁架老師,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及至后來,桂素月在為某國際醫藥集團研發“終極疫苗”中因主動感染幾種病毒不治身亡,一個美麗的靈魂最終被“白色陷阱”無情吞沒,而該集團沒有放過她和她的科研成果,竟然利用“我”,違背倫理道德進入死去了的人的意識,去窺取他們想要的疫苗成果信息。這雖然是作者在結尾構想的一種科幻式結局,但正是作者對于資本殘忍程度的悲憤控訴。面對這個讓人窒息的現實,作者卻沒有幻滅,她在小說的結尾寫道,桂素月在傳給“我”的意識里說:“幫助我,不要把它(疫苗)變成斂財的工具。”“在她這即將幻滅的意識世界里,風的呼嘯、海的怒吼、沙的狂嗥,仿佛都是她的呢喃私語。她似乎在告訴我——生命一如既往地,在踽踽獨行……”哎!這“白色陷阱”是何其深邃,又何其令人執迷啊!《白色陷阱》給我們揭露的現實,又是多么的令人震驚和令人嘆息!但作者最終仍把警醒、良善的期冀留給了世界。
當然,筆者在這里還想就作品的某些方面與作者商榷。作品中三處提到桂素月“左手腕上有一塊燒傷的疤痕”,這或許也是她人生注定遭受挫折的某種隱喻,但作者沒有在傷疤上更多發揮。比如,能夠在桂素月試用疫苗而變得面目全非無可辨別后,“我”進入她的意識,憑借那只左手腕被人打斷的斷肢上有一塊熟悉的傷疤,一眼就認出了這名死者正是桂素月,再書寫她生前帶著的皮膚上的傷疤和心靈上的“傷疤”,從而使那塊傷疤愈加明顯、愈加讓人心痛,則小說的悲劇色彩會渲染得更加強烈,隱喻的效果會更加深刻。另一方面,對于余凝一味追求利益,其人其公司的結局,未有敘寫或暗示,對于部分追求“完美”的讀者來說,有些許遺憾。然而這一切,對于賈煜的這部作品來說,可謂瑕不掩瑜。
行走在科幻與現實之間,是賈煜的特色和優勢,也是小說未來的星光和宇宙。我們希望看到賈煜在屬于她的那片星空,更加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