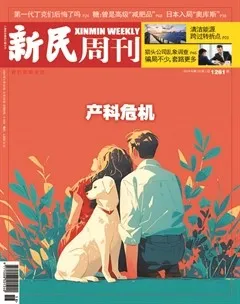第一代丁克們,后悔了嗎?
吳雪

曾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的生育,正在成為一種深思熟慮后的選擇。
上世紀80年代,丁克這一概念傳入中國。丁克,是英文Double Incomes No Kids的縮寫,指的是夫婦雙方都有收入且不生育的家庭模式。丁克概念被引入后,受到很多高學歷高收入家庭的熱捧。
三十年過去,第一批丁克已步入中老年,有人從容淡定、不改初心,也有人遺憾后悔。“丁克”歌手李健態度十分豁達,面對鏡頭時他直言:“我又不是什么瀕臨滅絕的物種,基因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沒必要延續自己。”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目前,中國有超過60萬個“丁克”家庭存在。從生理原因導致的“被丁克”,到中途反悔的“白丁”,再到用養寵物代替養孩子的“丁寵”,每一種丁克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
知乎一位題主在回答丁克夫妻的結局時,高贊的一條回答很精辟:“看起來是幸福的,因為不幸福的丁克要么離婚了,要么跑去生娃了。”
“鐵丁”的堅守?
65歲的梅姐結婚40年,是中國首批丁克夫妻。“我和先生年輕時都在忙自己的事業。結婚前幾年,兩個人全國各地跑,在一起的時間屈指可數。等兩人結束異地生活,定居下來之后,猛然發覺自己已經過了生育年齡,成了第一批丁克。”
“丁克”一詞在引入到中國后,其概念已經本土化,不再局限于已婚夫婦,也包括沒有生孩意愿的未婚群體——這點可從當前的丁克實踐得以佐證,網絡上的丁克社區匯聚了大量已婚、離異和未婚人群,他們共同的核心標簽就是“不想要孩子”。
丁克群體還逐漸衍生出各種細分標簽——鐵丁:從現在起直到宇宙毀滅,堅決不生;白丁:丁克數年后因各種原因反悔,白白做了一場丁克夢;被丁克:由于生理原因無法生育;丁寵:以養寵物代替養孩子;偽丁克:年輕未婚,玩心大,還沒有作決定的能力。
以初代丁克為例,理由各不相同。社會學家李銀河,在上世紀80年代,選擇做了丁克, “我們這個歲數,好多人連想都沒想過這種可能性。”丁克的決定是李銀河和王小波結婚前就商量好的,兩人一致認為,有人把生孩子當作維持婚姻的要素,他們感情很好,沒有這個需求。她面臨的輿論壓力很大,特別在工廠工作,不生孩子,人們會以為你有毛病,生不出來,不是不想生。

李銀河和王小波,可以算中國第一代丁克家庭。

沒有生育需求的,還有生活在上海的75后艾米夫婦。艾米是山東人,30歲時結婚。夫妻倆骨子里認為養育孩子責任太重大,高齡生育成本更無法承受。丁克的前些年,艾米試圖說服母親接受她的決定,但效果不佳。母親擔心親友的眼光,也擔心未來女兒婚姻不穩定。“以后男方萬一想要一個小孩,你怎么辦。”
十幾年過去,艾米和老公感情穩定,沒有孩子的婚姻反而自由自在、堅不可摧。母親見狀,“催生”的鋒芒才漸漸收了起來。“丁克必過父母關”是一個普遍現象。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呂永林,1975年出生,是一枚“鐵丁”。他直言,成年人應該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縱使最親近的人也無權干預你的生活。
呂永林最早丁克的原因是對小孩子不是“特別有感覺”,沒有小孩似乎不是人生的遺憾。另一個比較強烈的理由是,他不想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中,因為有了小孩兒,讓自己變成一個不想成為的人,或者去做一些所謂“降志辱身”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呂永林的愛人發現,周圍做父母的人好像對孩子有一種依附意識,父母渴望在子女身上尋找某種價值。“我也有顧慮,如果自己要了小孩兒,將來會不會成為那樣的老人。”
丁克的理由多種多樣,但初代丁克所處的輿論環境并不友好。《老友記》中扮演Rachel的詹妮弗·安妮斯頓因不生孩子飽受網友質疑。她回擊道:“社會一直在強加給女性一把生育枷鎖,或許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不只是生育和繁衍。”
還有一些人成為丁克的原因是來自原生家庭的影響。
在《最好的決定》一書中,十六個主人翁之一的米歇爾·休內芬,童年從未受到過父母的關注,只有嫉妒。母親覺得她和妹妹麻煩又惱人。父親與孩子們很疏離,父親與他們的交流是當牛奶灑了或者孩子們開口要錢時,父親大發雷霆。
米歇爾·休內芬30多歲時,身邊朋友們對孩子的渴望讓她驚訝,而她對此無感,且形容自己的家庭是“令我極度困惑甚至驚恐的”。
丁克的理由多種多樣,但初代丁克所處的輿論環境并不友好。《老友記》中扮演Rachel的詹妮弗·安妮斯頓因不生孩子飽受網友質疑。她回擊道:“社會一直在強加給女性一把生育枷鎖,或許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不只是生育和繁衍。”
“白丁”反悔
丁克一族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大概是以后如何解決養老問題?陳娜夫妻也有同樣的困惑。
51歲的陳娜對目前的丁克生活比較滿意。北京三環一套130平方米房子,貸款已還完,閑暇時還能全世界旅游,“天大地大自由最大”的日子讓人好生羨慕。但前不久,陳娜的丈夫生病住院,不好的感覺一下子襲來。陳娜想過,如果丈夫真的倒下了,生活還得過,現在自己能動,年齡大了就要打包住進養老院。“護工看我沒有兒女做后盾,萬一虐待我呢?”
陳娜開始學習心理學知識,苦練瑜伽冥想,為將來做鋪墊。她希望學會如何從心理上應對孤獨和恐懼。
艾米對未來的養老相對樂觀,養老金正在持續積累,保險早就買好了,幾條養老路徑隨時備選,比如,和幾個好朋友買一處別墅抱團養老,也可以回山東老家和妹妹一家協同養老,住養老院是“不能動彈”時的最后一步。 但也有丁克族反問:“誰知道養老問題怎么辦,有孩子的人就一定知道嗎?”
調查數據顯示,35—40歲是“白丁”概率最高的年齡段。“我身邊丁的,基本都白丁了。”今年38歲的志波表示。 志波和老婆丁了8年,目前沒有“變節”的打算。“那些當了爹的哥們,連踢球都戒了。我能熬夜看球,安靜看書,周末睡懶覺,不用進家長群討好老師,還能錯峰上班。想想這個,就能丁住了。”
志波很堅決做丁克,他打趣說,即便買彩票中了五百萬元,也絕不變卦。而初代丁克中,有些人早已從“鐵丁”跨入“白丁”。比較而言,男性丁克的反悔來得致命,即婚姻關系的瓦解。女性丁克則面臨更為復雜的狀況。
燕子選擇在43歲高齡生娃,連她自己都意外。42歲那年,燕子在日本經歷了一場地震,眼看著經過的女孩幾秒被壓在廢墟里,她腦袋嗡一下, 歇斯底里地去刨上面的廢墟,手指扎破了石板仍紋絲不動。
那一刻,燕子突然覺得想要個小孩。無法描述那一刻的轉變是什么,就像上天的旨意。38歲的獨生女喬伊,和父母相差40多歲,在經歷了親人相繼離世后,喬伊開始對年齡焦慮和悲觀,她反悔了,后悔沒早些要孩子,陪伴爸媽久一點。扛不住公婆頻繁催生,喬伊最終妥協。

依靠技術實現人工輔助生育。
但相比年輕人,中年人選擇逃離丁克隊伍,需要更大勇氣和更多的錢——人工輔助生育,以及突然多出來的育兒支出。燕子的年紀,幾乎是輔助生殖技術的上限,超過44歲,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成功率都極低;喬伊生完娃后,身邊沒有幫手,公婆快80歲,之前生病,留下了后遺癥,現在自顧不暇。她把自己困在了婚姻,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走。
喬伊和愛人早早為自己買了保險,他們打定主意以后孩子不用為他們的養老負責。雖然高齡生娃遭了罪,但看到孩子健健康康,也覺得值了。喬伊有時會安慰自己,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生孩子的最佳年齡,也不需要給自己那么多條條框框。她聽過關于什么時候要孩子,最好的回答是:當你想要一個孩子,想成為母親的時候。
有丁克女性試圖通過冷凍卵子,留給自己一顆“后悔藥”。事實上,特別是單身女子養育孩子,和我國目前法律存在一定沖突。關于冷凍卵子的高昂成本及其成功率還有待商榷。有業內人士直言,非常反對將冷凍卵子形容為一份“未來的保險”,因為這更像是一張“昂貴的彩票”,同時還涉及諸多法律以及社會倫理問題。
“被丁克” 潮流與無奈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趙夢晗的相關研究表明,大多數人丁克的原因更多出于理性考量。主要是經濟負擔比較重,孩子無人照料,以及越來越多的女性對于自身的職業發展有擔心。而男性在選擇丁克上的現實阻礙相對小一些。
近年來,因為經濟原因放棄生育的“被動丁克”家庭在全國各地,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多有存在。今年3月,世紀佳緣發布《單身男女結婚那點事》婚戀觀調查報告,解讀了當前單身男女對生育觀的不同想法。其中,近六成有婚史男性認為,相比設置離婚冷靜期,更需要“生娃冷靜期”。
在影響單身男女生育觀念的各種因素中,排在前三的分別是:家庭經濟實力、個人精力和個人職業發展。其中,61%的單身男性與73%的單身女性認為,家庭經濟實力是決定是否生育最重要的影響要素;44%的單身男性與56%的單身女性把“個人精力”放在了第二位。

有孩子的家庭也未必能走出養老困境。
44歲的李女士成長于西北某省會城市,之所以沒能盡快落實生育意愿,主要是當時兩人經濟條件一般,雙方家庭沒有提供經濟支援,且雙方父母明確表示不會幫忙照料孩子。在推遲生育的過程中,兩人看到有孩子的家庭圍繞孩子,生活“雞飛狗跳”。
被丁克的群體,還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生理原因。55歲的上海男士沒要孩子,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年輕時太太身體不好,倆人輾轉了多家醫院,求助無果。掙扎到四十多歲,依然膝下無子,索性對外宣稱“丁克”算了。在年輕人群體中,還出現了不少“偽丁克”,他們簡單以為丁克約等于自由,不用內卷、不用負責、自由比天大。這一潮流無形中也影響了一批不婚的年輕人。
然而,丁克決定不是兒戲。比方說,日本高度老齡化、少子化,曾是領銜丁克潮流的東亞國家。丁克至晚年的單身老年,沒了年輕時的自由灑脫,開始瘋狂相親。有意思的是,很多老人的相親要求,還停留在年輕時候的價值觀。比如男性希望對方能照顧自己生活起居,女性則在意收入等外在條件。從外人的視角來看,饒有意味。一邊是不愿結婚的年輕人,一邊是忙著相親的老年人,仿佛是兩個不同的時空,重疊在一個社會。(艾米、陳娜、喬伊、志波、燕子、小樂、梅姐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