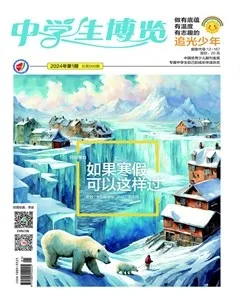看,它們在發光
那些時刻我一直記得,那些書我真的讀過,那個人我一直愛著。
初秋歸家路上,我倚著車窗,像往常一樣注視著外面的風景。有那么一瞬間捕捉到光束穿過層層遮蔽的樹葉間,頓時光影萬千,隨而斑駁搖曳的金線映照在我的臉上。
每次坐車都喜歡靠著車窗,只是因為能夠欣賞沿途風景;每次寫作業總是喜歡放著自己喜歡的歌曲,只是因為慶幸自己能夠擁有片刻的輕松;每次喜歡獨行在人煙稀少的街道里,只是因為自己獨愛那種無人問津的氛圍。那年我十七歲,在如此浮躁的世界里,一直往前走,沒有想過回頭。倏爾停下來,忽然發現有些東西竟在背后閃閃發光。
從兒時起就住在一個小鎮上,那兒依山傍水,沒有奔流不息的車輛,更沒有燈紅酒綠,有的只是滿是叫喝聲的老街,只是路旁老爺爺賣的熱湯面,只是樹影中流浪貓睡熟的身影。那時,天不大亮就被父母從沉睡中拉出來,急急忙忙洗漱之后就趕去上學,在路旁買一碗熱湯面作為早餐。
以前總是會在那樣的午后時光遠望著蔚藍的天空,和小伙伴暢想著以后的未來,那時候以為,這就是永遠。
邁入青春期后,我還是愛和同伴打成一片,有時打鬧中無意被傷到,很疼卻故作深沉地說不疼;考試很差,明明很傷心卻故作樂觀地說,就一次小測驗而已;被老師批評后明明很羞愧,卻故作釋然地說沒事,任他吵。會認真聽課,也會課上帶著幾個人一起開小差;會認真寫作業,也會給睡覺的同桌打掩護;會討厭那些愛搞惡作劇的小男生,也會欣賞成績有待提高但有很多奇思妙想的同窗。
那時,總覺得自己很獨一無二、隨性。經年之后,在一次和好友的交談中,無意中發現她的想法與感受與我相似,我一邊應和,一邊釋然地笑著明白:原來我們都好強,都愛展示自己。那時的我們是多愁善感的,那種多愁善感,不似文人的那般透徹,而是夾雜著童稚與成熟的純澈。
倏爾,我望向窗外的大樹,同樣也是陽光斜照,光影斑駁,驀然想起了截然不同的一個午后:幾只紙飛機千轉萬轉地穿過樹干,嚴肅的教學樓上歡呼不斷。不巧,一群人的視線同樓下走來的老師對接,隨后映入眼簾的便是他直逼人的手指,剎那間走廊中的人消失不見,唯有朗朗的讀書聲回蕩在老師的耳畔。我靜默地笑著,好友不解,我淡淡地說著,沒事,只是想到從前的事罷了。
高中生活很嚴格。最起碼我能將年級主任每周一次宣講的百字要求一字不差地說出來。我們每天都能看到通報牌上值班老師的粉筆字龍飛鳳舞,也常談論到這個那個制度很奇葩,嚴格的環境里我卻能和朋友找到空子:遲到的時候總是讓她以意外為理由幫忙請假,上課傳紙條你幫我看老師、我幫你打掩護……那個時候,我十六七歲,沒那么多故事可講,可同窗的友誼卻一直銘記于心,長久而彌足珍貴。
平凡的生活中也會有朦朧的暗戀,自此,少女的思緒有了模樣,筆尖也有了走向。
那些時刻我一直記得,那些書我真的讀過,那個人我一直愛著。
人總是在不斷的失去中長大的。
當手里的試卷再也變不成童年的紙飛機,當電視機里的肥皂劇再也變不成童年的動畫片,時光帶走的不僅僅是記憶中的瑣碎,時光留下的也不僅僅是點點的溫情。
回頭看,有些東西正在時間的長河里閃閃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