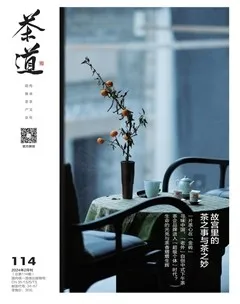燈明宮樹色,茶煮禁泉香
楊巍



一座故宮,橫跨明清600余年。這6個多世紀,雖是風云變幻,卻是茶香彌漫,滲透于宮廷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從日常飲用、藥用到祭祀、宴飲、賞賜,都離不開茶。
明清兩代,愛茶、懂茶者莫若乾隆,他品茶鑒水,辦茶宴,作茶詩,建茶舍,茶范凡十足。“燈明宮樹色,茶煮禁泉香。”宮闕里,杯盞間,是雍容華貴的皇家氣象。
壹
日飲:皇家日用茶
明初朱元璋下旨廢除團茶、一律改貢芽茶后,擺脫了外形束縛的茶,隨著制茶技術的不斷進步,由單一的綠茶漸漸演變出多茶類。
正式形成于唐代的貢茶制度,歷宋元明的承襲與完善,至清已臻于完熟。在幅員遼闊的版圖上,共有13個省進貢茶葉,品類繁多、形狀各異,如龍井茶、碧螺春、普洱茶、武夷茶、銀針、鄭宅茶、珠蘭茶、六安茶、天柱茶、八仙茶等等,匯聚了各省的名茶。就形態而言,有散茶、餅茶、團茶、磚茶、柱茶、茶膏等。包裝形式,更是多姿多彩,如金屬(錫、銀制)罐、陶瓷罐、紙盒、筍葉等。
茶入宮后,便由專設的機構來儲藏與管理宮廷用茶,并配備相應的管理人員。清宮就設有茶庫、茶房、御茶房、御茶膳房、奶茶房等機構,各司其職。皇后、壽康宮皇太后、南三所阿哥以及皇子皇孫成婚后在宮中的居所,也有各自的茶房,這類茶房屬操作間性質,由太監或宮女置備茶飲、小吃等。
于是,每年春來,茶庫就會陸續將來自各省進貢的各類名茶收儲,讓皇室能在一盞茶里品嘗南方駘蕩的春色。
三宮六院用茶,每月定期定量從茶庫領取,身份、等級不同,分配到的茶葉數量也有差別。以黃茶為例,皇后茶房、貴妃茶房、妃嬪茶房每月例用的茶分別為六百包、三百包和一百五十包。各機構用茶亦由茶庫定量供給。比如,乾清宮、武英殿每月領散茶三斤,內閣每月領散茶五斤等。
貢茶品類豐富,飲茶方式也很多元。除清飲外,還有奶茶,這是清人入關前就有的生活習慣,且是待客重要禮節:“滿族有大宴……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茶”。在各類筵席中,奶茶也是必不可少的。光祿寺就專門配備11名蒙古人,專事朝廷筵席上奶茶的熬制。
與貢茶一樣,制作奶茶用的乳牛頭數份例也有一套等級森嚴的制度。比如,“皇上每日乳牛一百頭,皇太后二十四頭,皇后二十五頭,貴妃四頭,妃三頭,嬪二頭,阿哥娶福晉后八頭。”
最懂茶、喝茶也最講究的莫過于乾隆。他一生喝遍天下好茶,自創以梅花、佛手、松子仁入茶烹以雪水的“三清茶”,六下江南時隨身攜帶方斗稱量泉水重量,寫有200多首茶詩,首創重華宮茶宴,擁有春風啜茗臺、干尺雪、竹爐山房等15處茶舍,留下“君不可一日無茶”的佳話。
慈禧太后則喜歡“以花點茶”一一喝茶時加入少許金銀花、菊花、蓮花、梅花、桂花、玫瑰、茉莉等香花,茶香更深。
貳
藥用:藥茶“養生黨”
清宮里,也有很大一部分貢茶是藥用的,而茶最早就是以藥的面目進入人們生活的。許多關于茶的傳說,多以茶治病療疾為目的,如大家都熟悉的神農氏嘗百草,以茶解毒。歷代醫書中,也有不少茶藥方。清代,記錄藥茶的著作就更多了,以茶代藥的代茶飲是宮廷日常保健養生的必需品。嘗遍山珍海味的皇室貴族,都是不折不扣的藥茶“養生黨”。
比如,具消食解膩之功效的普洱茶就很受寵。方以智云:“普洱茶蒸之成團,西番市之,最能化物與六安同。”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云,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苦瀒,逐痰下氣,刮腸通泄”,“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乾隆也有詩云:“獨有普洱號剛堅,清標未足夸雀舌。點成一碗金莖露,品泉陸羽應慚拙。”(《烹雪用前韻》)
據《宮女談往錄》記載,慈禧太后晚飯后,“敬茶的先敬上一杯普洱茶,老太后年事高了,正值冬季,又剛吃完油膩,所以要喝普洱茶,圖它又暖,又能解油膩。”
由普洱茶熬制而成的普洱茶膏,內用外敷都合用。俄國學者葉·科瓦列夫斯基曾這樣寫道:“此外還有一種特制成小方塊的緊壓茶,非常的昂貴。其汁液苦澀黏稠,可用普洱茶或者是其他的茶熬制而成。其中經常還要加入各種藥材,甚至高麗參。咀嚼這種茶可以生津、幫助消化。”(《窺視紫禁城》)
清宮舊藏的普洱茶膏就有“肚脹受寒時,用姜湯與茶膏同煮飲,使身體出汗即愈,當口破舌喉受熱疼痛時,用五分茶膏噙口過夜,即愈。當受暑,擦破皮膚出血時,將茶膏研面敷患處,即愈”的說明。還有人參與茶混合熬制的人參茶膏,具補氣生津、補脾益肺等多種保健功效。
還有一款“仙藥茶”,在清宮檔案中被反復提及。該茶由六安茶、烏龍茶,配以紫蘇葉、澤瀉絲、石菖蒲、山楂加工而成,有減肥消滯、化濁和中等功效,對感冒、中暑引起的頭疼腦熱,以及病后消化不良、惡心嘔吐等癥狀也有不錯的療效,是四季必備之良藥。
叁
茶禮:皇家儀式感
在祭祀、朝會、經筵、視學、節日典禮等宮廷禮儀中,茶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滿滿的儀式感與皇家氣派。
最早見諸文字記載的茶祭,是在南齊。據《茶經·七之事》引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乾飯、酒脯而已。”《南齊書·禮志》亦有“永明九年……昭皇后茗、炙魚;皆所嗜也”的記載。
清初,各項儀式多用酒,后多以茶代酒。比如,供奉歷代皇帝圣容像的壽皇殿,每天都會以茶上供:“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壽皇殿中龕上供每日用普洱茶五錢,東龕上供每日用普洱茶五錢,安佑宮中龕上供每日用普洱茶五錢,東龕上供每日用普洱茶五錢。”(《宮中雜件》卷號四,第2088包,《物品類·食品茶葉》)
清代朝會有大朝與常朝之分,大朝是元旦(大年初一)、冬至和萬壽節(皇帝誕辰),常朝就是日常的上朝。常朝上,“上進茶,王以下文武各官,俱就坐次,行一叩頭禮畢,光祿寺執事人員,賜各官茶,各官就坐次行一叩頭禮,飲畢,再行一叩頭禮。”
遇到像萬壽節這樣的大朝,茶禮的排場就更大了。1790年,朝鮮后期文臣徐浩修以行團副使、禮曹判書的身份專門赴京參加乾隆80歲的萬壽慶典,回國后寫了日記體旅行記《燕行紀》。書中出現了32次與茶有關的內容,主要記錄了從7月16日-8月20日這段時間的宮廷茶禮。
經筵日講是帝王為講經論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是宮中重大教育活動。比如,1652年,“春秋各舉經筵一次”,經筵前一日,皇帝和文武百官祭拜孔子,經筵禮上,君臣一同品茶議政。1787年,乾隆特命演奏《抑戒》之章,以樂清耳,以茶悅心,所用之茶由光祿寺承辦的奶茶。
視學儀是皇帝聽取國子監祭酒講四書的禮儀。如1669年康熙朝的視學儀:“上幸太學,行釋奠禮……禮畢后,滿漢講官進講,講易經、四書等,之后賜王以下各官茶。次日,于太和殿賜座賜茶”。《(康熙)大清會典》)賜坐賜茶是皇帝給講官最高的禮遇。
此外,藉田禮。千秋節,皇太后大慶、問安,宮中大婚,皇后、貴妃、妃、嬪、皇太子、諸王、公主、王妃冊立冊封等慶典,也有飲茶、賜茶的環節。
肆
宴飲:無茶不成席
皇家各類宴席中,更是少不了茶。茶宴始于魏晉,興于唐,宋代漸成規模,知名者如延福宮茶宴,愛茶懂茶的宋徽宗就曾為群臣親手點茶。到清代,茶宴的規模越來越大,最有名的茶宴,就是干叟宴和重華宮茶宴。
千叟宴,是清宮中規模最大、參與者最多的皇家盛宴。1713年,適逢康熙帝60大壽,各地官員極盡奉迎之能事,鼓勵一些老者進京祝壽。康熙一高興,決定在故宮外的暢春園舉行“干叟宴”,共有1800余人參會。后來,又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和乾隆六十一年(公元1796年)舉辦過3次,兩次在乾清宮,一次在皇極殿舉行。1785年這次,多達3000人參加,最高齡者104歲。1796年,參會人數再升級,達3000多人,另有受邀賞而未入座的5000人。此宴共設席800桌,桌分東西,每路6排,每排最少22席,最多100席。如此巨大的宴會規模,放在今天,也是妥妥地入選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
盛宴開席,第一步即“就位進茶”。樂隊奏樂,御膳茶房向皇帝父子各進茶一杯,王公大臣行禮。皇帝飲畢,再分賜群臣共飲。進茶、賜茶,用的都是紅奶茶。宴后,所用茶具也皆賜飲者。受賜者接茶后,原地行一叩禮謝恩。
重華宮茶宴,始于乾隆年間,自正月初二至初十日,擇吉日舉行。乾隆本身就是一個愛喝茶愛作詩的文藝皇帝,便效法古代文人雅士,把文士茶會搬進了自己的私人寢宮。受邀赴宴者,皆由乾隆欽定,主要內容就是飲茶作詩。最初,人無定數,多為內廷當值詞臣。后定為72韻,乾隆親自出題,會前預告。也有“御定元韻”,是臨時命題,現場“考一考”這些詞臣的作詩功力。當時,直接在宮內參會賦詩者僅18人,取“學士登瀛”之意。詩成,先后進覽。乾隆隨即賜茶、頒賞珍物,受賜者頓感無上榮耀。君臣所作之詩,都收入《御制詩集》。
席上,有一道主打茶品——乾隆自創的“三清茶”。該茶品甄選上好的松實、梅花、佛手,以雪水烹之。有時,也有加入龍井新茶沖泡。有詩為證:“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潔。松實味芳腴,三品殊清絕。”(《三清茶》)他還命人燒造御制三清茶詩茶壺、茶碗、茶盤等,茶宴結束后,與會者們“懷之一歸”。除皇太后大喪外,重華宮茶宴年年辦,一直延續到道光朝,共有60余次,但都遠不如乾隆朝之盛。每年除夕及正月十五,皇帝還會賜外藩蒙古宴,由進茶大臣向皇帝進茶。
伍
賜茶:“天朝”的厚賞
賞賜是皇帝獎賞、籠絡、撫慰臣子的一種常用手段。賞賜品種類多樣,茶便是其中最常見的。
有清一代,賞賜有例行賞賜和非例行賞賜之分。前者是指按規定或慣例向臣子、外藩、國外使臣等進行賞賜。后者則隨意性很強,完全看皇帝心情。“洗盡炎州草木煙,制成貢茗味芳鮮。筠籠蠟紙封初啟,鳳餅龍團樣并圓。賜出儼分甌面月,瀹時先試道旁泉。侍臣豈有相如渴,長是身依瀣露邊。”(查慎行《謝賜普洱茶》)字里行間,盡是受賜的欣喜與激動。“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阮福《普洱茶記》)普洱茶,在清宮中是上得了大臺面的茶,除皇室日飲外,也常用來賞賜臣下,數量也較大:“嘉慶二十五年賞醇親王、端親王、惠郡王、大阿哥綿悌普洱茶吃,每位一月用六兩,一年共用二十二斤八兩。賞如意館畫畫人等普洱茶吃,每月用二斤八兩,一年共用三十斤……”。
賞給外藩各部的茶,數量更大,也更頻繁,品種以普洱茶、安化茶為主。《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中,僅是關于賞賜外藩茶葉的記載,就有數百條。比如,“康熙元年十月十日,賞喀爾喀達爾汗親王茶一竹簍,浩齊特部阿賴崇額爾德尼郡王茶一竹簍,喀爾喀布木巴西喜貝子茶一竹簍,車根固木貝勒之四品臺吉滿西里茶一竹簍。”
以蒙古為代表的西北游牧民族,食肉飲酪,十分仰賴可解油膩的茶,故有“寧可三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之說。
向來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朝,對外國使臣的賞賜則是厚往薄來,以彰顯懷柔遠人、德化四夷的天下觀。這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乾隆皇帝的賞賜清單中便可窺得一斑。現摘錄若干:
擬賞英咭喇國王:普洱茶八團,六安茶八瓶,武夷茶四瓶。
酌擬加賞英咭喇國王:普洱茶四十團,武夷茶十瓶,六安茶十瓶,茶膏五匣。
擬隨敕書賞英咭喇國王:普洱茶四十團,武夷茶十瓶,六安茶十瓶,茶膏五匣。
酌擬加賞英咭喇國副使:普洱茶四團,六安茶四瓶,茶膏一匣。
賞副使之子哆嗎·嘶當東:茶葉二瓶,磚茶二塊,女兒茶八個,茶膏一匣。(故宮掌故叢編:《英使嗎嘎睨呢來聘案》)
從國王到全部使團成員,人人有份,豐厚的賞賜。不過,從帶有“口”字旁的國名、人名來看,滿是赤裸裸的鄙夷。很顯然,乾隆把大洋彼岸的英國也當成像安南、朝鮮一樣來朝貢的藩屬或蕃夷了,全然是一副居高臨下的傲嬌姿態來對待。
殊不知,使團滿載而歸后不到50年的時間里,英國就用船堅炮利轟開了清朝的大門。戰爭背后,是茶葉與鴉片的博弈,落后與先進的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