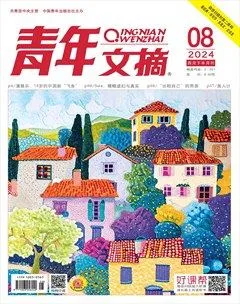一個二本大學教師決定去家訪

大學教師黃燈被人所知,是因為她對100 多名80 后90 后的觀察與講述,寫成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揭開了大學“精英教育”的另一面,出版后引發了社會的廣泛討論。最近,黃燈又出版了《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以下簡稱《去家訪》)。
郁南、陽春、臺山、懷寧、陸豐、普寧、佛山、饒平、湛江、遂溪、東莞、廉江、韶光、孝感……5 年,她利用周末與寒暑假,去了20 多個學生家中,不乏跋山涉水的漫長旅途。
黃燈說,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是一本立足講臺視角的教學札記,那么《去家訪》是走下講臺、走進學生家庭實地考察和親歷的家訪筆記。這讓“二本學生”有了更完整的表達。
日常生活在學生少年時代都是“教育資源”
在校園,黃燈對學生的了解基本來自她對學生的直接觀察或者學生對她的講述,但黃燈始終覺得,每個學生的背后都是一個家庭的支撐,如果只停留在學校范圍,對一個孩子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于是,她決定去家訪。
家訪的路其實在寫《我的二本學生》之前就已經踏上。2017 年暑假,應2010級學生黎章韜邀請,黃燈家訪的首站是云南騰沖。“去家訪這個決定是對的。”黃燈說,“我看到了一個開闊、豐富、綿密而又糾結的世界,這個世界鏈接了學生背后成長的村莊、小鎮、山坡和街巷,也召喚了他們的父母、祖輩、兄弟、同學和其他親人的出場。”
黃燈教過的農村學生,父母幾乎都有外出打工的經歷,當一個名叫羅早亮的學生說自己父母從來沒有長期外出打工時,黃燈產生了好奇。去家訪后,她才明白,羅早亮的媽媽從兄弟姐妹的不同命運軌跡發現了兩個關鍵點:一是家庭要有盼頭,必須重視教育;二是孩子出生后,帶好孩子比外出賺錢更重要。
“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在父母陪伴下長大的孩子,盡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學,但從他們的狀態來看,那些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加內向、不自信、容易緊張。”黃燈說,“隨著家訪的家庭越來越多,我更加深刻地感知到,不同的家庭教育會給孩子們帶來完全不同的影響。”
在《去家訪》的出場人物中,除了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是重要角色。黃燈發現,如果一個孩子能得到祖輩的愛,長大之后,他們的內心往往會更柔軟一些,這是她之前不曾意識到的。黃燈看見何健站在爺爺墳前的鄭重和追念,看到何境軍扶著中風的爺爺在客廳散步……“也許是祖輩的愛更無條件,父母會要求孩子的成績、排名,而祖輩只希望孩子健康長大。這種無條件地接納會給孩子很多勇氣和力量。”
“父母的生計、勞動的歷練、祖輩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這些具體的日常生活,在學生的少年時代,都是一種‘教育資源’。”黃燈說,“這些才是他們更為根本的成長底色。不談社會結構,單純從個人層面,家庭教育對學生的權重,也絕對不會比學校教育輕。”
學校教育能幫孩子擺脫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
黃燈自身的履歷并不“光鮮”:出生于湖南農村的多子女家庭,1992 年讀大專,畢業后在工廠干過文秘、會計;1998 年工廠難以為繼,她決定考研,被武漢大學錄取,2002 年考上中山大學博士;2005 年開始,成為廣東一所二本大學的教師。
看著自己的學生們,黃燈有時候會很糾結:一方面,現在上大學的“性價比”已經沒那么高了,但這些孩子和家庭付出那么多,又抱有那么深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上了大學,他們有了更多在社會上立足的機會。如果再拉長時間去觀察,可以發現,很多學生的前途比沒有上大學會好很多。
黃燈強調,《去家訪》中講了諸多家庭對孩子成長至關重要的影響,并不是否認學校教育。相反,學校教育可以幫助孩子擺脫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我曾經一度認為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是絕對的,但去家訪之后發現,原生家庭影響很大,但對于主動性強、生命力強的孩子來說,是可以擺脫的。”
黎章韜在大學喜歡看課外書,閱讀量很大。在父親的木藝作坊接待客戶時,他發現,與客戶的交流很少直接觸及產品,而是聊其他話題。這讓黎章韜意識到,“說到底,與客戶產生共鳴后,他們信任我、認可我,進而認可我的產品”,這無形中為家庭搭起了一種新的銷售模式。
黃燈坦言,在去家訪之前,她對二本學生的整體去向是比較悲觀的。但當她有機會貼近孩子們的“來路”,看清他們一路走來的過程,發現對這些孩子來說,考上二本大學是一件很難的事,但無論社會的縫隙多么狹小,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
去家訪,不僅僅是自己作為旁觀者的觀察,對學生來說也是大學課堂的延伸,有了重新認識家庭與家鄉的契機。一個名叫吳浩天的學生告訴黃燈,老師沒來之前,自己從來不覺得生活的村子有什么特別,“現在覺得還蠻值得一看”。
一位名叫張正敏的女生,之前對爸爸與哥哥充滿了抱怨——不可否認,重男輕女的家庭確實連累了她。當她重新了解家庭后,發現爸爸本來就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當城鎮化進程裹挾他前行,他的努力也沒有得到回報時,他的一些行為也就有了“重男輕女”之外的解釋。
“傳統中國”的教育啟示
黃燈去家訪還有一個“私人目的”,作為一位母親,對于很多困惑她的家庭教育問題,希望能在與學生家長的交往過程中得到啟發。
“我們這些通過讀書獲得工作、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教育觀念上可能傾向于‘愛與自由’‘與孩子做朋友’等理念。但我發現,我的學生家長的一些傳統教育理念,其實是有效的,尤其對孩子品格的錘煉非常有效。”黃燈說。比如,父母保持一定的威嚴身份,孩子往往更容易形成好的習慣,于魏華爸爸為了讓他專注學習,無論多累,晚上都要陪他做作業,堅持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他能管好自己;羅早亮媽媽堅持孩子一定要勞動,要分擔家務,絕不嬌慣孩子。
在潮汕之行中,黃燈穿梭于各個原生態村落,深刻感受到“傳統中國”的日常。與建筑一樣保存完好的,是當地傳統生活方式和民風民俗的傳承。黃燈說:“我觀察到,潮汕的孩子,往往更能認同勞動、實干的觀念,更有集體和團隊意識。”
《去家訪》書中寫到的孩子,幾乎都是勤快的,勞動是生活的日常。黎章韜在小學就熱衷和村里的小伙伴們一起撿垃圾、拾廢鐵;羅早亮從7 歲就開始學著做飯……
這讓黃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農村待過的人都知道,每個人都要參與勞動,在家里有家務,其實這對一個人的能力培養是非常好的”。同時,勞動讓孩子的情感更加飽滿,“他們會更加心疼、理解自己的父母,也更珍惜自己得到的東西”。
黃燈認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孩子心理脆弱不安,與從小缺乏勞動鍛煉有關系,“他們沒有切膚的痛,也就沒有切膚的快樂,他們的生命經驗是空蕩蕩的”。
此外,父母也不要為了給孩子提供一個所謂更好的學習環境、成長環境,而去刻意營造一個假的環境,“孩子應該和父母一起分擔家庭的責任,讀書并不是‘天大’的事”。
因為家訪,黃燈進一步堅定了一個判斷:她龐大的二本學生群體,構成了中國大學生的大多數,成為社會的重要支撐;他們的家長,作為勞動者的主體,以自己的勞作和付出,同樣構成了中國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基石。
“所有片段、場景和抵達,在我腦海中繪就一幅動態而清晰的畫卷,接通了一個豐富而真實的中國。”黃燈說。
(摘自2024 年1 月26 日《中國青年報》,胡凝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