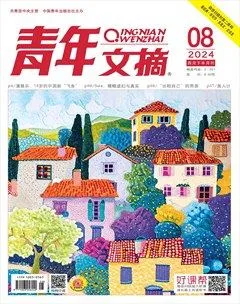《留校聯(lián)盟》:用傲慢與偏見治愈生活

《留校聯(lián)盟》就像一張充滿膠片質(zhì)感卻又歷久彌新的照片,在圣誕鐘聲敲響時,壁爐前取下的治愈人心的禮物。而這份禮物,也讓我?guī)е斫馀c感恩迎接新的一年。
有影迷評論說,《留校聯(lián)盟》像《死亡詩社》和《放牛班的春天》,刷過這些影片的觀眾大概都不陌生,關(guān)于老師和學(xué)生、教育與成長之間的故事。而《留校聯(lián)盟》雖然講的也是師生故事,卻不是老師啟發(fā)學(xué)生精神世界的套路,而是一個缺點滿滿的古怪老師和一個問題少年在相互較勁中逐漸和解與救贖。
故事開始于1970 年的圣誕節(jié)前夕,在一所貴族寄宿學(xué)校里,古代歷史老師保羅嚴(yán)苛刻板,說話尖酸刻薄,于是校長要求他假期留校監(jiān)督無法回家的學(xué)生。
而搗蛋少年塔利成為唯一被迫留校的學(xué)生。囿于父母離異的破碎家庭,塔利性格叛逆屢屢闖禍被迫轉(zhuǎn)學(xué)。留校對這對性格孤傲的師生來說無疑是一場血雨腥風(fēng)。
而同時留校的,還有廚師長瑪麗,她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悲劇,兒子在戰(zhàn)爭中犧牲,獨留她一個人。
于是, 一個固執(zhí)的老師、一個喪子的母親和一個迷茫的年輕人組成了“留校聯(lián)盟”,在平安夜之際,相聚在一場圣誕派對上,在大伙歡聚的時刻,他們各自經(jīng)歷著悲傷。
在學(xué)校里,保羅古板的行事風(fēng)格讓校長和學(xué)生都不待見他,但保羅對學(xué)生的唾罵和校長的施壓毫不在意。他常常孤身一人,窩在辦公室做學(xué)術(shù)研究。
塔利瘦削冷峻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敏感脆弱的心。他渴望父母的愛而不得,只能以叛逆出格的方式來反抗。但母親的一次次冷落,讓孤獨與傷痕在少年內(nèi)心滋長。
或許邊緣人的內(nèi)心深處總有一絲惺惺相惜,一場波士頓大冒險,成為他們的破冰之旅。
原來古板的保羅也曾是哈佛的高才生,因被貴族同學(xué)抄襲論文反被誣陷,遭學(xué)校開除。從此只能當(dāng)一名中學(xué)老師。
而當(dāng)塔利見到患精神病的父親時,父親依然認不出他。那一刻,希望化為泡影,塔利也成長了,他必須接受父親發(fā)瘋、父母離異的現(xiàn)實。
保羅的刻薄是一層保護殼,塔利的叛逆是一種渴望愛的掩飾。相互剖開秘密之后,兩人開始惺惺相惜。塔利會替保羅化解尷尬,而保羅犧牲自己被學(xué)校解雇,保全了塔利的升學(xué)機會。此刻他們更像一對地位平等的朋友在交流,又像一對相互理解的父子在為對方解難。
瑪麗作為出身底層的黑人,她的兒子要參加越戰(zhàn)才能獲得白人階級輕而易舉的升學(xué)機會。她拷問命運的不公:“我的兒子深埋地下,而那些含著金鑰匙的孩子卻能睡在安全又溫暖的床上。”但瑪麗最終也在妹妹剛出生的孩子身上治愈了喪子之痛。
保羅、塔利和瑪麗,三個年齡、種族、性格差異明顯的人,從一開始充滿傲慢與偏見,到中間悲傷軟化,到最后敞開心扉,消融彼此的孤獨,很像我們?nèi)粘I钪衅胀ㄈ说男穆窔v程,所以我們感同身受,能夠理解那份深埋心底的情感。
《留校聯(lián)盟》沒有波瀾起伏,沒有逆轉(zhuǎn)命運,甚至結(jié)尾有點讓人悲傷。就像一條小溪靜靜流淌,直面生活的瑣碎,命運的失意悲涼,而在矛盾隔閡化解后,人物彼此之間能找到慰藉,給生活中的我們傳遞出一股堅毅的力量。
電影與此前火遍全球、同為奧斯卡大熱門的《奧本海默》和《芭比》相比,它的故事顯得平淡而“老派”,但冬日的格陵蘭島,古典的配樂,加上膠片感十足的鏡頭,在20 世紀(jì)70 年代的這個舊世界中,導(dǎo)演佩恩用笑料嘲諷虛偽和權(quán)力,用自嘲寬恕失敗和不幸,用克制展現(xiàn)悲憫的人生,直到結(jié)局也并不圓滿,卻始終呈現(xiàn)著普通人生活的厚度和溫度,傳遞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電影中,保羅送給塔利和瑪麗的圣誕禮物是同一本書:馬可· 奧勒留的《沉思錄》,馬可是古羅馬皇帝,他的人生哲學(xué)觀就是認真樂觀地生活,善于思考,保持理性。這也是電影暗含的主題。
就像保羅說的:“生活就像雞舍的梯子, 又臭又矮。”那又怎樣呢?我想用羅曼·羅蘭最經(jīng)典的名言來回答:“認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
面對一地雞毛,我們痛苦過,也掙扎過,我們脆弱過,也勇敢過,盡管世界苛刻,生活艱辛,我們還是會重拾信心,樂觀向上,那就是對命運最無聲而堅定的反抗。多年后,當(dāng)再次翻開圣誕電影收藏夾看到這部電影時,那股溫煦的情感又會徜徉心中,治愈當(dāng)前生活的一片狼藉。
(本刊原創(chuàng)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