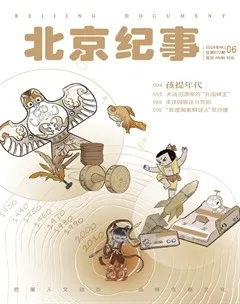從喜歡“遠足”,到被稱之為“北京城癡”

2019年10月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刋的記者王劍英,在對我作了采訪之后,以“北京城癡朱祖希”為題寫了一篇專訪。
這篇專訪以拙作《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后結晶》入圍中央電視臺2018年度中國好書,并以該書英文版參加第71屆法蘭克福書展首發式作為切入點,對我本人數十年來孜孜以求,遵循先師侯仁之先生所開辟的科學道路,對古都北京所作的研究和業已取得的成果,作了至為熱誠的深度報道。
今天,我擬借《北京紀事》之邀,把我從打小喜歡遠足,到高考時報考北大地質地理系的淵源略作一點敘述。
出生寒門卻酷愛“遠足”
那是在在80多年之前一個凌晨,我出生在一貧寒的書香之家——年屆40歲的母親生下了我。
這是一個“書香寒門”之家:我的太公(曾祖父)是舉人,爺爺(祖父)是秀才,到我父親這一輩兒,雖已沒有了科舉之設,不用去為求得“一官半職”的前程而嘔心瀝血,但也當了一家制作糕點店鋪的大伙計;母親雖不識字,但卻是一位能耐得住勞作,且相當精干的女人。我們兄弟四人,我最小,還有一位姐姐。我們朱家原先由老一輩掙下的一點點家業,早已被抽大煙的“小爺爺”(我祖父的弟弟)倒騰殆盡……我們是寄住在外婆家的一間祖屋里的。后來,大哥被抽了壯丁,二哥三哥給人做了學徒工。家境雖然清苦,但尚可勉強度日。
只是“屋漏偏遇連夜雨”,我父親在我4歲的時候,竟不幸病故了。臨死之時,只給我母親留下了一句話:就是要飯,也要讓孩子去念書……
原來,我們朱氏家族有一個用宗祠的田租辦學的傳統,且也已辦有一所學校——浦江縣私立樸里小學。凡朱姓子弟都可以在這所小學免費入學。因此,當我在年屆6歲的時候,就進入該校上了一年級:“大羊跑,小羊跑。跑、跑、跑……”我大聲地讀著課本里的課文!
樸里小學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總共4個班,一位校長、兩位先生,三門課——國文丶算術和習字(寫毛筆字:一天大楷、一天小楷)。先生對三門功課的要求都很嚴,而且每篇作業都批改、寫評語,包括背課文、寫作文、做算術題、寫大楷、小楷等,稍有不慎,便會有輕則“留校放晚學”、重則“打手心”作懲罰。但是,每個學期都有一次“遠足”,即春游、秋游——由先生帶著學生,扛著校旗、背著書包(實際上是帶著炒米粉、玉米餅子、番薯一類的干糧)到城外去郊游,或游山玩水,或走訪名勝古跡、古村落等。不想,就是在這一次又一次的“遠足”之中,埋下了我熱愛大好河山,喜歡探訪名勝古跡的濃烈興趣,而且在高中畢業填寫高考志愿時,一連三個志愿都填寫的是“地理”類專業。
因為在當時,還沒有設“旅游”專業,當然更沒有像“旅游學院”一類的大學。當時我的第一志愿的專業填的是“經濟地理”;同時又想要到我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去讀書,因之第一志愿的學校一欄里,便就填的北京大學。不想,我竟如愿以償——考上了!
何以被譽“北京城癡”
盡管,我對新華社記者在專訪的文章中把我稱之為“北京城癡”稍有微詞,但在我心底里,卻還是樂于接受的。因為,我確確實實喜歡北京、熱愛北京,更樂意去探索蘊含在其中的種種奧秘!
1955年8月下旬,我懷揣著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和家鄉的一塊泥土,用一條兩頭帶鉤的竹扁擔,挑著母親給我準備下的行李,拜別老母和故土,先到杭州全國統一招生委員會去申請路費,然而乘火車北上抵達北京。
開學的第一天就是由地質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先生,向新同學致《歡迎詞》。緊接著,便又上了令我終身難忘,也是讓我終身受益的一堂課——“歷史上的北京”。這一課對我真猶如醍醐灌頂,如沐春風:
它讓我懂得了上課的重要性。因為老師在課堂上的授課,是對某一門課程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的講授。所以,一定要盡心聽講、作好筆記。與此同時,還要查閱老師指定的參考書并作好筆記或做成資料卡片。
要重視實際考察,使書本知識與實踐宻切結合起來,讓課堂和書本知識,通過實踐學得更扎實、更透徹。
要學會鑒別知識的真和偽,要懂得對科學知識的追根溯源。因為科學知識猶如自然界的河流,越是上游的水,就越純凈、越真實。
要學會善于聯想,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更要善于甄別、去偽存真,不斷積累。
這堂課也使我了解到,古都北京所擁有的歷史文化是多么的厚重——它猶如一座永遠也探索不盡的科學殿堂。
正是這堂課,像一顆充滿生機的種子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并促使我癡迷于對古都北京的探索——我曾爬上高大雄偉的城墻,撫摸過一座座歷經風雨,卻仍然屹立著的城門;我也曾流連在布設在大街兩邊,大小不同、長短各異,卻排列整齊的胡同之中;我也曾走進布局嚴整、花木扶疏、別有洞天的四合院;甚至,還深入地考證了永定河與北京城的起源、成長,乃至變遷之間存在的、血肉相連的關系。當然,我也曾徘徊在高大宏偉、金碧輝煌的故宮之中,并去探索它們那深邃的文化淵源和古代匠師們嘔心瀝血所創出來的人間仙境的意匠所在……以至在后來,還成就了我傳承師業、探索古都北京文化淵源的學術成果——《營國匠意》(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和《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后結晶》(入圍“中央電視臺2018年度“中國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