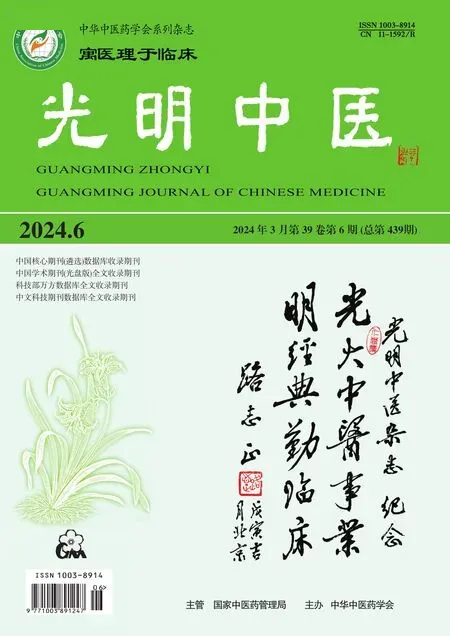刮痧療法臨床研究現狀與展望*
鄭涵尹 劉建材 李傳芬 鄒學敏
刮痧療法是指用特定的刮拭工具,在人體皮膚表面特定部位進行刮拭,達到疏通經絡、調節臟腑、防治疾病的非藥物療法。從古至今,刮痧療法在疾病防治和健康維護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刮痧療法由舊石器時代的砭石療法逐漸演變而來,經過歷代醫家的不斷探索和改進,發展成獨具特色的中醫適宜技術。目前,刮痧療法有傳統刮痧、循經刮痧、全息刮痧、銅砭刮痧等。每種刮痧療法都具有各自的理論特點和臨床應用優勢。現將刮痧療法的臨床研究情況綜述如下。
1 研究現狀
1.1 傳統刮痧古人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發現,身體的某些部位被石頭或木頭摩擦或者按壓后,疼痛等不適癥狀可以減輕或消失。久而久之,人們便主動運用一些工具(砭石、飯匕、湯匙、碗口、銅錢、香油線等)刮拭身體皮膚,從而緩解疾病帶來的不適癥狀。這種方法經過歷代醫家在臨床實踐中反復驗證總結,逐漸發展成為刮痧療法。早期的刮痧療法被稱為傳統刮痧,由于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僅以實踐經驗為指導,故也稱為經驗刮痧。清代醫家郭志邃所著的《痧脹玉衡》對刮痧療法的適應證、禁忌證、注意事項等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并總結了大量的痧證治療經驗。由于傳統刮痧具有獨特的療效,在民間廣為流傳,一直沿用至今。肖梓濰等[1]根據“刮痧先刮頭、刮頭要致密”的原則,采用依次刮拭四神廷、顳三片、維風雙帶和項叢的頭部特種刮痧療法治療失眠患者,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張媛[2]則將腹型肥胖劃分為胃型肥胖、腸型肥胖和腰型肥胖進行分經刮痧,疏通局部經絡治其標,并用手指點穴調節臟腑功能治其本,雙管齊下,標本兼治,從而迅速有效降低腹型肥胖患者的腰圍和體質量。丁金磊等[3]提出的“特色整經刮痧技術” 是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的有效方法。該技術先通過手掌指關節或肘部在病灶反應點或區域進行點壓、彈撥,再用特制刮痧板配合純天然特質精油進行刮拭、摩擦,使局部皮膚“出痧”,從而達到疏經通絡、活血止痛等作用。
傳統刮痧以臨床經驗為指導,無需辨證,就近選經選穴,采用特殊的手法和(或)刮痧工具,治療相關的疾病,具有確切的療效。因其直觀簡便、易學好用,對臨床推廣應用非常有利。然而,傳統刮痧由于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難以形成獨立的學科體系,不利于深入研究和發展。
1.2 循經刮痧循經刮痧以藏象學說為理論基礎,以經絡學說為理論指導,以皮部學說為落腳點,通過刺激經絡循行部位和相關的穴位,使其出痧,以透邪于外,并通過經絡將刮痧的治療作用傳達于與之對應臟腑器官,恢復臟腑生理功能,從而防治疾病[4]。循經刮痧由楊金生教授首先提出,他強調了中醫臟腑經絡腧穴理論對刮痧療法的指導作用[5],并通過多中心臨床隨機對照試驗證明了循經刮痧理論的正確性,對循經刮痧的治療病種、操作方法、操作工具、操作步驟、適應證、禁忌證等進行了規范化研究。
近年來,諸多學者針對循經刮痧開展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王秋琴等[6]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90例非急癥期腰椎間盤突出癥(LDH)患者隨機分為3組。結果顯示,循經加穴位刮痧組下腰痛評估表(JOA)評分、視覺模擬疼痛(VAS)評分以及血清白細胞介素1-beta(IL-1β)、血清白細胞介素10(IL-10)含量的改善情況均優于循經刮痧組和穴位刮痧組;而循經刮痧組和穴位刮痧組相關指標變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該研究表明,單純使用穴位刮痧可以起到和循經刮痧相同的療效,而經穴結合刮痧比單純循經或穴位刮痧效果好,循經刮痧和穴位刮痧具有疊加和協同作用。陳華等[7]對不同證型的變應性鼻炎患者進行刮痧治療,結果發現刮痧療法對肺氣虛寒型患者的近期和遠期療效均優于脾氣虛弱型患者和腎陽虧虛型患者。曾維軻等[8]則對同為肝陽上亢證型患者采用不同的刮痧手法進行干預,其中,對照組使用平補平瀉手法;觀察組以補法刮腎經、瀉法刮肝經,結果顯示觀察組療效優于對照組。上述研究表明,循經刮痧對相同疾病的不同證型療效有差異,相同證型選用不同的補瀉手法療效也有差異。因此,循經刮痧需以辨證為基礎,循經選穴,并根據臟腑虛實情況選用合適的補瀉手法。另外,姚芳等[9]采用相同的刮痧方法在不同的時間對氣滯血瘀型LDH癥患者進行刮拭。其中,對照組刮痧時間為門診任意時段;觀察組則根據子午流注理論,將刮痧時間限定在申時(15∶00-17∶00)。經過6次干預,觀察組療效顯著優于對照組。劉彬等[10]的研究也取得了類似的結果。由此可見,根據子午流注理論,選擇某經絡對應的臟腑氣血功能最為旺盛之時實施循經刮痧,可最大限度地發揮經絡、腧穴的功能,達到防治疾病的最佳效果[11]。
循經刮痧的提出,使刮痧療法有了中醫臟腑經絡腧穴理論的支撐,使刮痧療法發展為循經選穴、內證外治的辨證刮痧,進一步提高了臨床療效,拓寬了適應證范圍,對刮痧理論體系的構建和學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3 全息刮痧生物全息理論認為機體的任何相對獨立部分的每一位區都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特定整體部位的變化,都是整體的縮影[12]。張秀勤教授[13]將生物全息理論用于指導刮痧療法的選區配穴,創新提出了全息刮痧法。根據所在部位的不同,全息穴位區可以分為耳部全息區、頭面部全息區、四肢全息區等。
耳部血管神經豐富,與大腦皮質聯系緊密,并且與軀體內臟通過神經系統存在著密切的對應關系,是人體全息性最強的器官[14]。劉鳳選等[15]將耳部全息刮痧操作方法分為操作前評估、耳部基礎刮痧、辨證選穴重點刮痧、耳部按摩4個步驟,體現了辨證施術的治療思路,在失眠、便秘、肩周炎的治療中取得了較好的療效。頭部全息刮痧在改善睡眠質量方面療效顯著,并且具有不強求出痧、刮痧板不直接接觸皮膚、對場地無特殊要求、可由家屬或患者本人進行操作等優點,增加了患者舒適感、體驗感和依從性,可操作性強,具有極大的社區推廣普及潛能[16]。
朱平等[17]研究表明,對脾胃相應的四肢全息區進行刮痧治療,可以激發脾胃的各項生理功能和自調功能,從而降低胃癌術后腸內營養不耐受癥狀發生,使患者早日達到腸內營養目標量,促進術后康復。值得注意的是,此研究中每次治療都選取不同部位的全息穴區進行刮拭,避免了由于刮痧部位“痧”未消退而導致的治療中斷,保證了刮痧的連續性,縮短了治療周期,有利于快速康復。
由此可見,全息刮痧所選刮拭部位相對集中,與病變部位對應性強,面積較小,能減少刮痧時間,提高臨床療效。同時,全息刮痧取穴部位多,選擇范圍廣,可交替選取各局部器官的同名全息穴區,使治療不間斷,還能提高機體對刮痧刺激的敏感性。并且,全息穴區多位于手足頭部等部位,對治療環境、治療時間的要求很少,操作簡便易行。因此,全息刮痧作為一種新型的刮痧療法,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1.4 銅砭刮痧銅砭刮痧是李道政教授在砭石療法的基礎上總結提煉出的新型刮痧療法。銅砭刮痧以八大核心理論為指導,具有鮮明的臨床特點和優勢[18]。
首先,銅砭刮痧選取由黃銅特制的“虎符銅砭”作為刮痧工具。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黃銅具有引痧的作用,使皮膚在刮拭的過程中更容易出痧,有利于痧毒的排出;第二,黃銅本身具有消毒殺菌的功效;第三,黃銅的熱傳導性強,具有導熱速度快、散熱速度慢的特點,可使刮拭部位保持一定的溫度,有利于加快氣血通行,疏通經脈瘀滯[19,20]。
其次,銅砭刮痧以“通”為核心,以通為補、以通為瀉、以通為治。通過反復的刮拭,刺激皮膚經絡穴位,促使出痧,以祛除邪氣,使氣血津液流轉通達,又通過自身溶痧,推陳致新,調動自愈力,從而達到瀉實補虛、調和陰陽的目的[21]。因此,銅砭刮痧既可用于實證,也可用于虛證,還可用于虛實夾雜證,并且無明顯不良反應,安全性較高[22]。
另外,“四井排毒”也是銅砭刮痧獨有的理論和方法。王鱈等[23]認為四肢末端為十二經絡井穴所在之處,為體內外聯系的通道,具有交通陰陽氣血、祛邪于外的作用。對于化療藥物奧沙利鉑所致周圍神經病變,可以通過首先刮拭督脈、膀胱經,然后刮拭四肢末端部位的“四井排毒”法,使體內蓄積的邪毒以“黑痧”的形式排出體外,達到較好的治療效果。銅砭刮痧的“四井排毒”法不僅在刮拭的過程中通過“黑痧”散邪排毒,在退痧的過程中也會激發機體的免疫功能,對刮拭部位的腧穴產生持續的刺激作用[24]。
最后,銅砭刮痧充分借鑒中醫的整體觀、肝膽論、谿谷論等觀點,改進了刮痧操作范圍和操作手法。劉宇等[25]治療痰飲證的研究充分體現了銅砭刮痧的上述特點。①選擇的刮拭范圍廣泛,包括上肢經絡穴位、背部經絡穴位、雙脅肝膽經、膝下經穴等。②刮痧操作時間長(綜合調治2~3 h,局部調治0.5~1 h)。③手法柔和深透(“徐而和”),以刮透為標準,尤其重視骨縫、肉縫中的充分刮透(谿谷論)。
總之,銅砭刮痧在選擇性吸收中西醫理論的基礎上創新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刮痧理論體系,在一些疑難雜癥的非藥物療法上實現了突破,在刮痧領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2 現狀與展望
研究設計不合理,優勢難以體現。近年來,針對刮痧療法的臨床研究多采用加載設計方法,即在其他治療的基礎上加用刮痧療法,或者刮痧療法與其他療法聯合使用。由于設計的變量較多,缺少對非處理因素的考量,導致研究存在混雜偏倚,并不能排除非處理因素對結果的影響,因而難以體現刮痧療法的獨特優勢。建議加強單用刮痧療法的效果評價研究,并與主流治療方法進行對照,找出刮痧療法在某些病證(如頸椎病、肩周炎、腰背痛、失眠等)中的獨特優勢,篩選出刮痧療法的優勢病種,進一步形成專病治療規范。
操作標準不統一,療效具有差異性。刮痧療法是一種中醫適宜技術,其操作方法至關重要,如果操作方法不規范,會直接影響臨床療效,也可能存在安全隱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發布的技術操作規范標準中,對刮痧的術語、定義、手法、操作步驟、注意事項等進行了規范。然而,目前仍然沒有針對具體疾病的刮痧操作規范或指南。研究表明,刮痧所選的經絡、穴位、刮痧工具、介質、操作手法等無統一標準,可能是導致刮痧療法對相同疾病產生不同療效的原因[26]。可見,刮痧療法的操作標準問題亟待解決。今后,研究者應對刮痧療法的經絡、穴位選擇,刮痧工具、刮痧介質、刮痧手法等進行標準化研究。另外,已有研究發現電動砭術與人工砭石刮痧療法具有相同的療效,特制的智能刮痧板可以很好地控制刮拭的速度和力度[27]。因此,智能刮痧儀器的研發也是促進刮痧操作規范化、標準化的研究方向之一。
理論與臨床脫節,缺乏深入研究。盡管刮痧療法的應用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刮痧理論的建立和發展卻明顯滯后。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或借鑒各種學說作為刮痧療法的理論基礎,構建了刮痧理論體系,并進行了大量的臨床試驗,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然而,目前針對刮痧療法的臨床試驗大部分為探索性研究,研究結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刮痧療法的有效性,并不能充分解釋刮痧理論的正確性[28]。理論與臨床脫節,二者不能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必然導致低水平試驗重復,深入研究難以開展。今后的臨床研究中,應當針對性選取研究切入點,加強對刮痧理論的驗證性研究。如循經刮痧對歸屬于同一經絡的不同病證是否具有相同的療效?對于相同的病證采用不同部位的全息穴刮痧是否具有相同的效果?是否具有協同作用?銅砭刮痧的“四井排毒”法是否會影響刮痧療效?
研究范圍局限,不利于大面積推廣。研究顯示,刮痧療法的研究機構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接受治療的患者也有一定的就醫選擇傾向性[29]。因此,刮痧療法的應用和研究范圍比較局限。這無疑會增加研究者和患者的主觀傾向,容易導致選擇偏倚,最終的研究結果難以得到廣泛認可。建議各研究機構加強交叉合作,開展跨地域、多中心、大樣本的隨機對照試驗,獲取高質量的循證醫學證據,促進刮痧療法的大面積推廣應用。
3 小結
綜上所述,近年來刮痧療法的臨床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主要體現在通過大量的臨床研究驗證了刮痧療法的有效性,并初步建立了刮痧的理論體系。傳統刮痧逐漸發展成為理、法、術一體的循經刮痧、全息刮痧、銅砭刮痧。然而,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刮痧療法的臨床研究還存在明顯的薄弱環節,還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筆者對近年來中國刮痧療法的臨床研究進展和現狀進行了系統闡述,并針對相關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旨在為刮痧療法的臨床應用和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