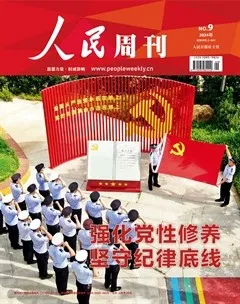做好綠色金融大文章面臨新挑戰
楊濤
當前,綠色金融被納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的五篇大文章中,也已成為金融高質量發展以及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著力點。在國家“雙碳”等戰略目標引領下,綠色金融經歷了多年快速發展。同時要看到,綠色金融的發展仍然存在“大而不強”等矛盾,需要重新審視一些基礎性、原則性問題。
綠色金融亟須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的“數量性指標”已經在全球領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30.08萬億元,同比增長36.5%;Wind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共發行綠色債券802只,共計11180.5億元,已連續兩年發行規模超萬億元。但要看到,在綠色金融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存在質量、結構、效率不足的問題,綠色金融“有效供給”仍需改善,“運動式”“一刀切”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二)要真正實現全面的提質增效,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還需有效融合。傳統綠色金融大多支持標準的綠色、低碳經濟活動,而轉型金融則服務于特定“非綠行業”,以引導其合理“轉綠”“降碳”或退出市場。人民銀行也在按照“急用先行”原則,從煤電、鋼鐵、建筑建材、農業等重點領域入手,優先支持技術先進、碳減排效應顯著的領域,通過金融要素引導其轉型變革。同時,如何有效地甄別轉型金融支持對象與金融產品標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三)在金融強國建設的戰略目標下,綠色金融不能“單兵突進”,而需處理好與其他四篇大文章的關系。這是新形勢下推動綠色金融增量創新的重要著眼點。例如,綠色金融與科技金融的融合重點可涵蓋多個層面,包括面向綠色、低碳相關的科技企業與科技創新,更好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支持和引導科技企業在創新活動中進一步保障綠色與可持續原則等。綠色金融與普惠金融的結合點,則可考慮在為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家庭提供普惠金融服務時,加入引導其趨于綠色低碳的要素,也可針對中小微綠色低碳企業,提供綠色與普惠疊加型金融服務。綠色金融與養老金融也有許多共識點,從保險業角度看,養老與低碳是行業最關注的焦點問題。在養老保險設計中可以充分體現綠色產品與綠色運營特征,養老財富的管理也離不開綠色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投資與產品。綠色金融與數字金融更是密不可分,數字金融手段有助于解決綠色金融的成本效率難題,而數字金融發展也需考慮綠色底線,因為新技術應用很可能帶來高碳、高能耗的結果。
綠色金融需重視需求側關鍵點與有效需求培育
金融支持綠色、低碳與可持續發展不是目的,而是金融功能落地的中間環節。重要的是要從最終需求側入手,基于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分析、落實。
(一)宏觀層面。金融支持綠色發展需厘清最終目標的優先次序。通常情況下,國家戰略與政策實施目標包括增長、就業、結構調整、可持續發展等,當前則需在實現“雙碳”目標過程中,充分考慮穩增長、保增長。同時,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或許人類社會會迎來更高能耗的時代。因此,綠色發展并不意味著限制能耗,而是追求在更高能效比的基礎上,優化資源與能耗的投入產出,平衡成本與收益。
(二)中觀層面。應根據經濟部門與產業結構的差異性,系統梳理支付結算、資金配置、風險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金融功能在綠色金融領域的需求配置,以及相應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子行業中綠色金融的實際價值定位。
(三)微觀層面。需深入發掘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居民部門的綠色金融需求特點,更加有針對性地創新和優化產品與服務供給,尤其是在綠色信貸與綠色債券之外,努力彌補其他金融產品類型的缺失。
綠色金融健康發展離不開環節要素的保障
(一)數據要素保障。例如,碳賬戶是綠色金融的重要數據基礎設施之一。通過碳賬戶對各類經濟主體的碳行為進行智能監測、動態核算和科學評價,從而為綠色治理與金融服務提供數據參考。再如,綠色金融發展中存在大量信息不對稱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會使我們面臨“漂綠”“假綠”挑戰。對此,通過推動綠色數據信息的標準化建設與互聯互通,可以使得綠色金融服務主體更好地識別與判斷項目的風險收益特征。事實上,隨著數據要素到數據資產的創新探索成為當前熱點,在綠色金融領域推動數據資產化,也有助于為綠色金融創新提供重要的“數據增信”。
(二)改善風險識別與監管,優化治理機制。綠色金融的有效探索,還需要更精準地對金融產品的綠色與環境效益進行計量、評估與評價。這要求推動環境信息披露的強制性和規范性,強化可持續信息披露要求。同時,考慮到許多中小金融機構缺乏綠色項目準入分析能力、專業化風控體系,也難以基于中長期數據分析來判斷綠色活動的風險特征,所以還需要構建專業性的中介評估體系與評估模式,確保綠色金融項目真正符合特定標準和要求。
(三)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在支付結算基礎設施建設中,也應該充分考慮綠色金融產品發行與交易的特點,不斷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充分保障綠色金融產品的順暢交易、價格發現、風險控制、統計監測與跨境協調等。
(四)構建新形勢下的綠色金融文化。積極落實中國特色金融文化建設的要求,發揚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綠色“精髓”,努力構建新形勢下的綠色金融文化,把軟規范逐漸轉換為標準化的硬規則,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市場主體行為與認知。
需在開放條件下認識綠色金融發展前景
(一)綠色金融發展需堅持“走出去”與“引進來”并重,在國際視角下探索綠色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近年來,我國在二十國集團(G20)框架、“一帶一路”倡議等平臺機制下不斷推動綠色金融交流合作,國家之間的聯動日益密切。伴隨著我國綠色產品出口持續增長、綠色跨境貿易場景更加豐富,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中資企業“走出去”的重要領域,與之相對應,綠色金融服務也獲得了“走出去”的新機遇。同時,國內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市場處于快速增長過程中,更好地利用外資、外資金融機構的參與,也能為綠色金融發展帶來新助力。
(二)推動綠色金融的制度型開放。所謂制度型開放,是指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的開放,在綠色金融領域亟須探索制度層面的“國際共識語言”。在政府層面,包括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央行和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IPSF)、《“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GIP)等都發揮著相關作用,國內綠色金融相關產學研用組織也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
(三)需審慎直面近年來國際上的反ESG浪潮。在反ESG浪潮影響下,美國的可持續投資資產占總管理資產的比例在2022年快速下跌到13%,低于2014年18%的水平;歐洲2022年可持續基金的資金流入明顯減少,2023年則出現了資金外流。近日,美國四大銀行摩根大通、花旗銀行、富國銀行、美國銀行退出“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美國10個共和黨執政州集體向巡回上訴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氣候披露新規違反憲法。諸如此類事件,也警醒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綠色金融國際共識自身的變化,同時避免在綠色金融發展中出現過猶不及,尤其要避免綠色與ESG評價的長期主義“短期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來源: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