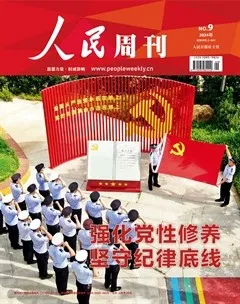東方文化派的當代價值與問題所在
趙東旭
所謂“東方文化派”,本非自覺的一個文人派別,而是對手規劃的統稱。1923年11月,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一文,將梁漱溟、梁啟超、章士釗、張君勱等人劃為東方文化派,并稱東方文化派是“代表農業手工業的封建思想(或稱宗法思想)”。
事實上,東方文化派遠不止這幾個人,而其形成也有特定歷史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傷亡幾千萬、波及數億人的戰爭給歐洲造成了巨大損失,動搖了西方文明的權威,給汲汲于模仿西方文明的中國人敲響了一記警鐘。同時,辛亥革命后,中國雖然成立了名義上的共和制,但社會沒有發生實質變動,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在1916年袁世凱死后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深淵,這無法不讓人反思:西方文明是否適合中國?于是便出現了一批學者,他們質疑西方文明的權威性,主張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發掘、研究、宣揚傳統文化之優長,為中國與世界尋找未來的出路——這便是東方文化派。
毛澤東曾經下論斷: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他同時補充道:“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即,單一個學說并不能改變民族的面貌。一個民族能夠自立、自強,其根本動力來自內部。從這個角度來說,東方文化派之所為也是中華民族爭取精神主動的一次努力。
杜亞泉認為,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乃性質之差異,而非程度之差”。西洋文明是動的文明,崇尚競爭,強調對抗;中國文明則是靜的文明,講究調和,順其自然。西洋是充血癥,中國是貧血癥。盲目照搬西洋文明,是以本國之“祖產”換西洋之“政券”,難免精神破產。其救濟之道,首先要系統調理中國固有文明,然后以之為依據,吸收融合西洋文明,進而救濟全世界。
梁啟超從1918年12月至1920年3月于歐洲進行了一年多的考察,親眼看到了歐洲社會經濟蕭條、生活困難、政治動蕩的嚴峻現實。在《歐游心影錄》里,他認為西方思想界正處于“混沌過渡時代”,需要輸入中國、印度文明,加以調和。于是梁啟超指出,對待本國文化要持一個尊重愛護的誠意,再以西方方法研究它,然后綜合中西文明,貢獻于全人類。
陳嘉異學術理論功底極深,他將中國原理總結為四條:其一,獨立的、創造的;其二,能調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其三,能調節民族精神與世界精神;其四,由國家主義而達世界主義。他提出中國人有發揚東方文化之大任,要用科學方法整理舊籍,理清東方文化的價值所在,然后擇善而從,繼而與西方文明相交換、融合,創造一種最高義的世界文化。
梁漱溟比上述學人更進一步,他否定了東西方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與西方走的原本不是一條路。即,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加上“理智運用現量的”印度文明,世界進化的規律乃是西洋、中國、印度依次復興。因此,梁漱溟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以上四人為東方文化派代表,他們均致力于喚醒中國文化自覺,以固有文明為本位,保存、研究、選擇、比較、吸收、融合、創造、推廣。他們對于中西文明的獨到見解至今仍值得借鑒。然而歷史的現實是,東方文化派的理論并沒有成為指導中國人走向勝利的思想,而是不斷遭到質疑與批判,最終在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面前黯然退場。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學者對于東方文化派的失敗已有總結,如,他們高估了西方文明的危機,對中國封建文化的危害卻估計不足;他們全然不顧中西方的時代性差異,只強調性質差異;他們提不出具體可行的路徑,只能陷于一廂情愿的空想;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在開歷史的倒車;等等。這些批判是全面且準確的,但如果拉長歷史視角來看的話,筆者認為東方文化派失敗的深層歷史原因在于傳統文化的去實體化。
所謂“去實體化”,指的是傳統文化喪失了在政治體制(上層)與社會生活(基層)上的實踐、變革的能力。
首先,在政治安排上,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權利、義務、選舉、公民、主權、邊界等為基本理論預設的現代國家體制已經建立起來,并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通用體制。本土傳統并不能提出超越這一體制的新方案。陳嘉異大談中國是“天下的國家”,試問:天下思想如何能夠制止西方國家的利益沖突?它連當時國內軍閥的利益沖突都阻止不了。
其次,在社會生活上,西方傳來的聲光化電構成了民眾的基本物質生活,“個人”被確立為經濟、社會與法的基本要素。瞿秋白揶揄當時鼓吹“東方精神文明”的論者曰:“時時刻刻在那里促進他們所反對的物質文明之發展:如買火車票,點電燈,用自來水,吃酒席,穿洋布等。”梁漱溟亦從生活現狀感受到了東方文明的危機:“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
由是可見,東方文化派的歷史性失敗不在他們所描繪的“中體”不美——西方哲人構想的理想國也從未實現過——而在于提不出切實有效的“中用”來。學者批判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把矛頭對準了“中體”(三綱五常),然而即便將“三綱五常”替換為“仁義禮智信”,甚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缺乏“中用”的內在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換言之,理論再精美、立意再高超,也未必能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生存、溫飽、發展的問題。而對方法、方案、工具的忽視,乃是“獨尊儒術”以來的一大弊病,傳統思維的重體輕用、重道輕器之影響不可謂不深遠。如梁啟超所批判的,國人信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過于輕視“器”的用處,自鳴得意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會產生出一些“西裝式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和“大餐式的超凡入圣大本領”,這種心理遺傳下來,動輒談“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導致了“最愛說空話的人,最受社會歡迎”。
況且,中國民間的實際行為模式與信條,未見得是東方文化派們標榜的各種“精神”,民眾之所想所愿所為,亦未必符合精英們設計的宏大愿景。魯迅曾言“中國根底全在道教”,這是儒家士人的視野盲區。試圖作出一定改變的是梁漱溟,梁漱溟不滿足于玄談,而是試圖讓文化落地,成為中國人的基層日常生活,鄉村建設便是他的實踐。然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并不成功,已經有學者指出,失敗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重視知識分子而輕視農民。梁漱溟的失敗,固然有個人局限性、客觀環境不利等原因,但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原本就缺少平民視野,不僅梁漱溟如此,東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或多或少有這點毛病。
我們不必苛責百年前的人,他們是嘗試者,彼時之中國也不具備實踐其理論的客觀條件。但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今人,要弘揚傳統文化,我們有必要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今天的全球處在危機與動蕩之中,西方式現代化已經難以為繼,中國新一輪文明論應運而生。它能否汲取傳統中的有益成分并活用之,解決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推動人類進步,決定了這場運動能否發展為東方的“文藝復興”。無論如何,中國在弘揚傳統文化的時候必須注意修正輕視“器”的問題與精英主義問題。輕視“器”就是不扎實,基礎不扎實談何創新?要獎勵基礎研究,行長期主義,少些“超凡入圣”的玄談。精英主義就是脫離群眾,要走群眾路線,加深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如是,優秀傳統文化將在新時代迎來新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未來可期。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