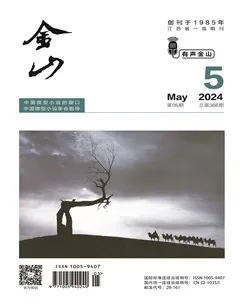突破模式:汪曾祺小小說的“隨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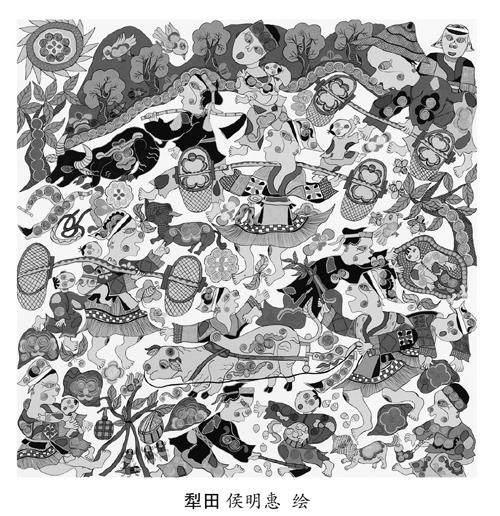
謝志強(qiáng),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出版小說和文學(xué)評(píng)論集35部,發(fā)表小小說近3000篇,多部作品被譯介至國(guó)外,部分作品入選大、中、小學(xué)語文教材和考題。曾獲中國(guó)微型小說年度獎(jiǎng)、小小說金麻雀獎(jiǎng)、中國(guó)小說學(xué)會(huì)年度排行榜(小小說)、《小說選刊》雙年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兩次獲浙江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獎(jiǎng)。
談?wù)勍粼鞯男⌒≌f《打魚的》。
我想起了汪曾祺對(duì)小小說的看法。一是,1985年,汪曾祺說:“我要對(duì)‘小說這個(gè)概念進(jìn)行一次沖決。”此處所指的概念,就是定義,也是模式。汪曾祺就是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有破有立,顛覆了模式的同時(shí),也影響了未來小說的走向。他運(yùn)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筆記小說的方法,從“怎么寫”顛覆了過去的“寫什么”(宏大敘事),從而開啟了中國(guó)當(dāng)代小說的一扇別樣之門。
二是,汪曾祺說現(xiàn)在的小說太像小說,他要寫不像小說的小說。他在一篇談小說結(jié)構(gòu)的文章里,說“結(jié)構(gòu)的原則是:隨便”。那“隨便”是“苦心經(jīng)營(yíng)的隨便”,他明確表示:“我不喜歡結(jié)構(gòu)痕跡太重的小說。”比如莫泊桑、歐·亨利,他們“耍了一輩子的結(jié)構(gòu),實(shí)際上是被結(jié)構(gòu)耍了”,他倒是喜歡“好作家完全不考慮結(jié)構(gòu)”的契訶夫,那是對(duì)小說的解放。當(dāng)代短篇小說的主流是契訶夫式的小說,其標(biāo)志是“沒事”,或說“沒戲”。
汪曾祺的大多數(shù)小說是小小說。起初,他界定為散文化小說,后稱筆記體小說。我將其稱之為新筆記小說。為讀者稱道的甚多,就如同他在《陳小手》中所說:“陳小手活人多矣。”汪曾祺的新筆記小說里,他不也“活人多矣”?
多年來,評(píng)論界對(duì)小小說多有定義,還引用美國(guó)的三條小小說概念。記得其中有一條是歐·亨利式的意外結(jié)局。
文無定法,小小說按定義(概念)寫,會(huì)怎么樣?還有,習(xí)慣了小小說“有事”(故事),但是“沒事”怎么寫?
我讀當(dāng)代國(guó)內(nèi)外小說,甚至將長(zhǎng)篇小說的一節(jié)、一段拎出來,當(dāng)小小說。我意識(shí)到,小小說首先是小說,然后,才是小小說,它包涵了小說的基本關(guān)系元素,當(dāng)然,我也發(fā)現(xiàn)了小小說唯有的獨(dú)特之處:體量小,螺螄殼里做道場(chǎng)。寫人物是要?jiǎng)?wù),但寫的方法獨(dú)到,提取人物性格中的一點(diǎn),放大,夸張,不及其余,所謂“扁平人物”能更為“鮮活”,還有細(xì)節(jié)跟人物配套。小小說運(yùn)用細(xì)節(jié)的分法,跟長(zhǎng)、中、短篇小說有明顯的不同。一個(gè)有含量的細(xì)節(jié),可照亮全篇、撥亮人物。汪曾祺引用老師沈從文的話:貼著人物寫。小小說細(xì)節(jié)的運(yùn)用,就是貼著人物運(yùn)行中的細(xì)節(jié)寫。小小說一旦被定義,有概念,就“僵化”了,模式化了。因?yàn)椋⌒≌f有多種可能性,作家要探尋這種可能性,要保持一種包容和開放的狀態(tài)。
言歸正傳,來品讀汪曾祺的新筆記小說《打魚的》。此篇是他小小說極端“隨便”的一例。有文友說,《打魚的》不像小小說。我說,汪曾祺就是寫出了不像小小說的小小說,那是對(duì)我們習(xí)慣了定義小小說的一種顛覆和冒犯。
汪曾祺的小小說,也有模式,先寫一般的氣勢(shì),后寫具體的“個(gè)例”。他竟能那么瀟灑地放開,然后,像打魚的那樣收網(wǎng)。模式是雙刃劍,它使一個(gè)作家有了辨識(shí)度,也形成了一個(gè)作家的套路。可是,我喜歡汪曾祺的套路。究其原因,他那氣氛鋪敘,有趣有味,拔出蘿卜帶出泥,有生活氣息,有人間煙火,有人情世故。汪曾祺是經(jīng)驗(yàn)性的作家,他寫的都是經(jīng)歷過的熟悉生活。
《打魚的》,三分之二篇幅,寫一個(gè)行當(dāng)——打魚的不同方法,帶著鮮活的水氣。而且,他寫得不枯燥,不刻板,其中有規(guī)矩,有樂趣。提網(wǎng),收網(wǎng),放鷹,收鷹,那也是汪曾祺寫作的隱喻:放和收的自如自在。放則放得開,收還收得住。
起頭兩句:“女人很少打魚。”然后引出“打魚的有幾種”,兩個(gè)短句各為一個(gè)自然段,與列舉的“幾種”長(zhǎng)段落構(gòu)成短與長(zhǎng)的交錯(cuò),這樣,生成了節(jié)奏。當(dāng)代小小說要有節(jié)奏感,換句話說,是當(dāng)代小說的脈搏。汪曾祺竟然在氣氛的鋪敘中寫出節(jié)奏(不也是人物的脈搏嗎?),那是不顯痕跡的苦心經(jīng)營(yíng)的“隨便”。
尤其是他采取論文式的列舉:一種一種一種,故意的模式卻有靈動(dòng)的節(jié)奏,而且貌似刻板的表達(dá)卻是自如的呈現(xiàn)。其中有詳有略。“一種是板罾的。”“一種是撒網(wǎng)的。”又是短句各獨(dú)立為自然段,卻不細(xì)說,不展開,這種省略,與開頭的兩個(gè)短句形成了呼應(yīng),起了調(diào)節(jié)敘述“呼吸”的作用,錯(cuò)落有致,詳略得當(dāng)。
起首一句“女人很少打魚”,實(shí)為后三分之一的具體寫“一男一女”提前打了招呼——汪曾祺不經(jīng)意地來了個(gè)懸念。在都是男人打魚的常規(guī)中,突出寫“女人”打魚。先寫一般,再寫?yīng)毨!蛾愋∈帧穭t是性別相反,先寫一般都是女的接生,再寫陳小手這個(gè)男的接生。
一男一女,是夫妻,打了一天的魚,卻聽不到說一句話。這一句有味,一是存在不露面的關(guān)注者,也就是汪曾祺:作家關(guān)注是一種憐憫的情懷;二是生活使這對(duì)夫妻疲憊或?qū)W⒉⒛酰磺斜M在不言中。但能聽見舉網(wǎng)和攪水的聲音,還追加三個(gè)字“也很輕”。生活之重與聲音之輕逸。
作家要明確自己的站位。關(guān)注什么人是站位的標(biāo)志。汪曾祺的關(guān)注持續(xù)著,“有幾天不看見那對(duì)夫妻”,寫人卻寫衣,衣的顏色和款式,可見關(guān)注的細(xì)致。本是妻子趕魚,卻換成了一個(gè)小姑娘,穿著母親原來的皮罩衣,點(diǎn)出了衣與身的不配套。但她趕魚的動(dòng)作像母親,一脈相承。當(dāng)然母親的境況,讀者自會(huì)想象。
汪曾祺寫了一家“打魚的”命運(yùn)。小小說也能夠?qū)懗鋈宋锏拿\(yùn)。尤其寫了女性的命運(yùn):母與女的接替。
汪曾祺的語言簡(jiǎn)約,說出的僅是“冰山一角”。結(jié)尾一句:“秋天的水已經(jīng)很涼,父親的話越來越少了。”做與說、人與物、重與輕、冷與暖的關(guān)系中,呈現(xiàn)出了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境遇。
“女人很少打魚”,女人成了“打魚的”,那是迫不得已。汪曾祺寫出了打魚的女人的命運(yùn),與列舉的種種打魚的男人形成了對(duì)照,突顯出“這一個(gè)”。猶如一盞燈,照亮了所有的打魚的,有光亮,有溫暖。汪曾祺說過,他寫作,是給人間送溫暖。
汪曾祺見多識(shí)廣,寫過許多行當(dāng)。造屋的(《金大力》)、求雨的(《求雨》)、救生的(《陳泥鰍》)、修車的(《戴木匠》)、收字紙的(《收字紙的老人》)、撞鐘的(《幽冥鐘》)、打鐵的(《邱麻子》)、做棺材的(《少年棺材匠》)、做豆腐的(《王居》)、遛鳥的(《瞎鳥》)、護(hù)秋的(《護(hù)秋》)、寫字的(《子孫萬代》)、畫像的(《畫像》)、吃戲飯的(《三列馬》),等等。延伸閱讀,欣賞汪曾祺怎么寫?都是先放后收,收住,還留“口”,不封死,敞開著,那種“隨便”,可謂收放自如了。
關(guān)于小說如何表達(dá),集編劇和演員于一身的捷克作家茲旦內(nèi)克·斯維拉克,72歲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其身為電影導(dǎo)演的兒子,否定性地指出,父親的小說“尤其缺乏電影制作不容忽視的戲劇拱門”。但是,斯維拉克仍堅(jiān)持碎片化的表達(dá),追憶童年萬花筒般的片段,那是系列小小說的寫法。由此區(qū)別了父子倆關(guān)于小說和電影的差異。
汪曾祺從事過戲劇創(chuàng)作,而他的小小說卻相反——沒戲。當(dāng)今文學(xué)藝術(shù)各個(gè)門類越發(fā)細(xì)分,值得思考的是:小小說怎么做唯有小小說該做的事兒?汪曾祺和斯維拉克的小說,是一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