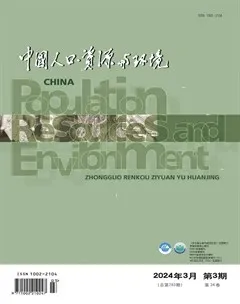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生態文明建設:企業環境績效的提升演變
陳林 王佳瑩 周立宏



摘要 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發揮國有經濟的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體制改革戰略,對強化企業環境績效產生了積極的政策效應。該研究通過構建產量競爭博弈模型,收集上市公司的環保投資數據,實證檢驗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環境績效的作用。研究發現:①整體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表現;②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發揮民營企業的創新與效率優勢,推動國有企業集約化發展與清潔生產技術革新,因此對自身環保意識較為薄弱的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改善作用較為明顯;③對于所處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較低的國有企業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環境規制的替代工具,對其環境績效的改善作用更為顯著。據此,該研究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提升國有企業環境績效表現,進而有助于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各政府部門在實際中應繼續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發揮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獨特優勢。但在推進過程中仍然要注意分類改革,切忌“一窩蜂”上馬。具體而言,對于已承擔環境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應保留其環境治理的主體地位;而對于尚未承擔環境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可注重盡快推動相關的國有企業改革。該研究不僅為理解國企改革的微觀環境績效提供新的視角和證據,也為進一步推動宏觀層面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經驗證據。
關鍵詞 國有企業改革;混合所有制;環境污染;環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
中圖分類號 F276. 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03-0166-11 DOI:10. 12062/cpre. 20230904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堅向縱深推進”是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之一。全方位地加強生態環境保護,離不開國有企業及其相關改革的配套。這是因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體,國有經濟在其中的主導地位必須貫徹如一。黨中央、國務院推行的與國有企業相關的體制改革,如何更好地嵌入“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使污染防治攻堅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主體推進,是當前學術界亟須解答的兼具理論與實踐意義的重大命題。
早在2015年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中發〔2015〕12號)便初步提出了國有經濟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中的重要角色——“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適時調整主要污染物指標種類,納入約束性指標”“黨政機關、國有企業要帶頭厲行勤儉節約”。可見,宏觀的、全國性的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企業這一微觀主體的行為變革,更離不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占據主導作用的國有企業的全方位配合。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要“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其中國有經濟的環境績效正是“做優”的重要表現維度。因此,提升環境績效,為生態文明建設做出貢獻,正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內在要求。不難看出,“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內的國企改革戰略與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是相輔相成的,甚至應該進行二者互融的“頂層設計”。
2016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原環境保護部進行了“頂層設計”的早期嘗試——聯合印發《關于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的意見》(發改環資〔2016〕2028號),提出“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環境治理”。由此可見,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可能是這一輪“頂層設計”的突破口。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一直承擔著就業、稅收等政策性任務,具有一定特性[1-4],地方政府因而較多注重國有企業經濟績效,相對忽略其環境治理問題。混合所有制作為新的國有組織形態,能夠發揮非國有資本的創新及管理優勢,有助于國有企業環境績效的改善。當然,對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絕不能“一窩蜂”上馬[5],而應“對癥下藥”,分類分層有序推進。但目前學術界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國有企業環境社會責任的理論解讀仍較鮮見,國有企業的分類改革也缺少生態文明建設層面的參考依據。為此,本研究主要通過構建產量競爭的博弈模型,并利用上市公司數據庫中的企業環保投資數據,運用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分析范式,探討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對不同國有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進而為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提供新的視角和證據。
1 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中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關于國有企業環境績效表現的爭鳴探索。部分學者研究認為,國有企業作為環境保護、污染治理的排頭兵,承擔了環境治理的主要責任,并且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表現比民營企業相對更好[6]。但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一方面,國有企業可能面對更寬松的監管,或繳納相對更少的排污費,進而帶來更嚴重的污染問題[7];另一方面,官員可能更關注國有企業的經濟活動,而忽略了其環保投入[8]。由此可見,國有企業是否承擔了主要的環境治理責任,對于這一議題的討論,現有研究結論仍然莫衷一是,需要更深入的理論探討。
二是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存在環境治理效應的爭鳴探索。本研究所關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主要是指在國有企業中混入非國有資本的程度。學界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與環境污染的理論研究雖起步較晚,但至今已取得較多成果。Ohori[9]最早將環境稅、關稅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引入混合寡頭模型中,研究發現在最優的環境稅及關稅下,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會促使環境得到改善。Bárcena?Ruiz等[10]以政府限制排放總量作為環境規制的替代變量,發現當邊際成本處于特定范圍時,國有企業混改后的環境污染問題將得到改善。Wang等[11]在模型中納入了企業減排行為,發現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提高降低了總產出,進而降低了企業的污染排放水平。也有學者對此持不同觀點。Beladi等[12]建立的模型同時考慮混合所有制改革與排污稅因素,發現在國有企業中混入非國有資本會通過降低排污稅率來提高總產出水平,進而不利于環境治理。Wang等[13]放松了產品無差異的假設,認為在國有企業中混入非國有資本會導致環境問題的惡化,且對環境的損害程度取決于商品的可替代程度。還有研究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是非線性的,具體效果取決于國有企業自身是否重視環境問題[14]。目前學界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討論仍存在較大爭議,并且缺乏基于中國微觀數據的實證檢驗。本研究嘗試將國有企業自身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以及所受到的外部環境規制約束納入理論框架,重點探討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對國有企業環境績效表現的影響,試圖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給予新的理論與經驗證據。
三是關于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理論依據的爭鳴探索。部分研究嘗試從產權性質或經營目標等維度對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的“類”進行界定。代表性研究中,董輔[15]將國有企業分為競爭性國有企業與非競爭性國有企業;高明華[16]將國有企業分為公益性國有企業、壟斷性國有企業以及競爭性國有企業;黃群慧等[17]提出將國有企業劃分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業性三類,并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因“類”制宜。也有研究通過實證檢驗不同類別國有企業的改制效果,為分類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從企業所屬的層級屬性而言,相比于地方國有企業,中央企業經濟活動更為復雜,政治負擔更重,并且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改制對這類企業的經濟績效影響較小[18];從地區市場化程度而言,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政府放權意愿越強,能夠減少國有企業過度投資行為,進而提升企業經濟效率[19];從所屬行業性質而言,相比于壟斷性行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對競爭性行業國有企業經濟績效的提升作用更為顯著[20]。總而言之,國有企業應根據不同功能定位進行分類改革。然而,大部分研究仍主要以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作為分類考察依據,忽視了在新時期經濟轉型發展的背景下,國有企業所承擔的環境治理責任。為此,本研究重點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不同國有企業環境績效表現的影響,為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提供新的視角。
2 理論分析
2. 1 模型構建
構建產量競爭的混合寡頭模型,重點考察在各地方政府環境規制強度不同,同時國有企業自身對環境污染問題重視程度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對國有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研究深入探討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對國有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進而為混合所有制改革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提供新的視角與證據。研究發現:①整體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提升有利于改善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表現;②相比于自身環保意識較強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對環保意識較為薄弱的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改善作用較為明顯;③相較于所處地區具有較強環境規制的國有企業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對環境規制強度較弱地區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的改善作用更為顯著。
基于以上結論,本研究總結得出如下政策啟示:①堅持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關鍵在于發揮制度優勢,而國有企業改革是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研究證實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能夠顧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方案,各政府部門在實際中應繼續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進而發揮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獨特優勢。②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緊密結合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特征,完善非國有資本參與內部決策的機制,進而為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國有企業的科學決策提供理論基礎;完善國有企業內部的現代企業制度,加快實現內部治理結構由三會一層到四會一層的轉變,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清晰界定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以及黨組織等的權力與責任,形成各部門之間的有效制衡,逐步建立能夠科學決策的治理體系;響應市場化經營體制機制,不斷激發國有企業清潔生產的活力與動力。③改善外部治理環境,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環境規制約束[34]。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建立并完善相應的制度體系,尤其要出臺針對性的法律法規,將因放松規制而導致的污染問題納入規章制度,并對相關負責人進行追責。政府部門要加強引導,監督本地國有企業在環境治理中的貢獻,真正起到強化國有企業外部環境規制約束的作用。④政府部門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時要注意依據企業類別和企業所在地的發展特點進行分類改革,因企制宜、因地制宜,避免“一窩蜂”地推進。對于已承擔環境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而言,仍然要保留其環境治理的主體地位;而對于尚未承擔環境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起到較好的環境治理效果,因此應注重對這部分國有企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參考文獻
[1] 陳林,唐楊柳. 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基于早
期國企產權改革大數據的實證研究[J]. 經濟學家,2014(11):
13-23.
[2] 劉小玄,李利英. 改制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J]. 中國工
業經濟,2005(3):5-12.
[3] 陳林,萬攀兵,許瑩盈. 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股權結構與創新行
為:基于自然實驗與斷點回歸的實證檢驗[J]. 管理世界,2019,
35(10):186-205.
[4] 李文貴,余明桂. 民營化企業的股權結構與企業創新[J]. 管理
世界,2015(4):112-125.
[5] 陳林. 自然壟斷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自然實驗與成本函數
的分析[J]. 經濟研究,2018,53(1):81-96.
[6] LIU T S,ZHANG Y F,LIANG D P. Can ownership structure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25:58-71.
[7] 龍碩,胡軍. 政企合謀視角下的環境污染:理論與實證研究[J].
財經研究,2014,40(10):131-144.
[8] 李月娥,李佩文,董海倫. 產權性質、環境規制與企業環保投資
[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6):36-49.
[9] OHORI S. Environmental tax,trade,and privatization[J]. Kyoto
economic review,2004,73(2):109-120.
[10] B?RCENA?RUIZ J C,GARZ?N M B. Mixed oligopol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J]. Spanish economic review,2006,8(2):139-
160.
[11] WANG L F S,WANG Y C,ZHAO L H. Privat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 mixed duopoly with pollution abatement[J]. Economics
bulletin,2009,29(4):3112-3119.
[12] BELADI H,CHAO C C. 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
[t J]. Economics letters,2006,93(3):343-347.
[13] WANG L F S,WANG J. 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 Economic systems,2009,33(4):389-396.
[14] PAL R,SAHA B. Pollution tax,partial privatization and environmen
[t 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15,40:19-35.
[15] 董輔. 從企業功能著眼 分類改革國有企業[J]. 改革,1995
(4):40-47.
[16] 高明華. 不同類型國企的改革趨向[J]. 人民論壇,2013
(S2):37.
[17] 黃群慧,余菁. 新時期的新思路:國有企業分類改革與治理
[J]. 中國工業經濟,2013(11):5-17.
[18] 魏明海,蔡貴龍,柳建華. 中國國有上市公司分類治理研究
[J].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7(4):175-192.
[19] 蔡貴龍,鄭國堅,馬新嘯,等. 國有企業的政府放權意愿與混合
所有制改革[J]. 經濟研究,2018,53(9):99-115.
[20]李禹橋,陳林. 國有企業分類改革與高管薪酬[J]. 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2(4):14-25.
[21] 楊春學,楊新銘. 所有制適度結構:理論分析、推斷與經驗事實
[J]. 中國社會科學,2020(4):46-65,205.
[22] SINGH N,VIVES X. Price and quantity competition in a differentiated
duopoly[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84,15(4):546.
[23] 邢斐,何歡浪. 貿易自由化、縱向關聯市場與戰略性環境政策:
環境稅對發展綠色貿易的意義[J]. 經濟研究,2011,46(5):
111-125.
[24] ULPH A.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governments
and producers act strategicall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0(3):265-281.
[25] 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70(3):473-483.
[26] 萬攀兵,楊冕,陳林. 環境技術標準何以影響中國制造業綠色
轉型:基于技術改造的視角[J]. 中國工業經濟,2021(9):
118-136.
[27] 陳林,萬攀兵. 城鎮化建設的鄉鎮發展和環境污染效應[J]. 中
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1,31(4):62-73.
[28] 周黎安. 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
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J]. 經濟研究,2004,
39(6):33-40.
[29] 張順明,余軍. 內部貨幣與我國最優關稅政策研究[J]. 經濟研
究,2009,44(2):18-31.
[30] 姜英兵,崔廣慧. 環保產業政策對企業環保投資的影響:基于
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改革,2019(2):87-101.
[31] 楊興全,尹興強. 國企混改如何影響公司現金持有[J]. 管理世
界,2018,34(11):93-107.
[32] 陳斌,吳超鵬. 我國股權分置改革市場反應的實證研究[J]. 上
海財經大學學報,2008,10(6):72-79.
[33] 葉琴,曾剛,戴劭勍,等. 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中國節能減排技
術創新的影響:基于285個地級市面板數據[J]. 中國人口·資
源與環境,2018,28(2):115-122.
[34] 高艷紅. 政府與再生資源企業二次污染防治行為的演化博弈
分析[J]. 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28-39.
(責任編輯:劉照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