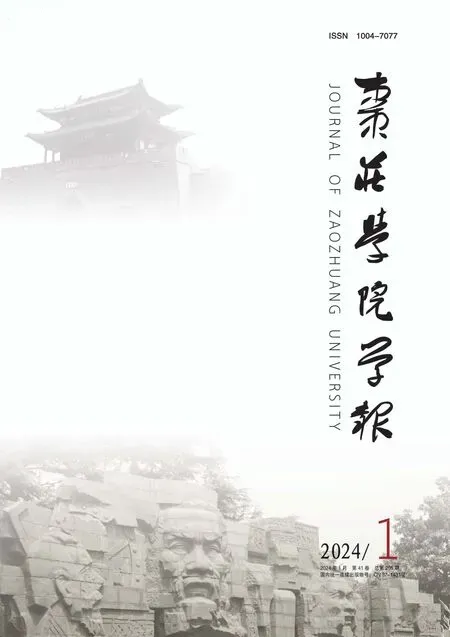周代薛國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
楊 晶 苗夢瑤
(1.棗莊市博物館,山東 棗莊 277102;2.山東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薛國為古老邦國,傳世文獻中對于薛國祖先、姓氏以及分封史有著較為系統的梳理和記載。《左傳·定公元年》記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1](P2131)《左傳·隱公十一年》亦在記述“滕薛爭長”[1](P1735)一事中指出,薛國為任姓之國。此外,《國語》《詩經》《戰國策》《史記》《漢書》《通志·氏族略》等傳世文獻對其也有著墨。通過諸多文獻可以看出,任姓薛國在夏商時期便已存在,至西周初年重新獲封。經過多年來的考古發掘,目前已知的與薛國相關的墓地遺址主要是薛國故城和前掌大遺址。
一、周代薛國遺存概況
周代薛國遺存主要是前掌大和薛國故城遺址,這兩處遺存在時代上有著前后相接的關系。
(一)薛國故城
位于滕州市官橋鎮與張汪鎮之間,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對此處進行了持續性調查、試掘、發掘,發現了戰國時城墻(外城)、城壕、城門,春秋時期和西周中晚期小城(內城),東周、漢代的冶鐵、制陶和居住遺址以及兩周時期至漢代的墓地。[2]
戰國時期的城墻(外城)保存較好,四面墻體完整。據實測,城墻總周長10610米,其中,東墻長2280米,南墻長3050米,西墻長2030米,北墻長3250米。墻外四面有城壕,城墻寬30米左右,城壕寬25~30米。每面城墻有城門3處,其中東中門應該是薛國故城內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城內還發現了7處居住遺址、3處手工業作坊遺址以及宮殿區等。故城東部還發現了3處墓地,編號為MD1—3。其中,MD1是戰國時期的積石槨墓,傳為孟嘗君田文墓。MD2已經探出大、中、小型墓葬20座,考古報告中公布了其中的9座,時代為春秋戰國時期。此處早前曾發現了一批春秋早期的“走馬薛仲赤”和“薛子仲安”青銅簠。MD3為漢代墓地。
在薛國故城東南部發現了一座春秋時期城址,小城的東、南墻很直,相交之處約95°;西、北墻向城外凸出,呈現不規則的長方形形狀。東西約650米,南北約600米,面積約40萬平方米。城外北部等地清理出上百座同時期的墓葬。另外,20世紀90年代在春秋城中部還清理出一座西周中晚期的城墻,城內面積僅數萬平方米,城內還清理出一批西周中期晚段、晚期小型墓葬。
根據考古報告,幾座墓葬在年代、等級身份上存在差異,下面將僅對春秋時期薛國高等級墓葬作一簡單的介紹:
M1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向為33°,有生土二層臺、殉人坑。墓主人側身屈肢,頭向北,面向東。葬具為一槨三棺,槨蓋板上殉一狗。殉人兩具,分別位于腰坑和內槨室北部,均無葬具。隨葬品集中發現于二層臺頭箱內、棺槨之間以及骨架附近,有銅、陶、玉、石和蚌器等1149件,大多數保存較好。銅器以銅容禮器為主,另有車馬器、兵器、雜器等,共計599件。銅容禮器包括鼎8件、簋6件、鬲6件、簠2件、壺3件、舟1件、盤1件、匜1件。陶器主要有蓋豆6件、罍6件。根據隨葬銅器組合與特征來看,時代應該屬于春秋早中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套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7件列鼎和1件陪鼎,按照用鼎規格來看,應該是薛國君級別的墓葬。
M2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無墓道,墓向為20°,有生土二層臺,一槨二棺,腰部下有殉人坑,臺上放置一長方形木箱,木箱長2.72米,寬2.6米,殘高1米,板厚0.1米。葬具為雙槨雙棺,外槨蓋頂殉狗一只。殉人四具,分別位于腰坑和內槨室南部。隨葬品主要放置于器物箱、槨室附近以及棺內,有銅、玉、石、蚌器等554件。銅器有禮器、車馬器、兵器、生產工具、雜用器等,其中禮器包括鼎8件、簋6件、鬲6件、簠2件、壺3件、舟1件、盤1件、匜1件、小罐1件。陶器4件,均為陶罍。據隨葬器物特征而言,該墓葬的年代屬于春秋中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套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7件列鼎和1件陪鼎,用鼎規格與M1一致,應該也是國君級別的墓葬。
M3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向為14°,有生土二層臺、腰部下殉人坑,臺上放置一木箱,箱內放置銅器、陶器等隨葬品。殉人坑的形制及人骨架因被盜擾而不明。隨葬品大部分被盜掘,剩余隨葬品集中發現于二層臺上的木箱內、槨室四周及棺內,剩余74件,其中銅容器1件提梁壺,上刻有銘文“薛侯行壺”。二層臺木箱西北角有陶罍4件,東北角有銅提梁壺和鹿角飾各1件,蚌魚、銅矛、銅鏃、銅鈴、骨簪等散亂在槨室四周及棺內。墓葬中出土了帶有“薛侯”銘文的銅器,可判定是薛國國君的墓葬。
M4破壞嚴重,棺槨室被鐵路所壓,僅清理其北頭的隨葬器物箱,長3.6米,寬2米,殘高0.5米。隨葬品主要放置于器物箱之中,另外器物箱外也遺留部分隨葬品。主要有鼎10(7件列鼎和3件陪鼎)件、簋6件、鬲6件、簠2件、壺3件、舟1件、盤2件、匜1件、盉1件、鳥形杯3件、鑒1件、矛1件,還有陶罍6件、骨器1件。該墓葬的年代也屬于春秋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列鼎規格與M1、M2一致,應該也是國君級別的墓葬。
此外,在M6、M9小型墓中也存在腰坑和殉人等相關習俗,但從墓葬形制及用鼎規格來看,明顯低于上述幾座墓葬,應該是春秋時期薛國低級別貴族墓葬。
(二)前掌大遺址
位于滕州市官橋鎮前掌大村周圍,東與薛國故城相隔不足2公里。從1964年開始,對此處持續進行考古,目前可知前掌大規模巨大,面積在上百萬平方米以上,為“聚葬合一”型聚落結構。經詳細鉆探和考古發掘,目前已發現8處相對集中且相對獨立的墓葬區,按照墓Ⅰ至墓Ⅷ順序依次編號,累計清理了150余座商周時期墓葬。[3]
墓Ⅰ區,通稱“河崖頭”墓區或“村北”墓地,位于村北小魏河轉彎處,經過前后5次發掘,共計清理了大、中、小型墓葬35座,其中,僅“中”字形或“甲”字形大墓就清理了12座,規格在8處獨立墓區中最高。墓Ⅱ區,通稱“南崗子”墓地或“村南”墓地,位于村南遺址區中心“南崗子”最高處,經過前后5次發掘,共計清理了中、小型墓葬76座,尚未發現類似于墓Ⅰ區帶墓道型大墓,從規格來看,雖然次于墓Ⅰ區,但明顯高于其他墓區。墓Ⅲ區,位于前掌大村中南部,經過前后2次發掘,共計清理了中、小型墓葬25座。墓葬Ⅳ區,位于村西南角,因被大肆盜掘而確認。墓葬Ⅴ區,位于前掌大村東南、于屯村北,經過前后2次發掘,清理了中、小型墓葬23座。墓葬Ⅵ區,位于村西南部,2004年清理了1座被盜較大的墓。墓葬Ⅶ區,位于村中部偏西處,清理了7座墓葬。墓葬Ⅷ區,位于村中部偏東處。
發掘報告將墓地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商代晚期的27座墓葬,第二期為西周早期早段的34座墓葬和5座車馬坑,第三期為西周早期晚段的12座墓葬。諸多專家學者有不同看法。[4]就整個墓葬和堆積時代而言,從殷墟三期后段延續至西周早期,部分墓葬到了西周中期前段。[5]
根據前掌大出土的大量帶有“史”符號的青銅器來看,“史”是商周時期的一種族徽符號或職銜,而此處是“史”族的家族墓地。發現的以“史”為族名或人名的有銘銅器的數量可達170余件。[6](P577~582)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于陜西岐山北寨子的“亞薛鼎”和傳世西周早期的薛侯鼎銘文中有著“薛”與“史”符號共存的現象,這間接反映了薛國與“史族”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馮時先生指出,薛侯以“父乙”為廟號,銘末錄族徽“史”,說明周之薛侯源自殷商之史氏。“史”在殷商時期的地位和職能,多與軍事等密切相關,且地位較高,因此以官為氏。[7](P583~597)如此看來,周代的薛國應該就是來自商末的“史”族,而前掌大正是商末周初“史”族在棗滕地區的始封(居)之地。
前掌大遺址的年代最晚是在西周中期偏早階段,而與之相隔不足2公里的薛國故城的年代則最早可追溯到西周中期,兩者之間在年代方面存在前后承接的關系,今薛國故城應是前掌大“史”族即薛國在西周中期之時所遷之地。此外,在前掌大村東部5公里外還發現了東萊、大韓等一些東周時期的墓地,有學者認為這些墓地國別族屬為薛國。
二、薛國的商系文化因素
文獻記載中的薛國自夏立國,而從考古方面來看,薛國在棗滕地區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商末周初,也就是前掌大遺址所代表的薛國早期遺址,及而后遷徙至不遠處的今薛國故城遺址。綜合兩處規模巨大的周代薛國遺址來看,其墓葬習俗方面有著明顯的繼承和發展關系,即繼承了商系文化,主要表現在腰坑殉狗、殉人、隨葬器物以及銅器上族徽和日名方面。
首先,“腰坑”“殉狗”葬俗是商系文化喪葬、祭祀制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之一。關于其功能和意義,學界早已有了詳細研究。周滅商之后,山東地區仍有不少墓葬設置存在腰坑、殉狗現象,薛國作為商代之時遷移而至棗滕地區的邦國,其墓葬也延續了腰坑、殉狗的傳統。前掌大遺址的殉狗現象非常普遍,約有81座殉狗墓葬,占了已公布墓葬數量的半數以上,其中殉狗1~2條最為常見,少數墓葬殉狗3條,多放置于腰坑、二層臺之上,有的也置于槨板或填土之內。與此同時,前掌大遺址中還有75座設置腰坑的墓葬,其中腰坑殉狗墓有60座,腰坑殉人墓有4座。在薛國故城遺址內公布的春秋時期的7座墓葬中,多發現有腰坑并內殉人,其中M1、M2、M8三座墓葬中均存在殉狗現象,置于槨板或二層臺之上。前掌大遺址作為西周早中期的薛國貴族墓地,頭箱、腰坑、殉狗現象十分普遍,帶有明顯的商系文化特征。隨著時間的推移,春秋時期薛國故城墓地內腰坑習仍有保存,固守了商系文化中的殉狗習俗。此外,近年來隨著大韓墓地相關材料[8]的公布,一些春秋晚秋至戰國時期的墓地中也存在腰坑、殉狗的現象,這無疑也是對商系文化的繼承,且持續時間較長。
其次,“殉人”之風在商代晚期墓葬中十分盛行,也是商系文化墓葬習俗的典型特征之一。前掌大遺址中的殉人墓約有11座,占比7%左右,其中殉人1~2具最為常見,殉人最多的M201為7具,多放置于腰坑、二層臺、墓道或填土之內。薛國故城內春秋時期的墓葬殉人情況較為常見,M1、M2、M3、M6、M9均存在不同數量的殉人,殉人數量一般為1~4具,多置于墓室底部的殉人坑以及槨室周圍,且基本未見葬具。此外,在大韓墓地中的大中型墓藏中也有著相當數量的殉人,數量一般在1至10人之間。[9]例如,在已經公布的M39中就有4具殉人分布在其槨室周圍。由此可知,前掌大遺址所代表西周早期的薛國與薛國故城所代表的春秋時期的薛國始終堅持商系文化中的殉人之風,這些都反映出薛國雖然長期生活在姬周文化的氛圍之中,但其殉人習俗仍然長期使用,未被摒棄。
再者,商系文化中有著自己獨特的隨葬器物組合,十分重視“酒器”在隨葬品中的地位,并隨葬較多的爵、觚、尊、卣、觶等商系酒器。前掌大遺址中的M11、M14、M15、M18、M21、M34、M38、M110、M120、M121等諸多墓葬均有商系酒器的出土,且在隨葬品中的占比較高,其組合形式大多為觚爵觶尊卣、爵觶尊卣、觚觶尊卣、爵觶等,這些無疑是繼承商系文化中隨葬器物組合的風格。由此可以看出,這些前掌大遺址中墓葬的年代雖然已經進入了西周早中期,但是仍然保持著原來的重酒傳統,并將這種傳統隨葬于墓葬之中,反映出其對商系文化的繼承。
此外,如同用不用腰坑是區分商人墓葬與周人墓葬的一個標準一樣,用不用日名、族徽銅器也是區分商人青銅器與周人青銅器的一個標準。[10]前掌大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帶有族徽符號的有銘銅器,其中帶有“史”族徽符號的銅器多達70余件,帶有“鳥”族徽符號的銅器近10件。與此同時,在前掌大遺址出土的銅器銘文中有不少涉及“父丁”“癸”“父乙”“□丁”“父戊”等具有商代風格的日名。這些無疑也反映了早期薛國商系文化遺俗。
綜上可以看出,從西周早期的薛國前掌大墓葬一直到春秋中晚期的薛國故城墓葬,甚至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期大韓墓地中的部分墓葬,仍然保留了濃厚且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商系文化因素。無論是頭箱、腰坑、殉狗、殉人、隨葬商系酒器,還是族徽和日名的使用,均能體現出商系文化對薛國的持續性影響。此外,前掌大遺址的西周墓葬中還存數量較多的與中原地區殷商系文化相近或相似的青銅器、玉器等,大部分陶器延續了商式風格。[3D]
三、薛國的姬周文化因素
薛國在商末周初,通過婚姻等方式加強了與周王和魯國之間的交流,如《詩經》載有“思齊大任,文王之母”[1](P516),《左傳》也載有“周公及武公娶于薛”[1](P2181),表明任姓薛國與姬姓周和魯國之間存在婚媾關系。有學者指出,西周初年,薛國之所以被分封為“侯”國,與太任為周文王母有著密切的關聯。薛國在墓葬習俗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姬周文化特征。姬周文化因素也成為前掌大遺址墓地和薛國故城遺址墓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體現在列鼎制度、隨葬器物組合以及隨葬原始瓷器、印紋硬陶、陶三足盤、銅鑾鈴、銅當盧、銅車轄等周式風格的隨葬品方面。
首先,在列鼎制度方面,用鼎禮制作為周代重要的用器制度之一,在春秋戰國時期習見于諸多邦國、族群貴族墓葬中,且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邦國用鼎禮制各有特色,并不完全相同,體現了兩周時期諸國文化禮制的多樣性。[11]春秋時期薛國故城的M1、M2和M4三座國君墓葬隨葬了列鼎。M1使用了8件青銅鼎,其中包括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的7件列鼎和1件陪鼎,與之同出的還有6件銅簋。M2使用了8件青銅鼎,其中包括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的7件列鼎和1件平蓋鼎,與之同出的還有6件銅簋。M4使用了10件青銅鼎,其中包括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的7件列鼎和3件形制形同、大小依次遞減的平蓋鼎,與之同出的還有6件銅簋。三座墓葬中的成套列鼎均是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遞減,且均搭配了不同數量的陪鼎以及相差一等級的銅簋,分別構成了7鼎6簋的鼎簋組合。春秋早中期姬周文化中對于列鼎制度有著嚴格的禮儀規范,從諸多出土的姬周邦國墓葬中也可以看出,基本隨葬大小相次的奇數列鼎以及搭配次一等級的銅簋。薛國與姬周邦國貴族隨葬的列鼎及鼎簋制度保持了一致性,也具有華夏文化的特性。
其次,在隨葬器物組合方面,薛國國君墓隨葬的銅禮器基本組合形式為鼎簋鬲簠的食器組合、壺舟的酒器組合以及盤匜的水器組合。[12]這些組合常見于華夏諸國貴族墓內。從隨葬器物的數量來看,薛國國君墓隨葬食器數量占比最多,有著明顯的“重食”傳統,這與姬周文化邦國墓葬中的情況相同。因此,在隨葬器物組合方面,薛國故城的春秋時期的墓葬表現出與姬周文化高度相似之處,說明薛國深受姬周文化的影響。
最后,在隨葬品方面,前掌大遺址西周早中期墓葬共計出土了41件原始瓷器、18件印文硬陶器、1件陶三足盤、2件青銅鑾鈴以及3件銅車轄。前掌大遺址中出土的原始瓷器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形態,其來源應是周王朝的賞賜或交流的產物。[13](P611~617)陶三足盤是由周人發明創造并使用的,是典型的周式器物。[4A]對于青銅鑾鈴、當盧和銅車轄的研究,學界更是存在豐富的研究成果,并擁有較為一致的觀點,即認為這兩種器物是周式風格的車馬器。[14]青銅鑾鈴、當盧和銅車轄在諸多西周時期的姬周邦國墓葬中均有出土,為典型的周式器物。有學者曾對前掌大遺址中出土的銅容器做過系統的研究,發現85種形式的銅容器中有31種屬于晚商至西周共有的器物形式,而見于西周早中期的器物形式也多達30種,并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前掌大隨葬的銅容器形式反映了商系文化因素漸少而周文化因素增多。[15]此外,發掘者在薛國故城的考古報告中指出,幾座春秋時期的薛國墓葬中出土的銅器紋飾中的諸多花樣與中原地區的上村嶺虢國墓地、洛陽中州路墓葬以及魯故城M46、M23等墓葬有著相似之處,這應該也是春秋時期薛國兼收并蓄姬周文化的產物。[2A]
因此,前掌大遺址展現了早期薛國隨葬了具有姬周文化因素的重鼎簋食器組合及諸多周式器物,如原始瓷器、青銅鑾鈴、當盧等;而薛國故城中的墓葬則反映了春秋時期的薛國在列鼎、鼎簋等用鼎禮儀以及隨葬器物組合方面與姬周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并且在銅器紋樣上也包含了豐富的姬周文化因素。
結 語
基于上文對于周代薛國故城、前掌大墓葬的年代及“史”族的來源、薛國墓葬中的商系文化及姬周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商末周初,中原地區的“史”族或者“史”族的一支遷移至棗滕地區的前掌大,這也是早期薛國,后于西周中期遷至今薛國故城范圍內,此后直到薛國滅亡再未遷移。作為周初立國于薛國,其墓葬較好地繼承了腰坑、殉狗、殉人、酒器、族徽及日名等商系文化因素。雖然大韓墓地等一系列墓地尚無法確定是否屬于周代的薛國墓地,但是從其墓葬習俗中可以看出,也存在著明顯的商系文化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及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西周時期薛國與春秋時期的薛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姬周文化的浸染,在列鼎制度、隨葬品組合以及風格方面體現出濃厚的姬周文化風格,并呈現出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