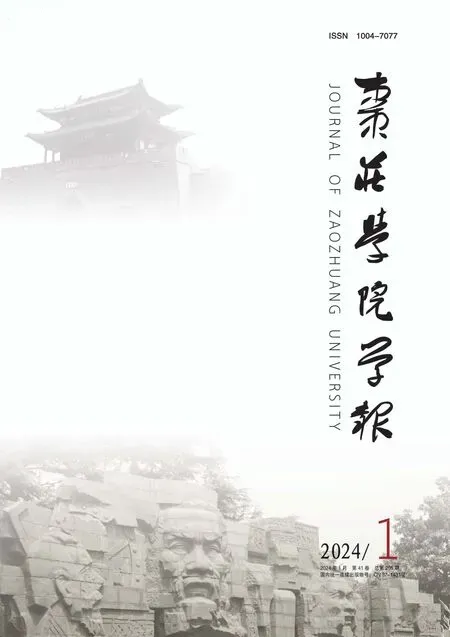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山東螳螂拳南傳港澳臺的歷史進程與文化價值研究
陳曉明
(山東省藝術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武術是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在社會、文學、歷史、哲學、生物、心理等層面蘊含著豐富的研究價值。本文以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將山東螳螂拳的南傳作為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予以考察。綜合運用文獻資料法、田野調查法、邏輯推演法等文化人類學方法完善對這一文化現象的認知,并試圖通過文化氣質、文化符號、文化轉譯等文化人類學理論兼以部分積極心理學理論進行深度解釋,最終結合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現實文化需求提出發展建議。
一、武術救國:山東螳螂拳南傳歷程
(一)山東螳螂拳南傳譜系溯源
本研究整理山東螳螂拳南傳譜系如下:山東螳螂拳創始人為王朗,下傳三個流派:一是太極梅花螳螂拳,由二代李秉霄傳趙珠,再傳梁學香,自梁學香處發揚光大,傳郝宏、姜化龍、孫元昌等,再至危鳳池、鮑光英及其徒霍耀池、趙竹溪及其徒鄺群威傳拳于香港;李昆山、衛笑堂傳拳于臺灣。二是七星螳螂拳,由二代少林寺僧、升霄道人傳李之剪,再傳王云生,再傳范旭東;范旭東之徒羅光玉受聘于精武會,傳拳于上海、廣州、佛山、香港。三是六合螳螂拳,由二代金葉傳魏德林,再傳林世春,再傳丁子誠,丁子誠之徒張祥三傳拳臺灣。
南傳代表性人物總共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投身武術救國。如羅光玉,精武體育會四大名師之一,螳螂拳南傳第一人,也是影響最大的代表人物。羅光玉1919年受聘于上海精武體育總會,后升任總教練之職,山東螳螂拳得以在上海傳播。后到廣州、佛山、香港、澳門等精武體育會組織任教,由此將山東螳螂拳傳到廣東、香港乃至東南亞。
其二,個人闖蕩。如鮑光英、趙竹溪,以經商、走鏢、行醫、開館為業,闖蕩于廣州、香港、澳門乃至越南等地,名聲鵲起,廣收門徒。
其三,赴臺灣傳拳。例如,李昆山于1933年參加山東省國術考試并獲第一名,后任教于山東國術館;衛笑堂曾在軍中擔任武術教官;張祥三曾在政治學校中擔任國術教練。
(二)南傳奠基者梁學香及其思想貢獻
涌現眾多山東螳螂拳南傳人物并非偶然,而是長期發展積淀后際遇時代變化的一次厚積薄發,其中起到奠基作用的是李秉霄一脈第三代傳承者梁學香。梁學香生于嘉慶十四年 (1810年),其主要貢獻有:
其一,編訂拳譜《可使有勇》《內功譜》《拳棍槍譜》,在山東螳螂拳教習方面,奠定了理論基礎,梳理了教學方法。梁學香在拳譜中明確說明六合棍取法于福山于氏,延續了山東螳螂拳開放吸納的傳統。
其二,使螳螂拳從地方拳種一躍成為膠東乃至整個山東的知名拳種。梁學香早年走鏢于河北滄州,其中一次就打敗了30余名強盜,其本人及螳螂拳得以名聲大振,為日后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其三,創新改革授徒傳統,不限單傳、不分內外弟子,傳藝極廣,遍布膠東諸縣。梁學香40余歲(約1850~1860年)時開班授徒,定堂號為“德順堂”。精武體育會在傳授形式上采取公開辦班、公開傳授的方式,破除了師徒之間的“單線秘傳”傳統做法。梁學香的教育理念與之相近,然而梁學香在傳承機制方面的改革,相較精武體育會提出打破門戶之見的改革早了近半個世紀,具有超越時代的先進性。
梁學香的改革促使山東螳螂拳內部形成了良性創新擴散的局面,為日后山東螳螂拳南傳打下了堅實基礎:一是各個支派爭相模仿學習,擴大了基礎人群,提高了優才的出現概率。二是進一步發展了“訪拳”的概念,帶藝從師、學藝后另拜它門成為經常性現象,提高了山東螳螂拳整體進化能力。三是提供思想準備,涌現了一批攜帶“開放思想”文化基因的門內人才,其中代表人物為羅光玉。
(三)精武名師羅光玉
根據上海精武體育總會編撰的《精武志》,精武體育會作為中國第一個“公共教育”型武術文化團體,主張摒棄門戶之見,不限單傳、不分內外、平等教學、公開傳授。[1](P1~4)根據《精武志》,羅光玉(1889~1994),山東蓬萊人。1919年,幾名沙俄士兵在海參崴擺下擂臺,羅光玉的師傅“螳螂拳王”范旭東被北方武術界推舉迎戰。范旭東與羅光玉兩人連挫沙俄拳擊手,名聲大振。消息傳至國內,羅光玉即被上海精武體育總會聘為教練。[1](P149~150)
羅光玉在上海精武體育總會執教多年,成績斐然。據文獻記錄,羅光玉胸襟寬廣,沒有門戶之爭的成見,能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拳法傳授于學員,所以其培育人才的成功率特別高。根據《精武志》,在1928年舉行的全國運動會第一屆國術比賽中,羅光玉的弟子馬建超、陳振儀皆獲優等,其中馬建超更是榮膺榜首、威震武林。1930年,羅光玉南下正式受聘于香港精武會,后又在佛山、澳門等地精武會任教。[1](P149~150)
(四)善于融合的趙竹溪、鮑光英
趙竹溪(1900~1991),山東掖縣人,年約30歲時南下廣州、香港、澳門經商,到90年代時門下已有傳人7萬。鮑光英(生卒年不詳),山東煙臺人,先在煙臺當鏢師,“九一八事變”后南下香港,開館行醫傳武。鮑光英弟子劉談峰參加革命工作,后在政府部門任職;弟子霍耀池名冠香港、澳門,人稱“江湖狀元”。在拳路的融合發展方面,趙竹溪的螳螂拳融合了少林太祖門與太極摩云掌,增添了南方奇門兵器套路,同時吸收詠春優點;鮑光英螳螂拳融入了通臂摔手的打法,同時又在螳螂拳中顯現長拳風格。
(五)組建“臺灣省國術會”的張祥三
張祥三,曾在政治學校任國術教練,隨校經湖南至四川,后赴臺灣。據張祥三《六合螳螂拳》所述:“來臺后與友人發起籌組臺灣省國術會。”“螳螂拳久為國人所推崇,祥三自幼習之,但以所學,不得示人。現也古稀,風燭殘年,如懷技入土,不如公諸于世。”[2](P39~43)
二、南傳的基礎:山東螳螂拳的內蘊氣質
(一)山東螳螂拳內蘊氣質的提出
綜合分析南傳代表人物業跡,例如梁學香改革、羅光玉傳拳、趙竹溪與鮑光安闖蕩江湖與融合各派、張祥三組建“臺灣省國術會”等,可以從中發現一種共同的氣質。這種氣質并非是個人氣質的偶然集合,而是源于山東螳螂拳群體的整體內蘊氣質,其突出例證就是梁學香對傳承機制的改革,在山東螳螂拳群體內部引發了互相借鑒學習的創新擴散現象,奠定了南傳的人力資源與思想基礎這一史實。按照埃弗雷特·羅杰斯在《創新的擴散》中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當創新具有相對優勢性(和現有的方法相比有相對優勢)、相容性(與價值觀、過去的經驗以及當前的需求相容)、易懂性、可試性、可觀察性等特征時,它們會被更快地采用。[3]
其中,“相容性”是特別難以達成的條件。在當時武術界的價值觀里,“單線秘傳”“內外弟子”的觀念根深蒂固。根據《精武志》,直到精武體育會成立,“摒棄門戶之見”仍是精武體育會武術改革斗爭的主要方向,由此可見梁學香改革所具有的先進性。[1](P22~225)
當時,在一般的武術門派中就傳承機制進行改革是非常容易因遭到“離經叛道”的道德批判而夭折的。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梁學香的改革基本沒有受到阻礙,反而在山東螳螂拳群體內部得到了傳播與推廣。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山東螳螂拳群體內部有一種區別于一般武術門派的“文化基礎設施”,以至于“開放改革”的思想在山東螳螂拳群體中較容易被人接受、開花結果。具備“文化基礎設施”理念的群體在觀念、信仰或思維上偏好,有利于整個群體取得進步。在《信息改變了美國》一書中,阿爾弗雷德·錢德勒教授指出,美國第一批移民所具有的新教徒文化崇尚“知識”,形成了“文化基礎設施”,不斷地推進美國從馬車郵站到互聯網的信息網絡建設歷程。[4]在山東螳螂拳南傳的現象背后,也蘊藏著這樣一種“文化基礎設施”,使得它能產生、容納并發揚梁學香改革這一創新性事件及其成果,這種“文化基礎設施”即是前文所述山東螳螂拳的獨特文化“氣質”。
(二)山東螳螂拳內蘊氣質解析
泰勒·考恩教授在《創造性破壞——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中指出:“文化氣質是指一個文化的特殊感覺和味道”,“良好的氣質能讓相對小的群體實現文化奇跡”。[5]
本文以山東螳螂拳各分支所共傳的《王朗創拳傳說》與《王朗訪友歌》為主要對象分析其內蘊氣質。雖然王朗其人的歷史考據仍然存疑,但由于門派內多年來形成了堅實的共同意識,相關敘事依然能實現教化作用,正如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所指出的:“虛構故事的力量強過任何的想象。”[6]
王朗自幼天資聰慧,師從嶗山三清宮羽化真人。數年藝成,羽化真人開導其說:“賢師莫若訪友妙。”王朗遂拜別師尊,挾技訪友,印證武功。后敗于嵩山少林寺僧人,出寺乘涼避暑,抬頭見樹枝之上螳螂捕蟬,螳螂進退有距,擒縱有法,長短并施,大有武功技巧,乃捕螳螂返家。以筆桿戲之,見螳螂自然抗拒之勢,悟出閃轉騰挪之勢、沾粘貼靠之法、勾摟采掛之技,是為十二柔法,又灌注十八名家宗法,并融入猿猴之靈巧,后入少林寺再戰得勝。明末,王朗曾奔走四方,組織復明義舉,云云。
王朗的傳說故事,不僅廣為流傳,而且其訪友交流還被編成了《王朗訪友歌》:“太祖的長拳為首,韓通的通臂為母,鄭恩的纏封尤妙,溫元的短拳更奇,馬籍的短打最好,孫恒的猴拳且盛,黃沾的靠身難近,綿世的回掌飛疾,金相的磕手通拳,懷德的摔捋硬蹦,劉興的勾摟采手,譚方的滾漏貫耳,燕青的占拿跌法,林沖的鴛鴦腳強,孟更的七勢連拳,崔連的窩里剖捶,楊滾的棍采入直,王朗的螳螂總敵。”與之相似,習武者交流時也常有經驗總結,如以下幾例常見武術歌訣:“八打八不打,習武要得法,遇敵莫容情,訪友不輕發。”“拳出如流星,變手如閃電,腰轉如滑車,腳步如鋼鉆,不動如書生,動之如猛虎,發勁如崩山。”類似武術歌訣還有很多,不再贅述。對其進行綜上分析后就會發現,山東螳螂拳的內蘊氣質有一定獨特性:
其一,“開放包容,視野廣闊”。王朗盡得“武學超群”的羽化真人真傳,學成之時得開明恩師點化:“賢師莫若訪友妙。”先敗于少林寺僧人而后又取勝這一跌宕轉折的敘事,更是確證了其“賢師莫若訪友妙”思想的真理性。
其二,“多元統一,善于融合”。通過流傳下來的諸多訪友歌,可以看出山東螳螂拳融合其他拳派的大致結構,而習藝者在融合多元流派、適應當下環境方面可以從中獲得可參詳的思路。山東螳螂拳在融合中不斷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拳種,如融合六合拳的六合螳螂、融合八卦掌的八步螳螂、融合少林長拳的長拳螳螂等。此外,趙竹溪、鮑光英在一路南下的過程中又吸納南派武術,體現了山東螳螂拳內在的張力與適應性。
其三,“積極尚智,應變機敏”。王朗以螳螂捕蟬為契機,對于“螳螂自然抗拒之勢”進行觀察、研究并開創螳螂拳,而且憑借其成功挑戰少林僧人。事后,其師云:“今十余年,能勝少林者鮮矣,今汝勝之,可謂螳螂之總敵。”如果說《魯賓遜漂流記》隱喻著對理性意識的推崇,那么王朗開創螳螂拳的過程中則得益于對智力因素的運用。另外,山東螳螂拳推崇勇進、快速,要求使用者機靈、敏捷、勇敢,連環出手如梅花成伍,騰挪躲閃、攻守相隨。
其四,“家國情懷,個性爽利”。王朗在反清復明的種種所為,足以凸顯其家國情懷。在接人待物方面,王朗知禮而不拘泥,同時又敵友分明,可謂“遇敵莫容情,訪友不輕發”。
三、膠東文化:山東螳螂拳內蘊氣質溯源
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之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7](P2)山東螳螂拳起源于膠東大地,其積極尚智、開放包容、多元統一、家國情懷等內蘊氣質與膠東文化密不可分,尤其是深受膠東當地“海洋商業”與“海洋邊防”文化的影響。
(一)膠東地理歷史文化環境
膠東,指山東膠萊河以東的半島地區。從現今的行政區域看,主要包括煙臺市、威海市、青島市,大略為古稱登州、萊州二州所在。膠東三面向海,一面臨河,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8](P1)膠東三面向海之處,以廟島群島為鎖鑰,自春秋時期以來,商通日本、朝鮮、遼東,扼守黃海、渤海,拱衛京津重地,成為北方海路之門戶。內陸以膠萊河形成自然分割,內有丘陵、平原等典型農業生產區域,自古盛產柞蠶絲綢、海鹽、魚干、黃金等經濟物產,海洋資源豐富,漁業發達。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膠東“海洋商業”與“海洋邊防”并重的文化。從春秋時期齊國開辟東通朝鮮、南通吳越的“海上絲綢之路”到近代煙臺、青島開埠,從北宋設立我國最早的海軍基地——“刀魚寨”到建立我國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北洋水師,膠東地區不僅形成了“積極、開放、多元、尚智”的濃厚經商傳統,更在遍布海防衛、所、堡、寨的軍民共融發展中生成了“尚武衛國”的家國情懷。
(二)膠東海洋商業文化與山東螳螂拳
最遲在龍山文化時代,膠東半島居民已經具備較強的航海能力。至春秋時期,《管子·輕重甲》記載,管子建議齊桓公:“吳越不朝,請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為幣乎?”討論通過海路與朝鮮、南方的吳越以及遼東的“發”人(當地居民)做貿易的可能性。漢唐時期,登州成為對外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到了北宋年間,由于受戰爭影響,登州成為軍港,廟島群島中的砣磯島成為北宋針對遼國的海上邊防最前哨,此時膠東的通商口岸南遷至密州板橋鎮(今屬膠州市)。明清時期政府禁海,至康熙初,康熙“喻兵部:山東青、登、萊登出沿海居民,向賴捕魚為生,因禁海多有失業……令其捕魚,以咨民生”,漁民因此常借捕魚的名義進行貿易;道光年間,以海運行漕運,促使膠東與江、浙、閩、粵建立了廣泛的商業聯系,半島南岸的膠州、即墨金家口、萊陽,以及半島北部的黃縣、煙臺、文登威海口成為商業重鎮。煙臺、青島相繼開埠后,膠東進一步加速了現代商業文明的發展。[8](P167~184)
長期的海洋商業歷史形成了膠東獨特的海洋商業文化。首先是積極勇敢,北上遼東、朝鮮,南下江、浙、閩、越,往內地沿小清河漕運或經濰坊至濟南,甚至在明清海禁時期也不曾斷絕民間“漁采貿易”。其次是聰明尚智,從早期的魚、鹽、絲綢,到后期的蘋果、花生,出口的棒槌邊花、粉絲、草辮,乃至典當錢莊及現代工業企業,膠東人善于開發經濟產品與服務。最后是開放、多元,與徽商、晉商壟斷一省之貿易不同,在膠東,除了黃縣幫、掖縣幫等本地商幫,亦有廣幫、建幫、寧波幫、關里幫、錦幫等外地商幫,皆被膠東人容納,互利共贏。[8](P299)
以山東螳螂拳為首的武術群體曾是膠東發達商業網絡的重要保障,他們活躍在行鏢、保館等一線,在與商幫的深度交融中,潛移默化地受到“積極、尚智、開放”等精神元素的影響。例如,梁學香、趙竹溪、鮑光英等人在行鏢中打響了名聲;六合螳螂拳的名家丁子誠本身就是黃縣巨富丁氏家族中人,其徒弟單香陵為梅蘭芳的武術教師。據丁子誠之徒張詳三《六合螳螂拳》所述:“招遠縣全縣勿論大小村鎮,老幼皆習拳術(種類繁多),可與河北滄縣伯仲之間”,“吾邑黃縣為京師通煙臺之要道,青島未開港之前,煙臺為魯省唯一之港口,故各行業之紳要,京都之顯宦,往來不絕。邑之城南有王姓巨富,廣交國術界人士,聘有家教,教授弟子,凡過境名師,無不聞名往訪。先師(丁子誠)游歷歸里后,因親戚關系,時往研究,亦獲益良深”。[2](P39~43)可見山東螳螂拳與膠東商幫、膠東海洋商業文化交集之深。
(三)膠東海洋邊防文化與山東螳螂拳
膠東一直是中國海防建設的重點區域。北宋年間,在現今的蓬萊丹崖山建設了我國最早的海軍基地“刀魚寨”,后又在廟島群島諸島建設烽火臺與炮臺,形成互相協防的海防體系。到了明代,先后在山東沿海設11衛,下轄14所、20巡檢司、243墩、129堡,其中在登州就有6衛。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繼光正式就任都指揮僉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3個營25個衛所,總督山東沿海抗倭戰爭并取得了巨大勝利,當地至今仍然流傳有“戚家拳”“蓬萊長桿號(戚家軍號)”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清朝以后,于1888年建成我國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北洋水師,駐防威海衛基地。[8](P195~217)
在數百年海防斗爭中,膠東軍民一體融合化特征明顯,民間習武者家國情懷非常濃厚,山東螳螂拳習練者尤其如此。例如,范旭東、羅光玉師徒拳斗沙俄擂臺;崔壽山力敵日本憲兵、拒絕向日偽軍授拳,被八路軍膠東區司令部許世友將軍聘為武術教官。1933年,在崔壽山倡導下,7位螳螂拳名師共同發起成立了萊陽國術館。在抗日戰爭期間,萊陽國術館先后有50多位學員投入抗戰第一線,其中,國術館第一批學員張家憲參加了著名愛國將領、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將軍部隊的大刀隊,在“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中,用大刀接連砍下7個日本鬼子頭顱后壯烈殉國。[9]
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文化符號的山東螳螂拳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一節中指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我國《“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中明確提出: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山東螳螂拳,經過21世紀初的南傳廣布,形成了根植齊魯、橫跨兩岸三地、遍布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活態傳承的文化脈絡,是活躍在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前沿的珍貴文化遺產。其“積極尚智、開放包容、多元統一、家國情懷”的內蘊氣質,可以作為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優秀例證。挖掘與利用山東螳螂拳文化意義,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服務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解讀山東螳螂拳文化價值
政治學家安德森將民族共同體視為“符號共同體”,認為民族共同體作為一種想象,其思維意識必須以符號為媒介。[10](P7~12)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文明發展中所形成的各種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民族成員確立民族身份、喚醒民族情感、產生民族認同的路徑和基礎,“文化符號”對于凝聚、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載體性意義。[11]為此,應重視仍在活態傳承、繁衍并橫跨廣闊地域的文化符號。結合南傳的山東螳螂拳來看,它仍在活態傳承之中,縱貫齊魯、海派、百越、港臺乃至東南亞的廣闊地域,共享傳承譜系、拜師儀式、技法體驗、文化轉譯等多維度意義,具有喚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顯著能力,是具有優良載體性功能的文化符號。
從現實來看,山東螳螂拳的傳承者已在當下自覺地開展不同的交流活動。例如,六合螳螂拳省級傳承人張道錦多年來堅持不懈地開展兩岸溝通學習活動,構鑄魯臺文化紐帶;廣州螳螂拳學會會長梁上燕組織滬粵皖螳螂拳山東尋根之旅代表團,開啟螳螂拳南傳百年尋根之旅;八部螳螂拳臺灣傳承人回上海傳徒授藝等。這種傳承人自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為,顯現出山東螳螂拳作為文化符號的內在潛力。因此,有必要對山東螳螂拳的文化符號功能進行系統分析,以便于對其加以充分利用。作為文化符號的山東螳螂拳,主要從體驗共享(針對學藝者)與轉譯共享(針對非學藝者)兩條路徑,影響大眾的文化感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學藝者的體驗共享
遍布天南海北的山東螳螂拳學藝者主要通過體驗共享來完成其內部血濃于水的感情紐結。
其一,共享傳承體驗。傳承譜系的核心是“師緣擬血緣”,更大的文化背景則是“天地君親師”的儒家道統。這種遠超于一般技藝傳授的情感鏈接,來自于武術不但是營生的手段,更是生死相關的技術、保家護國的本領。孫中山在《精武本紀》中言:“(豈)不知最后五分鐘之決勝,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蓋以振起從來體育之技擊術,為務于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系。”
傳承體驗包括尋根問祖、授徒儀式、戒律口訣與道德規范。通過傳承體驗,學藝者共享了宏大的意義和敬畏的情緒。根據積極心理學理論,“宏大的意義”緣于其從事了超越個人價值的事業,而“敬畏的情緒”則是其意識到自己從事了某種具有宏大意義的事業時所產生的最熱烈、最滿足的積極情緒。[12]
其二,共享修行體驗。首先,武術修行可以達成“心流”與“巔峰體驗”。當一件事情讓人專心致志、高度積極地發揮個人能力時,人就能迅速達到忘我的心理狀態,而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取得成功時,就能獲得極度欣喜、自我肯定的巔峰體驗。同一拳種的學藝者獲得“心流”或“巔峰體驗”的來源往往是一致的,對于這種“巔峰體驗”的共享則又形成了強大的認同感。[13]其次,從藝者互相訪拳、交流,會產生積極的社交情緒。對此,積極心理學理論將其解釋為快樂的尷尬和間接的驕傲。其中,快樂的尷尬指樂意對方調侃自己,獲得相互間的安全感和信任感;間接的驕傲,也叫“納奇斯”效應,指通過教導或指點某人,幫助其取得成功時所產生的驕傲感。[12]由此產生的情感紐帶,就是“同門情誼”。
(三)非學藝者的轉譯共享
相對于廣大的海內外各界愛國統一陣線而言,其中從藝于山東螳螂拳的畢竟是少數。因此,借助轉譯共享理論,將承載著“積極尚智、開放包容、多元統一、家國情懷”內蘊氣質的山東螳螂拳轉譯成文化產品,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其文化價值。[14]
其一,宣傳螳螂拳發展及南傳過程中所涌現的英雄人物與傳奇故事。例如,對于梁尚香、王云生、羅光玉等人的業績,通過紀錄片或影視、動漫等方式將其傳播出去。
其二,創新研發“綜合格斗螳螂拳”。終極格斗冠軍賽(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簡稱UFC)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綜合格斗賽事,中國女子綜合格斗運動員張偉麗在第二次UFC奪冠后,直言中國武術多有取法之處。從范旭東師徒以拳擊規則挑戰沙俄對手來看,相關規則不是中國武術登上國際擂臺的阻礙,中國武術有充分的底蘊與變化的張力,特別是山東螳螂拳“開放包容、多元統一”的內蘊氣質更適宜與任何國際規則融合對接。
結 語
山東螳螂拳南傳,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時代巨變的激蕩響應,而且結出了豐碩果實,如今形成了根植齊魯,遍布港澳臺、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的活態傳承的文化脈絡。山東螳螂拳作為內涵豐富、極具潛力的文化符號,應充分發揮其載體性作用,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服務。對此,嘗試提出如下建議:
其一,積極組織并鼓勵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主題的跨地域交流、學習與尋根問祖活動,并進行大力宣傳。
其二,立足“文化自信”,廣泛開展文化轉譯工作,弘揚山東螳螂拳“積極尚智、開放包容、多元統一、家國情懷”的內蘊氣質。具體來說,可以采用紀錄片、綜藝、影視作品、旅游宣傳、研學體驗等方式,以及重點面向青少年的動漫、游戲等數字文化作品。
其三,積極研發“綜合格斗螳螂拳”,培育攜帶“螳螂拳基因”的國際綜合格斗選手。邀請當前世界排名靠前的我國知名選手(如張偉麗、宋亞東、閆曉楠等)參詳螳螂拳技法,使之成為我國選手在國際擂臺上的“制勝一招”。
注釋
①譜系來源于訪談記錄與危風池《山東螳螂拳近代發展概況》講演材料等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