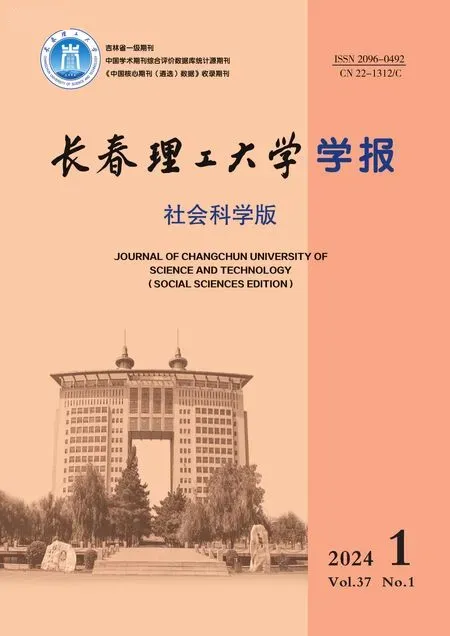民族新信仰的找尋:“科玄論戰”與唯物史觀中國化
——兼論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及其實現
鄭博勻,李寶艷,豆金雨
(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福州,350002)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今年是“科玄論戰”一百周年。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參與的思想論戰,“科玄論戰”在黨史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擬從“科玄論戰”的背景與焦點切入,明確馬克思主義者在論戰中的主要觀點,進而在馬克思主義者與其他思想流派的互動關系中反思其奪取話語權的主要策略,這對新時代增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凝聚力和引領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科玄論戰”概述
“科玄論戰”爆發于1923 年初,至1924 年底基本結束,是中國近代以來中西方思想文化第一次爆發激烈沖突的思想論戰。“科玄論戰”爆發之時已處于新文化運動的尾聲,有著深厚的近代思想文化背景。康有為、譚嗣同用西方科學思想對今文經學進行改造,實現了中國傳統經學的現代化鼎新,然而希冀在傳統儒學的框架內嵌入現代價值體系的守舊做法,終究在歷史實踐中失敗。20 世紀后,武昌起義的槍炮聲使王綱解紐,從政治上切斷了傳統觀念賴以存續的根基。新文化運動繼而喊出“打倒孔家店”等激進口號,千年構筑的孔教權威遭到進一步瓦解。“科玄論戰”爆發之時,在國人頭腦中維續千年的儒學系統遭到徹底解構。由于近代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探索的各種救國道路接連失敗,此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已從“船堅炮利”的物質、“鼎革之際”的改良等問題上轉移至對思想文化的關注,將思想文化問題放到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首位,而最為核心的問題是盡快尋求一種新的人生信仰與精神支柱。其中,建立或應有何種生活態度、人生目標是解決人生信仰的根本問題。當時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張君勱都清楚,中國思想文化史已經走到了變革信仰系統、重構哲學體系的關鍵時期。李澤厚指出,“科玄論戰”的核心分歧在于“現時代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一代)應該有什么樣的人生觀才有助于國家富強社會穩定?”[2]一時間,人生觀問題就成為了時代的焦點及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間研討的學術主題。
由于不同派別所持的學術傳統與代表立場相異,“科玄論戰”以“科學何以支配人生觀”為論戰焦點,在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差別何在、社會規律是否存在發展規律、人的意志在社會領域中的作用如何等問題上存在分歧,集中表現為以胡適、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以陳獨秀、瞿秋白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之間的沖突。論戰爆發于1923 年2 月張君勱為即將啟程赴美留學的清華大學學生作題為《人生觀》的演講,其將人生觀的特點歸結為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單一性的,因此“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3]10。他認為精神世界瞬息萬變,無法用科學的因果律度量。隨后,地質學家丁文江發表長文《玄學與科學》駁斥了張君勱的觀點,其篤信科學對建立中國現代文化的關鍵作用。科學派的觀點表現出對科學社會功能的深刻反思,具有強烈的唯科學主義色彩。就在科學派與玄學派論戰正酣之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高舉唯物史觀的大旗加入論戰,就人生觀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使論戰焦點更為深入。唯物史觀派指出,科學可以解釋人生觀,更可以改變人生觀,但對科學派持有的唯科學主義的論調給予批判。唯物史觀派的加入使這場論戰由學術之辯向社會理論之辯演化,他們提倡人們只有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調分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方能透過各種社會現象的遮蔽,從經濟基礎客觀尋找支配人生觀的決定性因素,從而在根本上解釋人生觀問題。而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人生觀問題,正是意圖帶領人們投身于改造社會的革命運動,并以此來具體安排人生道路。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在論戰中極大地拉近了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使得這場學術論戰帶上了階級斗爭的色彩。
馬克思主義者提倡的唯物史觀為重構民族信仰系統找到合理途徑,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階層在“科玄論戰”中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禮。在“科玄論戰”中,人們通過對各種派別政治主張與價值立場的鑒別與選擇,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道路[4]。究其原因,唯物史觀派在社會理論上克服了科學派與玄學派的理論片面性,在論戰方法上合理利用論戰策略,最終使得唯物史觀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初步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話語權。
二、“科玄論戰”中唯物史觀派的主要觀點
“科玄論戰”中,唯物史觀派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武器對科玄兩派的觀點進行批判,主要集中在科學觀、文化觀、歷史觀上。在論戰中,科學的唯物史觀對當時中國面臨的時代之問予以回應,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大眾化的進程。
(一)在科學觀上:肯定科學的作用而否定科學萬能論
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大旗,使科學一度成為了代表現代文明的獨有標簽。然而一戰的槍炮聲促使一些知識分子對科學進行反思,“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3]12。至此,一些知識分子對科學的質疑成為了“科玄論戰”的先聲。玄學派通過對西方唯意志論與中國心性之學的融洽,將人生觀歸結為主觀的自由意志,認為人生觀非科學的因果律所能支配,從而質疑科學的作用。而科學派奉行西方的實證主義,指出科學方法普遍適用于一切領域,人生觀受知識、經驗、神經構造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人生觀問題依然是科學問題。而唯物史觀派對科玄兩派都進行批判,實現了在科學觀上的理論超越。
針對玄學派完全脫離社會實踐而空談理性的唯意志論,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從唯物史觀出發論證科學可以支配人生觀,認為人類社會發展仍然具有科學的因果律。當看到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導致西方產生的各種亂象后,張君勱等玄學派產生了對自然科學的不滿,于是將“科學”與“人生觀”置于勢同水火的對立面。而事實卻是,現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思維的強勢擴張已不能容忍任何內嵌于社會生活的神秘對象了[5]。因此唯物史觀派用另一種恰當的科學形式來表征“人生觀”所折射的社會生活,那就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理解與運用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派認為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具有客觀規律,并且都通過科學的分析方法加以揭示。針對張君勱提出的九項人生觀理論,陳獨秀認為不論是婚姻制度的形成到女權主義的興盛,還是守舊到維新的制度觀念的嬗變,都是經濟、生產方式等物質動因變化而導致的必然結果。而人性中存在的悲觀樂觀的個人見解、宗教信仰的差異,都受制于時代及其社會勢力的變革。
針對科學派叫囂的“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論調,唯物史觀派也給予批駁。瞿秋白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三個向度揭示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瞿秋白指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達到了經濟的高度繁榮,但是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疑難病癥和精神病象也是之前的社會形態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單純科學技術的發展無法在自然的威權之下解放人類。在人與自身的關系上,瞿秋白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并無法滿足人的物質欲望,與此相反,技術的發明會刺激人的需要不斷膨脹。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科學技術成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機器,無法參與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他號召社會科學中的有定論派“在這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決定更正確的斗爭方略”[6],用社會主義制度替代資本主義制度以釋放科學技術的革命性。
(二)在文化觀上:紓解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
“科玄論戰”中科玄之爭同時也是中國思想界內部的東西方文化之爭。科學派大都推崇西方文化,強調人生觀應建立在西方科學的基礎之上。而玄學派則認為“中國傳統講‘天人合一’,自然與人生統一于道”[7],應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解決人生觀問題。唯物史觀派則看到了文化差異的本質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差距,從中紓解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實現了在文化觀上的理論超越。
“科玄論戰”時期的中國思想界普遍認為,西方文明是以科學為內核的物質文明,而東方文明則是注重心性涵養的精神文明[8]。一戰的槍炮聲使得部分曾經呼吁用西學挽救東方文明的知識分子開始宣布西方物質文明的破產,甚至大力傳介東方文明以圖扭轉西方文明的危機,以致一時間在中國思想界掀起關于東西方文明間優劣性的爭論。玄學派提倡用孔孟之道與宋明理學修養心性,認為東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法寶。而科學派則反對西方文明破產論,丁文江認為不可能有單靠內心修養卻完全擺脫物質條件而形成的“精神文明”,胡適指出“我們試睜開眼看看: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這樣不發達的交通,這樣不發達的實業——我們哪里配排斥科學”[3]6,他認為當時的中國還未得到科學的賜福,更無理由談及對科學的排斥。瞿秋白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深入剖析了文化的本質,認為文化是反映經濟基礎的各種社會心理的思想系統集合。玄學派學者們極力擁護的“東方文化”是宗法社會的自然經濟、飄搖中的封建制度、低下殖民式的國際地位的反映,同時西方文明的產生有其特殊的物質背景,因此也只能由西方資產階級所獨享。因此,瞿秋白指出,民族新文化應當以克服傳統宗法倫理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兩種文化的弊端為發展方向。而在實現路徑上,瞿秋白認為要實現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弱小民族的聯合,從而實現道德平民化與科學社會化。
(三)在歷史觀上:駁斥科玄兩派對唯物史觀的質疑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科玄論戰中運用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論闡明自己的觀點,并指出物質動因在人生觀問題上的支配作用。科玄兩派則質疑唯物史觀派的觀點,分別站在不同的立場指出唯物史觀在解決人生觀問題的局限性。唯物史觀派則逐條予以批駁,更加翔實地闡釋了唯物史觀。
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將唯物史觀解決人生觀問題等同于“機械的人生觀”。對此,陳獨秀解釋道,唯物史觀“以為人是物質造成的,歷史是人造成的”[9],肯定了現實的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則從多個方面對唯物史觀派進行詰難。其一,胡適認為唯物史觀只是一種用于解釋歷史的理論,而不能解決涉及對宇宙萬物看法的人生觀問題。在他看來,歷史觀只是人生觀的一部分,而唯物史觀從物質動因考察歷史,不能等同于解決全部的人生觀問題。為此,陳獨秀指出唯物史觀名為歷史觀,其實并不限于歷史,也可以運用到人生觀及社會觀。唯物史觀將歷史發展最本質的動因歸結于經濟,但胡適卻把文化、道德、宗教等精神現象與經濟的作用等同,認為其也可以變動社會、支配人生觀,本質上說是堅持了心物二元論。與夸大自由意志作用的玄學派一樣,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觀點。其二,胡適認為唯物史觀是經濟史觀,過度強調經濟的作用,而忽略了思想、言論、教育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因而這種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忽視了人的活動。為此,陳獨秀說明了經濟發展與人的活動之間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經濟發展要依靠人的活動;另一方面,人的活動能否順利實現要受到社會物質條件的限制。唯物史觀派有力地回應了科玄兩派的質疑,在論戰中展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力量。
三、“科玄論戰”中唯物史觀派建構話語權的主要策略
話語權是法國哲學家福柯提出的重要概念,可以將其解釋為一種基于話語影響或實踐力量而產生的話語認同力。話語權的形成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其產生是一個動態過程,最終表現為話語客體對話語主體在情感與價值上的認同。在“科玄論戰”中,唯物史觀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初步構建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科學性外,唯物史觀派所采取的論戰策略功不可沒。
(一)投合時好:完成與科學派的結盟
五四運動之后,社會心理儼然發生巨大變化,科學萬能論風靡一時,大家相信科學的方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科學已在中國社會獲得強勢話語地位[10]。由于普通民眾,甚至是學術界對傳統文化的厭惡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即便玄學派不反對科學,也并非提倡全面復古,但在論戰中科學派仍然理所當然地獲得了強勢話語權。福柯指出“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也不會有任何知識”[11]。這表明知識與權力相互滲透與影響有著必要性與合理性。可以看出,當科學派在社會中獲得了社會話語權之后,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知識的客觀性。科學派主將丁文江利用青年救亡圖存的迫切心情和對玄學的絕望與厭惡,篡改玄學派的人生觀理論,將玄學家與玄學謔稱為“玄學鬼”,更加鞏固了科學派在論戰中的優勢地位。而陳獨秀早期可以視作科學派陣營中的一員,在反對玄學派的態度上持有相同立場。鄧中夏甚至將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分為兩大陣營,“東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學的,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是真新的、科學的”[12]。唯物史觀派與科學派結成聯盟,借助科學的強勢地位擴大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影響力。但唯物史觀派同時也明確劃分了自身與科學派的界限,將論戰的方向引入到社會主義是科學的主題上來,使“科玄論戰”的內容得以深化。唯物史觀派在批判科玄兩派的過程中汲取了雙方的理論營養,尤其是在連同科學派痛擊玄學派之后,完成了對科學派的理論超越,才使得自己在論戰中后來居上,成為了最終的獲勝者。
(二)話語創新: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13]換言之,一種哲學要想在社會思想環境內落地生根,那么這種哲學同其受眾之間在思想基礎上要緊密貼合。因此,作為萌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想在中國實現大眾傳播,就必須完成其同中國本土文化的結合。但哲學大眾化的要旨絕非使大眾性的思想消解哲學的精神內核,而是使哲學精神為大眾所接受,哲學能夠滿足大眾的精神和生活需求[14]。在中國傳統儒家學說之中,儒學的存在是為現實服務的,體用合一是其重要特點。因此,中國人民的頭腦中一直帶有實用理性色彩的思想慣性。反觀西方傳統哲學,哲學以形而上的特點自居,總是高于生活,超越現實。即便是在反形而上的新哲學里,哲學也無法為現實服務。在個人命運與社會前途休戚相關的危機年代,面對傳統思想系統的崩裂以及風雨飄搖的國家,中國知識分子更需要找到一種變革社會有效途徑的思想理論。唯物史觀派在對科學派理論超越的論證中回到了現實,指出身、心、社會均有可預測的決定論與因果律。中國知識分子不愿再回到主張修心養性的宋學,也不愿再空喊漫無邊際的“自由意志”。經典馬克思主義話語主張使用階級話語,甚至認為愛國話語是能夠消磨階級話語的消極話語。但在論戰中,唯物史觀派卻將“救亡”的愛國精神融入對唯物史觀的宣傳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觀派摸清了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心理特點,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點找到了中華文化中與之相匹配的共性,將論戰方向引入到社會領域,指出了社會發展中的因果關系,從而加強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話語權。
四、“科玄論戰”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貢獻
“科玄論戰”作為1840 年以來中國思想發展的交匯期和分水嶺,在學理上促使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成為了繼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重要節點。具體來看,“科玄論戰”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現實,在現實的實踐中找到救國道路,并樹立馬克思主義人生觀。
(一)確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發展路向
唯物史觀派在“科玄論戰”中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分析與解決中國面臨的時代問題,使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迫切需要。其一,唯物史觀派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理論指導與實現路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效力得到了充分呈現。玄學派推崇孔孟之道與宋明理學,而科學派信奉唯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文化與科學雖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單靠文化和科學都無法完成“救亡”的使命,社會問題只能通過社會革命以達到更迭社會制度的方式才能得以化解。唯物史觀派通過對其科學觀、文化觀、歷史觀的初步闡明,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何以指導社會革命與解決社會問題,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中國現實的發展路向。其二,“科玄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開始將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論結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在“科玄論戰”之前,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多地宣傳唯物史觀,而很少提及辯證唯物主義。例如,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分為唯物史觀、經濟觀、社會主義理論三個主要部分。1922 年,陳獨秀的著作《馬克思學說》主要闡述了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理論。而在“科玄論戰”中,瞿秋白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中實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的歷史性結合,闡述了必然與偶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說明了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性與個人意志間的辯證關系。可以看出,“科玄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并非僅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一種哲學思想在傳介,而是切實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武器,充分展示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貢獻。
(二)實現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的發揚
人生觀問題不僅是“科玄論戰”的焦點,也是中國哲學關注的焦點。隨著“科玄論戰”的深入,中國思想界關于人生哲學的探討也進入了最為繁榮與鼎盛的時期。在新舊思想更替的關鍵年代,青年一代能否形成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新價值觀顯得尤為重要。唯物史觀派在論戰中圍繞“人生觀”問題對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進行闡述,旨在指導青年一代形成積極、樂觀、有前途的人生理念。唯物史觀在理論上的奠基,決定了唯物史觀派能在社會實踐中解決科玄兩派的人生觀理論沖突。玄學派抽取了人的社會性,強調要通過人的內省來達到自由意志的實現。而科學派則是完全否定人的個性與意識,在人生觀教育中否定社會實踐的作用。因此,科玄兩派脫離實踐來考察思維與意識的關系,均是二元論哲學的不同呈現。唯物史觀派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搭建了中國域境下人生觀理論的科學框架,論證出“主觀沒有絕對的能動性,而意志也不是絕對的自由,能動性和自由的活動最后被包攝在一定的客觀規律和科學法則中”[15]。具體來看,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教育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協調為最終目標[16],運用唯物史觀對人生理想、人生態度、人生價值進行闡釋與表達,即青年人應該擁有為實現國家解放、民族獨立的人生理想,積極向上、昂揚奮進的人生態度及勇擔社會責任的人生價值。經過“科玄論戰”的洗禮,一大批青年投身于革命救國的歷史洪流中。在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和革命運動的影響和塑造下,逐步形成堅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馬克思主義深烙于先進青年心中,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在中國逐步傳播開來。
(三)完成對中國道路的思想啟蒙
“科玄論戰”中,科玄兩派思想分歧的關鍵在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隔閡。玄學派主張運用“改造精神”以實行儒學式的立國之道,而科學派則認為應當采取“振興科學”以開啟歐洲式的發展之路。科玄兩派的思想都兼具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色彩,玄學派還帶有保守主義的成分,這些都與五四運動后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唯物的歷史觀”相斥,無法避免地脫離了“主體”與“實踐”,從而使科玄兩派提倡的救國道路成為空談。毋庸置疑,重視科學導向和強調精神修養使得愚昧盲從的中國在“重新發現人”的人本主義思想上得以深化,但科玄兩派都無法找到承載科學導向和精神改造的實踐主體,因而無法找到實現其目標的現實路徑。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使得中國思想界的關注點從“抽象的人”中脫嵌,開始關注“現實的人”,即“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7],“現實的人”根據社會需要與個人意圖能動地從事社會實踐活動。這一轉變使得中國思想界的主體性認知沖破了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間的徘徊,達成了目標與手段的辯證統一。中國的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人”,并思考如何達成“現實的人”的聯合,使中國之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都有了實踐主體基礎,自此馬克思主義完成了對中國思想界的重大啟蒙。經過“科玄論戰”,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深深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可以解決中國思想界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在論戰中實現了從理論引進到對中國道路進行價值規引的新高度[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