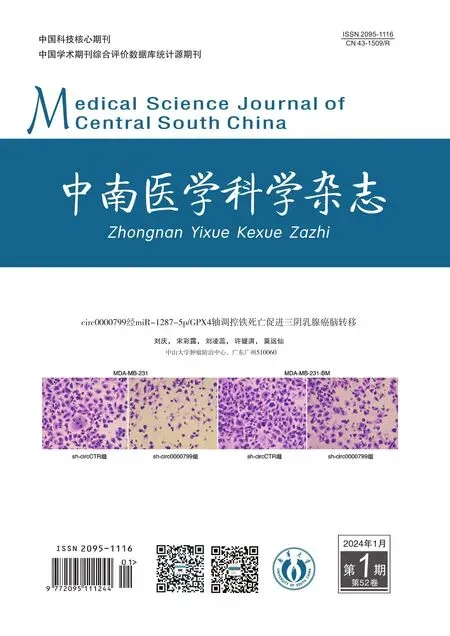髓系抑制性細胞調節炎癥性疾病中Th17應答的研究進展
賀烈娜, 何依芳, 何花, 熊靈鈴, 龍偉祥, 羅英, 雷愛華
南華大學衡陽醫學院 1.2019級醫學檢驗技術1班,2.2020級醫學檢驗技術1班,3.基礎醫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湖南衡陽421001
髓系抑制性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是一種不成熟的骨髓細胞的異質性群體,由組織損傷、炎癥以及癌癥等生物應激釋放[1]。Th17細胞作為CD4+T細胞亞群之一,通過分泌大量促炎細胞因子在炎癥反饋中發揮重要性能。研究發現,MDSC調控Th17應答的方式多種多樣,進而影響炎癥性疾病的進程[2]。本文綜述MDSC在不同疾病[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哮喘(bronchial asthma,BA)、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原發性膜性腎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和實驗性變態反應性腦脊髓炎(experimental allergic encephalomyelitis,EAE)]中對Th17細胞調節的作用及調控機制。
1 髓系抑制性細胞的概述
MDSC是在腫瘤、感染等病理條件下,髓系細胞分化發生障礙所產生的不同階段髓系細胞的集合。人MDSC定義為Lin-HLA-DR-CD33+或CD11b+CD14-CD33+細胞,進一步根據CD14和CD15的表達可分為CD14+CD15-的單核髓源性抑制細胞(monocyti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MDSC)和CD14-CD15+的多形核髓源性抑制細胞(polymorphonuclear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PMN-MDSC)兩類亞群[3]。MDSC可通過多種途徑發揮其免疫抑制功能。一方面,MDSC可通過干擾T細胞代謝來抑制T細胞的功能。例如,T細胞的激活與發揮功能需要精氨酸的參與,而MDSC通過高表達精氨酸酶-1(arginase-1,Arg-1)來抑制T細胞的活化。MDSC中STAT3的磷酸化可促進還原型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的兩個亞基gp47和gp91的表達,進而使MDSC釋放過氧亞硝酸鹽硝化T細胞受體,阻止T細胞活化[4]。另一方面,MDSC間接抑制機體免疫應答,如分泌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0等細胞因子誘導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擴增[5]。
2 Th17細胞
作為CD4+T細胞亞群,Th17細胞分泌的IL-17A~F、IL-22等促炎細胞因子在炎癥反饋中發揮重要性能。其中,IL-17可誘導C-X-C趨化因子配體(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CXCL)1、CXCL8、IL-8和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促進中性粒細胞和單核細胞在感染部位的募集和激活;IL-22通過刺激上皮細胞分泌趨化因子參與組織損傷和炎癥性疾病,發揮抗胞外菌和真菌的作用[6]。Th17細胞的產生和活化受多方面的調控。在炎癥中,IL-6促使致病性Th17細胞高度表達IL受體-23,并分泌大量IL-17和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來促進炎癥的發展,其中GM-CSF可通過作用于樹突狀細胞、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并促使其分泌IL-6和IL-23,而IL-6和IL-23又可作用于Th17細胞,這樣的循環周而復始,最終導致疾病惡化[7]。
3 MDSC在不同疾病中調節Th17細胞
3.1 在SLE中MDSC對Th17的調節作用
SLE是一種發病率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全身多器官慢性炎癥為主。研究發現,PMN-MDSC通過分泌大量的Arg-1使視黃酸相關孤兒受體γt表達上調,導致疾病惡化[8]。
研究表明,在狼瘡小鼠(MRL/lpr)模型中,MDSC表達的Arg-1通過上調miR-322-5p的表達來激活TGF-β/SMAD信號通路,進而使Th17細胞分化,致使小鼠出現脾腫大、腎臟損傷及蛋白尿[9]。使用抗IL-33單克隆抗體治療可緩解MRL/lpr小鼠炎癥[10],說明阻斷IL-33的MRL/lpr小鼠通過高表達MDSC和Tregs,使得Tregs與Th17細胞呈現免疫失調現象,進而使得Th17細胞及相關細胞因子水平降低,最終緩解狼瘡性腎病,其中也可能存在MDSC通過某種途徑抑制Th17細胞應答的機制,但其機制尚不明確。
綜上,MDSC在SLE中發揮雙重作用,MDSC分泌的Arg-1通過促進Th17的分化加重疾病嚴重程度;阻斷IL-33后,擴增的MDSC可能減少Th17細胞及減輕相關免疫應答緩解疾病。
3.2 在RA中MDSC對Th17的調節作用
RA是一種受遺傳、表觀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影響,表現為特征性的關節滑膜炎癥、骨損傷和全身炎癥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小鼠RA模型中,MDSC數量增多,并與Th17數量及IL-17A水平呈正相關;將MDSC從小鼠體內清除后,小鼠脾臟中Th17數量減少,IL-17A和IL-1β水平降低;而將MDSC過繼轉移到小鼠體內后,小鼠的炎癥程度加重,并伴隨血清IL-17A和IL-1β水平升高[11];提示MDSC能夠通過促進Th17細胞活化而加重炎癥進程。與之相反,向小鼠體內輸注包含總MDSC、PMN-MDSC、M-MDSC的MDSC后,小鼠體內脾組織中Th17細胞的數量明顯減少,而Treg的數量增加,關節炎癥得到顯著改善;而加入抗IL-10抗體后,MDSC抑制T細胞增殖的作用途徑被完全阻斷,而對Treg細胞起到了抑制其增殖的作用,關節炎癥及骨損傷未得到緩解[12];提示Th17增殖途徑被MDSC高表達的IL-10阻斷,從而改善關節炎癥。
3.3 在BA中MDSC對Th17的調節作用
BA是一種復雜的、異質性的慢性炎癥性氣道疾病,以氣道高反應性、炎癥細胞浸潤為特征。文獻報道,Th17分泌的細胞因子如IL-17A、IL-17F及IL-22可引起氣道中性粒細胞浸潤,誘導氣道黏膜細胞上皮化生,促進BA的發展進程[13]。MDSC在BA中發揮著復雜的作用。一方面,利用吉西他濱能夠顯著降低BA小鼠PMN-MDSC和Th17細胞的比例和數量,且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的表達顯著下調,BA小鼠的炎癥反應減輕[14]。另一方面,PMN-MDSC積聚在BA小鼠的肺部,與氣道炎癥呈負相關;而過繼轉移的PMN-MDSC可以抑制小鼠肺部的Th2型炎癥[15]。其中的相關機制暫未明確闡明,可能與建模方法和疾病微環境的不同有關。
可見,MDSC以不同的方式促進或抑制Th17的分化,從而在BA中發揮不同的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炎癥微環境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在不同病理情況下尋找與其相對應的靶向MDSC相關通路的機制尤為重要。
3.4 在IBD中MDSC對Th17的調節作用
IBD包含兩類疾病——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是環境、易感基因、免疫系統和微生物群之間一系列復雜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慢性炎癥,臨床表現以腹痛、腹瀉、血便、體質量減輕為主。作為CD4+T細胞亞群,Th17細胞在IBD中發揮雙重作用,研究發現,經葡聚糖硫酸鈉處理Argmye KO和對照小鼠11天后,Argmye KO小鼠相比于對照小鼠IL-17A水平下降,IL-17F表達增加,而小鼠主要表現為體質量顯著降低,結腸組織學染色切片中顯示更多的免疫細胞浸潤和杯狀細胞損耗,說明IL-17F發揮促炎作用[16];然而,將MDSC過繼轉移至Argmye KO小鼠體內后,IL-17A表達增加,IL-17F表達下降,小鼠出現體質量下降趨勢減緩及腸道炎癥細胞浸潤減少,提示IL-17A能有效減輕炎癥,這可能與IL-17A具有促進腸道黏膜修復和維持腸上皮完整性的作用有關[16]。
研究發現,與IL10-/-小鼠相比,IL10-/-IL17A-/-小鼠體內MDSC顯著增加、iNOS表達上調、體質量減輕、結腸杯狀細胞數量減少及出現炎癥細胞浸潤,而IL10-/-IL17A-/-Nos2-/-小鼠卻無上述表現,提示產生一氧化氮的MDSC可促進IBD的進展,可能的機制是Th17分泌的IL-17F依賴MDSC表達的iNOS,從而發揮促炎作用[17]。而SMM-189作為結腸固有層淋巴細胞中大麻素受體2型(cannabinoid receptor 2,CB2)的反向激動劑可通過誘導CB2的表達來增加MDSC的數量,進而抑制Th17細胞及中性粒細胞的活化,發揮緩解結腸炎的作用,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18]。
因此,MDSC在IBD中發揮雙重作用。MDSC分泌的Arg-1通過促進Th17細胞增殖并表達大量IL-17A發揮緩解IBD的作用;PMN-MDSC可能會抑制Th17細胞增殖。
3.5 在IMN中MDSC對Th17的調節作用
IMN是能引起腎組織固有功能病變的一種疾病,其病理表現是補體C3和lgG球蛋白累積的免疫復合物沉積所導致的腎臟上皮細胞增生。在狼瘡性腎炎小鼠中,MDSC分泌的IL-1β可促使Th17細胞生長發育加快,進而加重病程,表現為腎小球腎炎且腎臟出現明顯的組織損傷[19]。原發性膜性腎病患者血清中IL-17A和抗磷脂酶A2受體(anti-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抗PLA2R)水平與疾病活動呈正相關,同時,患者體內存在較高水平的IL-6、IL-10可促使MDSC產生Arg-1,進而使得Th17細胞產生高水平的IL-17A,與此同時,患者血清中抗PLA2R水平也隨之升高。而精氨酸酶受到抑制時,IL-17A和抗PLA2R水平下降,說明MDSC分泌的Arg-1可增強Th17細胞的免疫應答并促使其分泌IL-17A,進而促進疾病發展[20]。
3.6 在EAE中MDSC對Th17的調節作用
EAE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以特異性致敏的CD4+T細胞介導為主。IL-17A能夠破壞血腦屏障并促進神經炎癥,是參與此疾病的關鍵細胞因子。在EAE病程中,MDSC可通過分泌IL-1β和TGF-β促進CD4+T細胞分化為Th17,其中TGF-β在促進Th17分化和活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TGF-β信號的負調節因子Smad是Th17相關的miRNA-181c的潛在功能靶點,而miR-181c基因敲除通過破壞TGF-β誘導的Smad依賴性信號通路,抑制CD4+T細胞向Th17分化[21]。PMN-MDSC在EAE小鼠脾臟中顯著積累,促進疾病病程;但從自身免疫環境中分離的PMN-MDSC過繼轉移可顯著減少自身反應性T細胞的擴增,抑制致病性Th1和Th17免疫應答,從而有效抑制EAE的發展[22]。同時,骨髓內的PMN-MDSC是否具有炎癥或抗炎作用仍有待確定。
4 總結與展望
MDSC在Th17細胞參與的炎癥性疾病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具有強大的免疫抑制活性的MDSC可通過多種途徑,影響Th17的增殖與分化,進而在SLE、原發性膜性腎病等疾病中改變其病理進程。其中,在SLE中,MDSC通過miR-322-5p/TGF-β/SMAD信號通路來促進SLE患者體內Th17分化,從而加重疾病進程。但擴增的MDSC也可能在阻斷IL-33后通過減少Th17細胞,從而減輕相關免疫應答緩解SLE。在RA中,MDSC能夠通過頻率依賴或通過IL-1β依賴方式來調節Th17細胞以促進其疾病進程,而MDSC也可通過高表達IL-10,抑制Th17增殖,從而改善關節炎癥。
綜上,MDSC與Th17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較為復雜。在不同炎癥性疾病中,MDSC與Th17之間的調控作用不盡相同。深入研究MDSC與Th17之間的調控機制可能為炎癥性疾病的治療提供新策略,且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