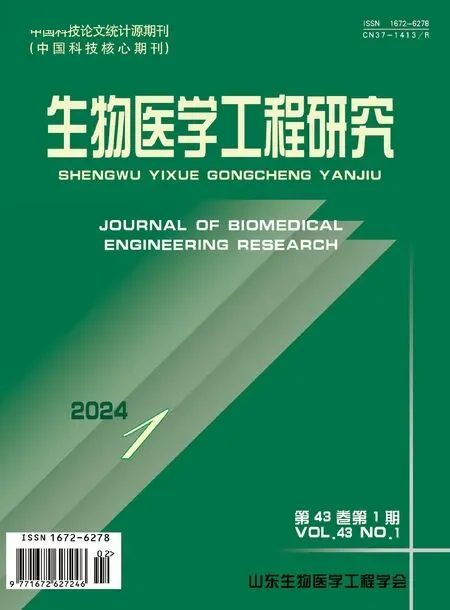經(jīng)顱磁刺激在腦卒中運動功能障礙康復(fù)中的研究進展*
黃蓮池,權(quán)璐,文斌,韋思宏,喬晉△,徐進△
(1.西安交通大學(xué) 生物醫(yī)學(xué)信息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生命科學(xué)與技術(shù)學(xué)院健康與康復(fù)科學(xué)研究所,西安 710049;2.四川數(shù)字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發(fā)展研究院,成都 610081;3.西安交通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康復(fù)科,西安 710061;)
0 引言
腦卒中是一種高發(fā)病率、高致死、致殘率的急性腦血管疾病,根據(jù)致病原因可分為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自1990年到2019年,全球腦卒中發(fā)病率和死亡率不斷上升[1],而在中國總體卒中發(fā)生風(fēng)險為39.9%[2]。其主要的后遺癥之一為運動功能障礙,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同時也給社會帶來經(jīng)濟負擔。因此,高效的運動康復(fù)治療方案至關(guān)重要。
經(jīng)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是一種無創(chuàng)、低痛的非侵入性電生理技術(shù),在1985年由Barker等[3]提出,對運動皮層尤其是深層神經(jīng)元的刺激,在較低的強度下相對電刺激,更容易實現(xiàn)。近年來,TMS在腦卒中運動康復(fù)領(lǐng)域作為評估指標或干預(yù)手段已得到了廣泛應(yīng)用,本文將重點圍繞近年TMS在功能評估、干預(yù)治療和恢復(fù)預(yù)測中的作用研究進行總結(jié),為后續(xù)相關(guān)研究提供依據(jù)和指導(dǎo)。
1 基于TMS的運動功能評估
在腦卒中運動功能評估方面,臨床評估主流手段仍是評估量表,包括美國國立衛(wèi)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等綜合量表;Ashworth痙攣量表、Brunnstrom偏癱量表、Fugl-Meyer量表、ARAT量表和Berg平衡量表等專項量表[4]。但臨床量表具有一些難以克服的缺點:首先,量表得分嚴重依賴于評估人員的專業(yè)程度和熟練程度,不同評估人員的具體判斷標準可能具有差異;其次,每種量表都有不同的評估側(cè)重點,臨床醫(yī)師和研究人員根據(jù)需要篩選所需量表并綜合分析;最后,量表是一種側(cè)重于外在功能表現(xiàn)的宏觀評估手段,難以表現(xiàn)一些更潛在的本質(zhì)性的功能變化。
因此,神經(jīng)信息的結(jié)構(gòu)成像和功能成像等客觀方法被越來越多地用于卒中患者的運動功能評估,例如提供結(jié)構(gòu)信息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和提供功能信息的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m, EEG)、肌電圖(electromyogram, EMG)以及基于TMS的評估指標,重要的是研究運動恢復(fù)的機制、減少現(xiàn)有評估方法無法解釋的變異部分[5]。
1.1 TMS指標
一定強度的TMS作用在運動皮層區(qū)域,皮層神經(jīng)元產(chǎn)生運動電位經(jīng)脊髓傳入對應(yīng)控制的效應(yīng)肌肉,從而產(chǎn)生可以由EMG記錄或肉眼觀察到的肌肉收縮,稱為運動誘發(fā)電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P)。在皮層脊髓束嚴重受損的患者中無法觀察到有效的MEP,可稱為MEP缺失。而在靜息期間能引起MEP的TMS刺激強度稱為靜息運動閾值(relaxed motor threshold, RMT),在任務(wù)期間能引起MEP的TMS強度稱為動作運動閾值(active motor threshold, AMT)。不同刺激間間隔(intra stimulation interval, ISI)的成對脈沖可得到皮層抑制與促進作用的測量指標,例如反映運動皮層興奮性的短間隔皮質(zhì)內(nèi)抑制(short interval inhibition and facilitation, SICI)、皮質(zhì)內(nèi)易化(intracortical facilitation, ICF)、短間隔皮質(zhì)內(nèi)促進(short interval intracortical facilitation, SICF)等,在國際臨床神經(jīng)生理學(xué)聯(lián)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IFCN)委員會的更新報告中對TMS的效用指標進行了詳細介紹[6]。
1.2 基于靜息態(tài)和任務(wù)態(tài)TMS的運動功能評估
不同的運動狀態(tài)會引起不同的皮質(zhì)脊髓激活,從而影響基于TMS測量的神經(jīng)生理指標。Taube等[7]發(fā)現(xiàn)在肌肉收縮期間采用TMS測量SICI比靜息期間更能反映爆發(fā)訓(xùn)練任務(wù)前后差異。因此更建議在運動任務(wù)期間而不是靜息期間進行神經(jīng)生理指標測量。Ding等[8]發(fā)現(xiàn)盡管慢性卒中患者靜息狀態(tài)下的SICI恢復(fù)到正常水平,但任務(wù)狀態(tài)下的SICI顯示出持續(xù)性的損傷,說明任務(wù)狀態(tài)下的SICI相對于功能相對完好的慢性期患者具有更高的敏感度。Hasegawa等[9]的研究發(fā)現(xiàn)運動想象任務(wù)期間由TMS引起的MEP幅度顯著高于靜息期間TMS引起的MEP幅度。Moriuchi等[10]研究發(fā)現(xiàn)在運動想象(motor imaginary, MI)、運動觀察(action observation, AO),視覺模擬量表(VAS)評分與MEP存在顯著正相關(guān),提示VAS可能反應(yīng)出MI+AO期間皮質(zhì)脊髓的興奮性,尤其是在復(fù)雜的MI任務(wù)中。對于皮層間連通性,任務(wù)態(tài)TMS評估同樣具有更高的敏感性[11]。
另一方面,在肌肉動態(tài)收縮期間,在運動相關(guān)皮層區(qū)域施加的TMS干擾了運動執(zhí)行過程中的神經(jīng)處理,被認為是“虛擬病變”,從而對運動性能產(chǎn)生影響。因此,可將真實刺激下的運動學(xué)特征(效率、準確率、平滑度和速度)相對于偽刺激下的運動學(xué)特征歸一化,研究不同人群對TMS引發(fā)的“虛擬病變”的敏感性[12]。
下肢肌肉的建議刺激狀態(tài)與上肢相反,在Alder等[13]對PAS調(diào)節(jié)下肢皮質(zhì)運動興奮性的系統(tǒng)回顧中得出,相比于行走狀態(tài),靜息狀態(tài)或輕微激活狀態(tài)下的肌肉對應(yīng)皮層受到PAS時,可觀察到皮質(zhì)運動興奮性(corticomotor excitability, CME)明顯提升,可能的解釋是在運動過程中軀體感覺輸入存在門控,因此行走時的體感誘發(fā)電位更小。
1.3 TMS-EEG的聯(lián)合評估
評估運動系統(tǒng)完整性的一個創(chuàng)新研究是將TMS與EEG結(jié)合,用EEG設(shè)備同步記錄TMS誘發(fā)的腦電信號,可獲得TMS誘發(fā)EEG電位(TMS-evoked EEG potential, TEPs),是在TMS刺激后產(chǎn)生的正(P)或負(N)的波形偏轉(zhuǎn),根據(jù)振幅潛伏期可分為不同的成分,例如在M1產(chǎn)生的N15、P30、N45、N100等[14]。其中,N45、N100與GABA能皮質(zhì)內(nèi)抑制存在密切聯(lián)系[15],具有分子層面的可解釋性。TMS-EEG方法的優(yōu)點在于不依賴于外周神經(jīng)通路的完整性,對于運動閾值下強度的刺激仍能產(chǎn)生反應(yīng)。此外,TMS-EEG還可以描述受刺激部位到遠處腦區(qū)的更直接的因果聯(lián)系,為分析不同腦區(qū)之間的連通性提供了新方法。TMS-EEG是大腦信號、偽跡和噪聲的線性組合[16],偽跡包括TMS誘發(fā)偽跡、外周誘發(fā)電位(peripherally evoked potentials, PEPs)等。Gordon等[17]提出了可有效去除PEP的優(yōu)化偽方法,可以獲得TMS直接激活皮層的真實腦電反應(yīng),且證明了TMS對體感輸入調(diào)節(jié)皮質(zhì)脊髓束的興奮性不敏感。
在卒中運動康復(fù)研究方面,Bai等[18]首次將TMS-EEG和基于運動誘發(fā)電位的綜合結(jié)果用于慢性卒中患者的皮層內(nèi)和皮層間網(wǎng)絡(luò)神經(jīng)生理學(xué)分析,發(fā)現(xiàn)同側(cè)TMS誘發(fā)的N100成分波幅降低,與同側(cè)RMT和MEP波幅顯著相關(guān)。同側(cè)M1表現(xiàn)出GABA-B受體介導(dǎo)的皮層內(nèi)抑制受損,特點是MEP持續(xù)時間縮短且幅度縮小。研究結(jié)果說明TMS誘發(fā)的N100可能是卒中恢復(fù)的一個有效標志。
2 基于TMS的運動功能康復(fù)方案設(shè)計
針對卒中患者的運動功能障礙,通常采用藥物治療、物理因子療法、運動療法和作業(yè)療法等[19]。隨著近年來TMS的推廣應(yīng)用,其在功能康復(fù)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康復(fù)方案的設(shè)計主要包括TMS的干預(yù)時間、干預(yù)腦區(qū)和干預(yù)模式等選擇,以及偽刺激設(shè)計方案。
2.1 干預(yù)時間
設(shè)計干預(yù)方案最關(guān)鍵的是確定卒中后康復(fù)干預(yù)的最佳時間。盡管卒中后數(shù)年仍有可能發(fā)生行為變化,但大多數(shù)人的行為恢復(fù)和快速變化發(fā)生在中風(fēng)后的最初幾周到幾個月內(nèi)[20]。因此,腦卒中恢復(fù)與康復(fù)圓桌會議(stroke recovery and rehabilitation roundtable, SRRR)建議相關(guān)研究提供患者患病時間、干預(yù)開始和結(jié)束時間等關(guān)鍵時間數(shù)據(jù)與核心測量指標[21];并制定了腦卒中恢復(fù)階段的定義標準:卒中發(fā)生后24 h以內(nèi)為超急性期、1~7 d為急性、7 d~3個月內(nèi)為亞急性早期、3~6個月為亞急性晚期、6個月后為慢性期[20]。急性期的干預(yù)在實踐上存在困難,因此,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亞急性期或慢性期。
2.2 干預(yù)腦區(qū)
最新的rTMS治療應(yīng)用循證指南顯示,在對側(cè)M1區(qū)域施加LF-rTMS對于亞急性期的手功能恢復(fù)是A級證據(jù)(明確有效),在同側(cè)M1區(qū)域施加HF-rTMS是B級證據(jù)(基本有效),慢性期間在對側(cè)M1區(qū)域施加LF-rTMS對手功能恢復(fù)是C級證據(jù)(可能有效)[22]。
盡管多數(shù)卒中后運動功能康復(fù)的研究關(guān)注M1區(qū)域,但TMS改善運動功能的可刺激區(qū)域并不局限于大腦皮層M1區(qū)。Hensel等[12]對對側(cè)和同側(cè)前頂內(nèi)溝(ant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 aIPS)的刺激效果與對側(cè)M1刺激效果進行對比。發(fā)現(xiàn)半球間aIPS連接更強的患者,在rTMS刺激aIPS時,抓舉準確性高;半球間M連接更強的患者在rTMS刺激M1時,抓舉速度下降更多。說明對不同區(qū)域施加rTMS對運動學(xué)特征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取決于臨床損傷和雙側(cè)M1和aIPS的半球間連接。結(jié)果證明了aIPS同樣參與上肢精細運動控制,為rTMS的干預(yù)方案設(shè)計提供新的思路。而對于嚴重損傷患者,高級運動區(qū)可能是比M1更好的調(diào)控靶點,例如運動前區(qū)(premotor area, PMA)在卒中后可能代償M1的功能,且在TMS影響下招募更多腦區(qū)參與運動功能重塑[23]。
2.3 干預(yù)模式
TMS按照脈沖產(chǎn)生方式可分為單脈沖經(jīng)顱磁刺激(single TMS, sTMS)和重復(fù)經(jīng)顱磁刺激(repeated TMS, rTMS),sTMS多用于檢查神經(jīng)功能狀態(tài)而rTMS更多的用于神經(jīng)功能的調(diào)節(jié)。在rTMS中,θ爆發(fā)式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 TBS)和配對聯(lián)合刺激(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 PAS)在近年來受到更多的關(guān)注。
2.3.1θ爆發(fā)式刺激 TBS刺激模式是一種簇狀節(jié)律式刺激,進一步可分為連續(xù)性TBS(continuous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cTBS)抑制皮層功能和間歇性TBS(intermittent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iTBS)興奮皮層功能[24]。相比于頻率固定的rTMS,TBS具有刺激時間短、不良反應(yīng)(頭皮疼痛)強度更低、癲癇發(fā)作風(fēng)險更低等優(yōu)點,將大大提高患者參與治療的依從性[25]。Ding等[26]首次采用TMS-EEG研究iTBS后的即時神經(jīng)適應(yīng),發(fā)現(xiàn)iTBS可以提高卒中后偏癱側(cè)運動皮層的固有頻率,提供了iTBS促進卒中患者上肢功能相關(guān)的固有頻率恢復(fù)的證據(jù)。Bai等[27]研究發(fā)現(xiàn)iTBS可促進慢性卒中患者皮層內(nèi)興奮,表現(xiàn)為iTBS相比于偽刺激有效增強了病灶同側(cè)MEP幅度和位于iM1的TEP的P30幅度,但對同側(cè)ICF、cSP和SICI無顯著調(diào)節(jié)作用。
2.3.2配對聯(lián)合刺激 PAS是一種基于Hebbian突觸可塑性原則的雙目標外周和中樞刺激方案,因此也可稱為Hebbian型刺激(hebbian type stimulation, HTS)。Revill等[28]將M1傳入刺激和M1活動按照時間關(guān)系配對的HTS結(jié)合運動訓(xùn)練的康復(fù)效果和單純運動訓(xùn)練的效果進行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兩組患者均表現(xiàn)出功能的恢復(fù),但只有當運動訓(xùn)練與HTS結(jié)合時,功能恢復(fù)才能隨著時間推移而保持,并與手部運動時血氧依賴水平(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BOLD)所反映的M1功能可塑性相關(guān)。說明HTS有助于保持M1與手部運動相關(guān)的功能恢復(fù)效果。Rosso等[29]研究發(fā)現(xiàn),相比于偽刺激,小腦-M1的PAS能有效改善手部靈活性,但不能改善握力,這種改善與同側(cè)初級運動皮層的激活增加有關(guān)。
在PAS基礎(chǔ)上,兩個線圈均對皮層進行刺激為皮層-皮層配對聯(lián)想刺激(cortico-cortical paired associative stimulation, ccPAS)。相比與單脈沖TMS,ccPAS具有時空特異性調(diào)節(jié)皮層連通性的優(yōu)勢[30]。Hooyman等[31]研究發(fā)現(xiàn),ccPAS可提高前額葉和運動皮層區(qū)域靜息態(tài)功能連接性,得出了ccPAS調(diào)節(jié)卒中患者運動功能的另一可能機制。
2.4 偽刺激方案
由于TMS在執(zhí)行過程中會在刺激部位產(chǎn)生輕微的疼痛感,因此如何設(shè)計偽刺激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常用的偽刺激設(shè)計方法包括:偽線圈、傾斜線圈、線圈遠離頭皮、強度設(shè)置為較低的運動閾值相對強度或設(shè)置為0[22]。但以低強度刺激作為偽刺激設(shè)計方案,可能仍會對刺激部位產(chǎn)生影響,進而影響對照組的刺激后評估指標[32],無法反映出方案設(shè)計的真實效果。
3 基于TMS的運動功能康復(fù)效果預(yù)測
3.1 功能康復(fù)預(yù)測模型
建立生理指標與初始損傷、康復(fù)的關(guān)系,對建立卒中患者運動功能的客觀評估體系和個性化康復(fù)方案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判斷個體康復(fù)潛能是否完全激發(fā),以及如何分配康復(fù)資源。
在卒中后早期進行評估具有好的康復(fù)預(yù)測價值,但相比于后期評估具有更高的預(yù)測難度。臨床評估模型中,自主肩外展(shoulder abduction, SA)和手指外展(finger extension, FE)的SAFE分數(shù)被證明是卒中早期的康復(fù)預(yù)測指標,SAFE和TMS、MRI指標結(jié)合的PREP模型也適用于卒中后72 h內(nèi)評估的恢復(fù)預(yù)測[33-34],可認為是多模態(tài)卒中后運動功能恢復(fù)預(yù)測模型的初步嘗試。改進的PREP2模型也在提出后得到Smith等[35]的驗證。該算法在基線時做出的預(yù)測對80%的被試2年后的恢復(fù)情況預(yù)測正確,83%的被試在3個月到2年期間的PREP2 上肢結(jié)果類別保持穩(wěn)定。該模型有預(yù)測長期病情改善、穩(wěn)定或惡化的潛力。
盡管如此,TMS引起的MEP對卒中后急性期上肢運動功能恢復(fù)預(yù)測的附加價值仍存在爭議。支持MEP預(yù)后預(yù)測價值的研究發(fā)現(xiàn),MEP+比MEP-的患者恢復(fù)效果好,而CCT正常的患者比CCT延遲的患者恢復(fù)效果更好[36]。但Hoonhorst等[37]研究發(fā)現(xiàn),在卒中48 h內(nèi)進行評估并預(yù)測卒中后6個月的恢復(fù)效果,TMS-MEP的引入未顯著提升預(yù)測準確率,而在11 d進行評估預(yù)測,結(jié)合臨床指標的模型比單獨的TMS模型具有更高的預(yù)測準確率。這說明臨床指標仍然具有較高的預(yù)測價值,因此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神經(jīng)生理指標相比于臨床評估指標的預(yù)測價值,并改進現(xiàn)有生理指標評估方法,設(shè)計出對急性患者更準確、更敏感的預(yù)測模型。
此外,預(yù)測模型的研究更多地采用多模態(tài)方法,結(jié)合多種神經(jīng)成像方法的優(yōu)勢,綜合多角度生理信息進行預(yù)測。Kumar等[38]將TMS和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結(jié)合,采用多變量邏輯回歸分析檢驗對急性腦缺血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復(fù)預(yù)測的準確性,對于卒中后3個月上肢運動結(jié)果,結(jié)合臨床量表、TMS指標和DIT指標具有最高的預(yù)測準確率,總體準確率為94.4%,敏感度94.9%,特異性95.8%。
3.2 個性化預(yù)測模型
恢復(fù)效果的個體差異給運動功能康復(fù)的預(yù)測帶來困難,為提高治療效果,需針對每個患者的具體情況量身定制治療方案,但對個性化運動恢復(fù)的過程、程度及其確切的神經(jīng)生理機制缺乏了解。因此,需找到準確、敏感的生物標記物來表征不同患者群的運動功能康復(fù)潛力,進一步完善康復(fù)預(yù)測模型,從而個性化指導(dǎo)康復(fù)訓(xùn)練方案的設(shè)計和調(diào)整。
從通用模型到個性化模型,要經(jīng)歷患者亞群的區(qū)分和針對不同特征的亞群建立局部模型。運動功能表現(xiàn)情況可作為劃分患者亞組的標準之一[39]。MEP狀態(tài)可作為初步的評估患者CST完整性的指標,獲得一致的MEP視為MEP+,否則視為MEP-。因此可對基于MEP劃分的患者亞組進行其他生理指標的研究[40]。而對于無明確的關(guān)于功能損傷分級的臨床共識的量表,可利用聚類分析進行亞群分類。Tscherpel等[41]為確定組間差異是否取決于初始運動障礙的嚴重程度,采用2維k-means聚類將亞急性早期患者通過ARAT分數(shù)和健患側(cè)相對握力評估分為輕度損傷、中度損傷和重度損傷三個亞群,表現(xiàn)出不同的TEP模式。
在個性化模型建立方面,Hussain等[42]利用EEG和MEP信號建立了基于線性判別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可個性化區(qū)分健康被試M1皮層的高興奮狀態(tài)和低興奮狀態(tài)的單被試解碼模型,模型對80%的被試成功判別了高興奮狀態(tài)和低興奮狀態(tài),在90%的被試中高興奮狀態(tài)下引起的MEP顯著大于低興奮狀態(tài)下的MEP。個性化分類器在不同參與者之間不能通用,表明健康個體具有獨特的大腦活動模式,為后續(xù)卒中患者的個性化預(yù)測模型和個性化神經(jīng)調(diào)控的應(yīng)用提供支持。
由于多維度模型能提供多角度、更全面的信息,更能表現(xiàn)出模型的個性化因素。Dimyan等[43]采用多維度評估方法(FMA、WMFT分數(shù)、ARAT分數(shù)、SIS分數(shù)、MRI、TMS、運動學(xué)參數(shù)、加速度計和基因組測試)在干預(yù)前進行評估,對訓(xùn)練的康復(fù)收益進行預(yù)測。
4 總結(jié)與展望
基于TMS的神經(jīng)生理評估指標具有簡單、直觀和可解釋等優(yōu)點,在皮層與外周神經(jīng)興奮性、可塑性評估方面已被廣泛應(yīng)用。而TMS-EEG作為一種新的皮層神經(jīng)功能探查方法,具有良好的應(yīng)用前景。TMS在卒中運動功能康復(fù)中也取得了廣泛應(yīng)用,對于一些簡單模式的TMS已經(jīng)形成了臨床專家共識,但基于客觀評估指標的TMS康復(fù)效果、TMS對不同腦區(qū)的干預(yù)效果等方面仍需進一步研究。而在恢復(fù)預(yù)測方面,現(xiàn)有研究結(jié)果表明了TMS與臨床指標的關(guān)聯(lián)、在康復(fù)預(yù)測方面的前景,以及設(shè)計個性化診療方案的可行性。未來仍需要大樣本研究提供TMS在運動功能康復(fù)方面的依據(jù)。并且未來研究趨向于臨床量表、結(jié)構(gòu)成像、功能成像等多模態(tài)結(jié)合,建立恢復(fù)預(yù)測模型,并探索建立個性化診療方案和預(yù)測模型的康復(fù)系統(tǒng)。功能康復(fù)生理機制的共性和個性仍需進一步探索,為形成多種模式TMS康復(fù)應(yīng)用的行業(yè)共識,以及建立個性化評估模型、個性化診療方案和個性化預(yù)測模型的全流程康復(fù)診療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