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敘事視域下《本巴》中的生命特質(zhì)
李婧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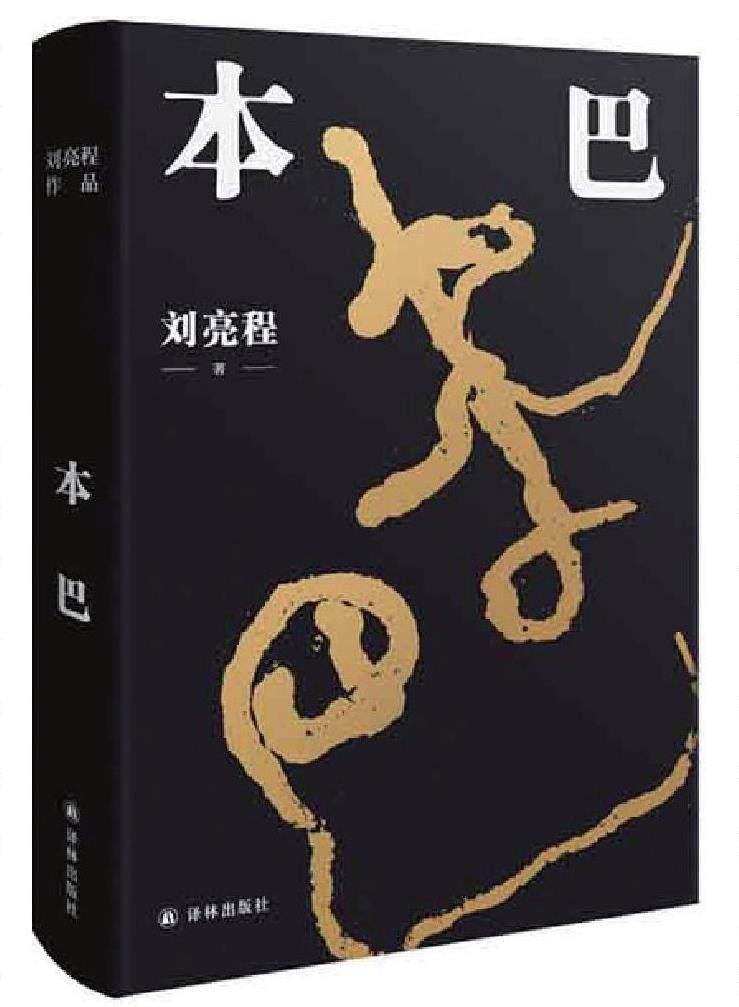
摘要:《本巴》是作家劉亮程摘取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詩《江格爾》中的史詩元素所再創(chuàng)造的文學文本。小說創(chuàng)造了青春永駐的本巴國度,講述了一個關(guān)于孩童與夢的故事,探討了民族與永恒的關(guān)系。《本巴》中具備宏大敘事的特點,這與它源自史詩相關(guān),作者如夢囈一般的文字貫穿著神性與人性的敘事脈絡(luò),勾連起一個宏大的世界觀,具體表現(xiàn)為時間與空間的原始世界的構(gòu)建、半人半神式的英雄形象刻畫以及重返童年時代,尋找童年力量,叩問生命本質(zhì)。
關(guān)鍵詞:宏大敘事? 神性書寫? 半人半神? 童年力量
《本巴》是作家劉亮程根據(jù)少數(shù)民族史詩《江格爾》所再創(chuàng)造的小說文本,由于它源自史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著天然的史詩性和神性書寫的特征,從而具備了宏大敘事的特點。關(guān)于宏大敘事這一概念,利奧塔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的話語體系依賴著一種合法化敘事,這種合法化敘事被看成一種宏大敘事,也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的元敘事,將人們在這樣一種元敘事下所進行的一切精神活動與物質(zhì)活動都視為正確的、合理的。“大致看來,宏大敘事本意是一種‘完整的敘事,用麥吉爾的話說,就是無所不包的敘述,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tǒng)一性。”本文主要借助宏大敘事的相關(guān)理論對《本巴》進行分析。在《本巴》中,其宏大敘事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通過對原始初民世界的構(gòu)造所呈現(xiàn)出來的一種歷史政治的構(gòu)想,塑造了典型的英雄形象,以及站在當下回望童年的原始記憶,去探尋關(guān)于生命本質(zhì)的推演。
完整的世界創(chuàng)設(shè)
在劉亮程的筆下,本巴世界是一個所有人都停駐在25歲美好年華的世界,無論是本巴民族的締造者江格爾還是被江格爾一手從童年世界拉到25歲的阿蓋夫人,本巴中的每一個人都停駐在了最美好的年歲中,哪怕是不愿長大的洪古爾也以自己最舒服的狀態(tài)生活著。這就打造了一個關(guān)于時間秩序的建立,時間的建立帶來了四季分明,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最基本的運作方式。“當人類對世界有了時間的劃分、季節(jié)的變化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時間狀態(tài)的形成,意味著人類由玄學的迷茫進入理性的清朗。” 時間秩序的建立意味著規(guī)則在逐步確定,本巴草原從原始的自然形態(tài)開始向社會文明的方向過渡。
除了建立時間,《本巴》中創(chuàng)立了基本的地理空間,草原、雪域、荒原、高山打造了一個基本的地域空間。這里關(guān)于地域空間的構(gòu)想是恢宏的,“碧綠的草地鋪展向遠處,閃著一帶水光的和布河,蜿蜒地流過草原,連接起馬鞍形的賽爾山和公主般俊俏的哈同山,更遠處是頂著天的阿爾泰山”。如此這般,一個美好的、壯麗的本巴國度在劉亮程詩意的文字描述下被勾勒出來。
在時間與地理空間創(chuàng)設(shè)完畢之后,接下來就是政治秩序的創(chuàng)設(shè)。本巴民族是一個由恥辱走向興盛的民族,這得益于江格爾的領(lǐng)導,因此《本巴》中有一個完整的政權(quán)建立的過程。江格爾的父親——烏仲汗在晚年日日醉酒,歲月漸漸磨平了他們的力量,導致了莽古斯的侵入。江格爾的誕生挽救了這一搖搖欲墜的民族,他在睡夢之中殺敵,并用雞鳴封住了夢的入口,以保證本巴王國的和諧安寧。這個由江格爾作為汗王,此外還有大臣、勇士、預言者等人物形象所構(gòu)建的一個國家關(guān)于領(lǐng)導階層的完備體系制度。
最后,《本巴》中創(chuàng)設(shè)了一個扭轉(zhuǎn)故事走向的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整本書敘事的重點,即拉瑪汗國哈日王的宣戰(zhàn)以及本巴王國洪古爾的應戰(zhàn)。通過洪古爾的“戰(zhàn)斗——失敗——被俘——營救”勾連起整個故事的全貌,彰顯了英雄果敢堅毅的性格特點以及忠于國家、忠于人民的美好品質(zhì)。因此,《本巴》中這種完整的敘事過程是符合宏大敘事的基本特征的。
神圣的英雄書寫
英雄形象大多是世界各族史詩文學的塑造核心,由于《本巴》是以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為原型進行的再創(chuàng)造文學文本,因此其中的英雄形象在延續(xù)了《江格爾》中的描寫之后,作者又對其賦予了嶄新的英雄韻味。
絕對權(quán)威——江格爾。江格爾的英雄形象是帶有神跡色彩的,他的神性體現(xiàn)在他同本巴草原一同誕生,英雄與日月共生,成長于世界的初始形態(tài),或者說他本身就作為世界初始形態(tài)的一部分,帶有著強烈的神命意志,他注定就會成為本巴的英雄和領(lǐng)導者。此外,他的神性是帶著使命感的,他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擔負著帶領(lǐng)本巴民族擺脫被莽古斯奴役的命運,打贏反侵略、反奴役的戰(zhàn)爭以及重振本巴民族的輝煌。“話說江格爾一出生,便將吉祥平安還給了本巴。” 江格爾可以在睡夢之中殺死敵人,讓敵人永遠在噩夢中受到折磨,讓自己的民族永遠沉浸在25歲的美夢之中。
英雄往往需要事跡來佐證自己之所以能成為英雄的合理性,江格爾的英雄合理性體現(xiàn)在他的神權(quán)任命、崇高武力以及臣民的臣服。由于他的神權(quán)任命以及崇高的武力決定了臣民的臣服,這種臣服性又進而確立了江格爾的絕對權(quán)威。因此,江格爾在本巴世界是絕對的話語領(lǐng)導者,他擁有著一種絕對的話語權(quán)力,這種絕對的話語權(quán)力是他擁有絕對權(quán)威的旁證。
半人半神——洪古爾和赫蘭。洪古爾相較于江格爾,他更具有人性的色彩,體現(xiàn)為原始初民將對英雄的美好愿景賦予在洪古爾的身上。洪古爾是具有人性的神化英雄,他的人性體現(xiàn)為他那不愿長大的塵世愿望,對阿蓋夫人美貌的向往以及對乳汁的貪戀,并且在出征——失敗——被俘的這個過程之中達到了巔峰,在喝下奶茶后瞬間變老,逃離了25歲的本巴美夢之后進一步得到了升華。洪古爾的出現(xiàn)證明了英雄可以失敗、可以被俘、可以有孩童般的惡劣,但同時他具備著勇氣,在所有人都不出去迎戰(zhàn)莽古斯的挑戰(zhàn)時,洪古爾奉命出征。在這一刻,他的英雄形象瞬間躍然紙上。
洪古爾在本巴王國是一個獨特的設(shè)定,他在別人處于青春年華時,自己始終處于少兒時期;同樣,他也是本巴王國里第一位走向老年的。除了在他的身上閃耀著人性的光輝之外,還體現(xiàn)著關(guān)于時間與生命的悲歌。劉亮程把關(guān)于時間與生命的思考傾覆在洪古爾的身上,人們對于衰老的恐懼源于對死亡的恐懼,源于對死亡之后的這種未知的恐懼。因此本巴國便人人都停留在了青春,可是這種青春漫長得令人絕望。唯有用生命的流逝去感知每一寸時光的變化,才能賦予生命最大的意義,這是歲月給予我們的恩賜。
赫蘭與洪古爾一樣,他的英雄形象帶有很強烈的人性色彩。首先是他出生以及出征不是為了家國大義,而是為了拯救他被俘的哥哥。他與洪古爾有著很濃郁的血緣紐帶,這種血緣紐帶的關(guān)系在兄弟二人失散后,用躲貓貓的游戲?qū)ふ覍Ψ剑尚值芏诉€是失散在了時光里。在漫長的歲月里,兄弟二人從未放棄尋找對方的信念。
其次赫蘭是一種智慧化身的產(chǎn)物,他利用搬家家游戲?qū)⒄麄€拉瑪草原攪得天翻地覆,將人們困住在游戲之中,困于時光之中,重返孩童的生活,瓦解了整個拉瑪草原戰(zhàn)斗力。并且他的這種智慧體現(xiàn)在作者賦予他一種打通世界的認知能力,赫蘭與他人最大的區(qū)別就是他發(fā)現(xiàn)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是他人構(gòu)筑的一個世界,自己成了他人敘事的產(chǎn)物。因此,在作品的最后,赫蘭作為下一任江格爾齊降生了,他從被敘事者轉(zhuǎn)向了敘事者,重新開始了下一個世界的講述。
顛覆與重構(gòu)。《本巴》中的英雄在繼承了《江格爾》的主要特征之外,劉亮程還為他們添上了厚重的憂傷感和無力感,因為每一位英雄不再無所不能,他們都受制于內(nèi)心深處的恐懼以及客觀時間的流逝。在他們的內(nèi)心深處都埋藏著恐懼,恐懼使他們擁有了人類最初始的情感。江格爾的恐懼在于年老體衰、力量不再,使他所帶領(lǐng)的民族陷入冰冷雪原之中;洪古爾的恐懼源于被俘時面臨殺頭的噩夢,而這也是他長到了車輪高就再也不長的原因;哪怕是強大到構(gòu)建了本故事發(fā)生的哈日王,也因為一種對成長的恐懼和對成人世界的厭惡而停留在母腹之中不肯降生,通過母親的肚臍來看世界,一只眼睛是天真,另一只眼睛是世俗。這種關(guān)于現(xiàn)實和幻想的濃重割裂感加深了哈日王身上的悲劇色彩,使得這部小說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正義與邪惡的對比。這也是被譽為“鄉(xiāng)村哲學家”的劉亮程在行文時的細膩表現(xiàn):強烈的黑白分明色彩、善惡的對比力量往往是不存在的,唯有時間成了萬事萬物的造物主,成了在風中不可消散的永恒。
《本巴》中呈現(xiàn)出來的這種對于傳統(tǒng)史詩的繼承性與顛覆性,將傳統(tǒng)史詩與時代發(fā)展的脈絡(luò)相聯(lián)合,賦予了史詩嶄新的時代氣息,從而完成了一種史詩的重組。“認清了史詩的真相之后,將其作為一種信仰和行動,突破了知識論的局限,在史詩的表演性實踐書寫中讓史詩獲得了新時代的生機。”
真摯的童年精神
宏大敘事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具備一定的主題性,劉亮程在《本巴》中一直在探討與追尋一個問題就是關(guān)于童年的力量,包括劉亮程本人也在后記中談到:“《本巴》是關(guān)于時間的童話史詩。”
人類往往是站在現(xiàn)在來回望童年,童年的精神力量是強大的、震撼的。因此在《本巴》當中,孩童的力量是強大的,越接近母腹,越接近生命的初始形態(tài)的力量就越強大。因此,還在母腹的哈日王策劃了整場游戲,將所有人控制在這場游戲中,俘虜了洪古爾,一腳踢開了赫蘭。由此看來《本巴》中也在追問著這樣一個問題:究竟什么是生命的本質(zhì)?孩子從生下來的那一刻,甚至在母腹之中就開始接受教育,我們的一生都在接受教育,那么接受了教育的人還是最本質(zhì)、最原始的那個他嗎?人類最原始的、最本質(zhì)的力量是否在教育的作用下發(fā)生了改變?這種源自生命最初的力量感是否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逐漸消磨殆盡?
此外,對于探討生命的本源問題,早期中國關(guān)于圖騰崇拜、動物崇拜等說法眾多。在探尋多樣化的生命本源的問題時,《本巴》給予了我們一種答案,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是偉大的,童年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童年的經(jīng)歷作為一個人最初的原始記憶,它在一定程度上構(gòu)建了一個人的大致性格與基本的處世態(tài)度。
作者將史詩中有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場面刻意弱化,反而是通過孩童做游戲的方式——“搬家家”“捉迷藏”和“做夢夢”來進行戰(zhàn)爭敘事的演進。將戰(zhàn)爭的殘酷削弱為孩童做游戲的過程,體現(xiàn)為一種反戰(zhàn)的、歌頌真善美的人類精神。
結(jié)語
《本巴》這部小說用輕盈澄澈的文字勾連了整個草原世界,貫穿了現(xiàn)實與夢境。結(jié)合劉亮程本人獨特的鄉(xiāng)村哲學經(jīng)驗為古老的史詩《江格爾》重新灌輸了新鮮的血液,接續(xù)了過去與現(xiàn)在的時代節(jié)點,讓史詩重新煥發(fā)了新的生機與活力。《本巴》中呈現(xiàn)了關(guān)于完整世界的構(gòu)造設(shè)想、史詩中的英雄接續(xù)上了現(xiàn)代的印記、作者于童年的回首之處叩問生命的本質(zhì),尋找關(guān)于人類真善美的童年記憶。因此,《本巴》具有一定的現(xiàn)代性的崇高美學價值與生命意識。
作者單位:喀什大學人文學院
參考文獻
[1]程群.宏大敘事的缺失與復歸——當代美國史學的曲折反映[J].史學理論研究,2005(01).
[2]傅道彬.《尚書》與早期中國文學的宏大敘事[J].北方論叢,2019(05).
[3]劉亮程.本巴[M].南京:譯林出版社,2022.
[4] 劉大先.世俗時代的史詩思維——論劉亮程《本巴》對《江格爾》的發(fā)展[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