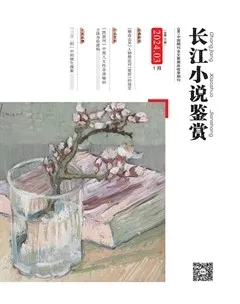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聊齋志異》人物塑造對(duì)《楚辭》的接受
羅娟
[摘? 要] 屈原及《楚辭》對(duì)于中國(guó)文人和中國(guó)文學(xué)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對(duì)《楚辭》的接受學(xué)習(xí)幾乎貫穿我國(guó)整個(gè)封建時(shí)期。許多文人極其崇拜屈原,并自覺(jué)地在其創(chuàng)作與審美追求上效仿屈原,自發(fā)對(duì)屈原的作品進(jìn)行接受,因而可以在后世許多作品中尋到屈原文章的影子。清代作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即在多個(gè)方面對(duì)屈原及《楚辭》進(jìn)行了模仿和借鑒,于人物塑造上主要表現(xiàn)為《聊齋志異》和《楚辭》兩部作品中都塑造出了處濁世、不屈惡、性癡情的士人形象,具有神性或艷情特質(zhì)的求愛(ài)女性形象和具備法官或助手性質(zhì)的男神形象。這三類(lèi)人物形象的塑造實(shí)質(zhì)上都折射著作者自身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向往。不同時(shí)代的文學(xué)作品,體現(xiàn)了文學(xué)的貫通性和不同時(shí)代文人心靈的相通處。
[關(guān)鍵詞] 《聊齋志異》? 《楚辭》? 文學(xué)接受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I20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2097-2881(2024)03-0003-04
一、引言
《楚辭》與《聊齋志異》同為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瑰寶,擁有著深厚的文學(xué)內(nèi)涵與美學(xué)價(jià)值。蒲松齡《聊齋自志》開(kāi)篇即言:“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zhǎng)爪郎吟而成癖……才非干寶,雅愛(ài)搜神。”[1]表明蒲松齡在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時(shí)自覺(jué)將屈原、李賀和干寶等人作為學(xué)習(xí)榜樣。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以其妙筆生花之才,創(chuàng)作出了眾多委曲變幻的故事,并于其中塑造了大量熠熠生輝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為普遍亦是最為突出的人物形象主要分為三類(lèi):士人形象、女性形象和男神形象。細(xì)察《聊齋志異》這三類(lèi)人物形象,不難發(fā)現(xiàn)其與《楚辭》中相應(yīng)形象的共通之處。以下,筆者在細(xì)讀《楚辭》和《聊齋志異》的基礎(chǔ)之上,試析《聊齋志異》中的士人形象、女性形象和男神形象對(duì)《楚辭》的接受及其表現(xiàn)。
二、士人形象的相通:處濁世、不屈惡、性癡情的士人
作家在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時(shí)往往會(huì)投入強(qiáng)烈的個(gè)人情感,這就導(dǎo)致筆下的人物或多或少呈現(xiàn)出作者自身的特質(zhì)或他們所認(rèn)同的理想人格。屈原在其詩(shī)作中提出“惜誦以致愍兮,發(fā)憤以抒情”(《九章·惜誦》),足以見(jiàn)得屈原作詩(shī)的目的就是發(fā)憤、抒情,自然而然,他筆下的士人也就成為了他發(fā)憤抒情的載體。同時(shí),蒲松齡作《聊齋志異》也是出于相似的用意,序言中作者自白仿效屈原,借“神靈怪物,琦瑋譎詭,以泄憤懣,抒寫(xiě)愁思”,表明其著書(shū)之目的亦是“發(fā)憤”,書(shū)中的神靈怪物當(dāng)然是蒲松齡抒寫(xiě)憤懣愁思的載體,而置身于其中的書(shū)生們,更是作者本人的化身。
《楚辭》經(jīng)歷了屈原始創(chuàng)、屈后仿作、漢初搜集、劉向輯錄和王逸匯編等歷程,目前作品保存最為完整的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共十七卷六十五篇。目前學(xué)界主流認(rèn)定為屈原所作的有《離騷》《九歌》《九章》在內(nèi)的二十六篇,這些作品以屈原自身政治遭遇和心緒懷抱為根據(jù),塑造了一位處濁世、不屈惡、性癡情的士人形象。其余篇目或由屈原弟子所作,或由屈原的崇拜者所作,對(duì)于屈作所塑造的形象不斷補(bǔ)充加深。
屈原出生于楚國(guó)舊貴族家庭,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后代,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博聞強(qiáng)識(shí),志向遠(yuǎn)大。早年間,屈原深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同時(shí)又兼管內(nèi)政外交大事。為實(shí)現(xiàn)“國(guó)富強(qiáng)而法立”(《九章·惜往日》)的美政理想,屈原于當(dāng)政期間制定多條法令,堅(jiān)決抵制舊貴族的“背法度而心治”(《九章·惜往日》)。然而,處于舊貴族專(zhuān)權(quán)、國(guó)君昏庸無(wú)常的楚國(guó),屈原的理想最終只能淪為空想。為政期間的辛酸坎坷、多年的流放經(jīng)歷使得屈原對(duì)世道的污濁有著清晰的感知,故而不斷地在作品中哀嘆——“世溷濁而不分兮”(《離騷》)、“世溷濁而不清”(《卜居》)、“舉世皆濁我獨(dú)清”(《漁父》)[2]……而屈原的人格魅力正在于哪怕身處濁世,與眾為敵,卻仍舊保持不屈惡、好修美的精神品質(zhì),堅(jiān)持“蘇世獨(dú)立,橫而不流”(《橘頌》),認(rèn)定“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tài)也”(《離騷》)[2]。司馬遷即是關(guān)注到屈原“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之“不屈惡”的品質(zhì),贊揚(yáng)其“雖與日月?tīng)?zhēng)光可也”[3]。
同時(shí),屈原又是一位“情癡”。他的癡表現(xiàn)在為國(guó)、為君、為民之上,屈原至死不離楚國(guó),哪怕處于流放之際亦是對(duì)故都魂?duì)繅?mèng)縈:“惟郢路之遼遠(yuǎn)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表現(xiàn)出對(duì)宗國(guó)的癡;一心侍君而忘我:“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離騷》),表現(xiàn)出對(duì)國(guó)君的癡;心懷天下百姓,以民生為己任:“長(zhǎng)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表現(xiàn)出對(duì)生民的癡[2]。種種優(yōu)秀品質(zhì)匯聚于一身,使得《楚辭》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成為了后世文人心中理想人格的典范。
《聊齋志異》中大量的書(shū)生形象實(shí)質(zhì)上就是《楚辭》中人物的降格。在具體的身份地位上他們由《楚辭》中出生高貴的士人,下降為出生平庸、輾轉(zhuǎn)求學(xué)的書(shū)生,但在人物原型上則表現(xiàn)出對(duì)《楚辭》所塑造的士人形象的效仿。
蒲松齡身處封建的清朝社會(huì),雖然具體的時(shí)代發(fā)生了轉(zhuǎn)移,但卻有著與楚國(guó)一般的渾濁不堪的世情,反映于文本之中,《聊齋志異》中的主人公幾乎都面臨著一片昏暗的世道。《成仙》中成生發(fā)出“況今日官宰半強(qiáng)寇不操矛弧者耶”的呼號(hào),將官吏等同于強(qiáng)寇[1]。《狐聯(lián)》篇中借狐女之口吐露世間“凡事皆以黑為白”的丑態(tài)[1]。處于曖曖之世,《聊齋志異》中的書(shū)生同樣顯露出“不屈惡”的美德:《席方平》中為父申冤,敢于只身前往地府,幾次三番遭受?chē)?yán)刑拷打而不懼,最終請(qǐng)得二郎神君為其父洗刷冤屈的書(shū)生席方平,其出入幻境的從容、面對(duì)黑暗政權(quán)時(shí)敢于直言的精神和置生死于度外的豪邁氣度實(shí)際上就是《楚辭》中“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的主人公的化身。
此外,《聊齋志異》中的書(shū)生亦傳承了《楚辭》中主人公“性癡情”的特質(zhì)。蒲松齡好寫(xiě)“癡”,書(shū)中的書(shū)生也往往具備“癡”的特質(zhì):秦生喜酒,明知酒中有毒亦欲“取盞將嘗”,毒酒為其妻覆于地,卻“伏地而牛飲之”(《秦生》),乃為酒癡;孫子楚“性遷訥,人誑之,輒信為真”(《阿寶》),為求娶阿寶自斷其指,之后更是兩次魂隨阿寶而返,幾近身死,乃是情癡;郎玉柱家境貧寒,屋內(nèi)無(wú)物不賣(mài),卻“惟父藏書(shū),一卷不忍置”(《書(shū)癡》),真乃書(shū)癡。由《楚辭》中為國(guó)、為君、為民而癡轉(zhuǎn)化為《聊齋志異》中的為酒、為情、為書(shū)而癡,折射出處于不同時(shí)代、不同地位作者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但就“癡”這一性情本身,則不得不承認(rèn)其體現(xiàn)了《聊齋志異》書(shū)生對(duì)《楚辭》士人形象的接受。
三、女性形象的接受:具有神性或艷情特質(zhì)的求愛(ài)女子
《聊齋志異》塑造了一眾艷麗多姿的女性形象,其中既有貼近于凡俗的凡人女性形象,亦有身姿妖嬈且大膽求愛(ài)的女妖、女鬼形象和遠(yuǎn)離俗塵、驚艷絕倫的女神形象。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的生成既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民間傳說(shuō)和文人幻想的產(chǎn)物,同樣也離不開(kāi)對(duì)中國(guó)古代浪漫主義文學(xué)淵藪《楚辭》的接受。
《楚辭》憑借著其塑造的眾多女性形象開(kāi)創(chuàng)了女性描寫(xiě)的新紀(jì)元。于內(nèi)在品質(zhì)上,《楚辭》女性形象所表現(xiàn)出的共同特征為熱烈且主動(dòng)地追求愛(ài)情。在《九歌·湘君》中湘夫人久等戀人不至之后便主動(dòng)追尋,駕飛龍、望涔陽(yáng)、橫大江,先自湘江北上,再轉(zhuǎn)洞庭西望極浦,行遍湘水湖畔尋覓愛(ài)人。《九歌·山鬼》中的山中女神亦是主動(dòng)擇取香花以贈(zèng)君,跨過(guò)險(xiǎn)難之路以會(huì)君,采摘靈芝留取歲華以待君。馬樂(lè)在《〈楚辭〉中女性形象的呈現(xiàn)及其文化成因》中認(rèn)為在楚國(guó)地區(qū),其巫風(fēng)特質(zhì)中最為顯著的即是“民神融合”“民神共娛”[7]。故而,就《九歌》誕生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和歷史背景而言,其中眾女性面對(duì)愛(ài)情積極主動(dòng)的行動(dòng)又離不開(kāi)祭祀活動(dòng)中娛神的需要。
于外在特征上,《楚辭》中的女性人物在不同的篇章中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質(zhì)。源自于民間祭祀活動(dòng)的《九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多具有概括性的美,帶有一定的虛幻神秘色彩。如《九歌·山鬼》中所刻畫(huà)的身披薜荔、頭帶女蘿、乘豹帶貍、善笑窈窕的虛幻的女山神形象。《九歌·湘君》中塑造的湘水女神概括性更強(qiáng),全篇對(duì)于外貌的描寫(xiě)只有一句“美要眇兮宜修”,展現(xiàn)了女神的文雅美好,之后便再無(wú)進(jìn)一步的展開(kāi)。相反,用于“招魂”的《招魂》《大招》中描寫(xiě)的女性形象出于吸引被招魂者的目的,則多帶有艷麗、艷情之美,描寫(xiě)得也更加細(xì)膩。《大招》中的女子具有“朱唇皓齒、豐肉微骨、姱脩滂浩、蛾眉曼只”[2]的特質(zhì),作者通過(guò)對(duì)女性艷麗的面貌、豐盈的體態(tài)和嫵媚的神色加以細(xì)膩地描寫(xiě),令其別具艷麗、艷情之色。獨(dú)特的女性內(nèi)在特質(zhì)與各盡其用的外貌描寫(xiě)手法為后世文學(xué)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藝術(shù)借鑒。
《聊齋志異》眾女性的普遍特質(zhì)亦表現(xiàn)為對(duì)愛(ài)情執(zhí)著而主動(dòng)的追求:妖女如《蓮香》中的狐女蓮香主動(dòng)夜往書(shū)生齋舍,自薦枕席,直至死后仍不忘舊情;鬼女如《聶小倩》中的聶小倩為求得與寧采臣終成眷屬,先是主動(dòng)現(xiàn)身為其解除危機(jī),再是精心侍奉高堂使寧母對(duì)自己由懼轉(zhuǎn)愛(ài),最后巧妙化解寧家子孫之憂,表現(xiàn)了其對(duì)愛(ài)情堅(jiān)持不懈的追求;神女如《錦瑟》篇東海仙姬錦瑟、《惠芳》篇女神惠芳等亦采取積極主動(dòng)的姿態(tài)爭(zhēng)相與男主人公遇合,錦瑟自薦不成轉(zhuǎn)而令其長(zhǎng)姊瑤臺(tái)為之說(shuō)合主婚,惠芳主動(dòng)上門(mén)自薦,雖多次遭馬母所拒仍不改心意。《聊齋志異》中哪怕靦腆如凡間眾女亦在對(duì)書(shū)生產(chǎn)生愛(ài)慕之情后表現(xiàn)出對(duì)愛(ài)情婚姻積極主動(dòng)的追求和捍衛(wèi):《連城》篇史孝廉之女連城為反抗不幸婚約而死,求得美滿婚姻后又由死轉(zhuǎn)生,甚至在生還之際說(shuō)出“恐事不諧,重負(fù)君矣。請(qǐng)先以魂報(bào)也”[1]此等有違封建禮教之辭。
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價(jià)值體系中,男性往往以贏得女性的青睞作為其價(jià)值存在的標(biāo)志之一,且女性形象愈是美好迷人,這種價(jià)值認(rèn)可的力度就會(huì)愈大。故而《聊齋志異》中眾多美好可愛(ài)的女性爭(zhēng)相向書(shū)生表示好感、主動(dòng)求愛(ài)行為的實(shí)際內(nèi)涵則又超越了《九歌》中的祭祀需要,而且潛藏著蒲松齡自我肯定的訴求[5]。
在進(jìn)行人物外貌描寫(xiě)時(shí),蒲松齡亦是繼承了《楚辭》中兩種描寫(xiě)女性的藝術(shù)手法。在部分篇章中作者采用側(cè)面描寫(xiě),以環(huán)境、行動(dòng)烘托女性之美,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帶有一定的神性、概括性色彩。如《嬰寧》對(duì)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寫(xiě)較少,主要突出其“笑容可掬”的性格特征,并采用了較多筆墨描寫(xiě)嬰寧所身處“空翠爽肌”的環(huán)境,以綠柳、桃杏、修竹、海棠等多種鮮花芳草襯托嬰寧的“容華絕代”。《神女》篇的神女“其眉目間有神氣”,具有一定的神化氣息。但同時(shí),亦有部分女性形象繼承了《招魂》《大招》中帶有艷情氣的外貌描寫(xiě)手法,呈現(xiàn)出艷絕的特色:如寫(xiě)胡四姐“嫣然含笑,媚麗欲絕”(《胡四姐》);西湖公主“鬟多斂霧,腰細(xì)驚風(fēng)”(《西湖主》);聶小倩“肌映流霞,足翹細(xì)筍”(《聶小倩》)[1]……作者通過(guò)對(duì)眾女神色、體態(tài)、肌膚的直接描寫(xiě)刻畫(huà)出一個(gè)個(gè)美艷動(dòng)人的女性形象。
四、男神形象的襲承:兼職法官或助手的男神
關(guān)于“神”這一概念,《說(shuō)文解字》中將其解釋為:“天神,引出萬(wàn)物者也。”[6]將“神”定義為天神。隨著時(shí)代發(fā)展,這一概念不斷得到完善,現(xiàn)代以來(lái)李劍國(guó)先生將“神”定義為世界的全部或某一部分的主宰者,并進(jìn)一步提出天神、人鬼、動(dòng)植物皆能成神[7]。同時(shí),也有學(xué)者結(jié)合巫文化將神分為物神、人神、天神、地神和鬼神五類(lèi),劃分得更為細(xì)致[8]。《楚辭》與《聊齋志異》都創(chuàng)作于鬼神迷信盛行的封建社會(huì),受時(shí)代認(rèn)知所限與個(gè)人情感表達(dá)的需要,作品中亦是塑造了大量的神靈形象。
誕生于“信巫鬼,重淫祀”的楚國(guó)社會(huì),《楚辭》中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神靈形象。《楚辭》中的男神主要擔(dān)任著兩種身份:一是抒情主人公陳述衷情的對(duì)象,即擔(dān)任著正義法官的身份。如《離騷》中“就重華而陳詞”,人神重華成為了“余”陳述懷抱、表明心志的對(duì)象;《九章·惜誦》中令五帝、六神、山川之神、人神皋陶共同承擔(dān)法官的身份,以驗(yàn)證自己“謁忠誠(chéng)以事君”的真實(shí)度,判斷自己的道德是否高潔完善。二是作為抒情主人公游覽天地的助手。淮南小山稱(chēng)屈原之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2],指出了眾多神靈在《楚辭》中所擔(dān)任的助手身份。如《離騷》《遠(yuǎn)游》中日神、月神等天神為“余”駕車(chē),風(fēng)神、雷神、云神等一眾氣象神為“余”前后奔走。《楚辭》中的男神形象亦脫離了本身的神異色彩而別具人情,成為了《楚辭》作者抒寫(xiě)心緒、表達(dá)情懷的工具。
然而,《楚辭》的一眾神靈無(wú)論是承擔(dān)法官的身份或是作為“余”之助手而存在,實(shí)際上都是借這些身份高貴、極具權(quán)威性的神靈形象來(lái)實(shí)現(xiàn)對(duì)自己人格的肯定,王逸就《楚辭》中月神形象的內(nèi)涵提出自己的見(jiàn)解:“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9]即看到了這類(lèi)神靈形象背后的象征性意義。
《聊齋志異》中眾多男神形象的塑造同樣與《楚辭》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與《楚辭》不同的是,《聊齋志異》大部分篇目里擔(dān)任正義法官的男神從《楚辭》中分散的眾神集中到鬼神“冥王”一身,由這一位鬼界法官承擔(dān)著裁定人間善惡的職能。這位法官對(duì)書(shū)生的道德有著極高的要求,得知書(shū)生為“名士”時(shí),則以禮相待,“待以鄉(xiāng)先生禮”,而一旦發(fā)現(xiàn)其行為不正“行多玷”,則立罰其做牛做馬,以贖罪孽(《三生》)。然而,這位法官在保持公正嚴(yán)明執(zhí)法態(tài)度的同時(shí)又兼顧人情,既會(huì)為人間女子節(jié)義所感,為書(shū)生“姑賜再生”,使得死者生還(《阿寶》);亦是賞罰分明,使善者受賞,惡者受罰:如在《王蘭》中的冥王授無(wú)辜而死、以醫(yī)治人的王蘭為“清道使”,而將為人邪蕩、以醫(yī)謀財(cái)?shù)馁R才“罰竄鐵圍山”。
與《楚辭》大量男神以“余”之助手的身份出現(xiàn)一樣,在《聊齋志異》中亦有眾多“助手式”的男神出現(xiàn),如《雹神》中的天神雖為神靈,卻尊敬作為凡民的王筠蒼,為其愛(ài)民之心所感而擇渠落雹。《白秋練》中“真君喜文士”,遇慕生求助便大力相助,免除洞庭龍王對(duì)秋練之母的責(zé)罰,解除書(shū)生愛(ài)情危機(jī)。
書(shū)生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郁郁不得志卻能輕易得見(jiàn)仙人,受各類(lèi)花妖狐魅乃至神靈賞識(shí)相助。這些充滿象征性意味而又別具人情的男神形象表現(xiàn)出了蒲松齡對(duì)《楚辭》借描寫(xiě)神靈以自我肯定、自我夸耀藝術(shù)構(gòu)思的接受和學(xué)習(xí)。
五、結(jié)語(yǔ)
《楚辭》和《聊齋志異》分別誕生于不同時(shí)期的不同作者筆下,甚至兩者的文體亦是截然不同,一者為詩(shī)歌,一者為小說(shuō)。但同時(shí),文學(xué)作品之間又是相通的,文學(xué)作品作為作者抒發(fā)情感、表達(dá)心緒的媒介,其中所塑造的人物也折射著作者本人的影子。正如郁達(dá)夫所說(shuō):“文學(xué)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郁達(dá)夫《五六年來(lái)創(chuàng)作生活的回顧》)文人寫(xiě)作作品,刻畫(huà)人物,所描畫(huà)的不過(guò)自身的心緒抱負(fù)。屈原和蒲松齡都是出于“發(fā)憤而著書(shū)”,蒲松齡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對(duì)屈原的學(xué)習(xí)和接受,體現(xiàn)了文學(xué)的貫通性,彰顯了不同時(shí)代文人心靈的共鳴。
參考文獻(xiàn)
[1] 蒲松齡.聊齋志異[M].長(zhǎng)沙:岳麓書(shū)社,2001.
[2] 方銘.楚辭全注[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1.
[3]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22.
[4] 馬樂(lè).《楚辭》中女性形象的呈現(xiàn)及其文化成因[J].蘭州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33(05).
[5] 李彥東.文人生態(tài)的存在與發(fā)現(xiàn)——從改編的角度論《聊齋志異》對(duì)楚騷傳統(tǒng)的模仿[J].浙江師大學(xué)報(bào),2001(04).
[6] 許慎.說(shuō)文解字(中華書(shū)局影印)[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63.
[7] 李劍國(guó)輯校.宋代傳奇集[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1.
[8] 岳文立.巫文化視野中的《聊齋志異》[D].河北師范大學(xué),2006.
[9]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diǎn)校.楚辭補(bǔ)注[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