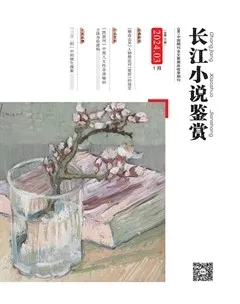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托馬斯的心靈復調解析
王忠陽
[摘? 要] 本文從昆德拉的復調結構藝術入手,重點分析托馬斯的心靈復調,探尋復調結構對塑造人物形象與深化主題的作用。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托馬斯為例,從“輕與重”“靈與肉”兩條線索出發,分析心靈復調在小說中的具體體現,真正體會一次復調結構與人物形象、主題的完美融合。
[關鍵詞] 復調藝術結構? 輕與重? 靈與肉
[中圖分類號] I22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3-0011-04
一、昆德拉的復調藝術
1.托馬斯對待愛情態度的復調
昆德拉在對托馬斯的感情生活進行刻畫的時候,運用了傳聲筒的寫作手法,讓托馬斯的感情生活看起來具有立體感,仿佛托馬斯的感情生活有棱有角一樣,每時每刻都有新的變化,或許這就是復調的獨特魅力。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強調:不要變奏,而要重復,而且始終直入事物的心臟[1]。很明顯,昆德拉在運用復調手法描寫托馬斯的心靈時就遵循了這樣簡潔而又有效的原則,不是反復重復一個片段帶來相同的效果,而是用不同的片段來豐富人物形象進而產生更加強大的感染力。
在直接描寫托馬斯時,“和特蕾莎在一起好呢?還是一個人好呢?”作者在評價托馬斯這個環節保持了沉默。通過對托馬斯各個方面的描寫,讓讀者自己去評價,形成獨特的小說人物印象。昆德拉筆下的小說人物形象都是具有思考性的,在此基礎上心靈復調將這眾多的人物心理瞬間串聯起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人物形象。在特蕾莎的部分,托馬斯的性格又是這樣被復調的,“托馬斯的不忠突然間讓她明白了自己的虛弱無助,正是這份無助的感覺,讓她感到發暈,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往下墜落的愿望。”[2]尤其是特蕾莎的部分就將托馬斯的人物性格鑲上了不同尋常的邊框,托馬斯的心靈里面充斥著無數矛盾的因子,在這些矛盾的因子進行膨脹的時候心靈復調就開始起到它應有的作用。表面上好像是在描寫特蕾莎,實際上是對托馬斯心靈的一種補充。托馬斯和特蕾莎在一起是享受著愛情的喂養而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則享受一種權利的征服。所以,特蕾莎在托馬斯內心的重量也是忽輕忽重的,這種重量無法衡量。作者直接描寫托馬斯這個人物的時候節奏比較緊湊,而在通過特蕾莎進行描寫的時候就比較舒緩。復調也有它自己的語言節奏,昆德拉在托馬斯部分比較冷靜客觀,而在特蕾莎以及其他部分是比較感性的,這就形成了一種循序漸進的心靈復調結構。這種心靈復調的運用不僅讓托馬斯這個人物形象更加豐盈,而且能充分引起讀者的思考。
這樣的復調藝術手法形成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與多元化。在沒有波蕩起伏的小說情節的時候,一個人物的塑造就格外地考驗作者的功底。作者在復調的藝術結構中,并沒有將自己的意識與人物的意識混為一談,而是將自己的意識作為眾多意識中獨立的那個意識,在介入托馬斯內心世界的時候,作者用自己獨立的意識將托馬斯的多方位精神世界呈現了出來。托馬斯的人物形象傳遞出的就是一種不確定、分離、特殊的感覺。這種人物內心的精神和性格是最不容易被完全挖掘的。托拉斯在第一部分的時候他的人物形象的涉及面還是比較窄,僅僅通過他對待女人、愛情的態度展開。而后面“輕與重”的復調手法看似比較隱秘,但是從多個角度重新塑造了托馬斯這個人物形象,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復調手法在隨筆中、在時間的對換中,行云流水地呈現著。
多元化與完整性本身就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將托馬斯的精神世界刻畫得比較完整的前提,就是要從多元化的角度去刻畫托馬斯的人物形象。昆德拉小說追求一種“徹底的簡潔”,在這種簡潔性的背后又能將人物的精神世界充分的多角度地表達,隨筆式的復調手法是功不可沒的。因此,小說看起來既簡潔又富有深意,昆德拉的復調實現了作者意識與人物意識相互獨立,簡潔又不失內涵這些難以兼備的優點。
2.主題的復調
昆德拉習慣性地將有關主題的論述穿插到人物的描寫中來,在人物的經歷中將主題融匯進來。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有三個最為主要的主題:人生、永恒、感情。昆德拉沒有將小說寫成故事,而是將小說豐富成有關于人生的一首詩,讀她的小說可以感受到詩的韻律。在小說的第一部分作者就闡釋了有關永恒的概念,到后面有關永恒的主題再一次出現。“永恒輪回是一種神秘的想法,永恒輪回之說從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遠消逝便不再回復”這是第一部分中永恒的概念,到后面永恒的主題變得更加夢幻起來。托馬斯的心靈復調必然和主題分不開,因為托馬斯就是一位在不斷探索人生的冒險家。主題的復調也是托馬斯心靈復調的一種展現。永恒的復調是在不斷深入的,每一次重復永恒的主題都在加深人們對永恒的思考。“人生如同譜寫樂章,人在美感的引導下,把偶然的事件變成一個主題,然后記錄在生命的樂章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第六部分將這種復調的手法運用到了極致。前面的各個部分之間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系,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安娜、斯大林、創世記”都可以成為昆德拉進行復調的工具,在對這些人物進行重新定義的時候也將有關小說的主題相對應復調化了。“復調”不是一個抽象化的形而上的東西,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一種寫作手法,可以改變小說結構并直擊小說主題。感情線也是昆德拉著重描寫的主題,無論是托馬斯還是特蕾莎都面臨著這個嚴肅而又滑稽的問題。當小說人物到了一種窘迫境地的時候,感情這虛無縹緲的東西就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每一次的敘述都是一次新的復調。
“隱含讀者”的產生就與文本的可延展性密不可分,托馬斯的人物形象在不同的讀者面前肯定有不同的解讀。昆德拉運用復調的結構藝術時,充分地將復調的文學性、意識的獨立性、時間的對位法緊密地結合起來。
二、托馬斯的精神世界
“最沉重的負擔壓迫著我們,讓我們屈服于它,把我們壓到地上。但在歷代的愛情詩中,女人總渴望一個男性身體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會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從全文來看,托馬斯的精神基調是冷漠、復雜、痛苦的,作為一個外科醫生,托馬斯在這個無價值可言的世界中表現出他自己獨特的思想態度。小說的本質是探詢人物的人心,挖掘存在的意義。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作者昆德拉運用復調的結構手法,將托馬斯的人物形象解讀出多種意味。昆德拉將小說詩學融匯到小說當中去,呈現出哲學與文學相融合的盛況。昆德拉研究的是有關“存在的問題”,因此在“輕與重”與“靈與肉”兩條線索中,復調就扮演了一種特殊而神奇的角色。昆德拉運用復調將托馬斯復雜的心理活動通過多層次的表現手法表現了出來。在“輕與重”“靈與肉”中,去聆聽托馬斯與這個世界的對話,通過他的愛情、事業、對永恒的態度,思考何為真正的“輕與重”“靈與肉”。通過托馬斯心靈復調的影響,托馬斯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也展現在讀者面前[3]。
1.模糊的“輕與重”
昆德拉的復調是重思辨而輕情節的,作者在情節中通過分析人物性格而得出深層次的思考,因此“輕與重”也是在思辨與道理中慢慢論述。首先,從與特蕾莎的感情開始,“輕與重”就如此得不穩定。在小說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就對托馬斯與特蕾莎的相處下了一個定義。“對這個幾乎不相識的姑娘,他感到了一種無法解釋的愛。對于他而言,她就像是個被放在涂了樹脂的籃子里的孩子,順著河水漂來,好讓他在床之岸收留她。”在沒有遇見特蕾莎的時候,托馬斯與女人們的關系是微妙的,他從來不會留女人們在自己的家中過夜,如果一個陌生的女子躺在他的身邊,他難以入睡。之前的托馬斯面對感情是放縱的、無拘無束的,而特雷莎的出現竟然改變了這一切,他在特蕾莎的身邊可以進入甜美的夢鄉。托馬斯面對感情是冷峻、客觀的,而特蕾莎卻是熱情的,這樣的兩個人一定會在“輕與重”面前無法抉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具有哲學意義,作者在復調中對“輕與重”進行全方位論述,并且運用多聲部去播放托馬斯的精神世界。托馬斯在愛情的存在哲學里,可以說是忽輕忽重的,對位法法則就是讓“小說去解讀小說”,將作者的思考與夢幻的敘述巧妙地結合在小說的行文之中。其次,在托馬斯的工作之中,這種“輕與重”就體現得更為明顯了。“但他已經感覺到,他已通過某種忠誠的誓言和他的這一決定聯系在一起,于是他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就這樣,他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他對于自己的工作是十分熱愛的,這是一份可以給他帶來激情與動力的工作,失去工作僅僅是因為他發表了一篇有關俄狄浦斯的文章,這篇文章代表了托馬斯的訴求,而這些言論在當時是不被理解的。關于托馬斯與俄狄浦斯故事之間的討論在小說中多次被提到。這就是昆德拉復調理論的突出之處,在隨筆式的行文中將人物心理層層解剖。對于作者的聲音與主人公的聲音,昆德拉運用了“寓重與輕”的手法,讓心靈復調看起來很普通卻具有非同凡響的效果。最后,關于托馬斯生命中“輕與重”的問題,我們落腳于“永恒性”的探討。“也許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星球,在那里人類可以不斷地重生,每一次重生都會提高一個層次”,關于永恒性的問題在小說一開篇就進行了討論,在小說深入展開的時候“永恒性”的話題再次被提及,在托馬斯的世界里,人類社會可以是無限循環的,他一方面渴望永恒的美好,一方面又無法直視人在世界上的痛苦與悲傷。托馬斯這個人物本身是具有雙重矛盾的性格的,所有他的世界里的“輕與重”是飄忽不定的,而那個“重”一旦消失,托馬斯的精神世界就開始暗沉了下來。托馬斯的心靈復調正是讓這種不穩定浮出水面,昆德拉筆下的復調在不斷創新的進程中,那種豐富性與神秘性是其他手法無可替代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部小說的情節沒有很復雜,小說節奏也是相對緩慢的,主題的展開也在緩慢地向前展開。作者在隨筆中推進小說的行文,在這樣的小說布局中,小說復調的結構無疑打開了小說人物精神世界的大門。真正的復調不是簡單地重復,而是在平行的線索中將人物的內心深化、細化、具體化,這才是復調藝術的魅力所在。無論在愛情上、工作上,還是對待世界的態度上,托馬斯的精神世界都是不可捉摸的,他有時是一個透明人,有時又洞察這個世界,他有時糊涂有時清醒。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個探不到底的深淵,作家只有從存在主義角度出發才能慢慢領悟。托馬斯的心靈復調最為獨特之處就是將這種矛盾性用最清楚的方式展現出來。從文體上、敘事角度上、情感上,都充分體現出心靈復調的優越性[4]。
2.分割的靈與肉
復調的本質就是對話,多種聲部的多重敘述才使小說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從昆德拉的心靈復調出發才可能更好地探索內心“靈與肉”的關系,“靈”是精神層面的,“肉”是肉體上的歡愉。托馬斯面對“靈與肉”的問題時,是毫不愧疚的,并且明確地認為靈與肉是相互分離的。當他和特蕾莎在一起的時候,他還經常與別的女性約會,對這個行為他總是有無窮無盡的辯解。“在托馬斯擁有眾多女人的生活中充當他的另一個自我,托馬斯對此無意理解,但特蕾莎無法擺脫這個念頭。”托馬斯與特蕾莎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十分大的差別。特蕾莎認為靈與肉是一個整體,當特蕾莎在與托馬斯進行交往的時候,她的身體得到了釋放。托馬斯卻把肉體的交往視為一種精神的寄托,或許因為他是外科醫生,所以他對身體如此的客觀與無感情。在小說中的每個章節我們都可以看出托馬斯對待靈與肉的關系,他認為靈與肉是相互不相關的個體,他愛特蕾莎的人,和他親近別的女人的身體這兩件事在本質上就絲毫不矛盾。“靈與肉”這條復雜的線索主要體現在托馬斯與特蕾莎身上,昆德拉在小說中對于托馬斯這種精神世界沒有做過多的解釋,而是通過俄狄浦斯的故事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來暗示了讀者。“對他而言,她就像是個被人放在涂了樹脂的籃子里的孩子”這句話點明了在托馬斯心目中他與特蕾莎之間的關系。托馬斯看見特蕾莎或許激起了他的保護欲,又或許特蕾莎身上的某些童真特質讓托馬斯為之動容。兩個人在交往的時候,兩個人的“靈與肉”仿佛在瞬間進行了交換。愛情讓兩個人對彼此陶醉,但是托馬斯更加追求心靈上的崇高,因此為了不讓肉體痛苦,他的思想將“靈與肉”進行了割裂。并且這種割裂在小說的行文中作者用復調手法充分地表現了出來。昆德拉運用了數字化的復調藝術結構,在這種藝術手法的影響下,好像人物都被照亮了,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照明,能夠將一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完整地呈現出來。
托馬斯的態度讓特蕾莎感到十分痛苦,僅僅是因為特蕾莎高舉“靈與肉的高度統一”。“她的靈魂失去了繼續充當旁觀者的好奇心,失去了先前的惡意和驕傲:它重又回到了身體最隱秘的深處,絕望地等待著有人來喚醒它”。特蕾莎對生活還是一如既往地充滿著熱情,她渴望“靈與肉”的統一,她渴望崇高,她追求自由,這一切都與托馬斯對待“靈與肉”的觀念截然不同。雖然“靈與肉”這個部分在寫特蕾莎,但是作者用復調的手法將人物訴求彼此穿插,從內容上做到了“人物補充人物”。托馬斯分割的“靈肉”觀,或許與他追求的“永恒觀”有一定的聯系,在他的世界里世界是不斷被探索的,另一個世界不存在死亡與消失,嫁接到“靈與肉”層面就是肉體是有限的,精神是無限的,有限的肉體不能滿足無限的精神,因此它們二者是彼此分離的。“靈與肉”體現的是人物與人物的矛盾性,進而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寓意更加明顯。
三、復調結構藝術與托馬斯人物形象總結
托馬斯的精神世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著重體現的,復調藝術不僅僅是一個機械的藝術手法,它可以將人物的內心世界精彩地呈現出來,并且賦予人物多層含義。在“輕與重”的概念面前,托馬斯的人物性格如此得不穩定,在“靈與肉”的面前,托馬斯又呈現出如此分裂的性格傾向,這些隱藏在人物內心深處的密碼是不容易被探索出來的,復調藝術手法卻將不可解的密碼破譯了,這在昆德拉的小說創作上可以說是偉大的成就。
在“復調”的藝術結構中探尋托馬斯的精神世界就是讓復調在我們的認知領域變得容易理解,復調的藝術對“托馬斯”這個人物形象塑造是極為重要的。除此之外,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也在昆德拉的小說創作中貢獻了一份力量,讓昆德拉的小說節奏變慢,結構深刻。托馬斯的心靈復調簡單卻深刻,卻把一種不可言表的矛盾性形象化地論述出來,給讀者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參考文獻
[1] 張彬杰,張雪慧.淺析蒙太奇視角下的文學敘事——以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為例[J].名作欣賞,2023(14).
[2] 楊苗燕.常讀常新的“輕”與“重”——重讀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J].書城,2022(05).
[3] 向琴.“輕”與“重”之間——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選擇困境[J].山西能源學院學報,2023,36(04).
[4] 薛展鴻.米蘭·昆德拉小說中的現代“烏托邦”研究——以《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為中心[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3(05).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