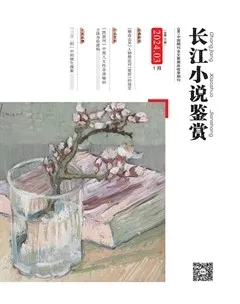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視域下對《沃許》的解讀
羅艷巍
[摘? 要] 作為福克納的經典短篇小說,《沃許》揭示了美國南方種植園經濟時期窮困白人生活的艱難境遇。本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為基礎,聚焦于探索小說主人公沃許的內心世界,揭示他自我覺醒的復雜演變過程,并探究他一生受到奴役的深層心理原因。人要堅守自己的人格,樹立正確的信仰,獲得屬于自己的尊重,追求真正的自由。
[關鍵詞]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威廉·福克納? 《沃許》? 精神創傷
[中圖分類號] I10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3-0020-04
一、威廉·福克納的《沃許》及創作動機
威廉·福克納作為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各類作品一直都受到國內外眾多讀者和評論家的關注。福克納的作品常常浸染著人物的復雜心理變化,加上福克納獨具一格的敘事方式,讓讀者沉浸于復雜的情節的同時,也激起了讀者對大量細節的猜測與想象。短篇小說《沃許》正是這樣一個經典的代表作品。
在福克納創作的小說《沃許》中,沃許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疾病纏身的老人,盡管他身為白人,生活卻十分貧寒。主人塞德潘與他進行交流相處時,雖然同為白人,但他們之間的相處并不平等,沃許對塞德潘是一種向高位者仰望的情感,同時也摻雜著對富人、上流階級的恐懼,對“英雄”般的人物心懷幻想,還有對上流社會權勢的無能為力。如果沃許能夠與塞德潘交談,也只能是以“他們殺了我們的人,但他們還沒有打敗我們,對吧?”這樣的語氣,或者簡單地回答“是的,上校”“好的,上校”。塞德潘處于美國南方傳統社會,在那樣的社會情況下,像沃許這樣的窮白人是沒有話語權的,他們只能屈服于上層權力,任由塞德潘這類人物隨意擺弄。在南方地區,只有少數人掌握著話語權,他們擁有莊園和奴隸,對北方人都懷有敵意,而塞德潘就是這類人的典型代表。多年來,沃許自認為自己是個白人,所以一直努力以塞德潘的方式與他進行交流,但始終未能獲得他的認可。沃許發現塞德潘勾引自己的外孫女,他默許了這一行為,也為日后的生活埋下了禍根。沃許以為彌麗為塞德潘剛剛生下后代,可以得到塞德潘的垂憐,但塞德潘卻毫不客氣地拒絕了他的請求。然而就在此時,塞德潘卻下令讓家里的女仆為剛出生的小馬駒找一個新的馬棚。在塞德潘看來,沃許和他的孩子們的地位甚至連家里的牲口都不如。沃許是孤獨的,他不屑于和黑人仆人交流,除了塞德潘之外,也沒有任何人和他交流,他也不會找到能傾聽和理解他的人。流言蜚語和偏見鄙視形成了一道屏障,阻礙著沃許這個窮白人與他人之間的交流。就連塞德潘家的黑人奴隸們都能夠隨意嘲笑他。面對鎮上其他人對他的猜測和嘲笑,沃許也無力回應,無論走到哪里,他都被猜疑和蔑視的目光所環繞。
福克納在《沃許》這部小說中巧妙地運用了主人公的內心獨白,以揭示主人公沃許內心深處的靈魂。“獨白是深層之我與他人和眾人的相會。 但我在這一相會中應該是純粹的、深層的、從自身內部出發的我,不摻雜任何設想的和強制的或借用他人觀點和評價,即不含有他人眼睛對自身的觀照。”[1] 福克納通過這種手法,將讀者帶入主人公的思緒和情感之中,讓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體驗沃許的內心體驗。這種獨白不僅僅是一種敘述方式,更是一種情感的傳遞和溝通方式,使讀者能夠與主人公建立起一種共鳴和情感聯系。福克納的這種寫作運用讓《沃許》這個故事更加生動和真實,讓讀者能夠更加貼近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福克納巧妙地利用獨特的敘述方式向讀者呈現了沃許在內心深處覺醒并最終爆發真實情感的情境。《沃許》強調描繪人物內心,以此推動故事發展。作者以一天為時間跨度,把故事事件壓縮其中,小說以倒敘開頭,回憶過去多年種種,最終回到故事發生的清晨。作者從現實出發,探尋歷史的縱深,并將歷史與現實緊密交織在一起。這種逐層遞進的特殊敘事方法讓讀者能夠沉浸在故事其中,同時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受弗洛伊德主義影響而掀起的一股文學潮流,義量掀起的一股文學潮流,在20世紀初席卷整個美國。它為現代作家探索和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及未知領域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弗洛伊德理論影響著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并為理解這些作品提供了一把鑰匙。把福克納作品中看似晦澀難解的描寫,放到弗洛伊德主義的顯微鏡下進行探究,一切便豁然開朗。諸如死亡主題、不倫之戀、象征、意識流等,都可以在弗洛伊德那里找到合理的解讀。“生活在弗洛伊德理論的大潮中,福克納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弗洛伊德理論的影響,并對他自己的創作產生深遠影響。福克納正是靠這種博采眾長、為我所用的精神,運用弗洛伊德主義去刻畫‘郵票般大小的故土,成功展示了現代人紛繁的內心世界,值得讀者反復體味。”[2]盡管福克納口頭上并不承認自己運用了弗洛伊德理論技法,但研究他作品的學者基本上都認為他不僅研究過弗洛伊德理論,而且有許多機會和可能去實踐它。福克納作品的內心獨白明顯地表明他對喬伊斯作品的借鑒,但同時也蘊含著典型的精神分析學派的因素。福克納的作品中常常出現內心獨白的形式,這種敘述方式使讀者能夠深入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感狀態。且這種敘述手法與弗洛伊德理論相呼應,都強調了潛意識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狀態的影響。福克納通過描寫人物的內心獨白,展現出他們內心情緒的復雜性和矛盾性,這一點與精神分析學派的思想十分契合。
二、憤怒的爆發
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來看,《沃許》這部小說通過隨著時間發展而事態的不斷升級向讀者展示了靈魂的釋放。時間不斷流逝,同時也留下了心理變化的痕跡,壓抑的憤怒也在最終爆發的道路上不斷積壓,最終釋放出來。時間實際上是精神和心靈的替代物,福克納精心安排了《沃許》中的時間,運用閃回的手法,將多個先前的事件壓縮在一天內發生,以表達主人公心理變化過程中壓抑程度逐漸變化的情況,引領讀者感知憤怒情緒逐漸爆發的過程。可以說,小說中,事件的升級變化始終引導著主人公心理的變化,而憤怒情緒也隨著情節發展不斷加劇。
沃許是一個貧窮的白人,他在過去的20多年里一直對塞德潘言聽計從。南北戰爭期間,當塞德潘與北方軍隊廝殺時,他花費心思打理塞德潘的家務事,“我在照看上校的家,照看他的黑鬼們”[3]。戰爭結束后,盡管塞德潘勇氣銳減,家道中落,沃許仍然忠心耿耿,“沃許在那里迎接他,樣子一點兒也沒有變:還是那么干瘦,還是那樣看不出年齡,淺色的眼睛探詢地凝望著,神情有點缺乏自信,有一點點奴性,還有一點點親熱”[4]。當他發現塞德潘勾引自己年僅15歲的外孫女彌麗時,他選擇聽之任之,“‘行啦,他說,‘要是上校愿意把緞帶給你,我倒希望你想著謝謝他”[5]。直到彌麗生下塞德潘的親骨肉后,沃許發現塞德潘對產后的彌麗十分冷淡甚至殘忍,“塞德潘出來了。他下臺階走進草地,動作是那么沉重而從容不迫,那在他年輕時原是匆促而急迫的。他并沒有正眼看沃許”[3]。在聽到塞德潘辱罵彌麗的話后,沃許終于認識到塞德潘虛偽的真面目,他毫不留情地將她比作一匹母馬。多年來,沃許一直壓抑著情緒,然而此刻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悲傷和絕望,他的人生理想徹底破碎了。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最終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他揮動著從塞德潘那里借來的鐮刀,擊中了曾經崇拜的“偶像”塞德潘。沃許自認為自己是一個白人,與塞德潘家中的黑人奴隸們不是一個等級的,當黑人們嘲笑他時,他也對塞德潘抱有幻想,而如今曾經的幻想全部破滅,塞德潘自始至終根本沒有將沃許看做是一個人,他和他的外孫女在塞德潘眼里什么都不是,哪怕沃許為塞德潘付出這么多年的辛苦,哪怕彌麗冒著生命危險為塞德潘生下孩子,他們也不如他的一匹馬重要,沃許看清了一切,心死的他,平靜地縱火焚毀自己的住所,這也導致了彌麗母女的不幸遇難。最終沃許緊握大刀,毫不畏懼地沖向前來逮捕他的人群。福克納安排一個個事件疊加敘述,層層鋪墊沃許的情緒,直至最后爆發絕望的憤怒,巧妙地展現了沃許內心情緒的變化和壓抑的積聚。他通過描寫沃許的行為和心理變化,能夠使讀者更加深入地理解沃許的心理發展和行為模式,讓讀者能夠深入體驗到他的痛苦和絕望。
三、自我的覺醒
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人的內心世界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最初的、最難以把握的部分,而自我則是從本我中發展出來并被現實化了的本能。在《沃許》這部小說中,主人公沃許最終自我的覺醒是引人注目的,這是一段漫長的過程。沃許是一位年紀較大、身體患有疾病的白人,他的生活極端貧困,因此他面臨著無法躋身上流社會的困境。塞德潘讓他住在一個連黑人都拒絕的簡陋棚屋里,那個棚子“看上去恰似一頭衰老的病獸,在它垂死的掙扎中怪嚇人地在那里喝水”[3]。沃許本人又懦弱膽怯、容易被他人擺布。他多年來一直小心翼翼地跟隨塞德潘,即使塞德潘對他如此,他仍然對塞德潘忠心耿耿。在沃許的心中,唯一能維持現在生活的方式就是依附于塞德潘,甘愿成為奴隸實際上是此時沃許對本我一面的表現,這種求生的本能讓他不得不選擇以這種方式生存下去。因此,當沃許和塞德潘共同享用威士忌時,塞德潘就坐在唯一的椅子上,而沃許則任意選擇一個箱子或桶作為自己的座位。在塞德潘喝醉之后,沃許就溫柔地安撫他,讓他入睡,然后靜靜地坐在椅子旁邊。不久之后,他就又躺到地上;即使是卑鄙的塞德潘勾引自己的外孫女導致她懷孕,沃許也為塞德潘有了繼承人而高興。可以說,為了討好塞德潘,他委曲求全,完全奴性地表現出來。
沃許對自我的覺醒過程感到困惑,主要表現為對塞德潘盲目自欺式的崇拜及其對自我實現的影響。最終,沃許目睹了塞德潘對產后的彌麗的殘忍態度,這一幕徹底改變了沃許的命運。塞德潘對彌麗的冷酷殘忍讓沃許對他的最后一絲希望也徹底破碎。絕望涌上心頭,他曾經視為英雄般的形象在他心中瞬間崩塌。此時,沃許的自我實際上已經覺醒,本我的重要性已經不復存在。
福克納絕妙地設計沃許最終揮向塞德潘的鐮刀,就是之前向塞德潘借的那把“舊鐮刀”,這象征著塞德潘終將用自己的鮮血來贖回過去的罪惡。沃許的仇恨來源正是塞德潘對他人格的侮辱,尊嚴的踐踏,最終喪失希望的沃許,點燃了棚子,也殺死了他的家人。沃許的自我覺醒雖然曲折漫長但是震撼人心,同時,這種自我覺醒的方式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他的報復也終要自食其果,走向毀滅的結局。但這對心死的沃許來說也是另一種超脫。
然而,如果沃許也處于白人上流社會中,他就不會依附于塞德潘,喪失自我,以致獲得自我覺醒時付出巨大的代價,最終也不會在自我和本我的沖突下陷入瘋狂。從小說中可以深切感受到白人社會中,財富和金錢才是硬通貨,上流社會的虛偽和殘忍,以及窮苦人民沃許對自我覺醒的艱難和無奈。
四、時代的創傷
作為心理學領域的先驅,弗洛伊德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貢獻對現代心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精神分析理論為當代心理學奠定了基礎。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創傷的概念,這為他后來提出的精神分析學說打下了基礎。此外,這一理論還對現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以及小說文本剖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精神創傷學理論作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是當代文學創作中常見的主題之一。許多小說家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都飽含著對創傷和心理缺失問題的探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導論》一書中,對創傷下了完整的定義:“如果在很短暫的時期內,某個經驗使心靈受到極其高度的刺激,致其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去適應,從而使其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4]弗洛伊德在20世紀時,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納粹反猶主義的迫害,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他的研究方向也發生了改變。他開始超越以往對個體無意識、性和欲望的分析,轉而關注現代文明和現代人所經歷的情感創傷。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和《悲傷與抑郁癥》兩部著作中,提出戰爭、意外事故、親人的喪失、失去愛人等是引起人類心理創傷的外部根源。
通過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創傷理論分析福克納描寫沃許內心充滿缺失感和時代造成的創傷的敘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真實歷史下被壓迫的沃許最終憤怒的爆發和自我的覺醒的曲折經歷。歷史上的美國南方是種植園經濟與等級制的社會。福克納對沃許內心的描寫為讀者提供了理解沃許心理變化和痛苦經歷的依據,美國南方的歷史為福克納的創作提供了真實的素材,小說中出現的“舊鐮刀”“黑人女仆”“馬廄”等元素都帶有濃厚的南方氣息,提醒著我們那段真實的歷史。在當時的美國南方社會,“在南方,一個人擁有廣闊的農田和許多奴隸,就會被認為是上流社會中的顯赫人物。所謂的‘精英們相信,在這個地區,要么是奴隸主,要么是被他人控制的奴隸。那些擁有廣闊農田和奴隸的人被視為上流社會的顯赫人物,而在南方,對他人的服從被視為‘失面子的一件事情”[5]。在如此殘酷的社會競爭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大量的犧牲品,其中既包括黑人,也包括許多處于社會底層的白人。沃許就是這眾多底層白人犧牲品之一。在當時的美國南方社會背景下,像沃許這樣的“窮白人”與黑人奴隸沒有區別,甚至不如能干活的黑人。沃許一生過著近乎赤貧的生活,忍受著生活的重壓,他的人格尊嚴被踐踏,甚至連自己的外孫女都要獻給主人。這樣的生活充滿了苦悶和壓抑,但他們只能按照本能行事,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不得不屈服于主人,討好塞德潘。
五、結語
綜上所述,福克納的小說為讀者預留了無限的遐想空間。通過閱讀,讀者能夠深切感受到在白人統治的社會中,底層人民對于自我覺醒的掙扎與困境。主人公沃許的命運注定是悲劇的,但是這種不可避免的悲劇足以給人震撼,引人深思。故事的結尾也是用這種悲劇呼喚著人的“尊嚴”,呼喚著人的信仰的重建,底層人民必須努力實現心靈的釋放,爭取自己的尊嚴。只有當他們看透社會本質,鼓起勇氣去尋求心靈的解放,才能更好地生活,獲得尊嚴和人格的肯定。因為福克納認為人類就是經歷著從毀滅到重生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自我的完善。他關注的是人類如何從困難的現實中走向未來,這也正彰顯了人類的不可摧毀性。同時,福克納的作品為現世提供了許多思考和啟示,引導思考社會的不公和個體的自我價值,激勵人們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尊嚴。
參考文獻
[1] 巴赫金.詩學與訪談[M].白春仁,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88.
[2] 夏君.弗洛伊德主義對福克納作品的影響[J].牡丹,2015(16).
[3] Faulkner W.Wash[M]//The Portable Faulkner.Malcolm Cowley,ed.Penguin Books,1985.
[4] FREUD S.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M].London:Vintage,1917.
[5] Joyner C.Sutpen's Honor: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Historians[M]//Faulkner:A Chievement and Endurance.Tao Jie,ed.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