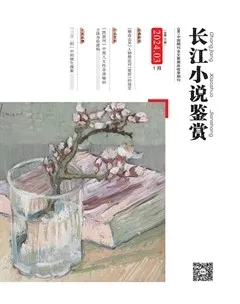勞倫斯小說《白孔雀》中原始自然與工業文明的對立
常夢嬌
[摘? 要] 《白孔雀》是勞倫斯的處女作,它以20世紀初期的英國鄉村為背景描寫了在現代物質文明的沖擊下青年男女在戀與愛的過程中面臨的種種阻礙。工業化革命最直接地破壞了原始自然的和諧與寧靜,在生態自然與文明的對立下,理想與現實的困惑給人們帶來痛苦的體驗,并使人們陷入倫理道德的掙扎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異化。勞倫斯以自己獨特的精神視角和塑造藝術將人們引入一個完整而美妙的自然生態世界,表現出了他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向往以及對機械文明價值觀的批判。
[關鍵詞] 勞倫斯? 《白孔雀》? 現代文明? 自然觀
[中圖分類號] I106.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3-0064-04
勞倫斯是20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主題多樣又相互關聯,大部分作品皆取材于他的自身經歷與生活感悟,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勞倫斯一直懷有原始的自然情懷,提倡人的自由發展與自然生存,他厭惡工業文明與商業精神給人類帶來的精神與肉體的沖擊,過著漂泊的生活,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在文字當中,對現代文明背景下的婚姻、家庭、兩性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人類靈魂深處進行挖掘,其作品對20世紀的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白孔雀》創作于勞倫斯的青年時代,其故事發生地是一個平靜原始的純粹世界,青山綠水的英格蘭中部農村,萊蒂和喬治兩個青年人在勞動與生活中逐漸產生愛慕之情并陷入愛情的漩渦,在一番掙扎之后,理性的現實生活驅散了天真的愛情,萊蒂拋棄了純真美好的自然之愛,選擇可以給自己帶來優渥生活條件的勢利主義者礦工主萊斯利。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打擊下,喬治意志消沉,迎娶了同樣精神空虛的梅格,接受了墮落的人生,兩對青年人均走向了錯誤的婚姻道路,靈與肉的撕裂感讓他們陷入精神困境。
一、自然觀與生態思想
原始自然與農耕生活一直是勞倫斯筆下的歌頌對象,在工業文明逐漸發達的時代,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被推到了邊緣,勞倫斯就是在此背景之下試圖擺脫物質生活和社會帶來的困擾,遠離衰落的文明而尋找自己理想的烏托邦之境,而原始的自然生活就是一塊美好純粹的凈土。在這種理想的家園里,自然萬物都充滿力量,人們作為自然之子有著強健的四肢、充沛的活力,四季輪回變換,景物從蔥蘢到枯寂,色彩從翠綠到秋黃,充分顯示出大自然的饋贈、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勞倫斯的原始自然觀念以倒退來探索人類文明的進步,用最原始的尋根理念來解釋現代現象,在原始的自然觀念之下,他又在宗教中找到了美好的“伊甸園”,這也是勞倫斯的原始自然觀念中的重要構成部分,用宗教本性來追憶曾經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場景,以此對抗工業文明。在此層面上,勞倫斯將小說中的原始文明神話化,代入人類古老的集體無意識,抒發的是人類心靈深處最自由健康的本能和直覺。勞倫斯在宗教的伊甸園中進行自我尋覓,為兩性之間注入充滿活力的感情關系,顯示出只有回歸人的原始本性,才能填補工業文明帶來的精神空虛和肉體墮落的弊端,以此來回歸自然。
勞倫斯在《白孔雀》中多次引用《圣經》里的背景或景物來隱喻故事的發展趨勢,同時善于用單純的景物來表現人物變化中的情緒變化,賦予自然景物以生命氣息,它們可以隨著人的心情而轉變,以顯示出主人公的情感立場和隱藏命運。在《禁果的誘惑》一章中,勞倫斯巧妙引用《圣經》中亞當和夏娃的故事暗指喬治和萊蒂的關系。燦爛明媚的一瞬間,夏娃在伊甸園,亞當的身影也投射在草地上,兩人在池塘的堤岸上通過對各種野趣的把弄表達出了自己的情感立場,單純的自然之子喬治懷著熱烈的愛,而萊蒂卻被物質束縛,牽掛著與萊斯利的訂婚儀式,像抱緊常春藤的樹木,不能像云雀一樣自由自在地幸福生活。而在《牧歌與牡丹》中,更是在一個愛情悲劇故事下,以兩人的不同態度來暗示了兩人的結局。
勞倫斯在人與自然的天然聯系之中追尋具有生命力的勞動、健康自由的身體、兩性和諧的愛情關系、回歸自然的原始生命,為此來構建理想的“伊甸園”,這種自然生態思想在《白孔雀》的背景布置和具體書寫之中可見一斑。勞倫斯對原始自然充滿了向往與熱愛,周圍的植物意象豐茂而充滿活力,象征著原始生活中人類的完美身體結構,一個完整的全人具備活的思想、精神、意識,在生活中獲得全方位的發展,“首先要由人的身體去感知生活,而不僅僅是依賴理智或純粹的精神。”[1]在勞倫斯看來,身體是人類生命的外在顯現形式,象征著具體的生命價值,而生命的本能就是追求人的自我實現與價值,有生命的地方就存在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又是個體獨立性與完整性的重要體現。小說中極力描寫了美好的自然風光與自然寵兒喬治的身體之美,“我的朋友是個年輕的農民,結實的身體,褐色的眼睛,一身白皮膚曬得黝黑,生出了塊塊曬斑。”[2]用身體的天然特征來表現個體的社會位置與品格發展。極具生命力的主人公喬治,一個年輕的農夫,身材結實,褐色的眼睛,白晳的皮膚在陽光的饋贈下已是曬得黑黝黝。婚前的喬治體格勻稱、四肢健壯,充滿了自然原始活力,他強健的身體像是一個巨大的生命體,是傳統生活與生命的典型代表,遠離工業文明沖擊與資本主義的侵蝕,在自然中棲身,正是勞倫斯向往純粹原始自然與理想自然觀的一種體現。
二、工業文明下的哀歌
勞倫斯是站在時代的交匯點來俯瞰工業文明給原始農村帶來的沖擊,在資本主義和自然尋根的矛盾下,做出選擇成為個體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新舊沖突、自我與他者、理性與感性的對立在他的筆下直接顯示出來。“勞倫斯生活的時代也是英國歷史上工業革命急劇推進的時期,在城市逐步將鄉村吞噬的過程中,英國也開始由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都市社會轉化。”[3]物質的文明沖擊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結構,人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宗教信仰等面臨巨大的挑戰,人們擁有了物質,精神卻處于空虛的狀態。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少見真誠與真摯的愛,或者說真誠與真摯的愛被異化,形成了畸形的愛與關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倫理體系的一些問題,這其中存在“非人化”元素和反叛情緒。
勞倫斯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和它使人異化的缺點,因此仇視現代工業文明,現代文明毀滅了人的自然天性,而他的處理方式卻是用兩性結合這種原始的性愛觀來應對“新事物”,用兩性感情和肉體上的沖突或結合來復歸自然天性。喬治作為現代文明的犧牲品,鑄成了哀歌主題與悲劇結局,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他誠摯樸實,向往純粹的愛情與萊蒂的愛;但是受到文明浪潮的影響,他渴慕文明,學習各種化學知識、植物學、心理學、學習叔本華的思想。面對異化畸形的愛情觀,喬治無力反抗,社會現實使他屈服,在時代的洪流中迷失自我最終與表妹梅格相結合。表妹梅格是一個充滿健康活力,卻沒有文化的人,她只能滿足喬治的肉欲卻不能緩解他心靈與靈魂上的痛苦,這種原始動物繁衍式的愛情麻痹了喬治,靈與肉的斷層使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之子淪落成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附庸者,從而陷入了“瘋癲”狀態。“在瘋癲中,靈與肉的整體被分割了:不是根據在形而上學上該整體的構成因素,而是根據各種心象來加以分割,這些心象支配著肉體的某些部分和靈魂的某些觀念的荒誕的統一體。”[4]喬治的“瘋癲”使他脫離現實生活、脫離生命體自身而處在一種游離狀態,這種錯亂粗俗麻木,擾亂了原始自然生命體的理性運動。從充滿生命力的狀態到精神呆滯,喬治活脫脫像是一個魔鬼,資本主義物質婚姻下的享樂主義讓他迷失自我,現代物質文明與他的原始狀態格格不入,他只能靠與朋友廝混和酗酒來麻木自己,陷入虛無與疾病。在小說的結尾,大家為自己跟他之間那種無形的隔閡而難受不已,而他孤零零地坐在一邊,仿佛一個罪人,在眾人之中身影逐漸變得模糊,暗淡了下去。這時的喬治完全變成一個墮落的行尸走肉,與開頭他的健壯形成鮮明的對比,他渴望現代文明卻又被現代文明反噬,在壓抑變態的“理性”中,他自我改造失敗而成為一個徹底喪失自我、機械麻木的空殼,這是喬治自我性格的毀滅,也是現代文明對人的悲劇性毀滅。
勞倫斯創作探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兩性之間的關系,是著力于物質文明下矛盾的時代給人們帶來的精神信仰危機,物質資料的豐富把金錢交易變成維系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道德倫理問題、人性的關系處理成為參與社會價值體系構建者的焦點。勞倫斯在原始文化中尋找突破工業文明弊端的出口,借返祖思維來進行理性的反思,通過寫時代交織下的各形各色的人從生命的底層尋找人類心靈的救贖,旨在描繪原始自然之美的重要性,在對人類最本真愛的歌頌中對西方工業文明帶來的壓抑扭曲之愛進行抨擊。
三、自然與工業文明對立下的倫理性愛情——異化的孔雀
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農村谷地被橫七豎八的礦井、高大的井架、冒著黑煙的煙囪所取代,到處可見陰沉沉的野草,矮小骯臟的煤灰棚子,與自然原始自然格格不入,形成了自然與文明的對立,而這種對立不僅體現在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上,更是對人的心理與本能的壓制,這種壓制又進一步給現代人帶來異化,造成現代人的悲劇。“自然與文明的對立,純樸自然的田園生活與散發著銅臭的工業文明之間的對立,是本書更深一層的主題。”[5]《白孔雀》創作的時代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較為成熟,工業生產的普及帶來勞資矛盾的日益激化,勞倫斯正是在資本主義現代機械文明中描寫人性的扭曲和倫理道德的矛盾,人性受到本能壓制,這必然會引起文明摧殘人間關系的現代悲劇。文中的每個人物形象都是悲劇性人物,他們都成了現代文明的附庸,勞倫斯通過對青年婚姻生活的沖突描寫反映出男女兩性在靈魂與肉體的對立,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女主人公萊蒂受過高等教育,讀過不少涉及現代婦女的作品,她少女時代活潑聰慧,受到大自然的影響生性自然豪放,充滿青春活力。在與喬治的交往過程中被他生機勃勃的生命力所吸引,兩性的愛情火花就這樣碰撞,在兩個人的心里掀起浪潮,這是一種人類原始的本能,它來自人心底的潛意識,將喬治和萊蒂吸引在一起。其情感立場的出發點本該是誠摯而純粹的,但是處在傳統與現代的文明交織點上,萊蒂在婚姻上表現出了兩重性:一方面,她愛慕喬治,發源于人類原始情感而依偎于喬治;另一方面,她又受到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而傾心于資本家萊斯利,萊斯利是上層社會現代文明的代表,他有地位、有物質,可以為萊蒂帶來富足的物質生活。面對傳統與現代文明的沖突,她選擇了現代物質文明,舍棄了底層的喬治,這種資本主義自私的本性必然使她的婚后生活快速陷入迷茫,靈與肉的沖突造成了她的婚姻悲劇。萊蒂迎合現代文明的倫理道德并在其中逐漸失去自我。在對教堂的場景描寫中,守林人安那貝爾揭示“白孔雀”意象正符合萊蒂,白孔雀傲慢地站在天使的頭頂上,安那貝爾認為那就是女人的靈魂,也可能這就是魔鬼,他將其稱為“卑鄙的畜生”,只會玷污了天使。這個意象是對萊蒂人物的寫照,也是對物質文明下異化愛的本質進行的諷刺。
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在帶領人們走向開放世界的同時,各種矛盾也被激化而蘊藏著巨大的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教訓使得西方人開始反思工業文明,物質文明一旦走向歧途會帶來人的異化,由此勞倫斯的拯救策略是在原始自然思維的帶領下激發人們的意識來扭轉理性異化的局面,通過對宗教和兩性關系的探索來理解現代文明人和原始人,把原始文化與原始思維看成西方現代文明的良策,以此來為麻木的工業文明注入一絲活力。在這個過程中,作者也通過對小說中人物的塑造而認識了自我,參照外在世界對自我進行了完整的建構。“小說家自己就是人類,所以在他和小說的素材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近關系,這在很多其他藝術形式中是沒有的。”[6]小說中的一群青年人從最初生活在夢幻田園中的自然之子變成現代物質文化影響下的資本主義畸形人,勞倫斯揭示了隱藏的生活,警示了盲目樂觀的現代人。他首先刻畫出了現代物質文明下受到壓抑而走向異化人生的個體,從中揭示主人公的本能扭曲,再次來提出解決的方法,即通過回歸原始自然、建立兩性關系以及宗教信仰等方式來發掘生命的本能。在靈與肉的關系中,勞倫斯傾向于兩者的自然平衡狀態,認為人的靈魂和肉體都是個體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性承擔著人的靈魂和理性思維,獸性承載的是人的本能和欲望,因此只有保持兩者的平衡才能真正地回歸到自然狀態,兩性和諧正是作者追求的理想狀態,缺少一方都會帶來情感的失衡。小說中對萊斯利的刻畫則是通過反面效應來警示人們不可打破身體與精神的自在平衡關系,否則只能擁有悲劇結局。萊斯利是一個肉體與精神嚴重失衡的資本主義煤礦主形象,一開始他身體健壯卻空有一副外表,原始自然的生命力沒有在他的身上顯現,機械統治下失衡的人生必然遭到破壞,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他被工業器械所傷害而失去完整的肉體,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缺失下,他顯示的是人的退化。工業化革命的弊端被凸顯,人的一切被機器化,思維和情感成為附庸,現代人的嚴重異化是作者深度思考的問題。“當大多數人對工業文明與技術進步頂禮膜拜的時候,勞倫斯卻敏銳地感受到文明遭到了腐蝕,意識到社會歷史的進步必然以人性的損害為代價,這是極為敏感和超前的。”[7]勞倫斯以回溯追蹤人的動物性來抵抗現代文明對人的侵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脫離了人類的社會性,具有抽象的特點,但是他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對人性自由意志和理性的探索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在此過程中生發出來的對人類道德倫理、精神肉體和兩性情感平衡關系的思考也具有重大價值。
四、結語
勞倫斯致力于探究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類自然本性和人類和諧關系的迫害,并積極提出解決的方法,在古樸優美、充滿生命活力的原始自然中尋找出路,以回歸安寧的自然生存空間。《白孔雀》向我們展現了英國現代社會中自然與文明的對立下深受工業文明侵蝕的人格分裂者,勞倫斯從批判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在其中融入了許多自身的經歷、理想與追求,表現出了工業化物質文明對人類天性的殺戮與壓抑,為此必須革除工業文明帶來的種種弊端,尋覓自然生態、保持人類情感關系的平衡,以恢復人類原本的獨立自我,這是作者對于處理自然與文明沖突的嚴肅探索,對于增強現代文明的問題意識具有珍貴的藝術價值。
參考文獻
[1] 殷企平,高奮,童燕萍.英國小說批評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 勞倫斯.白孔雀[M].劉憲之,徐崇亮,譯.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9.
[3] 羅旋.勞倫斯墨西哥小說殖民話語與主體性嬗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4] 福柯.瘋癲與文明[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5] 侯維瑞.現代英國小說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6.
[6] 福斯特.小說面面觀[M].楊淑華,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7] 徐彬.英國文學的倫理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