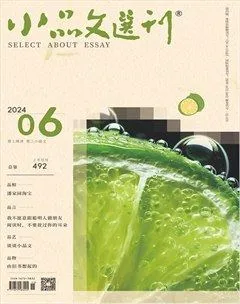臘月里的車站
馬慶民
進入臘月,車站開始人潮涌動,南來北往的,東奔西走的,大家像打了興奮劑似的,個個激情澎湃、干勁十足。那是因為醞釀了許久的鄉愁,將要化作一張歸家的車票——他們要回家過年了。
臘月里的車站,總能看到千姿百態的歸家人,有的拖兒帶女,有的大包小包、肩扛手提……而我印象最深的臘月里的車站,在老家村口一個簡陋的小院兒。
記得我剛上小學那年冬天,村里有幾戶人合伙買了一輛中巴車搞營運,線路會經過幾個鄉鎮、縣城,直通市里。不久,他們就把村口一處小院子改成了村子里的車站。那時的小山村還很封閉,鄉親們幾乎沒怎么見過汽車,所以這個車站的建立就是個“大事件”,成了大家茶余飯后最津津樂道的話題。大伙兒有事沒事就溜達到車站,一遍又一遍地去看那輛中巴車。我們這些小孩子更是喜歡在車站里跑出跑進,喜悅感不亞于過年。
但除了臘月,這輛中巴車并不經常出站,因為從村里去市里也就60多公里,不到兩個小時時間,愿意花錢坐車的人不多。平日里,這輛車五天才跑一趟,剛好都是村里人趕集的日子(逢農歷五、十趕集)。集會那天的乘客大多也都是十里八村提前預約好的,一大早出發,到傍晚集會差不多散完時,車子再晃晃悠悠地開回來,一路風塵,一路歡笑。
那時候的我很想坐一次中巴車,雖然沒有目的地,但我總覺得它應該能帶我去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所以放學后,我經常獨自一人跑去車站,看著那些坐車的人歸來,內心羨慕不已。
那年臘月的一天,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父親去了那個車站,坐上那輛車出了遠門。一到放學,我就跑去那個車站,滿心期待地等著那輛中巴車回來,盼著父親笑意盈盈地走下車來,手里帶著禮物。可我等到天黑,父親也沒有回來。一直到過小年了,我也沒等到父親。除夕父親仍沒回,年后父親還是沒回……直到母親告訴我,不要再去車站了,車子就是個害人的玩意兒。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不肯再去那個車站了,那里成了我不敢觸及的傷心地,哪怕不得已經過,我也會加快步子,看也不看地匆匆而過。
但后來大哥又去了那個車站,他也坐上那輛車,參軍去了遠方。每到臘月,我又開始忍不住去車站等他歸來,等著一身筆挺軍裝的大哥從車上跳下來,一臉笑容。再后來,我也在那個車站踏上了那輛車,參軍去了遠方。從此,那個車站便只剩下母親等待的身影。
如今,我居住在城市里,高鐵四通八達,也通到了我的老家,村里那個小車站早已被現代化的車站取代。又到臘月,我期待著很快又會見到那個車站,它已成了我一年到頭最深切的思念。
選自《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