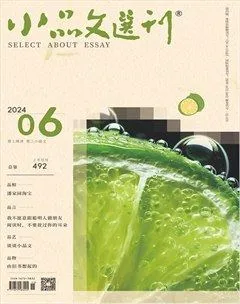慢慢告別
鄧安慶
告別已經預演過兩次了。
第一次臨出發前,嫂子打電話給母親,勸她和父親再在我這里住一段時間,畢竟未來一周都在下雨,回去了也不能做什么,加上我在旁邊應和,母親答應再住幾天。
第二次是一周后,我們已經出發到了蘇州北站,還有二十分鐘就準備上車,我卻發現來錯了站,本該去蘇州站的,再去已經來不及了,只好退票。
回去的路上,我非常自責。母親拍拍我的肩,笑道:“你是想再留我們住幾天,是啵?”
見父母絲毫沒有責怪我的意思,我嘗試著問:“要不住到月末再走?”母親說:“住得越長越走不了啊。”我回:“那就不走嘛。”母親笑笑:“走還是要走的啊,家里我也放心不下呢。”
母親忽然問:“我們在這里住這么久,電費、水費抵得上你一個人用好幾個月的吧?”
我愣了一下,忙說:“那都是小錢,不要在意。”母親嘆道:“在城里住睜開眼就要花錢,買菜要錢、燒水要錢、坐車要錢……一年下來辛辛苦苦,攢點錢不容易的。”我說:“我還年輕呢,掙錢不難的。”
母親看看父親,又看看我:“你爸這個病,不曉得用了你多少錢。你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我說:“爸爸身體健康最重要。等過完年你們再來。”父親痛快地回:“好!”
母親點頭道:“就看你爸到時候的身體情況了。過年前,他差一點沒有挺過來。”停頓了片刻,她接著說:“不過也沒有遺憾了。我們畢竟都來過你這里了。你百事都好,我們也都看到了。”
遺憾。我咂摸著這個詞。對父母,我有沒有遺憾呢?仔細想想,是有的,那就是時間不夠。他們老了,還會越來越老,走在他們身邊,我經常涌起悵痛之情。
我們能在一起的時間,是如此不足。我能做的是盡量地捕捉有關他們的細節,拍下來,錄下來,記下來。但是有一天他們不在這個世界了,我留下的這些有何用?這讓我害怕。
要趁著現在,慢慢地學會告別,不是嗎?他們只能陪我走一段,接下來的路還很長很長。
就像我們日常散步,常常走著走著,回頭看父母,他們落后許多,而我健步如飛時,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盡力地跟上來,埋怨自己拖了我的后腿。被他們“拖”著,何其有幸,又何其害怕,怕的是未來回頭,無人可等。
匆匆,太匆匆,還是到了要說分別的時候。離開的前一天,我拿出筆和本子,請父母在紙上留下他們的筆跡。
母親笑問:“我們寫字太丑咯,寫它做什么?”我說:“你們就寫嘛,我就想留下來作紀念。”
父親念過小學,會寫一些字;母親一天學都沒有上過,只念過掃盲班,不過自己的名字還是會寫的。他們像小學生一樣,乖乖地坐在一起,笨拙地拿筆在本子上寫自己的名字。
我又提議他們各自寫下“父親”“母親”兩個詞,他們一筆一畫地寫下來。寫好后,父親說:“你也來寫嘛。”我又在“父親”“母親”下面寫了“孩子”一詞。
這些年我寫了很多關于父母親的文字,每一次回到老家,我都要記錄與他們相處的日常。而現在他們終于坐在我的家中,也留下了他們的字跡。這算是滿足了我的一點私心。
最后,我請父親寫下“慢慢告別”四個字,父親寫完后,感慨道:“我會好好的,下次再來。你也要好好的,等我們過來。”
回武穴的高鐵是下午兩點多出發。當天上午十一點,母親就開始做午飯,其他菜都端上桌了,唯獨一盤土豆炒肉片還放在灶臺邊。
我本來要端走的,母親攔住說:“這個留著你晚上吃。”我說好。母親又說:“豬油我熬好了,在冰箱里。平時下面條你放點,會很香的。”我又說好。
母親接著想說點什么,看看我,扭頭去洗鍋,聲音小小地說:“你快去吃,菜要冷了。”我沒敢看母親,說了一聲好,轉身出去來到客廳,見父親正在費力地穿褲子,我上前幫他。
父親說:“你買的這條褲子很暖和。”我回:“那就好啊。”父親又說:“你買的鞋子也暖和。”我又回:“春天要來咯,你莫感冒了。”父親說:“要得要得,我爭取不感冒。”
為了方便送父母上車,我特意買了同一班次的車票,只不過我要到下一站無錫站下。坐地鐵,到蘇州火車站,這是我每天上班的路線。
母親攙扶著父親在前面走,我推著行李箱跟在后面。看著候車廳的人群,母親驚訝地問:“每天都這么多人嗎?”我點頭說是。
父親接著問:“你平時上班就是這樣趕來趕去的?”我又點頭說是。他們一時間沒有說話,我忙說:“這太正常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樣的。”
母親看著那些排隊的人,回頭跟父親說:“咱們第一次坐火車,慶兒那時候才多大?”父親說:“五六歲。”
母親“嗯”了一聲,雙手比畫了一下:“就那么大,睡在我們腿上……”說著又看向我:“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這么大了。真是不敢細想。”父親點頭:“是啊,不敢想。”
很快就輪到我們排隊出發了。送父母上了車,大行李箱也在車頭放好了,還來不及下去,車子就開動了。也好,能多陪他們一程。
短短十來分鐘,無錫站就到了,我下來后隔著車窗跟父母揮別。母親一直看著我,說了些什么,我聽不見。車子啟動了,母親揮著手,很快就遠離了我的視野,往家鄉的方向而去。那一刻,其實我并沒有多不舍,甚至可以說是麻木的。
可等我轉身往出站口走去,惆悵的心情陡然升起。等我再次返回蘇州的家中,推開門,是觸目驚心的空曠。
母親炒好的那盤土豆炒肉片還在灶臺上,父親穿的布拖鞋靠在墻邊,沙發上平日看電視時蓋的毯子疊得整整齊齊……
家里的每一處都有他們的痕跡,而我的心就像是怕痛的小動物一般,緊緊地縮成一團,每動一下都是戳心的難過。
沒什么好收拾的,地板上沒有一點污漬,衣柜里的衣服都一件件掛好,書架上纖塵不染……
母親給我留下了一個過分干凈的空間,我待在里面,如同飄浮無根的粒子,不知在何處停留。我又一次一個人了,可跟他們到來前的一個人,心態截然不同。
天一點點暗下來,對面的樓群亮起了燈,能隱約地看到有人在自家的廚房做飯。
我強迫自己起身去廚房,燜好了飯,土豆炒肉片也熱好了,端到飯桌上,習慣性地喊了一聲:“媽,筷子拿一下。”沒有人回應。
他們,真的不在這里了。
選自《人生與伴侶·綜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