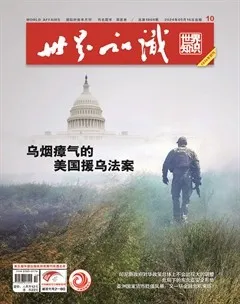《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包藏美國對臺戰略禍心
邵育群
4月2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85票同意、34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2024年印度—太平洋安全補充撥款法案》,該法案要求向美國的“印太伙伴”提供總額81億美元的援助,與《21世紀以力量求和平法案》《烏克蘭安全補充撥款法案》和《以色列安全補充撥款法案》一起通過,幾天后經參議院快速批準交由拜登總統即刻簽字成法,再次顯示出臺灣問題在美國全球防務中的戰略核心性。
法案具體內容及政策含義
《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主要目的是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行動,其中33億美元用于發展美國潛艇基礎設施,20億美元為向臺灣和其他美國主要盟友提供的“對外軍事融資”(FMF),19億美元用于補充五角大樓向臺灣提供的軍事服務、軍事教育及訓練,以及向地區合作伙伴提供的國防物品和服務。
法案的具體內容至少反映出美國“印太戰略”的三重政策含義:首先,美國“印太戰略”在安全上的重點是不斷加大對華軍事威懾。華盛頓戰略界基于“能力決定意圖”的邏輯,認為軍事實力的迅速上升終將改變中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唯有通過強大的軍事威懾才能遏制中方產生“用軍事手段改變印太地區秩序”的企圖;其次,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威懾能力正迅速下降,急需通過強化臺灣及美國其他地區盟伴的軍力,來阻止這種下降趨勢;第三,雖然美國忙于應付歐亞和中東地區的兩場危機,但從中長期看,“印太”才是其關注焦點,美國不會為了目前的兩場并行危機就忘記誰才是其真正的戰略競爭對手。
美國“印太戰略”中的臺灣定位
自美國將中國定位為其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后,其“印太戰略”對臺灣的定位就迅速清晰化。總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緣戰略棋子。2021年12月,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拉特納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臺灣位于“第一島鏈”的關鍵節點,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美國維護在該地區的核心利益至關重要。隨后,美國國內有學者對這種說法提出批評,認為其不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從美國政府的實際舉措來看,把臺灣作為美國地緣戰略棋子的做法是非常明確的,即通過對臺軍售、軍援、軍事訓練,強化臺灣“自身防衛能力”、美臺軍事關系以及臺灣與美國部分地區盟友的軍事關系,加大對中方的軍事威懾,以此防止中方挑戰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霸權。二是關鍵技術提供者,主要就是芯片。美國對華實行大國競爭戰略,競爭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關鍵技術。美國一方面施壓臺灣當局和臺積電,要求臺積電赴美辦廠,以確保芯片供應鏈在美國本土復制,另一方面不斷嚇唬國際社會,聲稱如果大陸“圍臺”“攻臺”,可能因芯片“斷供”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三是意識形態幫手。美國政府在實施其大國競爭戰略時不斷強化所謂“民主對抗專制”的敘事。在濃厚的意識形態底色映襯下,美國政府無視臺灣島內民眾對臺灣當局“反民主”的大聲批評,仍將臺灣作為“印太”地區的“民主優等生”。
加大地區沖突風險
美國“印太戰略”給臺灣的定位,及美國在“印太戰略”框架內不斷強化與臺灣關系的實際作法,正給本地區帶來越來越大的沖突風險。首先,美國與民進黨當局勾連謀求兩岸“永久分裂”。2016年5月,蔡英文在其“就職演說”中以模糊實質內容的說法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在大陸方面稱之為“未完成的答卷”后,不僅未做任何有利于改善兩岸關系的政策立場調整,反而在其第二任期提出“四個堅持”(堅持所謂“自由民主憲政體制”,堅持所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所謂“主權不容侵犯并吞”,堅持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前途,必須要遵循全體臺灣人民的意志”),其中第二個“堅持”是李登輝1999年7月提出的“兩國論”升級版。對此,美國政府公開表示蔡英文當局的政策是“維持臺海現狀”。2024年1月13日,“臺獨工作者”、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獲勝,美國政府在選舉前后通過各種形式對其施壓,根本目的是阻止賴成為第二個陳水扁,推進“法理臺獨”,損害美國在臺根本利益。但是,對賴清德表示將繼續蔡英文的“國防”“外交”和“對中國政策”,美國政府則表示歡迎。由此可見,民進黨提出“新兩國論”,推進“漸進臺獨”政策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樂見并推動民進黨當局和大陸的“脫鉤斷鏈”和“事實分裂”政策,妄圖將兩岸的暫時分離變成“永久分裂”。這種對“漸進臺獨”政策的默許和放縱是本地區安全風險不斷升高的最直接原因。

其次,美國不斷加大對臺軍售、軍援和軍訓,不僅不會提升其所謂“對華軍事威懾能力”,反而會進一步削弱中美就臺灣問題曾經達成的基本共識,直接沖擊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中美在三個聯合公報中明確了美臺發展的是“非官方關系”,而且美方在《八一七公報》中承諾,“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很明顯,出于推進大國戰略競爭的需要,美國違背了自己的承諾,不僅不斷突破美臺“非官方關系”的“天花板”,且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不斷加碼。此次得到通過的《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不僅包括對臺軍售,還涉及對臺軍援、軍訓,以及將臺灣納入美國與其地區盟友的軍事合作。美國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強化其在西太平洋日益不足的威懾能力,但卻忘記了一點,即,只有被威懾對象認為受到威懾時,該威懾政策才是有效的。對中方而言,美方在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問題上不斷挑釁,其所謂的“威懾”政策使其不支持“臺獨”、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承諾失去信用。美國國內一些學者警告說,當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之“威懾”和“再保證”環節失去平衡時,中美關系穩定將受到巨大沖擊,美國威懾政策本身也將對臺海和整個地區造成巨大的安全威脅。
第三,美國將臺灣納入美國與其地區盟伴體系的軍事合作,推動臺灣問題“國際化”,是地區安全風險上升的又一推手。美國的“印太戰略”試圖搭建所謂“柵格狀”(lattice-like)戰略架構,以期最大限度地壓縮中國崛起發展的時空條件。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把臺灣問題作為拉攏盟伴的抓手,一是推出諸多所謂“臺灣有事”的場景,二是不斷炒作各種“時間表”——比如“2027年武力攻臺”,以妖魔化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政策,三是把臺灣問題和性質完全不同的烏克蘭危機作類比,四是在其領導的各種小多邊軍事安全機制(比如美英澳三方安全聯盟、美日菲澳安全合作、美日菲安全合作)合作議程中扯入臺灣問題,五是推動北約向亞太轉向,把臺灣問題作為跨大西洋軍事合作的議題之一。而臺灣當局甘于做美國“印太戰略”棋子,積極配合美國的政策,以此尋求擴大所謂“臺灣的國際空間”。美國政府的上述政策同本地區大多數國家支持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的現實和對和平與發展的根本訴求相違背,是地區和平穩定的真正威脅。
2022年8月美國時任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臺事件后,美國戰略界吸取的“教訓”是,對臺灣的支持必須是實質性而非象征性的,因為后者將會直接引發美中軍事沖突。《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就是美國國會向臺灣提供的所謂“實質性支持”,明眼人都能看到,這種支持的實質是用臺灣民眾的安全和發展利益換取美國霸權在本地區的延續。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臺港澳所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