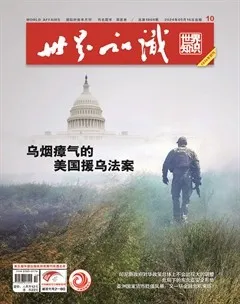俄戰略界拋出“俄羅斯堡壘”論
李勇慧?呂貞蓉

近來,在烏克蘭危機持續的背景下,俄羅斯戰略界學者再次拋出“俄羅斯堡壘”論,以剖析和反思俄文明和國家發展道路走向,將俄斯拉夫主義和新歐亞主義相關觀念推向了討論的高潮。“俄羅斯堡壘”論的提出反映了俄要加強國家的獨立性和主權完整,同時也需要開放;突出俄內部發展的韌性及俄對外政策的調整。然而,該理論也存在悖論。
不是一個新詞
在俄歷史上,“俄羅斯堡壘”一詞曾被用來形容俄羅斯與歐洲的關系,主要是指俄羅斯既要保持獨立,又要學習歐洲文明。具體來說,在與歐洲列強爭霸的年代,“俄羅斯堡壘”被用來比喻沙俄可攻可守。當沙俄戰勝歐洲列強時(如1812年俄法戰爭),這個詞被用來比喻沙俄向歐洲展示其獨立和強大,同時又有權選擇和決定與哪個國家發展關系。而當周圍混亂動蕩時,“堡壘”如同可靠的防御工事,俄可以在其中獨善其身,自給自足。
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后,俄羅斯著名戰略學者、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教授卡拉加諾夫在其《從非西方到世界的大多數》《“戰爭世紀?應該做什么”》一系列文章中使用“俄羅斯堡壘”來比喻俄內部發展與對外政策變化。這一理論受到俄學界和媒體的高度關注,俄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探討和解讀,俄羅斯和歐美媒體也進行了報道。
卡拉加諾夫自20世紀起就對俄外交政策產生著重要影響,此前他作為親西方學者中的一員,其文章專著在歐洲廣為流傳。而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他逐漸將視野轉向東方。
有四層具體含義
卡拉加諾夫的“俄羅斯堡壘”論主要是指:一方面,俄需要生存與發展。從這一層面而言,俄首先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潛力,鼓勵內部經濟、技術、智力、精神發展。當然,這也會產生負面影響,但它刺激了俄尋找非常規方法解決問題,迫使俄有效地集中和引導資源促進發展。另一方面,俄不能被孤立和自我孤立。俄的生存之戰及其向前發展亦離不開不同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如果把“俄羅斯堡壘”理解為自我孤立、自給自足是不對的,而是在西方制裁下俄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卡拉加諾夫還認為,“俄羅斯堡壘”理念應該是俄內外政策調整的基礎。具體來看,“俄羅斯堡壘”論有以下幾層含義:
首先,塑造俄羅斯文明的獨特性。在歐洲文明最輝煌的時代,俄吸收了歐洲文化,俄精英深受歐洲文明的影響。歐洲文化不是俄文化的障礙,是俄文明發展的支撐和前提之一,為俄打開了新視野。韃靼蒙古時期,俄繼承了宗教寬容和文化開放。因此,俄羅斯是東西文化兼而有之,奉行歐亞主義。當前,俄羅斯要發展自己獨有的文化。卡拉加諾夫指出,“一場關于俄羅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和一個獨特文明的未來的戰斗正在展開。俄羅斯正在遠離現代形式的歐洲—大西洋文明。它給了俄羅斯很多,但在很多方面俄已經不再需要了,更何況它越來越違背俄國家歷史傳統、文化態度和價值觀。而歐洲—大西洋文明本身也在迅速退化。”
其次,國際治理無效,需要重新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在俄戰略界看來,西方正在失去統治地位,世界力量的對比將發生根本變化,而針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討論也具有了現實意義。卡拉加諾夫認為,目前的國際治理體系已經崩潰,北約的擴張破壞了歐洲安全體系,大國之間重新展開激烈競爭,聯合國日漸式微。美國對于維護地區穩定失去興趣,轉而開始針對中國、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國挑起沖突,例如激化中印矛盾、破壞朝韓和解等。世界格局舊的領導者已經不具備領導能力,也無力應對目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等日益嚴峻的全球問題。他還指出,西方出于對自由民主制度的盲目自信“縱容”了中國的崛起,美國卷入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一系列沖突,這些舉動都大大削弱了西方陣營的力量。歐洲的領導人無意也無力成為世界格局的領導者,高層戰略思維的喪失使西方政治戰略呈現非理性特點。這些都表明世界需要制定新的規則,而俄羅斯、中國、印度理應承擔新規則和新體系“書寫者”的責任。
第三,俄羅斯文明應該兼收并蓄,故要重新定位外交優先方向。俄羅斯文明傳承了歐洲文明,但當前條件下俄應當在多宗教、多文化的新世界中,學習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正在崛起的國家的文明和文化,更加堅決地轉向亞洲。因此,俄應重新定位俄與各國的關系。
具體來說,對友好國家采取積極合作的戰略。在俄看來,中國是俄發展的主要外部資源,是具有穩定前景的伙伴,而且中國的外交政策理念與俄接近。中俄還極大可能成為新的世界體系的決定因素。而在經濟方面,俄羅斯不應對中國過度依賴,而應通過與土耳其、伊朗、印度、東盟國家、阿拉伯國家、朝韓兩國等的合作,確保合作伙伴多元性。印度是俄天然盟友。俄將印度視為其發展西伯利亞的重要技術和勞動力來源,印也擁有龐大的市場。而針對印度的外交政策應集中在推動印參與歐亞事務、調解中印關系、緩解印巴矛盾等方面,以阻止印度倒向西方陣營。此外,東盟國家也頗具市場潛力,同時俄應預防美國挑起該區域的沖突。對于阿拉伯國家,俄應當繼續保持與埃及、阿聯酋、沙特及阿爾及利亞的友好關系。
對不友好國家采取更具進攻性的戰略。身份政治(一種群體認同需求在政治上的反映)的崛起促使歐洲社會對于家庭、歷史、祖國等概念否定,西方舊有的對于國際關系的理論也逐漸失靈。卡拉加諾夫認為,俄應當與歐洲徹底決裂。在經濟、安全等方面俄則應審時度勢,與歐洲持友好態度的國家建立合作。
第四,專注于內部發展。除了外交戰略,“俄羅斯堡壘”論還著眼于俄內部發展。在精英培養問題上,卡拉加諾夫強調俄精英階層民族化的重要性。他指出,當前俄精英思想上的西化問題十分嚴重。在很長一段時間,歐洲國家打壓亞洲文明,并使俄以“亞洲性”為恥,但是現在非西方的國家和民族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俄羅斯的“亞洲性”將是成功的前提。當下西方的國際影響力降低,它們并不是世界的全部,而俄的信息和知識卻幾乎不涉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甚至中國和印度,有必要迅速加強和擴大與世界不同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聯系,從國家層面重視針對東方、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推動這些學科的教學和發展。

2024年5月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政府成員舉行會晤時表示,鞏固和加強俄國際地位、安全和主權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圖為會前普京與俄總理米舒斯京(左)一同走進會場。
在經濟發展方面,卡拉加諾夫強調需要建立一個從上到下進行控制的經濟體系,與此同時實現從下到上更加靈活的聯系。俄應最大限度地確保經濟的自給自足,同時在合作中避免產生對他國的依賴。因為國際局勢在10~20年內將會持續混亂,為了在世界中為國家和社會的生存進行斗爭,俄民眾必須摒棄個人的主觀愿望和野心。
在內部發展格局上,卡拉加諾夫認為,西伯利亞的廣闊資源保證了俄國際地位,要加大對該地區發展的投入。如果說彼得大帝開啟了通往歐洲的窗口,那么現在就是開啟通往東方窗口的時機。應當在西伯利亞建立“第三首都”,莫斯科將依然作為政治首都,而新首都應當成為俄經濟、軍事甚至精神中心。在交通方面,應將南西伯利亞與北方海航道連接起來,通往中國、東南亞地區;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西部地區建立鐵路通往印度、南亞和中東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應當從國家層面重視針對東方的研究,推動東方語言、民族和文化等學科的發展。
“堡壘”還是“橋梁”?
“俄羅斯堡壘”論的再現與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后俄與美歐關系出現的對抗性和零和性有關,俄學者看到這樣的關系將會長期存在于東西方之間,也深刻說明了俄曾經對西方文明依賴,如今面對新形勢,又要遠離西方文明的矛盾心態。
俄羅斯的斯拉夫派發展了“俄羅斯堡壘”論中的“自我發展原則”,其希望將自身與歐洲隔離,以加強俄羅斯本身的精神原則。他們強調保護自己的精神根源,這種精神根源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國時期。
俄羅斯的歐亞派不反對繼承和開放,但更加強調獨立和自我發展。在這一學派看來,三百年的歐洲大航海時代讓俄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幫助塑造了俄羅斯文化。俄小心翼翼地保留其中的歐洲遺產。但是他們也認為,要解決內部問題,最終要擺脫思想上的西方中心主義,擺脫行政階層的西方人、買辦及其特色思維。2023年俄出臺的新版“對外政策”構想取得了真正的突破,稱“俄羅斯具有獨特的文明”。俄要向北方和南方、西方和東方開放,但主要是東方和南方。
其實,在俄羅斯思想中就有用“堡壘”和“橋梁”來比喻俄羅斯文明歷史的辯證發展。“堡壘”能夠保護自己的精神根源,防御西方文明的擴張和入侵,是獨特的社會政治關系體系和地緣政治利益。“橋梁”能夠搭建本民族與外部世界的聯系,發展本民族文化。“堡壘”和“橋梁”是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只成為“堡壘”將會拒絕對話,必然導致文明民族主義走向極端,但只關注“橋梁”,使外部思想任意輸入,將會侵蝕“堡壘”內部的基礎。波蘭歷史學家瓦利茨基在其《俄國思想史》一書中指出,“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階層總體而言是西化的產物”,俄知識分子的思想深深受到法國啟蒙運動、德國黑格爾哲學、英國實證主義的影響。瓦利茨基還寫到,雖然俄思想家對歐洲思想耳熟能詳、奉若珍寶,但是正是這些在西歐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最早感受到了俄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特性。
從現在的俄羅斯學者的思考中,我們也能看到他們常陷入到二律背反的矛盾中,糾結于以“堡壘”還是“橋梁”作為文明和國家發展道路的方向。
(李勇慧為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呂貞蓉為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全球化進程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