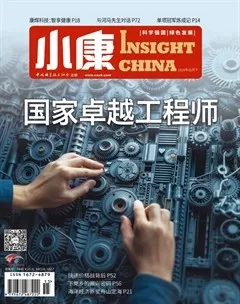李文昌:逐夢地下寶藏
孫媛媛

礦產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礦產資源勘查開發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
李文昌是昆明理工大學國土資源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艱苦的地質勘探事業已有44年。他致力于云南及“三江”地質找礦和研究,由他帶領的“云南省三江成礦系統與評價”創新團隊在找礦實踐和地質理論創新等方面屢獲重大突破,上萬億元的珍貴礦藏因他和團隊的努力而從沉睡千年的地底“浮出地面”,令世人嘆為觀止,更讓云南不負“有色金屬王國”的美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家礦產資源短缺的局面。
長期堅持在地質勘探一線,李文昌先后主持國家科技支撐、973課題和重大找礦工程10余項,在“九五”期間參加西南三江“溝-弧-盆”地質演化研究的基礎上,帶領團隊針對“溝-弧-盆與成礦”進行了系統研究,創新地提出了“多島弧盆成礦論”和“陸內構造轉化成礦論”,揭示了三江地質演化與成礦的內在聯系,合作研發了非線性礦產預測新方法和五套找礦集成技術,指出多個礦帶具有巨大資源潛力。對圈定的找礦靶區開展系統勘查,并和企業密切合作,發現評價了格咱銅礦帶和揚子西緣鉬多金屬礦帶;指導了蘆子園鉛鋅鐵銅等多個大型、特大型礦床的找礦突破;由他提出并負責實施的“云南省三年找礦計劃”,新增資源量潛在價值超過5萬億元。
2024年1月19日,“云南省三江成礦系統與評價”?創新團隊被授予“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稱號。李文昌教授團隊還曾先后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9項。個人獲云南省科技最高獎——杰出貢獻獎,并先后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李四光地質科學獎、“十佳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入選人社部“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國家“高層次人才支持計劃”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國土資源部第一批科技領軍人才、云南省第一批科技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結緣地質,逐夢“三江”
李文昌從小就喜歡親近大自然,對和自然相關的事物都很有興趣。而真正與地質結緣則純屬偶然:上高中時,一支地質工作小分隊借住他所在的學校,他們經常從深山峽谷中帶回一些其貌不揚的石頭,而這些石頭的真身竟是礦石,這使他格外著迷。為此,他填報高考志愿時選擇了地質學校。
因為種種原因,他第一個學歷是在昆明地質學校獲得的。初步接觸地質學,他對于各類礦石與地質架構充滿好奇,這就是他內心渴望了解和探索的領域,因此在學習上格外刻苦和認真。畢業時,他是400多名畢業生中6名優秀畢業生之一。“優秀畢業生”的評選條件非常苛刻,要求2/3的學科分數高于90分,如有一門課成績低于75分就不能入選。
中專畢業后,李文昌在地質隊做了好幾個礦的勘查,包括一些大型金礦,由于業績突出,后來又讀了成都地質學院(現成都理工大學)本科。在中國地質大學老師的反復動員下,繼續攻讀了該校的碩士和博士。身為優秀畢業生,其堅實的理論基礎為后續從事地質工作做了很好的鋪墊。
碩士畢業后,李文昌漸漸鎖定自己的探索領域,他對“三江特殊的地質結構、地質演化歷史是如何形成的”有著濃厚興趣,于是開始這方面的專項勘探。
一個人對于自己專業的熱愛是難以掩飾的,談及從事地質工作以后的狀態,李文昌接受《小康》雜志采訪時,興奮地說道:“地質學博大精深,對于一些區域的解剖實際上是非常有意思的,能夠把地下、地上整個宏觀地結合起來,研究地球的科學,興趣越到后面就越濃。”
隨著在三江區域勘探工作的深入,他開始做研究,開始帶研究生。三江成礦系統與評價系統創新團隊就在這個過程中慢慢開始成型。
“由于一直做項目、做研究,依托持續的項目支撐,形成了不同攻關內容的項目團隊。三江地區地質構造復雜,不同的地址構造單元伴隨演化形成不同的礦產,我們團隊深入研究的主題是每一個地質單元到底是如何演化的,經歷了哪些演化階段,形成了什么樣的礦產?在研究中我們獲得了一些新認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理論突破和指導具有重要的作用。現在針對國家戰略性關鍵金屬做得多一點。”李文昌解釋說。
現在,團隊有教授、副教授以及高級工程師等,穩定的成員有22人,此外,帶的碩士、博士等近100人。
破解三江成礦奧秘
“三江”地區是全球最復雜的造山帶之一,這里地質構造復雜,成礦條件優越,礦產資源潛力巨大,但高山峽谷和植被覆蓋,使得辨認難度大,找礦難度大,地質工作條件十分艱苦。
團隊的研究揭示了多個成礦帶區域成礦規律,并發現了多個大型、超大型礦床,普朗銅礦即是其中之一。
普朗銅礦位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東北部,礦區海拔3400~4500米,是一座以銅為主,伴生金、銀、鉬等多種金屬組成的超大型銅礦床。
在開發之前,由于當時交通特別差,這里人跡罕至,地質工作程度低。1998年,英國比利頓公司開展了三年風險勘查,在普朗發現了銅礦露頭,但打了3個鉆孔后認為,該礦品位低,規模不大,于2001年放棄了該項目。在很多人眼里,國外知名公司都放棄了,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地區就沒有了大礦?
當時任省地礦局副總工程師的李文昌,在給英國公司推薦普朗銅礦之初,已經對該區域有一些認識,加上后來做科研,發現該地區發育規模較大的斑巖銅礦礦化蝕變系統。他認定此區域尋找斑巖銅礦的潛力巨大。
2002年,李文昌爭取到國家項目,并主持編制了《西南三江南段有色金屬基地勘查總體設計》,將勘查目標鎖定在之前發現銅礦露頭的北部。他布置的第一個探槽和第一批鉆孔均揭露到厚大的斑巖銅礦體,實現了突破。
此后,他和團隊與企業合作承擔勘探,控制銅資源儲量達511萬噸(相當于10個大型銅礦),還帶動了周邊紅山、紅牛、爛泥塘等系列找礦突破,圈定的斑巖銅礦帶控制銅資源量達825萬噸。
目前,普朗銅礦已經大規模開發,社會積極效益顯著。
正是這種理論研究結合實地勘查,以及認識上的突破,最終在他人所放棄的礦帶上有了重新突破。普朗斑巖銅礦帶的發現與圈定,填補了我國印支期斑巖銅礦帶空白。通過對云南各成礦帶成礦規律深化研究,李文昌認為,云南找礦潛力巨大。
李文昌說:“三江地區是多個地質構造單元疊合在一起的區域,尤為復雜,要解剖這些礦帶里礦床的形成機制,必須研究它的地質構造演化歷史:如何成洋、洋陸如何轉化,碰撞造山過程如何形成礦床?……所有這些機制都需要我們深入研究。一個帶一個帶地解剖完以后,我們再復盤解剖每一個階段所產生的是什么礦。比如當時是一個洋,它在閉合的過程當中,分別形成什么樣的礦?閉合以后,陸塊和陸塊拼接在一塊兒,又會形成什么礦?碰撞完以后,到如今的構造轉化階段它又形成什么礦?……把這些階段一一理清楚,礦的形成規律自然就出來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江成礦系統與評價創新團隊突破“瓶頸”,破解了“三江”的成礦奧秘。
劉學龍是三江成礦系統與評價創新團隊核心成員之一,2007年在昆明理工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正式進入李文昌老師科研團隊,2010年攻讀博士研究生,也是師從李文昌教授。2013年博士畢業后來到昆明理工大學國土資源工程學院工作,一直從事西南三江地區的地質及礦產研究。他說:“破解成礦密碼,揭示三江成礦規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團隊在負責人李文昌教授的帶領下,翻山越嶺、爬冰臥雪,爬遍山山嶺嶺,去別人沒有去過的地方,看別人沒有看過的地質現象,若干次穿行于‘無人區,很多時候為去看一個礦點或評價一個礦床,可能翻山越嶺數天才能抵達,工棚下、牛棚里都可能是理想的露營地。為了破解成礦密碼,團隊歷盡千辛萬苦,甚至付出生命代價。”
李文昌和團隊一起,提出了“多島弧盆成礦論”和“陸內構造轉化成礦論”等成礦新認識,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在什么地方找什么礦的問題,發現和評價了多個大型、超大型礦床。針對不同的礦床類型,研究探索了西南“三江”高山峽谷和植被覆蓋等地貌景觀區多套有效的找礦集成技術。合作研發了非線性礦產預測新方法和五套找礦集成技術,指出多個礦帶具有巨大資源潛力,帶領團隊對圈定的找礦靶區開展系統勘查,并和企業密切合作,發現評價了格咱銅礦帶和揚子西緣鉬多金屬礦帶;直接指導了鎮康蘆子園鉛鋅鐵銅等多個大型、特大型礦床的找礦突破。
地質勘探艱辛中蘊藏著希望
從事地質工作異常艱苦,風餐露宿是常事,跋山涉水、穿越地質路線,多陡的山崖都要翻過去,多深的山谷也要越過……而他們探尋的正是國家需要的、緊缺的礦藏資源,比如稀有金屬、螢石礦、銅礦等。
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下持續工作是“三江成礦系統與評價創新團隊”常常面臨的生存狀況。
“我們工作的礦帶都是高海拔區,有時被大太陽曬了幾小時后,一場傾盆大雨突如其來,又或是被冰雹打得一塌糊涂。遇到類似種種挑戰,沒有堅強的意志,是堅持不了的。但是那么多年,不管是帳篷被壓垮,還是沒有食物可吃,我們在三江都堅持下來了。”李文昌表示。
有一次去深山老林勘探,團隊將近一個月幾乎沒有供給,“外面的東西沒有辦法弄進來,我們采取就地解決的辦法來度過。”像這樣的艱難時刻是李文昌經常會碰到的。“當面臨突發事件,怎么克服?怎么堅持?這就是對意志的磨練。現在人們都向往城市,向往交通條件好的地方,誰還在這么條件艱苦的環境下工作?但是我們團隊堅持下來了,這是很大的挑戰。”
沖突與兩難抉擇貫穿于勘探路途的始終。有時候,團隊要進山了,原來或許有路的,但找到路很不容易,于是他們找到民工開路,等到以為快要走到頭時,結果發現前面的路完全堵死了。“像這種挑戰,是退還是進?進退都是很難的,因為進來的時候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車推進到很深的地方了,等到退回去的時候仍然是非常艱難的。這種挑戰對人是很有考驗的,意志稍微薄弱一點,我可能就不干地質工作了。后來,哪怕車子走不通了,人也要繼續往前走。因為目標在引領著我們,要完成任務,完成我們的研究。此外,也會遇到懸崖峭壁,山坡很陡峭,是過還是不過?過了之后還能不能回來?這些都是在勘探過程中所必經的挑戰。”李文昌說。
常常為了要完成某項任務,他們早上七點出發,晚上十點才抵達目的地,完全靠兩條腿一步一步完成。在山上走一天,和在平地走一天的難度是無法相提并論的。有一次,在山上一直走到晚上十一點才摸到一條能走回來的路。“在山上你是很絕望的,因為山高林密,有很多野生動物出沒,加之天黑后的密林深處,人是沒有方向感的,要么走山脊,要么走山溝,而溝里的路很多時候是走不通的。只能憑著地質人的經驗摸索著走,地形又極為復雜,當時心里也會害怕。”李文昌回憶道。
不僅有生命的危險,還有健康的威脅。那么,支撐李文昌從事這項工作背后的動力是什么?他回答:我們被礦的規律所吸引,一旦進入其中,不斷發現新的規律和新的認識,自然就對這世界非常感興趣。一方面很艱苦,另一方面也有獲得感,不斷地獲得成果,給予我們繼續探索下去的動力。所以,不論結果與否,我們預測某個區域有礦,一定是要去那里調查驗證的,不管翻高山也好,越峽谷也好,盡管過程很艱苦,但一定要去驗證它。
提及李文昌教授的治學與為人,劉學龍滿是欽佩之情:“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李老師給我們這些學生做出了很好的榜樣。在每次的野外工作中,他帶領我們爬高山,下礦井,總是沖鋒在前,在一次次的工作中,他的言傳身教使我堅定了從事地質科研的信心和決心,是他激勵和指引著我在地質學專業領域里不斷地追求和探索。同時,李老師也像一位慈祥的父親給予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關懷。”
為高質量發展貢獻地質力量
戰略性礦產是國家資源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命脈,中國經濟騰飛,離不開戰略性礦產的有力支撐和保障。
在李文昌看來,地質學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因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依賴資源。礦產資源是重要的基礎支撐,沒有礦業,國家的發展就沒有基礎。只靠農業行不行?只靠互聯網大數據行不行?……沒有資源支撐,很多事情做不了。”
李文昌進一步表示,我國是礦產資源第一消費大國,沒有礦產資源支撐是不可想象的。去年,又開始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立足于國內,同時也要走出去,兩條腿走路才能保障礦產資源安全,這對國家的發展特別重要。“新興產業發展離不開礦產資源的支撐,如果關鍵金屬被他國“卡脖子”,沒有資源,怎么加工這些高新尖的科技設備?所以方方面面都涉及到礦產資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