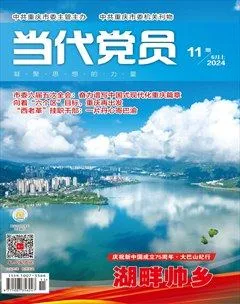湖畔帥鄉
馮驛馭 吳曼禎

4月的重慶,春意盎然、陽光明媚。4月15日,我們向渝東北地區的叢山峻嶺行進,來到大巴山南麓的重慶市開州區采訪。
開州區是劉伯承元帥的故鄉,素有“帥鄉”之美譽。早年,劉伯承離開家鄉參加革命時,彼時的開縣(今開州區)絕大多數群眾依然生活在極度貧困中。1949年12月,開縣和平解放,迎來新生,經濟社會發展由此步入正軌。如今,開州區城鄉面貌和群眾生活水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沿著高質量發展的寬廣大道闊步前行。
15日中午,即將抵達開州城區時,我們首先看到一片廣闊的湖面,這就是漢豐湖。城區的公園、道路、房屋,還有四周的青山綠樹,都倒映在粼粼波光里。湖光山色相輝映,一座“湖畔帥鄉”映入眼簾。
一座湖城的降與升
抵達開州城區時,驟雨初歇。
漢豐湖畔,一旁是湖光瀲滟,一旁是車水馬龍,一幅“城在湖中、湖在山中、意在心中”的詩意畫卷在眼前徐徐鋪開。
此行第一站,我們來到位于漢豐湖畔的開州博物館,只為讀懂這座“湖城”。
“1800多年前,漢昭烈帝劉備為開縣賜名‘漢豐,開州歷史上第一次有了獨立的建制。彼時,只有漢豐縣而無漢豐湖。”開州博物館館長王永威介紹。
2007年,三峽大壩即將啟動175米水位試驗性蓄水,開縣舊城區開始全面搬遷。廣大群眾積極配合移民工作,離開故土,奔向新的家園。隨著三峽大壩蓄水至175米,14.8平方公里的漢豐湖隨之形成。開縣舊城區漸漸沒入湖面之下,一座濱湖之城新生了。
年輕的開州新城,將走上何種發展道路?
如今我們看到的、開州人民享有的美景,正是開州當地始終堅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新城區規劃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把漢豐湖的“黃金地段”留給生態的成果。
漢豐湖形成以來,開州區保持漢豐湖自然岸線率超過80%,清運漢豐湖庫底老城搬遷遺留垃圾及底泥1500萬立方米,打造230萬平方米的園林景觀帶,修建親水步道15公里……
“說起漢豐湖的保護,我們是有底氣的。”開州區生態環境局黨組書記、局長趙新華介紹,近3年,漢豐湖水體綜合營養指數穩定小于50,群眾對生態環境滿意度有效提升。特別是2023年,漢豐湖入選“第二批全國美麗河湖優秀案例”,與浙江嘉興南湖、新疆賽里木湖等并列。
開州給漢豐湖以生態,漢豐湖以生態反哺開州。近年來,開州區環湖夜經濟消費規模達85億元,其中旅游綜合收入達78億元;舉辦國際半程馬拉松、漢豐湖農民龍舟大賽等賽事;成功創建國家園林縣城、國家衛生縣城……如今47平方公里47萬人的開州新城,因湖而旺,蛻變新生。
結束一天的采訪后已是傍晚,漢豐湖深藍色的水面倒映著開州的萬家燈火,近處的喧囂與遠方的安寧相得益彰。我們不禁感慨,如今的開州人民,正在新家園愜意“享湖”。
一只候鳥的去與留
漫步在漢豐湖畔,一個個特殊的池塘吸引了我們的目光。這些池塘的水面與湖面等高,窄窄的步道將池塘同湖面隔離開來。池塘里還種有荷花等水生植物,白鷺、野鴨等在此嬉戲。
“越來越多過去不常見的鳥類出現在了我的鏡頭里。”開州區自然保護地管理中心負責人黃亞洲是一位鳥類攝影愛好者,這些年,他的鏡頭記錄下了這些“精靈”。
他的鏡頭中,出現了中華秋沙鴨、青頭潛鴨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身影。“每年到漢豐湖越冬的雁鴨類候鳥超20種,數量達2萬余只。”黃亞洲說。
“不久前,我與同事泛舟漢豐湖上,驚喜地拍攝到斑嘴鴨正在繁殖。”黃亞洲說,這意味著漢豐湖生態環境優良,候鳥可以留在此地生存繁衍,變為“留鳥”。
“稀客”的到來和湖面的熱鬧,見證著漢豐湖的蝶變。
黃亞洲告訴我們,上文提到的池塘名叫“基塘”,是漢豐湖濕地保護的主要載體之一。他說:“十多年前,這些土地還是讓人頭疼的消落帶。”
消落帶的出現源于三峽水庫運行后水位季節性漲落現象。每年漢豐湖水位都會發生20多米的變化,受水位變化影響的土地區域即稱消落帶,其存在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減少等風險。
“為了治理消落帶,我們首先篩選了能在消落帶存活的植物,將其種植在消落帶上,發揮生態緩沖、景觀美化等功能。”黃亞洲介紹。
此外,開州區共實施約2000畝基塘、林澤等消落帶治理措施。種植在這些區域的植物,在水位下降消落帶露出時可作為生態景觀,水位上升被淹沒后也能正常生長,起到凈化水質、保持水土的作用。
消落帶治理不僅讓漢豐湖避免變成“臭水湖”,也為開州創造了巨大的生態價值,還在全國范圍內留下了寶貴的消落帶治理經驗。如今,湖南、湖北等地在治理消落帶時,就學習借鑒了漢豐湖的治理經驗。
來自安徽的黃亞洲2011年開始從事漢豐湖濕地保護相關工作。十多年來,他和鏡頭里的那些鳥兒一樣,把家安在了漢豐湖畔,成為開州的新居民。“開州這座城市很有親和力,我很喜歡這里。”黃亞洲說。
一片茶葉的苦與甜
離開風景如畫的漢豐湖,我們出發前往曾是重慶市十八個深度貧困鄉鎮之一的開州區大進鎮。
如今,大進鎮不僅順利脫貧,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質的改善,脫貧攻堅時期形成的茶葉產業,如今在鄉村振興新時期更是進一步煥發生機與活力,為群眾帶來新希望。
正午艷陽高照,我們駛上蜿蜒的山路,進入一片碧綠的茶園。
紅旗村村民廖伯軒剛剛結束上午的勞作,熱情地招呼我們去她家坐坐。說起茶葉產業帶來的變化,廖伯軒感慨萬千。
多年前,廖伯軒與丈夫在廣東務工,其間,丈夫不幸患病,整個家庭為治病花光積蓄,陷入貧困。脫貧攻堅期間,在大進鎮黨委、政府以及幫扶單位的悉心幫助下,廖伯軒一家脫了貧,但返貧風險依然存在。2022年,在大進鎮黨委、政府建議下,廖伯軒承包了紅旗村10多畝茶園,第一次有了自家的產業。
“自家有了產業,能就近照顧家人,生活比以前好多啦。”廖伯軒充滿希望。
作別廖伯軒,我們繼續沿著茶山攀登。不多時,眼前出現一座幾乎占據了整個山頂的茶園。
這座茶園的承包人是紅旗村村民、老黨員鐘義登。“最初,大進鎮要發展茶葉產業,許多村民都不支持,認為茶葉產業成本高,利潤兌現周期長。”鐘義登回憶,“我去鎮上聽了幾次介紹,心想咱們搞茶葉產業有前景,更想到需要有人站出來,承包一塊地,干出點成果給大家看。”
于是,2021年,鐘義登主動承包了130畝地用于發展茶葉產業。歷經一年多辛苦耕耘,2023年春,他的茶園迎來了初采。過去一年,茶葉產業為鐘義登一家帶來了40多萬元收入,也為其他村民帶來了發展希望。
“今年,咱們還要繼續努力,爭取能再采一次夏秋茶,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咧!”鐘義登說。
一片茶葉,對廖伯軒、鐘義登等大進鎮群眾來說,已是苦日子與甜日子的分界線,更是大進鎮從貧窮走向振興的關鍵一招。
大進鎮黨委書記全修橋介紹,大進鎮脫貧攻堅時期形成的支柱產業,同樣成為鄉村振興新時期的支柱產業。2023年,大進鎮茶葉產業綜合產值達3000萬元,預計2024年能達到5000萬元。
再次站在紅旗村的山麓,放眼望去綠油油的茶山延綿起伏。2019年,我們到大進鎮采訪時,茶園建設方興未艾,茶樹也才剛剛種下;如今座座茶山欣欣向榮,助力群眾增收致富,邁向更美好的生活。聽著這些故事,我們由衷地感到高興。
一曲山歌的憂與喜
次日,我們出發前往滿月鎮雙坪村。在盤山公路上,隨著海拔攀升,鬧市的喧囂慢慢隱去,山間的云霧越來越濃,四周環境越來越靜謐。
“悶悶沉沉眼不睜,昨晚陪奴到四更。四摔話兒都談盡,沒問我是好大生!”
忽然間,一曲山歌在群峰間響起,令人心神一振。我們感嘆,寧靜的山巔美景,一曲嘹亮的山歌來點綴正合時宜。
幾分鐘后,我們尋見了這位歌者。他叫凌發軒,是滿月鎮雙坪村村民。他還有個響亮的綽號——“山歌王”。
“20世紀70年代,我還是個孩子,就經常聽到大人們唱山歌。”老凌回憶,他最早聽到的山歌叫“薅草鑼鼓”——集體勞動時,在田坎邊上,一人負責唱,一人負責敲鑼應和,從早到晚,給勞動群眾打氣。當時,還是放牛娃的凌發軒,就成了“山歌迷”。
山歌雖有趣,但雙坪村的發展情況卻堪憂——原來雙坪村由尤坪、后坪兩村組成,其中后坪村三面環山一面臨崖,交通條件惡劣。凌發軒回憶,20世紀80年代,從后坪村前往大進鎮場鎮,單程就要走上三天三夜。
1999年,后坪村人下定決心,在海拔高約1700米的絕壁上鑿出一條路。這個看似天方夜譚的想法,后續被證明是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2001年,歷經艱險,懸崖天路貫通,凌發軒成了天路上的首批駕駛員——當年,他聽說開州城里舉行青年歌手大賽,便騎著摩托,冒著大雨,從后坪趕往開州城區參賽。
“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天!”凌發軒感慨。
滿月鎮是開州區最北面的鄉鎮,一度也是開州區最偏僻閉塞的鄉鎮之一。滿月通往外界的第一條公路,直到1980年才貫通。此后40多年時間里,滿月干部群眾一茬接著一茬干,逐步硬化、美化出村路、旅游路,橫亙在大山云霧間的城(口)開(州)高速公路,也從滿月鎮穿隧架橋而過。
路的改變,為滿月帶來產業之變。2021年,滿月鎮被確定為全市鄉村振興重點幫扶鄉鎮,如今正扎實開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工作,發展起藍莓、休閑民宿、生態礦泉水等特色產業。其中,馬扎營片區還被納入大三峽大秦巴接合部國際旅游度假區規劃,正申報創建市級旅游度假區。
旅游業發展起來了,相關的文化活動也辦得有聲有色——2023年8月,“滿月山歌音樂節”在滿月鎮舉辦,凌發軒登上舞臺,為來自各地的群眾獻上來自大巴山的歌聲。
如今,每逢旅游旺季,會有十幾輛汽車停到凌發軒自家開辦的“山歌王農家樂”院壩里,游客紛紛招呼請他唱山歌。“他們都是我的‘粉絲呢!”凌發軒自豪地說。
4月18日,我們離開滿月鎮返程時,經過了開州城區、漢豐湖畔的軍神廣場,劉伯承元帥的塑像英姿颯爽,望向遠方。
循著這目光,我們看向美麗的開州山水,不禁回想,100多年前,劉伯承元帥從這里出發,懷著為中華民族求解放的崇高理想,踏上革命征途。
如今,開州區已在推動川渝萬(州)達(州)開(州)地區統籌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成為魯渝東西協作的“重慶范本”,正朝著建設現代化新開州的目標穩步邁進。
這盛世已如您所愿。今朝開州充滿希望的湖光山色,正是今人對革命先烈美好理想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