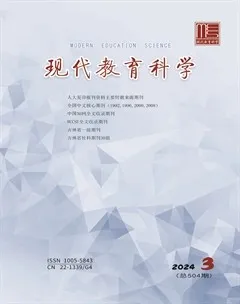解構與重構: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勝任力的優化理路
李思文 向天成
[摘 要] 鄉村定向師范生是鄉村教師的重要補充來源,教學勝任力作為衡量教學水平和綜合素質的重要指征,是其專業素養的本真體現,也是其基于鄉村教育的專業表達。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勝任力包含教學認知、教學能力、教學品格3個方面,但當前存在鄉性退場下教學認知失衡、技術裹挾下教學能力失準、理性規約下教學品格式微等問題。進一步剖析問題產生根源發現:條件性原因在于教學認知與文化割裂的沖突、直接性原因在于教學能力與制度預期的摩擦、本體性原因在于教學品格與工具理性的博弈。為進一步提升教學勝任力,打造高質量、專業化的鄉村教師隊伍,需注重教學認知——喚醒文化自信,實現精準化培養;提高教學能力——融通學踐場域,提供針對性指導;培育教學品格——構筑共治格局,強化持續性激勵。只有全面提升鄉村定向師范生的教學勝任力,才能以高質量鄉村教育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關鍵詞] 鄉村定向師范生;鄉村教師;教學勝任力;教學認知;教學品格
[中圖分類號] ?G6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5843(2024)03-0121-08
[DOI] ?10.13980/j.cnki.xdjykx.2024.03.019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其中振興鄉村教育是建設高質量現代化教育體系的關鍵一環,也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的重要基礎。鄉村要振興,教育必先行。而振興鄉村教育的關鍵是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核心是培養一批又一批優秀的鄉村教師[1]。如今,鄉村地區已從追求“有學上——為盡可能多的人提供盡可能多的教育機會”這一教育基本均等的基礎階段目標轉向追求“上好學——為盡可能多的人提供盡可能好的教育服務”這一教育優質均衡的高位階段目標。優質均衡、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成為新時代鄉村教育的目標追求。可見,鄉村教育基礎階段目標停留在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階段,而高位階段在于追求最大范圍優質教育的鵠的。質的均衡作為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高位取向,其核心邏輯在于鄉村教師專業素養。教學勝任力作為教師專業素養的本真體現,與職前培養這一重要環節息息相關。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培養是實現教育扶貧,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對于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只有全面提升鄉村定向師范生的教學勝任力,才能以高質量鄉村教育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勝任力”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學教授戴維 · 麥克利蘭(David·C·McClelland)于1973年正式提出的。勝任力是指個體高質量完成某項工作并取得良好績效的個人特征,是知識、技能、能力、信仰、動機的混合體[2]。教學勝任力是勝任力概念在教師教學領域上的延伸。學界關于教學勝任力的研究較為豐富,雖然對鄉村教師有所涉獵,但并未深入研究定向師范生這一群體,且多為應然層面“結果導向”的基準性、即時性測量,缺乏從實然層面“過程取向”的鑒別性、發展性考量。由于該群體在入學前就與生源地教育管理單位簽訂定向合同,對報考決策和職業規劃缺乏全盤考量,易受父母觀念和家庭資本等單向度影響,后續培養成效及履約意愿值得深入探究。鄉村定向師范生作為鄉村教師隊伍的儲備軍,教學勝任力作為教師的核心素養和關鍵能力,一定程度上折射其培養成效和勝任情況。以鄉村定向師范生為對象,以“報考—畢業”為完整時間鏈,基于共時性視野對其教學勝任力進行研究,基于歷時性視野管窺其教學勝任力問題及成因,以期為提升其教學勝任力、促進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提供優化路徑。
一、錨定:教學勝任力問題表征
在提取相關研究“共性”基礎上結合鄉村定向師范生“特性”,將其教學勝任力表征為教學認知、教學能力和教學品格。因此,本研究主要從這3個維度對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勝任力問題進行分析。
(一)鄉性退場:教學認知失衡
教學認知是發展教學勝任力的邏輯起點。第一,鄉土知識游離。鄉村定向師范生的知識結構優化既要“取材現代”,掌握現代教育所倡導的教育觀念、結構框架和研究范式,也要“取材鄉土”,掌握鄉村教育所內蘊的鄉土知識、鄉土傳統和鄉土智慧[3]。橫向對比來看,教學認知是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勝任力發展的突出短板。現代知識被冠以“自由、科學”等進步性贊譽,而鄉土知識被貼上“僵化、落后”等污名化標簽。在城鄉二元對立思維立場、教育改革中的技術導向以及新課改中的城市取向等裹挾下,鄉土知識囿于發展勢差、地理區隔而處于邊緣化境遇,難以內嵌于師范院校的培養模式,更遑論進入鄉村定向師范生的認知結構。第二,鄉土文化缺失。由于鄉土課程設置缺位、鄉村教育實踐缺失,鄉村定向師范生更偏好迎合現代化公共性的考評標準,忽視了鄉土化專業性的內在要求,容易造成鄉土文化內化的機械與滯后。守護鄉土是鄉村定向師范生責無旁貸的文化使命,鄉村定向師范生在現代理性的裹挾、技術力量的沖擊以及外部制度的規約下,關涉鄉土文化認同的內容則被“專業主義”所遮蔽,將發展視野局限于“專業之內”,“兩耳不聞鄉村事,一心只念專業經”便是當下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的真實寫照。按照教師職業的標準化、統一化強化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執教素養和教學勝任力,一旦“教師下鄉”便容易產生“水土不服”的鄉土疏離感和“南橘北枳”的教學迷失感。如此,更加快了鄉土文化的認同旁落和情感式微的腳步,進而陷入鄉土疏離懸浮的泥淖,消解其傳承與創新鄉村文化、引領與形塑鄉風鄉序的公共職能。
(二)技術裹挾:教學能力失準
教學能力是衡量教學勝任力的重要指標。對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勝任力進行理性反思,推演出現行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出于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目標,合乎現代理性與技術理性,但接踵而至的是鄉土理性的缺失與教學技術理性的偏狹。一方面,教學能力技術化。在人力資本視域下,教學技術理性被賦予了主導性地位的合法性論證,熱衷于在短時間內掌握普適性的操作邏輯,試圖通過掌握標準統一的教學技術驅動教學能力提升。但在專業資本視域下,駁斥了教學是“關于隱性的程序性知識的務實技藝”“一系列簡單的技巧”等刻板印象[4],需要重新確證教學的專業性、復雜性與協同性。在教學技術化取向和唯技術化思維范式的影響下,強化了教學內容的確定性和教學過程的統一性,固化了鄉村定向師范生作為教學程序搬運工和教學方式復制者的身份定位,其教學能力被窄化為“表演能力”。一旦脫離所屬場域,教學能力便失去根基、難以固存。在這種“水土不服”的現實境遇下,雖能保證鄉村定向師范生按部就班、亦步亦趨地“能上課”,但難以因地制宜、應時而變地“上好課”。另一方面,教學能力扁平化。由于任課教師缺乏基層教育經驗,不論是練習指導還是親身示范都過于理想化、書面化,加之鄉村定向師范生試講、說課對象的替代化、虛擬性,這種“缺場”的離身化教學實踐只能為其提供局部參與感,練習效果大打折扣。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將這種擺脫具體情境的時空延伸稱為“脫域”,這種脫域為個體贏得一種無與倫比的內在與外在的活動自由,但這種脫離束縛所獲得的自由帶來的卻是不安和焦慮[5]。見習實習作為教學能力提升的重要載體和抓手,自然秉持城市取向與就近原則,實踐場域通常遠離鄉村地帶,加之一線教師有所顧慮,并不放心將課堂下放給定向師范生,所以他們即使上臺實踐后也難以得到針對性指導和實質性幫助。教學實踐類型單一化、教學實踐參與形式化、教學實踐效果模糊化嚴重制約了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能力的全面提升。
(三)理性規約:教學品格式微
教學品格是發展教學勝任力的內源動力。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需要扎根》中寫道:“扎根,或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最基本的需求,但同時它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之一……每個人都需要多重扎根,進而形成他的整個道德體系、理智與靈性所構成的生存環境。”[6]唯有扎根其中,鄉村定向師范生才能獲得完整的身份認同,是實現培養“整全的人”的目標前提。但實際上,鄉村定向師范生在個體理性支配下面臨內外價值失真的雙重窘境。第一,外在價值失真。調查得知,鄉村考生生源大多出身農民階層,源于對父母單向度的服從、基于教師職業光環和定編定崗、減免學費等農村學生的需求關照[7],而觸發尋求互利的報考動機,是出于對風險規避的理性選擇和政策投機,而非熱衷于教師職業與鄉村教育。即使鄉村定向師范生報考熱度居高不下,分數線水漲船高,鄉村定向師范生為了能夠以優惠條件躋身高校并成為一名預備在編鄉村教師毅然決然選擇報考定向師范專業,但在畢業時由于對鄉村教師社會地位、薪酬待遇等外在價值認同度較低,也會引發心理落差與情感阻抗,影響職業認同與從教熱情,甚至產生違約行為。第二,內在價值失真。傳統鄉村教師生于斯長于斯,深受鄉土文化浸潤熏陶,與鄉村地區有著較為緊密的血緣、地緣聯系,其行為邏輯源于對鄉土的文化認同,同時也彰顯對鄉土的深厚情懷。然而,在城鎮化進程的挺進和現代理性的擴張下,加之鄉村定向師范生能培養的向城性,鄉村教育的獨有魅力被遮蔽,鮮明個性被漠視,致使其以一種反感和逃離的心態審視鄉村教育。雖然大部分定向師范生能肯定其專業在鄉村教育的獨特價值,但由于“嚴進寬出”的評審機制和對學業的低要求、松管制,不少師范生在理性規約與同化洪流中暴露出無助和迷茫。外部壓力的缺失難以激發內部情感與動力,專業情感懈怠、低迷則會成為一種學習生活的常態。鄉村定向師范生在對影響自身發展問題上必須直面的愿景與現實、應然與實然的沖突性矛盾中進行權衡取舍,從而造成專業發展的制約性與搖擺性,影響其教學品格。
二、研判:教學勝任力問題歸因
(一)條件性原因:教學認知與文化割裂的沖突
鄉村定向師范生對教學要素的全面感知與深刻理解決定其教學勝任力生發的自覺水平。教學認知的深化與拓展要訴諸具體課程予以保證。課程是學校培養人才藍圖的體現,因此課程設置是否科學合理,直接影響教學質量與培養成效。學科分化有利于知識的系統性、專業性,但學科去背景化的問題,不利于培養整全的鄉村教師。課程的價值取向表明對事物屬性或發展趨勢的認識傾向和價值偏好[8]。第一,課程“鄉”性缺失,文化認同被動化。鄉村定向師范生的課程設置充斥著“向城性”,主要著眼于城市教學的需要,與鄉土文化相去甚遠。定向師范生的課程結構與鄉村地區的特殊屬性在培養目標定位上存在錯位現象,課程內容凸顯的城市取向是對鄉土性、地域性文化知識的弱勢地位的強化[9]。鄉土文化是鄉村教育的底色,課程鄉土性的缺失引致定向師范生鄉土教學認知的局限和鄉土文化認同的被動,不僅在價值層面上消解其參與鄉村建設的主動作為,在觀念層面上割裂其對鄉土文化的理性認知,還在主體層面上遮蔽其本身負載的文化力量,使定向師范生與鄉村社會內生需求相脫節。第二,課程“深”性匱乏,學習過程淺表化。教學認知的全面性與專業性是教學勝任力的應有之義,也是鄉村定向師范生的重要指征。師范院校設計的培養方案與課程安排相對全面,但課程內容的多樣與學習精力有限的矛盾掣肘教學認知的深化,鄉村定向師范生難以在短時間內掌握多學科要領。難怪有同學提及,“鄉村定向師范生雖說是‘萬金油,但其實學得‘四不像”。多種課程冗雜交織招致其學習重心的偏移,學習焦點投至于見效明顯、考核頻繁的課程上,而有些理論性、文化性強的卻因難以直觀量化則被漠視,甚至對課程的價值效用持懷疑態度。課程適切性和靈活性不足、理論性與實踐性脫節,且對于新鄉賢文化資源開發利用不強,教學認知難以有效運用于鄉村境地。加之在“畢業即就業”“有編有崗”的政策保障下,鄉村定向師范生容易產生應付心理,影響其學習投入和內在動機。
(二)直接性原因:教學能力與制度預期的摩擦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教學能力作為鄉村定向師范生必備的關鍵能力,反映其對教學活動的領悟力、教學問題的應對力和教學情境的把控力。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出臺的關涉鄉村教師支持的政策文件,其中都多次提及“定向培養”“一專多能”,彰顯了鄉村定向師范生本土化特征。通過定向招錄的師范生生源存在個體預期與現實境遇的矛盾,因疏離鄉土文化底蘊,教學能力也難以契合鄉村情境。第一,培養過程“離鄉化”。文化主體指個體長期浸潤于文化,其思維和行為方式、生活方式體現著文化,又在代際相續中傳承、更新著文化[10]。文化回應教學法是教師將教學內容與本地文化要素關聯起來,確保教學內容和本地文化的適切性,最終實現文化傳承和創新的目的[11]。鄉土性是鄉村教育的文化底色,也是鄉村定向師范生教學理解與鄉土文化之間的聯系,表現出對鄉村社會的價值導向和情感指向。培養院校在教師教育教學現代化的感召下,缺乏開發以鄉土性地方性知識為主題的課程資源,盲目照搬城市教師培養標準和經驗,充分遮蔽了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地方性”價值。在城市文化的培養模式和價值導向下,鄉村定向師范生容易將城市學校作為鄉村學校的參照模板,盲目借鑒其教育教學方式,忽視鄉村學校獨特的教育現實與教育需求[12]。第二,教學實踐“書面化”。大多數專業課教師缺乏基層教學經驗,存在重理輕實、學科本位等路徑依賴,忽視鄉村學校對復合型鄉村教師的訴求。加之校內實訓基地建設的匱乏和與校外實踐基地之間常態化協同監管機制的缺失,致使中小學承擔的教育實訓職能缺乏統籌、指導與評估,見習實習期內一味讓定向師范生在后座聽學或“拿來即用”等無角色過渡的兩極現象明顯,不論是“放養式”還是“壓榨式”的教學實踐都難以使其教學能力獲得實質性提升。在培養院校“理想”制度的包裹下、在實踐學校“線性”考評的裹挾下,定向師范生難以深入鄉村教育獲得直接經驗并感知教學全貌,不僅影響其鄉土課程開發能力,也難以基于不同階層學生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建構恰如其分的教學方式。
(三)本體性原因:教學品格與工具理性的博弈
教學認知決定思維深度,教學能力決定實踐力度,而教學品格決定發展厚度。工具理性指人的行為由追求功利的思想動機所驅使,從純粹追求效益最大化角度出發,漠視情感和精神價值。由于社會資本的缺失,鄉村定向師范生基于對現實生活的考量,或出于對就業風險的理性規避和對有編有崗的功利追求的動機報考定向師范專業,與鄉村教師地位待遇差、工作任務重等現實形成鮮明的對照,并影響其教學品格。在精神價值層面上,“神圣化”與“污名化”相沖突。在傳統尊師重道的背景下,教師作為“愛”與“奉獻”的代名詞被賦予了獨特標識,體面的職業形象成為定向師范生的報考拉力。但培養過程中鄉村定向師范生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及社交空間均發生變化[13],城鄉二元對立思維立場以及教師職業“神圣化”與鄉村教師身份“污名化”的偏見矛盾掣肘其身份認同。在培養價值層面上,所教與所學相偏離。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存在“學非所教”“不識全貌”“理實脫節”等現實藩籬,造成所學的理論方法難以與實際教學相耦合,并影響價值判斷。對教學的理解停留于教學技術合理性的反思,即“怎么教”——“術”的層面,難以明晰教學內容合理性“教什么”以及教學價值合理性“為什么教”——“道”的層面[14]。多數鄉村定向師范生生于鄉村、學于城市,本身具有文化的先賦性優勢,但隨著社會現代化的不斷擴張,鄉土與城市二元文化間存在互斥與割裂,學于城市與工作于鄉村的強烈反差使其迷失自身身份定位并產生巨大心理落差,城市情結逐漸置換解構鄉土情懷[15]。他們即使在定編定崗的政策屏障下依然產生違約動機,根源在于鄉土情感的淡薄與教學品格的式微,難以由衷熱愛并投身于鄉村教育事業。
三、探求:教學勝任力優化理路
(一)注重教學認知:喚醒文化自信,實現精準化培養
“一切教育的關鍵在于教學內容的選擇,以及將學生引向事物本源的方式。教育關注的是,如何調動并實現人的潛能,如何使內在靈性與可能性充分地生成。”[16]當前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存在課程拼接、供需錯位的問題,與鄉村現實需求相割裂的“去結構化”課程和“去經驗化”教學,容易使其教學認知過于符號化和碎片化。為提升供需適配水平,重新激活文化自信,可從以下維度推進。
第一,出臺專業標準,兼顧“鄉村性”專業特質與“城市性”文化元素。國家應出臺針對鄉村教師的專業標準,強化定向師范生的鄉土文化意識,強調區別于城市教師的專業特質。要改變鄉村定向師范生的文化困境,應改變其單一性的專業技能導向和向城性的考核評價傾向,理性對待由城鄉文化之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沖突與斷裂所帶來的種種不適,從而擺脫文化困境。鄉村教師獨特的文化資本、文化生產并非彌補自身與城市教師的“差距”,而是自身在“差別”的生活實踐中的獨特創生[17]。強化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專業特質,培育文化生存與發展能力,既不是強調鄉土文化的片面生產,也不是回落到城鄉文化二元對立,而是回歸城鄉文化“共生性”生產,建立城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共識。
第二,優化課程設置,緩解專業“窄口徑”培養與崗位“全方位”要求之難。鄉村教師并非“語數外通吃、音體美全扛”的萬金油,而是以課程整合為前提的“一專多能”的卓越教師[18]。新時代鄉村定向師范生高質量培養需要從傳統“分段分離式”轉向具有新邏輯起點的“整合連貫型”的教師教育模式[19],也就是說,要立足本土需求統整課程資源,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實現課程交叉融合,滿足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多元認知發展需求并促進知識的整合遷移。在課程設置上,應體現鄉土文化的價值地位,堅持構建以鄉土知識傳遞、本土教材開發、地方課程開設、實踐活動支撐、鄉土情感認同的五位一體模式[20],這不僅是對課程主體教師文化意識的引領和構建,對鄉村“準教師”鄉土文化的啟蒙和傳承,還是國家對一種文化類型的態度和普及[21],有利于鄉村定向師范生認同、繼承與傳播鄉土文化。此外,還應重視鄉村定向師范生的教學研究能力,這是其科學探知教學現象、有效探索教學規律、積極創生教學模式的內源動力,不僅為鄉村教育實踐提供理論指導,更為其專業發展保駕護航。
第三,安排入職考核,疏通畢業“低門檻”與上崗“高難度”之困。由于鄉村地區師資較為緊缺,鄉村定向師范生畢業即上崗成為常態,傳統準入機制致使入職考核缺位。然而畢業順利不代表上崗順當,高畢業率慣性容易招致出口把關不嚴,“嚴進寬出”使得大批定向師范生走上一線教學崗位的同時也逐漸暴露其專業素養不高、教學能力不強等問題。借助考核機制提高入職門檻不僅有利于檢驗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培養質量,查找院校培養存在的薄弱環節與突出短板,也有利于以教學勝任力為風向標倒逼其調整優化定向師范生培養模式,以保障“輸出”質量。對于考核未達標的鄉村定向師范生暫緩工作分配,若二次考核再未通過,實行相應的退出機制。師范院校需改變原有以就業率與畢業率為根本指向的培養理念,建立以鄉土需求為導向的“院校培養—入職考核—培養優化”三位一體融合發展的循環反饋機制。
(二)提高教學能力:融通學踐場域,提供針對性指導
第一,借鑒契約學習模式,實行雙導師制。契約學習模式由馬爾科姆·諾爾斯(Malcolm Knowles)提出,該理論主張以學習契約為載體、以學習者需求為中心,基于自我導向、個性學習和終身發展的底層邏輯,強調教育者和學習者之間協商對話并簽訂個性化學習契約,通過尊重個體差異實施教學[22]。針對培養院校教師基層教育工作經歷缺位、“去經驗化”教學等問題,不僅要優化專業課教師入職聘任機制,還要遴選部分教學能力突出、教學品格高尚的鄉村教師,并聘為兼職教師。2021年《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優秀教師定向培養計劃》中強調“全面落實高校教師與中小學教師共同指導教育實踐的‘雙導師制”,并實行覆蓋城鄉兩種教學環境的“雙實踐”制度,此“立足鄉村、兼容城市”的頂層設計理念為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提供了行動指南和重要遵循。完善雙導師制度,組建一支強大的理論與實踐、專職與兼職相結合的教師教育工作團隊,通過“師徒制”進行傳幫帶,強化定向師范生基于鄉村教育的專業特質契合和教學能力考核。借鑒契約學習模式,雙導師與鄉村定向師范生簽訂專業發展契約,幫助其診斷自身薄弱環節與發展短板,促進其理論水平與教學能力兼融共進。
第二,突破教學實踐瓶頸,提供全息指導。全息不僅包含全部信息,還包含現象透視、全位指導和問題前瞻。全息理論投射到教育領域,在于解釋教育理論、問題與實踐的全息教育現象[23]。針對課程同質化和城市化取向、教學重理論思辨輕實踐經驗等問題,構建“U-G-S-D”四位一體全方位培養維度和“學習—見習—研習—實習”四位一體全過程育人維度,是破解教學瓶頸、提升教學能力的有效之方。改變傳統“走過場”“任務導向”的教學實踐安排,在專業課學習中不斷穿插實踐練習,以實現教學能力縱深發展。在研習方面,組織鄉村定向師范生進行教育專題培訓、教學案例觀摩研討,使其獲得即時、鮮活的現場體驗,體悟成功教學背后的教育機智。在見習方面,高校應與中小學建立常態化和協同化培養機制。改變“重形式輕過程”“重中間輕兩頭”的傳統做法,見習前明確實踐目標、提供實踐保障,并嚴格遴選意愿強烈、能力突出的教師進行指導。在實習方面,強化鄉村定向師范生“回流”的政策效應,統一安排其到履約地學校進行實習,避免因初入履約地而產生的不適與焦慮。為親近鄉土文化、適應鄉土教學,強調師生主動融入教學活動,共同建構學習意義,形成一種師生關系共生、學習內容生成、教與學共融的理想境界[24]。在實習角色上,突破傳統“實習”即“頂崗”模式,增加“助教”這一過渡角色,消解因不適而過早產生的抵牾心理和職業倦怠,通過“以老帶新、青藍結對”的方式錘煉教育教學基本功,激活專業成長內驅力。
第三,施行同質異構評價,強化在地發展。城鄉異質性是鄉村教師在地化發展的現實基礎,城鄉教師二者的客觀差異決定鄉村教師的在地化發展必須將城鄉教師的差異化訴求納入考量。在制度取向和施策理路上擺脫城市本位主義,立足鄉村定向師范生的在地性特質,健全同質異構評價機制。針對鄉村定向師范生的考核評價制度應與普通師范生有所區別的情況予以差異化設計,建立符合鄉村教育實際、契合鄉村教師身份特質、凸顯服務鄉村教育和鄉村振興戰略特殊使命的評價機制[25]。地方政府應成立省級鄉村定向師范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加強省市縣三級行政管理部門對鄉村定向師范生教育指導工作的統籌實施,在明確各方權責的基礎上結合培養院校實際、鄉村學校需求與教育部門意見,研商并制定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質量評價標準,以面向現代、立足鄉土、凸顯地方為評判準繩。摒棄“城市本位”“唯分數論”的線性評價觀,提倡評價主體多元性、評價過程發展性、評價方式增值性,凸顯鄉村定向師范生的鄉土化目標導向,強化其在地化教學能力。
(三)培育教學品格:構筑共治格局,強化持續性激勵
教學品格是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形成的品質和風范[26]。教學品格是鄉村定向師范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發展”的職業基石,也是推動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可從以下向度推進。
第一,文化聚能,厚植人文關懷。在選拔環節上,通過引導、咨詢等渠道加強鄉村定向師范生政策宣傳的廣延性,提供“決策緩沖期”,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影響決策理性而產生報考誤差。改變“唯分數主義”的遴選標準,增加面試環節以獲悉報考動機,選拔真正有志從教、志在鄉村的優質本地生源,提高質量與專業二者的適配度。在培養環節上,高校應將師德師風等軟性指標納入考評范圍,多層次多角度地考察鄉村定向師范生的教學品格。盡管定向師范生與鄉村社會具有空間距離,但并未阻斷與鄉村世界的內在聯系,當失去地緣文化的支撐時,若沒有教育的文化性支撐,血緣的文化性也難以發揮作用[27]。鄉村教師“下不去、留不住”的頑瘴痼疾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歸根到底是對鄉土文化認同與實踐的問題。還應開發與增設鄉村教育學、鄉村社會學、民藝民俗與教育、鄉村學生發展與管理等地方教育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課程,激活蟄伏于定向師范生的文化在鄉性。鄉土文化關涉鄉村社會內在秩序的建立和信任體系的構筑,需對鄉土文化祛魅并從內涵上重新確證其價值屬性,增強對現代文化的回應,建立符合社會發展與時代需求的現代鄉土文化。體悟鄉土文化內蘊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文化真諦,使鄉村社會成為鄉村定向師范生心之所向的精神家園,成為“有根”的鄉村教師的靈魂所系、血脈所在、精神所依。在空間上,需要加強鄉村定向師范生與鄉土文化的聯結。“空間是一種秩序”[28],鄉土空間關系表征鄉土文化群體的關系結構,有助于重尋鄉土之根、重振鄉土之蘊,充分彰顯其鄉土文化的主體身份,繼而喚醒鄉土文化自覺的主體狀態[29]。鄉土文化自覺的生成內蘊著鄉土責任感與鄉土情懷,是建立文化關聯、實現價值增值的過程。融入鄉村文化生態建設,通過“濡化”和“涵化”實現鄉村定向師范生的情感在地性復歸,以培育和發展教學熱情,既是樹立教學信念的過程,又是強化教學動機的抓手,更是增進教學投入的關鍵,最終指向高質量的教學活動[30]。
第二,情感賦能,實施美的教學。隨著技術進步、社會變遷以及生活節奏的不斷加速,現代社會進入了“加速時代”[31]。當加速邏輯浸入基礎教育領域時,以“速度”衡量刻度的“時間”便成為規訓學生學習的“戒尺”,“劇場效應”“囚徒困境”等異化現象在基礎教育領域比比皆是,鄉村地區也不外如是。社會加速批判理論認為,步調加速的核心是“在一定時間單位當中行動事件或體驗事件量的增加”[32]。“加速”帶來“節省時間”的假象,實則卻陷入“沒有時間”的惡性窠臼。正如馬丁 ·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言,“‘沒有時間造成的損失比浪費時間造成的損失要大”[33]。加速邏輯投射到鄉村教育場域,既表現為時間緊、活動密、節奏快等教學樣態,也表征為“唯分數論”、逐利心態、恐懼失敗等主體境遇。鄉村家長囿于經濟資本的匱乏,在“生計本位觀”的裹挾下進行家庭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隔代教育現象尚存;由于文化資本的缺失,其教育理念與方式難與學校教育同頻共振,異化為鄉村孩子融入校園文化的隱性阻力。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囿下,教學應充分關注學生的真實境遇和接受能力,充分考量城鄉地域差異,因地制宜地實施“慢”教學。這既彰顯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體現了對教育回歸育人原點的關注,使鄉村學生感受到春風化雨、循循善誘的人文關懷,同時也是對急功近利的超越、潛心育人的聚焦,使鄉村定向師范生體悟“工匠精神”的“慢工出細活”和“精品意識”的“術業有專攻”。強化“慢”這一教學理念,探尋與鄉村教育相契合的“教學節奏”,為鄉村定向師范生呈現有溫度、有深度的教學注入不竭動力。鄉村定向師范生除了在自我時間中的主體性存在,還需要在交融時間上與外在他者相聯系,在共同性的時間中構建與他者息息相通的教學共同體,這是值得憧憬的美好教學生活的應有之義[34]。打通城市與鄉村、高校與中小學之間的壁壘,為定向師范生提供聯結鄉土之“徑”,同時減輕鄉村教師的非教學性負擔,使其以信任和包容的心態走進鄉村視域和鄉土世界。“愛取代了恐懼,共同創造取代了控制”[35],與鄉土世界建立生命聯結的過程,也是充盈他者、完滿自身的過程,其教學涌現出鄉土之光,也潤澤生命之流。
第三,待遇增能,對標多元訴求。一方面,完善物質層面保障機制。鄉村定向師范生“鄉村即落后”“回鄉即失敗”的污名化認知以隱秘的集體潛意識形式一直存在[36],要強化其職業認同,必須滿足其作為社會關系的主體訴求。實行教齡累進工資制度,堅持貫徹“教師教齡越長,收入差距越大”的基本原則;實行鄉村教師職稱傾斜制度,設計差序傾斜標準,并適當放寬職稱評聘條件;實行鄉村教師分類補償制度,學校發展越滯后、地理位置越偏僻、師資力量越薄弱,對履約教師的經濟補償越高;健全鄉村教師社會保障制度,切實解決鄉村教師“職稱難”“住房難”“看病難”等問題。提高鄉村教師社會地位是教師深入鄉村、扎根鄉村的強大底氣。鄉村教師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代言人”,為鄉村教師搭建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平臺,有利于打破“城市人”與“鄉村人”的標簽區隔,彰顯“新鄉賢”的身份復歸和角色重拾,并為鄉村教育振興建言獻策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塑造“生態宜居”的鄉村形象。《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提出“促進鄉村振興應當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來實施,其中“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鄉村教師扎根鄉土的環境基礎。長期以來,由于鄉村發展相對滯后,被打上了“落后”“粗劣”等刻板烙印。因此,抓住鄉村振興的戰略機遇,打造綠色和美的鄉村生態,不僅是鄉村空間的升級改造,更是鄉村教師的理想棲居地,有利于實現人地情感聯結、人地關系再造的愿景。
參考文獻:
[1]游旭群.重塑教師教育培養體系,著力打造優秀鄉村教師[J].教育研究,2021(06):23-28.
[2]David C.McClelland.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J].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3(01):1-14.
[3]郝廣龍,黃培森.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現代化的向度、困境及其超越[J].當代教育科學,2023(08):52-60.
[4]〔美〕安迪 · 哈格里夫斯,〔加〕邁克 · 富蘭.專業資本:變革每所學校的教學[M].高振宇,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29.
[5]郭芳.公費師范生培養的“地方性”價值取向研究[J].教師教育研究,2022(04):39-44.
[6]WEIL S.The Need for Roots[M].Boston:Beacon Press,1955: 53.
[7]趙燕.鄉村定向師范生政策生源吸引力分析——基于社會交換理論的視角[J].教育學術月刊,2021(01):64-70.
[8]李森,崔友興.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困境與突破[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2):82-89,190.
[9]伊娟,馬飛.新生代鄉村教師鄉土文化缺失的現實表征與重塑策略[J].當代教育科學,2021(05):72-79.
[10][21]申衛革.鄉村教師文化自覺的缺失與建構[J].教育發展研究,2016(22):47-52;57.
[11]靳偉,裴淼,董秋瑾.文化回應性教學法:內涵、價值及應用[J].民族教育研究,2020(03):104-111.
[12][29]劉桂輝.新生代鄉村教師鄉土文化自信的缺失危機與培育路徑[J].當代教育科學,2023(02):55-62.
[13]張源源,薛芳芳.“前補償”抑或“后激勵”?——鄉村振興背景下定向師范生違約問題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2(06):44-56.
[14]張啟勝.中學教師教學勝任力的內涵要義、邏輯架構與發展路徑[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2(08):22-26.
[15]張春海,俞渤洋.新時代民族地區鄉村定向師范生身份重構的動因、向度與樣態[J/OL].民族教育研究,2023:54-61.
[16]〔德〕卡爾 · 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童可依,譯.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21:4.
[17]劉鋮,陳鵬.新生代鄉村教師“共生性”文化生產的可能與實現[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2(13):32-38.
[18]陳柏華,黃可人.跨界視域下小學多科教師培養的實踐探索[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1(26):30-34.
[19]孔敏.中小學初任教師勝任力的分析與建構[J].教學與管理,2019(12):57-60.
[20]朱燕菲,王運來,吳東照.類型化視角下地方公費定向師范生農村任教意愿的多維分析與對策審視[J].大學教育科學,2022(01):64-71.
[22]高虹.契約學習視野下成人教育發展的實踐設計[J].中國成人教育,2017(07):16-18.
[23]李慧萍,劉海舒,王漢江.高職院校“全息”勞動教育課程體系構建研究[J].教育與職業,2021(14):81-84.
[24]冉源懋,李思文.增強共生性和交往性:參與式教學的核心要領——基于“三教”理念下參與式教學實踐的解析[J].教育學術月刊,2023(08):74-79,86.
[25]容中逵,陰祖寶.鄉村教師在地性的意義澄明與實現圖景[J].教師教育研究,2023(03):19-24.
[26]侯秋霞.演繹真善美:教師教學品格核心價值的人本觀照[J].教育探索,2012(09):23-25.
[27]薛曉陽.鄉村學校“在鄉性”的危機與應對——以“鄉村文化教育”作為一種應對戰略[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01):84-95.
[28]〔德〕黑格爾.自然哲學[M].梁志學,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42.
[30]趙鑫,李之郁.教師教學熱情的學理架構、生成機制與提振路徑——戴杰思教學熱情學說述評[J].教育科學研究,2023(09):88-96.
[31]〔美〕托馬斯 · 弗里德曼.謝謝你遲到[M].符荊捷,等,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24.
[32]〔德〕哈特穆特 · 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M].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1.
[33]〔德〕馬克 · 維特曼.時間,快與慢[M].陳惠雯,任揚,譯.北京:文化發展出版社,2017:183.
[34]徐繼存,徐寧霞.朝向美好教學生活的教師時間:困境與重建[J].教育學術月刊,2023(10):3-12.
[35]〔美〕帕克 · 帕爾默.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M].方彤,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108.
[36]朱燕菲,吳東照,王運來.綜合評價視域下地方鄉村定向師范生培養的質量省思[J].中國教育學刊,2021(12):85-90.
(責任編輯:姜佳宏)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mpetency for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LI Siwen, XIANG Tiancheng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Rural orientation normal students ar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source for rural teachers.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teaching level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teaching competency is the true embodi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he professional expression based on rur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competency of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includes three stipulations of teaching cognition, teaching ability and teaching character,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t present, 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teaching cognition under the exit of rural areas, the inaccuracy of teaching ability under the coerc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slight format of teaching materials under rational regulation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found that the conditional cause l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eaching cognition and cultural separation, the direct cause lies in the friction between teaching 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ntological reason lies in the game between teaching character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team of rural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eaching cognition and achieve precise training; enhance teaching ability and provide targeted guidance; cultivate teaching character and strengthen continuous incentives. Only by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teaching competency of rural oriented normal students can we help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high-quality rural education.
Key words: ??rural orientation normal students;rural teacher;teaching competence; teaching cognition; ?teaching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