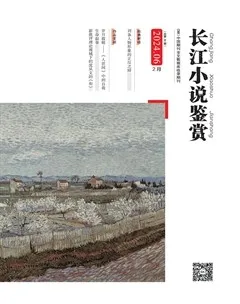《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美國知識分子形象
李雅雪
[摘? 要] 索爾·貝婁以其獨特的觀察與智慧,見證了20世紀后半期美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轉型。通過敘述美國當代社會中沒落知識分子的經歷,索爾·貝婁帶給讀者最忐忑而觸動人心的現實思考。貝婁型知識分子雖然執著地追求和堅持自己的理想,但是他們與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有著根本的不同,傳統上的英雄在經歷了艱辛的掙扎與最終的失敗與毀滅之后,留給人們的是一種悲壯的、高尚的美,而貝婁型知識分子留給人們的則是一種荒誕的、充滿喜劇色彩的悖論。他們無法徹底地成為“局外人”,又拒絕與現實世界相融合,最終淪為“晃來晃去的人”(貝婁同名小說),在不停地尋找與逃避中掙扎。本文試圖定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美國知識分子形象,探究他們的特征,最后分析此類人物精神困境的成因。
[關鍵詞] 索爾·貝婁?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美國知識分子
[中圖分類號] I106.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6-0011-04
一、引言
索爾·貝婁(1915—2005)因其“深刻地認識了現代文化中豐富的人文內涵,并對其進行了細致地剖析”而榮獲了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是對西方社會混沌和癲狂的一種真實而藝術的再現,顯示了一名杰出的作家對人類命運的深刻關注。貝婁以幽默諷刺的語言方式,將深邃的思想與現代語言有機地結合起來,描繪了在新舊價值體系中苦苦思索、尋找自我解放的內省個體。貝婁的小說以美國知識分子為中心,描寫他們的境遇與心態,展示他們遭受的苦難和心理危機,并以知識分子的視角審視傳統價值觀的瓦解與物質文化興盛背后所隱藏的精神危機。這是知識分子們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同時也是貝婁的心中所想。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貝婁晚年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第10本小說。小說中的貝恩和肯尼斯是貝婁反復書寫的美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貝恩在愛情的一再挫折面前,成了一個優柔寡斷甚至缺乏獨立人格的落魄知識分子,為了尋求自我解放而逃離到了植物研究的世界。而敘述者肯尼斯是一個性功能低下者、半吊子的知識分子,他想在舅舅的幫助下把精神進化到更高的層次,這正是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追求。在小說中,貝恩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但每一次都會卷土重來,即便是人工杜鵑花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給予他沉重的打擊,貝恩還是選擇了去北極研究那些鮮有人知道的苔蘚。苔蘚是靠著空氣中的養分來維持自己的生命,貝恩則是從科學研究中找到新的人生方向,從頭再來。而肯尼斯在經歷了無數磨難后,終于取得了對女兒的撫養權,他終于有機會把自己的女兒撫養成人,讓這個世上少了一個傷心欲絕、因心碎而死的人。
二、知識分子的定義
貝婁本身就是位學者、教授,他把自己融入小說中,在小說中表現當前知識分子的困境。他們不再貧困,不用再為衣食奔波奮斗。隨著知識分子社會價值的顯現,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在逐步提高,甚至在自己有所貢獻的領域里備受推崇。在演講臺上他們風光無限,然而走下了講壇的他們,撤去了表面的榮光,內心卻比一般大眾有更多的無奈、困惑和疲憊。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在為社會立德立言,忽然之間,他們好像對一切陌生了起來,對自己曾經堅持的觀點、曾有的信念懷疑了起來。真實的世界與理想總是很遙遠,付出的努力有時卻導致了相反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追隨者中有很多是知識青年,他們處在那個特定時代的狂熱中,追隨自己所謂的理想,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事后卻在為這個破滅了的神話理想而懺悔[1]。
知識分子不是萬事通,在某一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人,他的學識的博與精往往只是相對于這一領域而言,出了這一領域,在其他學科面前,他也是和其他人一樣的門外漢。索爾·貝婁撤去了知識分子身后的光環,把他們放到了瑣碎的日常生活中,這群在各自領域里曾取得過輝煌成就的人,在強大的社會現實面前,卻像個孩子,像小學生,甚至是文盲,他們把現代生活文明與現代思想文明的結合理解得過于簡單化了,以至于在現實中焦頭爛額,陷于可笑可憐的境地。知識分子的自謗、自嘲、自諷并不少見,其實這也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為了取得一種暫時的心理平衡,“至于未來,既然我們已經盡一切可能誹謗了自己,它無論怎樣都嚇不倒我們了”[2]。
三、《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知識分子特點
1.內心孤獨的理想主義者
在貝婁的小說中,知識分子所遭受的孤獨,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脫離人群而遭受了身體上的孤寂,而且還包含了深深扎根于他們心中的空洞、迷茫與沮喪。他們的寂寞,一方面源于他們自身所具有的敏感、孤僻的個性,另一方面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有別于一般的普通群眾,他們擔負著“社會責任”與“使命”。貝恩期望在自由的精神家園中,不斷地追尋理想層面的知識與愛、家園與和諧社會。他以愛為先,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意志來對待愛,在他心靈的神圣之地里,始終懷有一種對永久的親密關系的執念,也就是對愛與善的渴求。貝恩認識到了這樁完美的婚姻實際上是一個騙局,于是他就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在了一株杜鵑花上。這株神秘且不可捉摸的杜鵑花時常讓他心情舒暢;當他忙于家務瑣事時,他便與杜鵑花為伴,試圖填補心靈上的空白,尋找心靈的棲息之所。然而,當他意識到這株杜鵑花是假的人造之物時,他的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引以為傲、給予他慰藉的植物世界也離他而去。總之,他在物質化的世界里忍受著愛情的磨難,在已經物化的名利場中追求純真的愛情注定他孤獨的一生。
肯尼斯也堅定地相信“愛是圣潔靈魂的本質,是塵世間的溫馨之源”[1],因此,他在特麗基身上投入了與在貝恩舅舅身上同樣多的精力。肯尼斯確實是個精神領袖——只是在不合適的時候,他為貝恩沒有聽從他的忠告而苦惱,被特麗基的固執弄得焦頭爛額,而他自己的生活已經一片混亂,卻還要操心別人的事。他們在生活與精神上都陷于兩難境地,原因在于他們希望緊跟著20世紀的腳步,進入被普遍認為是理性合理的世界里。事實上,他們越努力讓自己的生活像別人那樣合乎情理,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古怪。畢竟,拉亞蒙一家人并沒有接受知識倫理,而特麗基也認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標準是荒唐可笑的。用肯尼斯的父親的話來說,他們“太有野心了,想試圖與美國對抗,以此來檢驗他們時常流露出來的自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直接放棄了建立自己精神家園的任務,而是選擇了以現實生活為準則的生活方式。他們還會繼續朝自己心中的精神樂園前進,因為他們是理想主義者。
2.逆流而上、堅守本心的行動派
有一回,肯尼斯陪同貝恩到日本京都交流講學,日本的植物學家帶著他們作了一個特別的參觀——看脫衣舞表演。貝恩五十多歲,也不是沒見過這樣的場面,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震驚,他被嚇得不輕。這些觀看表演的人中,有生物學家,有工程師,還有專門發明精密儀器的偉大發明家——他們發明電子顯微鏡的可以把土星環的影像傳回地球。他們什么都不管,只盯著舞臺上舞動身軀的女郎,完全被吸引住、無法自拔。貝恩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表演嚇了一跳,不過他在精神上的震撼遠比生理反應要大得多。這是一場超乎他想象的演出,在這場演出中,性與愛情截然分離,演出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使人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喪失了自己的主動權。這樣,人和動物有什么不同?
愛情的沉淪,是當時社會的痼疾,但是貝恩不愿讓愛情成為金錢和地位的附屬品,也不愿將愛情看作是性的享受。于是他拋棄了瑪蒂爾達,也無視貝貸爾的請求,對那些骯臟的表演表示憤怒。他渴望的愛應該就是弗洛姆所說的“成熟的愛情”,因此,他最終來到了北極。貝恩對北極的苔蘚充滿了自信,就像他對愛情抱有信心一樣,盡管他在愛里飽受挫折。“這些極地苔蘚被凍成了冰塊,95%以上都是冰塊。但是隨著溫度的升高,它們又會恢復活力,并且變得更為茁壯了。這個生長周期可能會持續上千年之久[2]。苔蘚的生態學特性,正如人類在文明時代所渴求的愛一樣。盡管生存條件很艱苦,但是它的精神卻堅韌不屈。冰凍不是死亡也不是終點,其生命之源深埋于自身之中,一旦機會來臨便會重新煥發出旺盛的活力。
弗洛姆認為,“成熟的愛情”是人類的最高機能的表達,其衰敗的原因在于西方社會的結構使人“異化”,使人成為機器,而非有感情會思考的人。而一臺自動化的機器是沒有愛情的,只會去交換,于是,愛情就成了一場交易。但貝恩卻反其道而行之,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堅守著自己的愛。他對愛的執著追求,就像北極上的苔蘚,在嚴寒中等候著一個契機來打開自己塵封的心靈。事實上,他的愛已經有了一種超越的意義,那是一種對這個時代的抗爭[3]。
3.具有現代西西弗精神的樂觀主義者
貝婁型美國知識分子以樂觀主義為代表的處世態度是:樂觀主義并不意味著“安于現狀”,等待著命運的審判;他們采取了一些行動,雖然他們的行動遭到了一再的挫敗,他們進行著永無止境的抗爭,這使他們變成了現代的西西弗。西西弗雖然來自希臘神話,但現在的人也面臨著和他相似的情況。現代人所處的生存環境是荒蕪的,而這個境遇又是一種客觀的、強大的力量,無時無刻不在向人施加壓力。不過,比起西西弗來,人類就更慘了。西西弗死后被諸神送進了地獄,他不會再死一次,他可以繼續和命運抗爭。但是人生就是在生死之間,有一個終點,很有可能發生的事就是有人以生命為代價卻無法改寫自己的結局。最可笑的是,人就像是一顆微不足道的塵埃,從一個意外中走來,然后又回到了虛無之中。人生很容易就會逝去,而這個荒謬的世界,卻永遠地存在著。
貝婁知識分子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荒唐命運,但是,他們并沒有放棄抗爭的權利,哪怕結果是一次次的反復失敗。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是神話中的人物,他的抗爭既不能說成功,也不能說失敗,他總是能走到山下,又能走到山頂,沒有一塊滾落的石頭能逃過他的抵抗。貝婁知識分子意識到了他們最終必死的結局,明白了這無望的荒謬超過了他們自身的存在時間,并且他們也許會在他們短暫的一生中面對著無數的失敗;但是,他們還在抗爭,他們深知抗爭的精神是不滅的,抗爭的尊嚴是永恒的,他們想成為當代的西西弗。貝恩在經歷了多次的背叛之后,并沒有放棄,反而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學研究之中,尋找著一條新的道路,為自己的靈魂尋找著歸宿[4]。貝婁的知識分子在荒誕的處境中,仍抱有信仰,是當代西西弗,即使生活是一種過程、一種衰敗,他們也要使之變得悲壯而又神圣。但是,貝婁型知識分子的樂觀并非盲目膚淺的樂觀主義,它是一種高揚在悲觀與虛無主義基礎上的樂觀主義,他們的反叛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反叛,而是為爭取自己的尊嚴而進行的抗爭,這種抗爭是永無止境的,是現代的西西弗精神。在腐朽的年代里仍能堅持人類的尊嚴,這正是貝婁所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所給予我們的啟迪。
四、美國知識分子精神困境形成原因
1.社會發展
20世紀70年代,美國正處于一種艱難和動蕩不安之中,內憂外患。對外既要面對中越之戰的慘敗,又要同蘇聯展開激烈的軍備競賽;內部局勢動蕩,官僚政治一團糟,讓人們苦不堪言;經濟秩序不穩,犯罪和離婚率居高不下。深刻的社會危機極大地打擊了美國人民的自信心,美國人在極度的絕望中要么尋求快樂,要么將痛苦訴諸于宗教甚至巫蠱之術,全社會陷入一種精神荒蕪的狀態。小說《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正是基于這樣的社會環境而創作的。
美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不但造成了貧富分化、勞資對立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且還引發了“地位革命”,造成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被邊緣化,知識分子的理想破滅;與此同時,貧富不平等和勞資矛盾激化也使知識分子的社會安全感和道德標準受到沖擊,激發了他們為國家作貢獻的內部動力。正是在這樣一種動力的驅使下,他們開始了變革,維護正義,掃除社會弊端,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美國社會發展的巨大變革勢必會對知識分子產生一些影響,特別是在精英文化被徹底拋棄的后現代語境下,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識分子將不可避免地被排斥在外。
2.傳統精神的沒落
美國是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其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第一。在一個機械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步調也受到它的調控。大量利用能源和機械,使得工作的本質發生了變化,技術被分割成幾個簡單的操作步驟。人力、物資、市場,都是用來生產和銷售貨物的,在這樣的工業文明時代,人們受到的對待與物品并無兩樣。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在現實面前,一切知識分子的抵抗都是徒勞的,他們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斗爭,甚至要摒棄自己一直信奉的精神準則。
二戰后的滿目瘡痍,在現代西方人們的心靈上留下了長久的陰影。人們迷失了方向,失掉了信仰,對理性產生了懷疑。人們在混亂的戰后生活中驚慌失措,甚至失去了生活的能力。人們的收入不斷增長,生活水平也在不斷地改善,而每個人都被限制在狹窄的工作場所和居住場所,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無力。各種典型的失范現象比比皆是,文化的斷層也相當明顯,范圍也越來越廣泛,而新的價值觀還沒有產生。就像我們所見,有些相反的價值觀被宣揚出來:電視、雜志等在鼓吹享樂和消費主義,而學校和教堂則竭力勸誡人們節儉和禁欲。知識分子們無法接受人們拋棄了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也無法從現實社會的價值觀念中汲取讓自己前進的精神力量。
五、結語
美國著名作家奧茨是這樣評價貝婁以及他的創作的:“在他最精粹的段落中,他所關心的不是別的,而是我們文明的命運”[5]。貝婁縱橫文壇達六十余載,留下了豐富的文學著作,他的著作大都表現出對人類社會的命運的關懷,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著作。貝婁之所以選擇知識分子作為小說的題材,一方面是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位知識分子,他對知識分子的生活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更為主要的一點,貝婁對混亂與破碎世界中人的心理狀態十分關心,而知識分子與人的精神價值之間的緊密聯系,使得貝婁把其視為自己的寫作目標[6]。貝婁在創作這些知識分子人物形象的時候也是在表現自己,這就是貝婁的創作動機。在貝婁自己的生活中,他同本諾一樣,也有如離婚、法律訴訟和精神崩潰等遭遇,同樣的,和他筆下的人物一樣,貝婁也在不斷尋求拯救自己的方法。貝婁始終肩負著自己作為一名美國知識分子的責任,那就是通過藝術來拯救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加繆曾說,“在光亮中,世界始終是我們最初和最后的愛。”這也許是貝婁型知識分子最偉大的理想,也是貝婁自己的心聲。貝婁在他的每一本書中都帶著這種信仰,讓人在合上書本沉思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一種令人動容的力量。
參考文獻
[1] 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單德興譯.陸建德校.三聯書店,2002.
[2] Bellow, Saul. More Die of Heartbreak[M]. New York: Penguin,2004.
[3] 喬國強.新世紀美國貝婁研究概述[J].當代外國文學,2012(03).
[4] 孫堯.索爾·貝婁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問題[D].黑龍江: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5] 汪漢利.索爾·貝婁小說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6] 陳亞斐.索爾·貝婁在《赫索格》中對知識分子的文化構建[D].湖南:湖南師范大學,2011.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