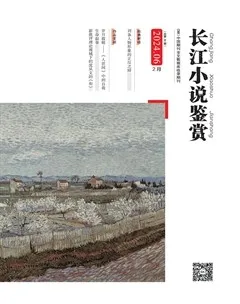《長路》中后現代主義荒誕反抗及其現實意義
鄭清荷
[摘? 要] 《長路》是美國作家科馬克·麥卡錫的經典后啟示錄小說作品。《長路》是在末日的極端背景下展開,敘述了一對父子推著裝有生存口糧的手推車前往南方海岸尋得最后生機的故事。傳統道德范式不斷崩塌,生存資源面臨殘酷競爭和掠奪,后啟示錄世界的真實與荒蕪再現。個人倫理選擇面臨困境,理性認知遭受斷裂與重建,家庭倫理關系缺失,希望文明尋找未知,人類倫理道德面臨威脅和挑戰。父子倆一次次做出艱難的理性抉擇,以保留人類最后的生存機會和道德尊嚴。小說中多處隱喻購物車、火炬、好人、槍、嬰兒,都有多重深刻含義,是末日下艱難處境的還原和呈現,以及父子倆最終倫理選擇的揭示。
[關鍵詞] 《長路》? 馬克·麥卡錫? 荒誕感? 虛無主義? 加繆
[中圖分類號] I106.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6-0047-04
《長路》是美國作家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經典后啟示錄小說作品。麥卡錫是美國當代文學巨匠之一,被譽為“海明威與福克納的繼承者”。《長路》(The Road)這部小說于2006年正式出版,同年獲得普利策獎,獲得廣泛關注并翻拍成電影。這部以末日為背景展開敘述的后啟示錄小說是作者站在后現代主義立場上獻給全世界的最后挽歌,對末日的描寫讓人身臨其境,使讀者深感其中的孤獨與絕望。《長路》是在末日的極端背景下展開,敘述了一對父子推著裝有生存口糧的手推車前往南方海岸尋得最后生機的故事。在向南的路上,他們面臨著重重挑戰和抉擇,不知名的災難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舉目所見遍地的荒蕪、黑暗、灰燼與煙塵。荒蕪又無人的絕望和孤獨,人和世界的斷裂,人本身為了求生存而異化,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危機不時出現。傳統道德范式不斷崩塌,生存資源面臨殘酷競爭和掠奪,后啟示錄世界的真實與荒蕪再現。個人倫理選擇面臨困境,理性認知遭受斷裂與重建,家庭倫理關系缺失,希望文明的尋找未知,人類倫理道德面臨威脅和挑戰。危機四伏的末日旅途,生死難料,父親在兒子的不斷提醒下,一次次做出艱難的理性抉擇,以保留人類最后的生存機會和道德尊嚴。末日之下,父子倆是“拿著槍做好人的冒險者”。小說中多處隱喻購物車、火炬、好人、槍、嬰兒,都有多重深刻含義,是末日下艱難處境的還原和呈現,以及父子倆最終倫理選擇的揭示。末日下的世界是不確定的、偶然的、難辨是非的,但人性亦或是人心中的理性仍能成為點燃混亂世界和混亂人心的最后一線火種。南行的路上,兒子不斷追問父親:“我們是誰?”這一問題引發末日里人們的深刻思考和自我叩問。極端的生存狀態,積極明確的生死態度,不斷深挖著個體精神深處關于自我和自我覺醒的深刻意義和探求。最終,在尚留一線生機的南海岸,兒子從瀕死父親的手中接下了代表著人性良善、理性文明、希望信念的微弱火種,繼續走在逃離末世的道路上,尋求生存,叩問自身,也追問世界。二戰之后,后現代主義成為文學界關注的新焦點,其中,加繆的荒誕理論及其思想價值脫穎而出,影響深遠。加繆在其著作《西西弗神話》中詳細闡述了他的“荒誕理論”和“反抗理論”,加繆這樣闡釋荒誕:“荒誕說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荒誕感,一種‘激情,一種‘感知,一種‘精神疾病。”[1]荒誕的本質是“荒誕感”,加繆說:“荒誕人都是孤獨的個體,與世界、與時間形影不離的人,不為永恒做任何事,又不否定永恒的人。”[1]西西弗是荒誕人的代表,他是荒誕英雄,是浪漫派荒誕人。他既因其生活激情迸發,也因其困苦。西西弗被定罪,轉而被拋入歷史洪流,在孤獨和艱難中一直活下去。荒誕人的存在及其現實意義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在荒誕感知中直面人生和現實,摒棄絕對虛無主義,懷有反抗荒誕人世的激情,堅持不懈,再創造一點人生價值”[1]。荒誕人的積極面主要表現在形而上的反抗,這種反抗是孤獨的個體反抗,因不滿生存狀況而奮起反抗造物主。“反抗者之所以褻瀆背叛神明,是希望產生新的神明,甚至自己成為神明。”[1]這種孤獨艱難中生存求索生命價值和意義本身即是一種自我叩問,更是一種自我覺醒。他們面對荒誕的世界,唯有反抗,才能阻擋荒誕。因此,只能在荒誕的形而上孤獨中叩問個體存在的意義,人與其自身陰暗面進行著永久的對抗。
一、末日下的荒誕感:人的異化與倫理困境
末日里惶恐不安求生的人們,精神長期緊繃,人和世界的關聯是斷裂的,人和人之間信任危機重重,人陷入“非人”的狀態。父子倆一路南行為求得末日下最后生存的機會,途中遇到無數次考驗人性的問題,迫使人重復陷入不同的倫理困境之中。小說中,三個反復出現的“追問”凸顯出人的異化和理性掙扎。其一,人性被置于生存和理性之間,該如何抉擇?其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否尚存一線可能?其三,人心之中的善與愛能否在不確定的世界里得以堅守和延續?這三個問題反復出現在兒子在任何條件下追問父親的問題里,在兒子尚未成熟仍保留一絲童真的心靈里,生存和人性置于同等位置。每次兒子發現自己和父親還活著時,馬上就會問父親,他們有沒有為了生存機會而扼殺他人的生存機會,有沒有自己傷害或威脅了他人的生命。談人性的前提是求得生存,生存之后在人性的不斷叩問和敦促之下理性與求生的本能開始無盡斗爭,人性此時置于中間,亦正亦邪。人和世界的關系處于破碎和斷裂狀態,人和人基本的信任和良性合作的關系也陷入不穩定之中。“那幫人遲早會趕上來殺了我們。他們會強暴我,強暴他,先奸后殺,然后拿我們飽餐一頓,是你不肯面對現實。”[2]父子倆除了要時刻警惕各種災難和自然危險的突降,更時刻警惕著人的到來和威脅。睡覺都要時刻留意細聽著是不是有腳步聲,是不是有人在附近。此時,人和人的關系回到了最原始的野生動物之間那種瘋狂搶奪生存資源,互相搶占生存領地的殘酷競爭和惡性循環。不能被別人發現,盡量隱藏自己的蹤跡;不能和別人有任何聯系,哪怕是最簡單的說話交流;不能和別人建立任何關聯,更不可能也不可以信任除了父子彼此二人之外的任何人。末日之下,人的最基本的社會屬性也被瓦解,因此,人再次陷入“非人”的狀態。
未來人類如何繼續向前,“是否應該重拾文明和理性”“是否依然高舉人性中善與愛的火炬”成為擺在眼前的倫理選擇。走過漫漫長路,父子倆歷經各種艱險和考驗來到了南海岸,經歷了生存考驗,擺在面前的是未來發出的考驗。末日下,人類喪失了世界范疇內的時間感,各種范疇下的時間觀念盡失。“沒有待辦事項,每個日子都聽從自己的旨意。時間,時間里沒有后來,現在就是后來。”[2]父子倆歷經了考驗,走過了過去,站到了現在,至于未來,沒人知道它在哪,或者是否還有到來的可能。對于父子二人來說,現在就是未來。陷入極度饑餓時到底要不要吃人?陷入危險時,到底要不要殺人?遇見瀕死的同類,要不要施以援助?這一系列苛刻的問題亟待回答。瀕死的父親給了兒子關乎生命的囑托,這也是父親一生的生活經驗,他告訴兒子:“記得隨時帶上槍,去找好人,但不要輕易冒險,不能冒險。”[2]人類站在生存和理性中間,如利劍般橫在頭上的倫理問題在父親的最終囑托中揭開了部分答案。“帶上槍”以保衛自己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去找好人”是人類生命理想的初心也是追尋的歸宿,“不要輕易冒險”是人心中理性賦予人以明辨是非的判斷和謹慎。孩子最終在父親的最后囑托下,高舉從父親手中接過的火炬,走向遠方的海平線,直至消失。
二、不確定世界里的荒誕人:摒棄虛無與形而上反抗
世界是充滿荒誕感的,但荒誕世界里的人是如西西弗般的積極反抗者,是激情勇敢的反抗者。人類在荒誕感逼迫之下激發出人性最深處的頑強堅韌,積極面對,叩問和追求自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這樣定義荒誕人的積極之處:“荒誕世界里的荒誕人直面人生,不逃避現實,摒棄絕對虛無主義,懷有反抗荒誕人世的激情,堅持不懈,或許能創造一點人生價值。”[1]自尼采吶喊出“上帝死了”的聲音后,西方世界陷入一片虛無。加繆這樣界定和描述虛無主義:“當人們不再相信現實存在和人生,把人生隸屬于某些價值,以致很難擺脫現實困境,這就陷入了虛無主義。”[1]心中的上帝突然崩塌,信仰失落后陷入無家可歸的落寞精神中,人類被放逐到自由而孤獨的原始狀態。面對虛無,人們還能再做些什么?這些行動還能帶來意義和價值嗎?很快就分出了兩種結果,一種是消極虛無主義,它表現為人類的絕望、深沉、無欲、疲乏和無聊等出現的一系列精神消極;與之相對應的便是積極虛無主義,深陷虛無主義之中,但表現出人本能存在下的意志活力和行動冒險等。顯然,小說中的父子用行動踐行著他們積極虛無反抗者的身份和選擇。在將近南海岸的地方,“父子倆飲食無虞,但離行抵海岸,尚有一大段距離。他知道自己在毫無理由承納希望之處投注希望,明知世界日日趨向黑暗,卻寄望沿海保有清明的日光”[2]。這是父子二人對荒誕世界發出的最強的精神聲音。在絕望中寄托希望,在廢墟的精神里重獲新生。在不確定的世界里,在信仰失落的精神里,反抗者既積極抗爭也積極爭取,唯有反抗,才能阻擋荒誕。當世界帶給人無盡的麻木與遲滯的絕望時,信仰的失落成為刺向人們精神世界的第二把利劍。“世界凝縮到只剩原始、易辨析的核心元素,萬物名號隨實體沒入遺忘。神圣的話語失卻其指涉,也丟失了現實。”[2]世界走向末日,信仰走向失落,人心走向失智,人類的意義無處探求,這些都直指向人對其本質存在和意義的不斷追問。
三、現實意義:倫理選擇與自我覺醒的實現
無法擺脫的荒誕感,難以逃離的荒誕世界,反抗者只能在荒誕的形而上孤獨以及在對這種孤獨和虛無的反抗中,叩問個體存在的意義。“你們是誰?”“我們是誰?”成為父子倆和陌生人都無法回答的問題。存糧散盡、殺戮四起、惡棍滿目的世界里,父子倆如何判斷自我,如何求得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成為倫理選擇和自我覺醒的棘手前提問題。對于“人”的客觀準則已經崩塌,世界對“人”的人性底線幾近消失,如何做人?如何生存?只有心里的理性給出最后的約束和底線。父子倆在面對和化解每一次威脅和抉擇時,也逐漸找到了自己作為“人”最后的倫理選擇和理性救贖。人和世界的道德倫理關聯在于人和其他生靈的關聯,在于人和人的關聯,即人與外部世界的關聯和人自身內部的選擇。“遠處傳來狗叫聲。哪里來的小狗?不知道。我們不會殺死它吧,爸爸?不會,我們不殺它。我們不殺狗,他說,我保證。”[2]此處,狗代表了父子倆對其他生命的態度和理性選擇。不威脅人類生命的其他生命存在也會得到生命的尊重和生存權利的保留,人類沒有不擇手段地爭取著成為世界所有生靈的統治者和主宰者。人自身內部的理性選擇和倫理堅守主要體現在父子倆面對“我們是不是好人?”這一問題的態度和解答。“我們還是好人嗎?他說。是啊,我們還是好人。我們永遠是好人。對,永遠是好人。[2]”“好人”似乎成為了求得生存之后亟待回答的第二個問題,也是父子倆對于道理倫理選擇的直接回答。沿路前行,身形佝僂。骯臟,破敗,絕望。
小說中有多處隱喻的筆觸貫穿始末,如“購物車”“槍”“嬰兒或嬰兒尸體”“火炬”都是具有深刻引申含義的代名詞。這四個名詞也串聯起以父子倆為代表的同群體人類的倫理選擇和自我覺醒的整個過程。“購物車”載滿生存資源才能確保人類最基本的生存可能,同類之間也會發生生存資源的搶占、偷盜和爭搶。因此,末日之下人和人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競爭關系,對生存資源進行無止境爭奪。這種爭奪使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以及人對世界的安全感所剩無幾。“槍”是從始至終都拿在父親或者兒子手里的必備武器,人和人之間的惡性競爭關系使父子倆不能相信遇到的任何人,他們必須時刻拿起武器保衛自己。這也體現了人在倫理選擇當中無可退讓的生命保衛的權力,以及自我覺醒的本能保護意識。一路上遇到許多尸體,其中焦黑色的嬰兒尸體被懸掛起來晾曬的場景也多次出現。“嬰兒”代表了一個種族生命和群體的延續,嬰兒的非自然死亡和被族群內部成員殺害的事實,成為“食人族”違背人性、拋卻理性、回歸獸性的有力證明,這與父子倆代表的人類群體處于兩極位置。在陷入倫理困境時,在生死難料時,在理性迷茫時,父親總會提及“火炬”的存在。父親在自己的瀕死之際,這樣囑托他唯一的兒子,也是他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延續,“你得拿上火炬往前走。真的有火炬?你知道的。它在你心里,它一直在那里。我能看見[2]”。這“火炬”是末日下人類生命的地圖,也是迷津,導向無法復位的事物、無能矯正的紛亂。此時的“火炬”,正是人心里尚存的最后一點人類理性的底線,是對美好與良善的最后寄望,是堅守倫理道德的最低防線,是與世界至暗時刻反抗斗爭的微弱星火。放下火炬,生命陷入至暗,理性和道德轉瞬崩塌。和父親道別之后的孩子接過父親精神世界的光明火炬,遠望前程,回望來路,消失在海岸的更南處。
四、結語
“如何在荒誕的世界中獲得幸福?”是面對荒誕世界的終極問題,拒絕自殺是一種路徑,自殺意味著對荒誕的妥協。“加繆相信人的本性是拒絕死亡的。”正確的反抗形式既非仇恨,也非不滿。反抗,是忠于生活的熱愛,避免在尋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過程中陷入另一種人在荒誕世界中的異化。荒誕人的勝利意義在于無視生活的沉重,享受生活。“西西弗享受走下山坡那段時間的自由,應該設想,西西弗是幸福的。”末日下的荒誕彌漫在整個世界,荒誕威脅也考驗著荒誕人的肉體與精神,荒誕人與消極生命反抗到底,他們不斷地求生存,求生活,求幸福,一直竭盡全力地積極地活下去。在沒有方向的道路上不斷前行,既不停下腳步,也不畏縮返回;在未知的世界中保留人性本真的良善和倫理道德,在不確定的世界里摒棄虛無,在自我叩問、自我發覺和自我覺醒中找到新的生命意義和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
[1] 加繆.人性的荒謬與怪誕:西西弗神話[M].李妍,譯.吉林: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
[2] 麥卡錫.長路[M].毛雅芬,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