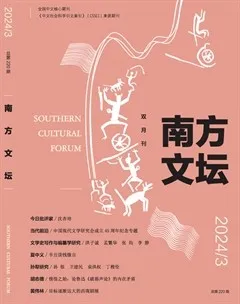世界文學中的“小文學”:魯迅以德文為媒介對保加利亞小說的譯介①
20世紀初,當中國讀者建立世界文學觀時,一個文學群體引起了他們的特別關注:“弱小民族”,又被稱為“被侮辱和被壓迫/損害的民族”②。雖然這類文學通常指代東歐國家和巴爾干地區產生的作品,但其定義并不嚴謹③。正如“民族”一詞的內涵會隨著語境和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前面修飾詞(弱小/被侮辱/被壓迫/被損害)所傳達的思想也各有不同。在20世紀的前30年中,這類文學的界定在不同歷史時期借鑒了不同意識形態的思想,包括泛亞主義、無政府主義、威爾遜主義和馬列主義等。盡管這一概念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被介紹到中國的相關文學作品切切實實地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巨大共鳴。魯迅就是其中的領軍人物。對這類文學而非西方主流文學的特別關注,成為魯迅“拿來主義”的一大特點。
這種分類方式很好地呼應了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身份建構,并成為一種與帝國主義抗爭的有效手段④。這種類比還與國人對皇權專制的反感相關。借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論斷,也許魯迅等人在弱小民族的文學中看到了類似的民族寓言式的表達,所以倍感親切⑤。不可否認,將中國現代文學與弱小民族文學進行類比的行為背后隱藏著重要的政治動機。正如石靜遠所言,這種類比促進某種“世界文學聯盟”(a world literary alliance)的形成,其政治任務是將全球的苦難與壓迫投射到中國的民族事業上⑥。然而,如果我們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一現象,這種類比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學傳統在世界古代文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們如何將中國文學與鮮有世界影響力的弱小民族文學一視同仁?除了政治動因,包括魯迅在內的諸多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文學與弱小民族文學兩相比較的過程中,是否也有其他方面的收獲?假定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學有大小之分,魯迅等人對小文學的青睞究竟意味著什么?
中國對弱小民族文學的關注讓我們聯想起德勒茲和瓜塔里在解讀卡夫卡時提出的小文學概念(kleine Literatur,法文:littérature mineure,英文:minor literature,也被譯為“少數文學”或“次要文學”)。德勒茲和瓜塔里認為,小文學有3個特點:語言的去地域化、個人與政治的直接聯系,以及闡釋的集體性⑦。我們可以將魯迅等人對中國現代文學類比為弱小民族文學的嘗試看作他們將中國現代寫作從傳統文體習慣中剝離出來的努力⑧。這一過程也使中國現代文學政治化,并在作家個人與中國政治現實之間建立了直接關聯。由此,中國現代文學的每一次寫作或闡釋都對中華民族集體意識的形成起到了促進作用。
魯迅在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一文中提出了民族語言自覺的重要性。魯迅強調在追求文學形式一體化的同時,要求保留民族自身的獨特性⑨。這一過程不僅需要借鑒外國文學,還需要吸納失傳已久的中國古典傳統,而小文學的立場正好能幫助魯迅實現他的追求。加入少數派不僅意味著反西方文化霸權的姿態,自我邊緣化的舉措也幫助魯迅創造出有別于傳統文化的新文學。魯迅民族寓言式的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奠定了基礎。其在語言上的創新、內在強烈的政治驅動力以及對國民性的探究,與德勒茲和瓜塔里對小文學的期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為了更好了解小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作用,我們需要對中國對弱小民族文學的閱讀和接受有更深刻的了解。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強調翻譯在多文學系統中的重要性。他認為外國文本的翻譯和借鑒可以成為小文學的活力源泉,因為這種實踐能鼓勵弱小民族文學的轉型⑩。對弱小民族文學的引進和翻譯是中國知識分子建構自己小文學話語的重要起點。因此,本文特別關注魯迅翻譯保加利亞現代作家伊凡·伐佐夫(Иван Вазов,1850—1921)的兩篇短篇小說《戰爭中的威爾珂》和《村婦》,以探討魯迅對小文學的關注,以及他對民族主義和語言政治的理解11。
伐佐夫被稱為“保加利亞文學之父”,是保加利亞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地位與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相當。他是世界范圍內被閱讀和研究最多的現代保加利亞作家。自從1396年奧斯曼帝國侵占保加利亞以來,保加利亞經歷了近500年的奴役。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保加利亞文學作品多數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懷,伐佐夫的作品也是如此。保加利亞民族獨立斗爭的復雜經歷激起了中國作家的強烈共鳴。這也是伐佐夫的作品走入魯迅視野的原因。此外,保加利亞的農耕文化在伐佐夫的作品中也有諸多體現。這對尋找表現農村生活文學手法的中國作家來說,也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魯迅是伐佐夫作品的第一批中文譯者12。魯迅對“叫喊和反抗”的民族作家的偏愛引導他選擇了東歐文學13。魯迅首次翻譯的伐佐夫短篇小說《戰爭中的威爾珂》發表在1921年《小說月報》的“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上14。這篇短篇小說后來被收入1922年出版的《現代小說譯叢》。該選集收錄了周氏兄弟所翻譯的30篇短篇小說,其中大部分可以算作是弱小民族文學作品。1935年,魯迅翻譯了伐佐夫的第二篇小說《村婦》,發表于生活出版社的《譯文》最后一期15。雖然該刊的正式編輯是黃源(1906—2003),但幕后主力其實是魯迅和茅盾16。《譯文》對文學作品的選擇并不帶有強烈的政治取向,但選篇多少反映了編輯們的個人觀點和品位17。
魯迅的外語能力決定了他在接觸弱小民族文學時必須倚仗中介。雖然魯迅的日文水平毋庸置疑,但日本當時對東歐小國及其文學的介紹非常有限。為了閱讀和翻譯保加利亞文學,魯迅主要依靠了當時能找到的德語出版物。魯迅通過德語接觸世界文學的時間與歌德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相距約百年時間。此時德國關于世界文學的介紹可謂層出不窮。鑒于魯迅對德語資料的依賴,了解德國話語如何影響魯迅對世界文學以及小文學的理解就顯得尤為重要。有學者列舉了魯迅的大量德語藏書,以及這些資料在魯迅閱讀寫作過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以證明了魯迅“德語化”的傾向18。不過,這種觀點簡化與低估了魯迅的知識背景和修養。誠然,正如帕斯卡爾·卡薩諾瓦證明的那樣,世界文學的建構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且可能被嚴重等級化19。哈里什·特里維迪也感嘆,小文學往往需要依賴主流語言的翻譯來獲得認可,而這一做法強化了世界文學中的等級制度20。然而,我們不應忽視魯迅等翻譯家的自主性和自覺性。他們絕非全球市場上同質化和商品化文學產品的全盤接受者。魯迅對世界文學的認知建立于他對中國文學的看法之上21。盡管魯迅可參考的資料有限,但他的世界文學觀獨立于德國本土的論斷,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
一、作為路徑的德國
盡管魯迅依賴德語資源,但他對世界文學的解讀展現了一種艾米莉·阿普特提出的“外中心”(ex-Centric)立場,有效抵制了阿普特筆下的兩種霸權22。這種“外中心”立場使魯迅得以避開當時世界文學話語中的文化普泛性,提升主流之外的小文學的價值。從現存的魯迅藏書記錄來看,他早期對世界文學的了解主要來自德文資料的閱讀23。但是,我們不能就此認為他對世界文學的思考完全依賴于德文資料的論述。魯迅所擁有的德文書籍在介紹世界文學時采用了各種不同的角度。這些書籍有的側重于西歐文學和文學流派,如艾拉·曼施(Ella Mensch)的《人人都能使用的文學會話詞典》(Litterarisches Konversations-Lexikon für Jedermann),有的則突出民俗傳統,強調德國文學的獨特性,如古斯塔夫·卡普勒斯(Gustav Karpeles)1898年出版的《文學漫談》(Literarisches Wanderbuch)。還有一些著作,如約翰內斯·舍爾(Johannes Scherr)的《世界文學插圖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teratur)和保羅·維格勒(Paul Wiegler)的《世界文學史:外國詩歌》(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Dichtung fremder V?lker),則強調古代文學,著重介紹包括中國、印度、埃及在內的非歐洲文明的文學作品。這些書籍大多以歐洲為中心,極少涉及東歐的文化和文學。雖然俄羅斯文學——尤其是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因現實主義盛行而引人矚目,但除此之外,德國書籍對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文學往往鮮有涉及。在少數提及非俄羅斯的斯拉夫文學的書籍中——例如卡普勒斯1901年出版的《古今文學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von ihren Anf?ngen bis auf die Gegenwart)和維格勒的《世界文學史:外國詩歌》——論述一般也都很簡短,而且往往忽略現代文學。為了更廣泛地了解包括保加利亞文學在內的斯拉夫其他語種文學,魯迅買了兩本專書:卡普勒斯1905年出版的《新文學漫談:斯拉夫卷》(Literarisches Wanderbuch:Neue Folge:Slawische Wanderungen)和伊日·卡拉塞克·澤·洛維茨(Ji
卡拉塞克的《斯拉夫文學史》是魯迅了解斯拉夫文學最重要的參考資料24。作為捷克裔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卡拉塞克以詩人的敏感和抒情的風格講述斯拉夫文學,這使他的書有別于魯迅其他德文資料。除了對捷克文學的詳細描述,此書還對波蘭、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保加利亞和波希米亞文學進行了探討。在魯迅擁有的所有德文書籍中,只有卡拉塞克的書詳細介紹了保加利亞現代文學。由于魯迅對近現代世界文學最感興趣,這本書成了魯迅的重要指南。在翻譯伐佐夫《戰爭中的威爾珂》的后記中,魯迅將保加利亞文學的曙光定格在19世紀末俄土戰爭(1877—1878年)之后,即保加利亞文化擺脫土耳其統治和希臘東正教禁錮之后25。魯迅還指出,保加利亞的現代文學打上了民族苦難的烙印,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傾向26。魯迅的觀點與卡拉塞克《保加利亞文學》(Bulgarische Literatur)一章的開篇如出一轍,這一證據清楚地表明魯迅對卡拉塞克著作的直接借鑒。魯迅在后記中還稱伐佐夫為文體家,這同樣與卡拉塞克的評論相呼應。
盡管伐佐夫是當時最杰出的保加利亞作家,并獲得了國際聲譽,但在大多數德國文學評論家對世界文學書寫中,保加利亞文學整體都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存在,更遑論對伐佐夫的關注。魯迅的德文世界文學書籍中幾乎沒有一本提及他的名字,只有卡拉塞克是個例外。他在介紹保加利亞文學的開篇就指出伐佐夫是保加利亞當代最杰出的作家。伐佐夫也是卡拉塞克著墨最多的一位。魯迅有可能在閱讀卡拉塞克1906年的著作之前就接觸過伐佐夫的名字。1905年,魯迅最初接觸世界文學時所依賴的德國雜志《來自外國語》(Aus fremden Zungen)上刊登了伐佐夫的短篇小說《尤佐爺爺在看著》(Дядо Йоцо гледа,德文名:Der alte Joko sieht),并附有作者的傳記27。然而,魯迅從未提及這篇短篇小說,也未在自己的序言中使用該傳記作為參考28。從魯迅的論述和選篇推斷,即使魯迅通過《來自外國語》注意到了伐佐夫的存在,卡拉塞克的文學史對魯迅的影響仍要大得多。
卡拉塞克的個人判斷直接影響了魯迅對保加利亞文學的理解。魯迅的斷言——過度強調民族苦難和高漲的愛國熱情導致保加利亞缺乏偉大的詩人——正是遵循了卡拉塞克的判斷29。事實上,在19世紀,保加利亞就有佩科·斯拉菲可夫(Петко Славейков,1827—1895)和赫里斯托·博捷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1848—1876)等著名詩人。卡拉塞克自認是現代詩人中的佼佼者,是象征主義、頹廢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實踐者。因此,保加利亞沒有偉大詩人的觀點是卡拉塞克從個人閱讀體驗出發提出的一個相對有爭議的觀點。魯迅在《戰爭中的威爾珂》的序言中省略了論斷來源,使卡拉塞克夾帶私人感情的論斷變成了一種客觀陳述。與此同時,魯迅將伐佐夫塑造成偉大的散文家,并與保加利亞詩歌創作的貧瘠進行對比,更強化了這一印象。這種對比同樣沿襲了卡拉塞克的敘述,卻有誤導之嫌。事實上,伐佐夫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他最初還是以詩人的身份登上保加利亞文壇的。
這種混淆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魯迅對保加利亞現代文學了解的匱乏。畢竟,除卡拉塞克的書之外,魯迅的主要補充資料是伐佐夫的德文譯者瑪麗亞·約納斯·馮·薩塔恩斯卡(Marya Jonas von Szatánska)在伐佐夫小說集中撰寫的前言。魯迅在序言的寫作過程中,也從該前言中提取了伐佐夫生平的細節。有趣的是,馮·薩塔恩斯卡稱伐佐夫是保加利亞最著名的詩人,他的小說成就僅次于詩歌成就30。魯迅顯然沒有采用這一論斷,但他在后記中提到了馮·薩塔恩斯卡描述的伐佐夫的愛國詩歌。此外,魯迅還提到了伐佐夫對包括戲劇在內的其他文學體裁的貢獻,以此證明伐佐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這一論斷只在馮·薩塔恩斯卡的前言中出現過,并非卡拉塞克的觀點。事實上,魯迅參考的兩種德語材料的論述并不完全一致,與論述人的身份有關:卡拉塞克是一位對斯拉夫文學以及伐佐夫的創作有獨到見解的現代詩人,而作為譯者的馮·薩塔恩斯卡則毫不掩飾對伐佐夫文學才華的崇拜之情。
盡管存在種種不一致,魯迅還是準確地抓住了伐佐夫文學創作的主要特點: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卡拉塞克和馮·薩塔恩斯卡都著重論述了伐佐夫創作中的這些主題,強調人民解放、民族自豪感,以及英雄主義為保加利亞文學尤其是伐佐夫文學創作的核心。卡拉塞克的書中特別提到了一個感人的細節:伐佐夫在意大利游覽時,聽到一位英國人贊美當地的美景,他回答說他知道一個地方比這更美,意指自己的家鄉——巴爾干的玫瑰園31。而這一細節也被魯迅收入到自己的介紹中32。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雷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Universal-Bibliothe)為魯迅提供了接觸小文學原文的機會。該出版社以出版黃色封面的世界文學著作聞名。魯迅翻譯的兩篇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都依據了馮·薩塔恩斯卡在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譯作《保加利亞女人和其他短篇小說》(Die Bulgarin und andere Novellen)33。而這本書是萬有文庫中的一本。從魯迅的藏書記錄來看,這似乎也是他擁有的唯一一本保加利亞文學書籍。根據周作人的說法,東京出售德文書籍的書店并不多,南江堂是東京唯一一家專門經營德文出版物的書店。那里出售的大部分德文書籍以醫學院和大學師生為讀者群,也有一些文學叢書,包括雷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數以千計的此類書籍以平裝書的形式印刷,封面為特有的黃色,每本售價為10到50美分,像魯迅這樣的學生也完全買得起。
自1867年雷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出版的第一本書開始,這套叢書以低廉的價格、良好的質量和廣泛的發行量,成為普通讀者閱讀文學作品的一大選擇。這套叢書支持人文教育,將其視為促進社會文化進步的有效手段。它還旨在通過樹立德語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來強化德國的民族認同感34。雷克拉姆將不同國家的經典作品與大眾文學混合發售,推廣了一種新穎的世界文學模式。萬有文庫率先向德語世界的讀者介紹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35。其中許多作品還免收版稅,這也有助于雷克拉姆出版社保證低成本的原則。萬有文庫最初旨在面向來自不同階層不同經濟群體的德國讀者,最終卻也惠及了德國以外像魯迅這樣的世界文學讀者。
由于萬有文庫堅持不懈地出版小文學作品,魯迅得以接觸到來自弱小民族的大量現代文學作品。對魯迅來說,這套叢書是他接觸世界文學最重要的窗口。當時,魯迅已經對弱小民族的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這些文學作品在其他語言中很難找到,但雷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提供了很多選擇。如果魯迅找不到他想要的書,他或者通過丸善書店和相模屋書店訂購,或者在二手書市場上尋找36。雖然這些書并沒有花費魯迅大量的金錢,但他為收集這些書所付出的努力卻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魯迅收藏的幾乎所有弱小民族文學的書籍都來自雷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包括伐佐夫譯本37。
德文資料無疑是魯迅了解包括保加利亞文學在內的弱小民族文學的重要渠道,也為魯迅世界文學觀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素材。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魯迅在選擇文學讀物時缺乏自己的獨立思考。首先,魯迅的德文書籍種類繁多,每一本都展現了作者對世界文學的獨特見解。如果魯迅是世界文學主流話語的追隨者,便不會特別關注受人忽視的弱小民族文學。此外,在翻譯文學作品方面,雷克拉姆出版社的萬有文庫收錄了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大量書籍,其中也包括歐洲文學經典,這些作品在日本圖書市場上遠比保加利亞等邊緣國家的作家作品更為常見。盡管如此,魯迅還是積極地尋找那些鮮為人知的作家作品。這種決心體現了他對世界文學的獨特品位,而這種品位并不一定是由德國圖書市場決定的。與德國出版業對經濟效益的看重相比,魯迅更重視小文學獨到的文化資本。因此,盡管德文資源是魯迅接觸世界文學的重要途徑,魯迅的世界文學觀與德國主流大不相同。
二、民族主義的變奏
伐佐夫與魯迅都是民族精神的倡導者和代表。不過,他們的創作方法有所不同:魯迅在作品中以犀利的筆觸探尋民族性問題,痛斥中國的弱點和不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伐佐夫常常在作品中歌頌保加利亞的祖國和人民,雖然筆法中不乏諷刺辛辣的部分,但是出發點大多積極向上。可以說伐佐夫在描寫保加利亞人民的優缺點時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而并不像魯迅那樣字字見血38。伐佐夫在頌揚保加利亞近代民族斗爭史的同時,也揭示了勝利的代價,展示了戰爭頻仍和社會動蕩給普通家庭造成的巨大傷害。伐佐夫在詩歌上更多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但他的小說更接近現實主義。他最受歡迎的小說《軛下》(Под игото)主張喚醒民族力量,被稱為保加利亞的《戰爭與和平》39。作為一個俄羅斯文學的愛好者,伐佐夫受到19世紀俄羅斯文學,尤其是現實主義作品的啟發。他本人也在保加利亞之外聲名鵲起:他是第一位作品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的現代保加利亞作家40。
1878年,保加利亞擺脫了土耳其數百年的統治,實現了獨立。雖然俄國是反土耳其的主要力量,但保加利亞志愿者也參加了這場戰爭。俄土戰爭后,部分保加利亞的土地仍在土耳其統治之下,保加利亞的自治權也因俄國對保加利亞政治的嚴重介入而受到損害。當保加利亞最終收回土耳其控制的領土并在1885年實現完全統一時,俄國的宿敵奧匈帝國擔心在巴爾干半島出現一個聽命于俄國的強大國家,于是誘使塞爾維亞進攻保加利亞。同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爭爆發。塞爾維亞曾與保加利亞共同對抗土耳其人,過去盟友的入侵使得許多保加利亞人感到驚訝。直到保加利亞成功保衛了自己的領土,歐洲主要大國才承認了保加利亞的統一。經歷過政治、社會和文化動蕩的伐佐夫傾向于描寫保加利亞解放和統一的艱難歲月。魯迅翻譯的兩篇短篇小說都以這段歷史時期為背景。1886年的短篇小說《戰爭中的威爾珂》以1885年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爭為中心,而1899年的《村婦》則發生在1876年土耳其統治的最后時期。
《戰爭中的威爾珂》圍繞農家男孩威爾珂和他作為士兵的成長經歷展開,以問題形式結束:為什么保加利亞人必須與他們的兄弟塞爾維亞人作戰?《戰爭中的威爾珂》并不是一個復雜的故事。這個經歷了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爭的農家男孩最終失去了左臂。威爾珂的天真無邪與引發兄弟國家戰爭的大國權謀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魯迅在譯文后記中強調了伐佐夫的批判,并稱這篇小說是伐佐夫“悲憤的叫喚”41。魯迅翻譯的第二篇短篇小說是伐佐夫1899年寫的《村婦》。故事以保加利亞著名詩人、民族英雄赫里斯托·波特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1848—1876)的戰敗和死亡拉開序幕。雖然伐佐夫與波特夫私交甚篤,并深受其詩歌和革命激情的鼓舞,但波特夫并不是主人公。故事講述了農婦伊里扎英勇救助波特夫青年戰友的故事。魯迅在后記中對伐佐夫筆下具有代表性的保加利亞村婦進行了評論:迷信,固執,然而健壯,勇敢;對革命事業及美好未來的承諾抱有堅定的信念42。
魯迅選擇的兩篇小說是馮·薩塔恩斯卡翻譯的伐佐夫作品集《保加利亞女人和其他短篇小說》開篇的兩篇小說。事實上,讀伐佐夫作品長大的保加利亞讀者大多對作品集中的第三篇短篇小說《他會回來嗎?》(Иде ли?德文:Kommt er zurück?)更為熟悉,這是時至今日保加利亞小學生的必讀書目。故事以兩個孩子對兄長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場上凱旋的翹首以盼為主線,極力渲染勝利大軍歸來的歡快氣氛。殊不知兩個孩子的兄長已經戰死沙場,再也不可能回家。與魯迅翻譯的兩個故事相比,這個故事有力地譴責了戰爭的殘酷,揭露了戰爭給普通家庭帶來的傷害。雖然三篇小說都探討了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土耳其之間的沖突,但與另外兩篇不同,這篇小說的人道主義壓倒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主題。魯迅之所以選擇前兩個故事,很有可能是看重前兩個故事的民族主義特征。
盡管魯迅認為伐佐夫的作品簡單,但他也承認其有動人之處43。魯迅翻譯的兩篇短篇小說都沒有將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視為表面價值。通過描寫天真卻真誠的保加利亞普通人,尤其是農民在戰爭中的經歷,伐佐夫突出了普通群眾對自己同胞的熱愛。與魯迅在《阿Q正傳》等農民題材小說中對中國國民性的尖銳批判相比,伐佐夫對保加利亞農民的態度要寬容得多。在魯迅看來,通過軍事暴力實現的民族獨立并不能算作全面的革命勝利;相反,他的中華民族救亡愿景立足于啟蒙民眾,要求將他們從保守陳舊的觀念中解放出來。相比之下,伐佐夫并沒有尋求對保加利亞大眾的思想改造。相反,他贊美保加利亞農民的淳樸以及他們對自己民族國家毫無保留的愛。
魯迅和伐佐夫的不同態度還體現在他們對各自國語運動的態度上。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左翼作家倡導無產階級文學的重要時期。作為左翼作家聯盟的領軍人物,魯迅積極參與了關于創造大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和文學形式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伐佐夫的兩篇小說通過對保加利亞農民的描寫,為無產階級文學提供了范本,他們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與政府的官方話語截然不同。也許正因為此,魯迅在第一次翻譯伐佐夫作品的十多年后,于20世紀30年代重拾伐佐夫的作品。不過,從魯迅后記的評論來看,他對伐佐夫的文學手法并不完全滿意,魯迅的譯文也偏離了伐佐夫對國語的態度。
三、語言的解域化
無論魯迅選擇伐佐夫兩則故事的動機如何,兩個故事中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魯迅的譯本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這得益于魯迅對德文腳注以及德文譯者闡釋的翻譯,以及對腳注的補充44。但與此同時,伐佐夫對農村方言的大量使用,讓他的故事承載了濃重的鄉土氣息。作為保加利亞現代文學的先驅,伐佐夫對口語的保留確立了他民族作家的地位。然而,對于通過德文譯本閱讀小說的魯迅來說,卻很難感受到這一語言特征,更遑論體現在自己的中文譯本中。
伐佐夫對保加利亞現代語言和文學上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詩歌及散文創作奠定了現代保加利亞文學語言的基礎45。在魯迅翻譯的兩篇短篇小說中,伐佐夫的寫作風格也發生了變化。在1886年的《戰爭中的威爾珂》中,伐佐夫在描寫和對話中使用了大量地方用語,包括今天保加利亞人幾乎無法辨認的方言詞匯46。相比之下,伐佐夫晚期作品的語言更接近今天標準的保加利亞語。他僅僅在對話中偶爾出現非慣用詞匯,以保留方言帶來的真實感。譬如,在1899年的短篇小說《村婦》中,他使用的語言大多已經標準化。但是,在土耳其官員侮辱保加利亞平民時,伐佐夫依然保留了一些土耳其語,譬如“異教徒豬玀”(свини гявурски)和“人渣”(хънзъри)等古老的土耳其借用語47。這些詞可能未必復現了土耳其官員的真實說話方式,但卻營造出一種“土耳其”的氛圍。
魯迅并非完全不知道伐佐夫在語言上的努力。在翻譯《戰爭中的威爾珂》的序言時,魯迅強調了伐佐夫語言上的貢獻,即在文學創作中夾雜日常用語以及家鄉方言的做法極大豐富了保加利亞的文學創作48。然而,伐佐夫對方言俗語的信手拈來使得譯者極難捕捉其修辭的精妙。例如,伐佐夫的同音雙關語在譯文中根本無法呈現。在翻譯和轉譯過程中,隨著與原文愈行愈遠,語言上的繁復含義也被層層簡化。例如,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威爾珂最初的綽號是“巴布爾奇科”(Папурчик),可能是因為他瘦高的外形酷似蘆葦(папур)的緣故。在故事的高潮部分,當威爾珂從地上站起來大喊戰斗口號時,他成了地平線上唯一突出的目標,吸引了敵人的火力。此時,威爾珂的戰友們用他的綽號稱呼他,把他比作戰場上一根孤獨挺立的蘆葦,頗具喜感。另外,威爾珂的綽號還與“中尉”(подпоручик)一詞發音相似,這也成為威爾珂在軍隊中的新綽號。馮·薩塔恩斯卡在翻譯時保留了部分雙關語,將原來的綽號改為“烏瑪利丹”(Umalejtan),與德語“中尉”(Unterleutnant)的發音相似,但犧牲了蘆葦的典故。而當魯迅將這個綽號音譯為“烏瑪利丹“時,所有的諧音雙關都不復存在了。
伐佐夫經常使用農村方言,這也給翻譯帶來了困難。由于方言在早先的故事中出現得更多,馮·薩塔恩斯卡在翻譯《戰爭中的威爾珂》時犯的錯誤比翻譯《村婦》要多很多。完全依賴德文譯本的魯迅也重復了這些錯誤。例如,魯迅稱后備軍首領伊凡·摩利希維那(Иван Морисвинята)為“狠毒的人”49,沿用了德語修飾詞Grausamen50。然而伐佐夫使用的修飾詞實際上更接近于“暴躁的”(liut)51。同樣,魯迅“第一個軍官”的翻譯52沿用了德文翻譯Der erste Offizier53,但保加利亞原文實際上指的是一位姓氏以字母“I”開頭的上尉(Капитан И.)54。更明顯的誤譯出現在對行軍預備役人員的描述中。在原文中,預備役軍人用黃楊樹枝裝飾步槍的槍口,但馮·薩塔恩斯卡卻描述他們“嘴里叼著小黃楊樹枝”(Im Mund halten sie kleine Zweige von Buchsbaum)55。馮·薩塔恩斯卡對保加利亞語句結構的混淆導致她誤解了這句話。而這個原文中沒有的這個細節被魯迅從德文原封不動地照搬了下來56。
盡管有這些零散的誤譯,馮·薩塔恩斯卡和魯迅的譯本都在各自語言允許的范圍內基本保留了故事的原汁原味。事實上,魯迅的大部分誤譯都源自德文誤譯57。這種相對的“準確性”表明了魯迅作為譯者的謹慎和努力。然而,魯迅缺乏靈活性的“硬譯”,或如王璞所稱,魯迅的“間接忠實”(indirect fidelity)58常常使譯文顯得突兀。例如,魯迅將德語短語“做客”(zu Gaste kommen)59譯為“來做客人的”60。而保加利亞語原文中的“來做客”(да ни дойдат на гости)61指的不是歡迎客人,而是指兇殘的土耳其人的不請自來。魯迅對德文“客人”的直譯(比中文“客人”的理解更含糊)抹殺了隱含的危險性,失去了敘事的張力。除了這些誤譯,魯迅逐字翻譯更常見的副作用是文字上的生澀。魯迅的譯文“饑餓克服了市鎮”62是德文der Hunger erobert die St?dte63的直譯。保加利亞的原文為“饑荒奪取了城市”(глад град превзима)64。雖然中文動詞“克服”是德語“征服”(erbert)的一種正確翻譯,但它與“市鎮”的不匹配造成了語言上的脫節。
魯迅的硬譯策略與漢語現代化有關,但這種生硬的逐字逐句譯造成了一種刺耳的效果,而且這種效果在保加利亞原文和德文譯本中是不存在的。這樣的直譯往往阻礙了中國讀者充分領略伐佐夫文字的魅力。魯迅在翻譯《村婦》中大量的風景描寫時,更為明顯。生澀的造句,諸如“河流在深處單調的呻吟的作響”或“它荒涼的站著,和上帝親手安排的它的山洞”之類,隨處可見65。雖然魯迅譯文中幾乎所有的語義單位在德文版中都有對應,但綜合效果卻使描寫失去了原有的抒情性。魯迅試圖將一個冗長的分句放在一個詞前面作為修飾,違背了漢語措辭的規律。例如“真會將人刺在那刀尖在日光下發閃的刺刀上”66之類的詞句,讓人看得一頭霧水。魯迅的“硬譯”造成的異乎尋常的詞句組合,部分可能是受他所使用的德語文本的啟發,但這些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生硬之感。
魯迅的翻譯最終為伐佐夫的寫作注入了一種原文所沒有的文體上的不成熟。雖然中國讀者可能會認為這種不成熟是當時保加利亞文學固有的,但事實上,這種粗糙與現代漢語的誕生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在現代漢語的萌芽階段,魯迅等作家不得不直面外語對漢語的挑戰,同時還要處理古典與白話文風格之間的齟齬。魯迅在這兩種文體之間的斡旋在翻譯中尤為困難。
保加利亞語言的現代化具有自身的特點,在保加利亞民族主義的建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保加利亞現代作家面對的挑戰與魯迅不同,他們的任務在于通過現有方言尋求新的書面語言,同時盡可能地摒棄土耳其統治遺留下的語言的束縛。而漢語改革的目標是構建中國的民族語言。與伐佐夫采用現有的保加利亞方言一樣,許多中國人,包括20世紀30年代的左派人士,也努力向大眾學習,致力于創造一種大眾能夠理解的語言。然而,魯迅選擇了一條更為曲折的道路。他將中國的白話和德語的句法與詞匯結合起來,使他的翻譯成為另一種小眾的存在。
魯迅在1931年與瞿秋白(1899—1935)的通信中討論了他在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立場。瞿秋白強調翻譯在塑造現代漢語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正確的白話”的絕對標準:從日常對話中直接采用便于大眾理解的漢語67。瞿秋白主張公開、謙虛地向人民學習——這種方法更符合無產階級理論,即優先考慮群眾的話語權。魯迅并不反對參考大眾的口語,但他也主張通過硬譯引入新的表達方式,借用外語的語法和詞匯來豐富漢語68。魯迅沒有提出一種絕對“正確”的語言,而是將漢語想象成一種“活”的語言,尊重其自身發展的軌跡。他在各種語言之間協商,旨在將漢語從成型的語言體系中解放出來。他的硬譯揭示了語言蛻變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也可以被視為民族成長的狀態。
伐佐夫的寫作目標可以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術語來描述:他使自己的母語擺脫了土耳其語的影響,并通過構建煥然一新的保加利亞語來實現母語的本土化。魯迅的翻譯并沒有復制這一目標。相反,我們見證了魯迅如何通過模仿弱小民族文學作品中所謂語言轉換來檢驗漢語的語言潛力。他的硬譯實踐是他漢語創新的一部分,以期充分發揮漢語變革的潛力,由此避免傳統漢語寫作風格所決定的“地域化”的風險。魯迅看似笨拙的語言實踐并沒有遵循一條既定的路徑,而是為多重路徑的不同語言表達形式開辟了新的可能。歸根結底,魯迅通過硬譯的方式引入弱小民族文學,有助于他挑戰現有漢語系統的正統性及其既有陳規和表達結構。他自愿以“小”的姿態來激發漢語潛力。
魯迅所提倡的小文學在助力魯迅彰顯個人語言風格的同時,也幫助他借用弱小民族的集體力量去對抗帝國主義。小文學也為中國文學的復興和內容風格的變革做了準備。正如勞倫斯·韋努蒂所言:“好的翻譯是小眾化的:它通過培養異質話語來釋放其他的可能性,幫助標準語和文學規范敞開大門,接納外來事物、次等事物和邊緣事物。”69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眾的邊緣地位——它“小”的特質——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它暗含了對主流標準持續抵抗的力量。通過將中國經驗與弱小民族的經驗相提并論,魯迅在中國讀者與自身文化過去的輝煌之間注入了變革的緊迫感。通過對保加利亞等文學的翻譯,魯迅不僅借助小文學的革命精神重塑中國的民族性,也認可了小文學作為世界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促進了解域化世界文學共同體的建立。■
【注釋】
①文章的英文版發表在雜志《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上:Xiaolu Ma,“Minor Literature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World Literature:Lu Xuns Translation of Bulgarian Literature via German Sourc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5,no. 1(2023).因為篇幅限制,原作者在英文論文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刪節。
②陳獨秀在1904年發表的《說國家》一文中將世界各國分為被外國欺負的國家和列強兩大類。參見宋炳輝:《弱勢民族文學在現代中國:以東歐文學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5頁。隨后,“弱小民族”一詞出現在李紹裘1911年的一篇文章中。見李紹裘:《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方式》,《邵中學生自治會期刊》1911年,第2-3頁。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期刊中,“弱小民族”出現的頻率很高。當時“弱小民族”與“被侮辱/被壓迫/被損害的民族”幾乎可以互換使用。另一方面,關于被侮辱/被壓迫/被損害民族的論述至少可以追溯到1921年出版的《小說月報》“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盡管這些術語被頻繁使用,這些標簽所代表的國家多種多樣。為統一起見,本文使用“弱小民族”來涵蓋繁復的形容詞所帶來的多重含義。
③雖然一般東歐文學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弱小民族文學,但實際上,中國讀者將弱小民族文學和被侮辱/被壓迫/被損害文學聯系在一起的文學有三類:1.歐洲國家的文學,不包括那些公認的強國,如英國、法國和德國;2.亞洲國家的文學,如印度、韓國和越南的文學,通常不包括日本;3.文明古國的文學,如希臘、波斯、阿拉伯文學。參見宋炳輝:《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2期。
④宋炳輝:《弱勢民族文學在現代中國:以東歐文學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10頁。
⑤Fredric 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Social Text,no. 15(1986).
⑥Jing Tsu,“Getting Ideas about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a,”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Urbana)47,no. 3(2010):297-98.
⑦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trans. Dana Pola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18.
⑧這并不意味著魯迅或其他作家在構思現代漢語寫作風格時完全摒棄了傳統。魯迅的抒情方式很大程度上仍然得益于他的中國古典文學訓練[Jon Eugene von Kowallis,The Lyrical Lu Xun: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ed. Xun L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與伐佐夫一樣,魯迅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的詩歌和散文創作風格迥異。
⑨Emily Sun,On the Horizon of World Literature:Forms of Modernity in Romantic England and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21),38.
⑩Itamar Even-Zoh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ed. Lawrence Venuti(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201.
11為了便于理解,本文沿用了魯迅對兩個小說標題的翻譯。
12在魯迅之后,也有其他中國作家翻譯了伐佐夫的作品。1923年,茅盾在《婦女雜志》上發表了伐佐夫的短篇小說《他來了么?》(Иде ли?)。這篇小說被收入中學教科書,使伐佐夫的名字在中國讀者中廣為流傳(余志和:《希望引起中國讀者的共鳴——我譯〈保加利亞中短篇小說集〉》,《文藝報》2018年7月9日)。胡愈之出版了《失去的晚間》(世界語:Perdita Vespero;保加利亞語:Една изгубена вечер)。隨著伐佐夫越來越受歡迎,孫用于1931年出版了從世界語翻譯的伐佐夫短篇小說集,題為《過嶺記》。
13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525頁。
14魯迅在1921年8月6日給周作人的信中提到,他已經翻譯了《戰爭中的威爾珂》的大部分內容;他還討論了主人公名字的音譯和內涵。見魯迅:《210806致周作人》,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04-405頁。他于8月17日完成了翻譯,參見魯迅:《210817致周作人》,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08頁。他還寫了一篇后記,于8月22日完成,參見魯迅譯:《戰爭中的威爾珂》,載《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412頁。
15魯迅在1935年6月3日給黃源的信中提到了翻譯伐佐夫《村婦》的計劃(魯迅:《350603致黃源》,載《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74頁)。魯迅當時最主要的計劃是翻譯果戈理(1809—1852)的《死魂靈》。8月9日,他告訴黃源,他可能沒有時間翻譯伐佐夫的作品(魯迅:《350809致黃源》,載《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517頁),但他還是在9月6日完成了翻譯(魯迅:《350906致黃源》,載《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534頁)。
16施曉燕:《〈譯文〉月刊在生活書店的出版和停刊》,《上海魯迅研究》2017年第4期。
17除了伐佐夫的故事,此期的譯文大多是俄蘇短篇小說。這一選擇符合魯迅的喜好。他一生都對俄羅斯和蘇聯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
18Huiwen Zhang,“Lu Xun contra Georg Brandes: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EU-topías.(Interculturality,Communication,and European Studies)14(2017):141.
19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trans. M. B. Debevois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0Harish Trivedi,“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The Indian Context,”in 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ed. Susan Bassne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9),15.
21Daniel M. Dooghan,“Old Tales,Untold:Lu Xun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14,no. 1(2017):57.
22“外中心”視角可以被理解為立足于中心之外的視角。有學者指出邊緣文學與中心文學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取決于世界文學整體的權利之爭,而是基于主流文學和邊緣文學在文化挪用中不對稱的價值體系。[Thayse Leal Lima,“Transl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Centric,”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26,no. 3(2017/07/03 2017):468.]
23魯迅一生中最常用的兩種外語是日語和德語。不過,這兩種語言在他接受世界文學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魯迅日文藏書中有關世界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書籍大多出版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左翼文學運動。另一方面,魯迅收藏的德國世界文學書籍主要是1920年以前出版的。后者應該是他早期了解世界文學的主要參考資料。參見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3卷,北京魯迅博物館,1959;中島長文:《魯迅目睹書目:日本書之部》,宇治中島長文1986年自資。魯迅并非對日本在世界文學介紹上的努力一無所知,但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仍不遺余力地收集德文資料,這說明日本圖書市場上缺乏他感興趣的資料。他的藏書中還有兩本英文書:John Drinkwater,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New York & London:G. P. Putnams Sons,1923);John Albert Macy,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ed. Onorio Ruotolo(New York:Boni & Liveright,1925)。然而,由于魯迅的英文知識不足,且這兩本書的出版日期相對于他的德文著作較晚,本文不將這兩本書視為主要資料來源。
24卡普勒斯的《新文學漫談:斯拉夫卷》在選題上極為挑剔。該書的目的不是全面介紹斯拉夫文學,也沒有提及保加利亞文學。而卡拉塞克的書則相當全面,涵蓋了許多其他書中未提及的斯拉夫小文學。魯迅似乎經常參考這本書,因為他在給弟弟周作人的多封信中都提到了這本書,還翻譯了其中的一部分供周作人參考。他甚至還抱怨過翻譯卡拉塞克的困難。具體參見魯迅:《210713致周作人》,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91頁;魯迅:《210716致周作人》,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96頁;魯迅:《210806致周作人》,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04頁;魯迅:《210825致周作人》,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09頁。
251396年,保加利亞被奧斯曼帝國占領,巴爾干地區所有被征服的基督徒(包括保加利亞人)都被置于君士坦丁堡希臘教區管轄之下。隨著19世紀希臘和保加利亞民族主義的興起,這種局面變得難以維持。保加利亞復興的雙重目標是復活獨立的教會(1870年獲準)和政治獨立(1878年實現)。
263241484952566266伐佐夫:《戰爭中的威爾珂》,魯迅譯,載《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410、411-412、412、411、397、403、397、408、404頁。
27《尤佐爺爺在看著》是一個較為輕松愉快的故事,為慶祝保加利亞獨立而寫。故事主要圍繞一個瞎眼的老農夫展開,講述他如何用僅存的理智迎接保加利亞的獨立。這篇故事與魯迅喜歡的文學風格相去甚遠,這可能是魯迅不太關注它的原因。
28感謝崔文東提供的原文資料。《來自外國語》的傳記部分描述了伐佐夫在保加利亞現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這可能引導魯迅去了解伐佐夫的作品。[Georg Adam,“Iwan Wasoff,”Aus fremden Zungen 4(1905):122.]不過,該傳記也記錄了伐佐夫詩歌方面的才華,并列舉了他的不少重要詩作,而魯迅的序言并未提及這些細節。此外,同一期還收錄了另一位保加利亞作家阿列科·康士坦丁諾夫(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863—1897)的作品。如果魯迅以《來自外國語》為主要資料,很難解釋他對這位作家的忽視。
29Ji
30Marya Jonas von Szatánskas,“Vorwort,”in Die Bulgarin und andere Novellen(Leipzig:P. Reclam,1908),4.
31Karásek ze Lvovic,Slav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2,97-98.
33值得注意的是,馮·薩塔恩斯卡書籍標題的德語譯文與保加利亞語標題在定冠詞和不定冠詞的運用上有細微差別。中文因為沒有定冠詞和不定冠詞的區別,所以這個細微差別在魯迅的翻譯中并沒有體現。如果完全按字面翻譯,小說標題應為《一個保加利亞女人》,而德文翻譯為《這個保加利亞女人》。伐佐夫選擇“一個”而非“這個”(特指主人公)可能是有意為之:它強調了故事主人公并不是特殊的某一個,而代表了普通的保加利亞婦女。德文翻譯則將重點放在了主人公帶的特殊性上。《戰爭中的威爾珂》也有類似的變化。原標題為《一場戰爭中的威爾珂》而不是《這場戰爭中的威爾珂》,凸顯保加利亞普通人在任何一場戰爭中都可能遇到的困境。德文譯名將重點轉移到了具體的一場戰爭,即1885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爭上。
34Georg J?ger,“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Erfolgsfaktoren der Programmpolitik,”in Reclam. 125 Jahre Universal-Bibliothek 1867—1992,ed. Dietrich Bode(Stuttgart:Reclam,1992),29.
35Lynda J. King,“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A German Success Story,”Die Unterrichtspraxis/Teaching German 28,no. 1(1995):2.
36周作人:《南江堂》,載鐘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第566-567頁。
37熊鷹:《魯迅德文藏書中的“世界文學”空間》,《文藝研究》2017年第5期。
38Clarence Augustus Manning and Roman Smal-Stocki,The History of Modern Bulgarian Literature(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60),85.
39Charles A. Moser,A History of Bulgarian Literature 865—1944,Reprint 2019 ed.(Berlin;Boston:De Gruyter Mouton,2019),98.
40Manning and Smal-Stocki,The History of Modern Bulgarian Literature,80.
42伐佐夫:《村婦》,魯迅譯,載《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728頁。有趣的是,伊里扎的宗教信仰促使她冒著生命危險,在土耳其軍隊逼近的夜晚前往修道院,請求僧侶為她的孫子祈福。然而,她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孫子的康復源于她的善行,而非僧侶的祈禱。她的醒悟打破了宗教的權威,建立了上帝與普通人之間更簡單的關系。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伐佐夫的原著中,伊里扎并沒有被革命激情所驅使:她冒著生命危險救男孩是出于對基督徒和保加利亞同胞的責任感,而不是出于對戰爭事業本身的支持。事實上,她批評了戰爭導致的無謂犧牲。因此,雖然魯迅沒有對故事本身進行改動,但他在后記中的解讀實際上稍稍偏離了伐佐夫的原意。
436065伐佐夫:《村婦》,魯迅譯,載《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729、716、713頁。
44例如,在《戰爭中的威爾珂》中,伐佐夫沒有提及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戰爭的年份(1885年),只給出了12日這一日期。馮·薩塔恩斯卡為了便于讀者理解加上了年份,魯迅的譯本也重復了這一點(伐佐夫:《戰爭中的威爾珂》,魯迅譯,載《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404頁。Iwan Wasow,“Welko im Kriege,”in Die Bulgarin und andere Novellen[Leipzig:P. Reclam,1908),40;Ivan Vazov,“Vǔlko na voina,”in Sǔchinenie(Sofia:Paskalev,1911),119.]
45Moser,A History of Bulgarian Literature 865—1944,101.
46僅以故事的前兩行為例,“閣樓”(потон)、“棚屋”(сламник)、“王國”(царщина)等日常用語都是地區性詞匯,甚至很少出現在詞典中。
47Ivan Vazov,“Edna bǔlgarka,”in Sǔchinenie(Sofia:Paskalev,1911),6.
50Wasow,“Welko im Kriege,”32.
51Vazov,“Vǔlko na voina,”113.
53Wasow,“Welko im Kriege,”38.
54Vazov,“Vǔlko na voina,”118.
55Wasow,“Welko im Kriege,”32.
57魯迅偶爾會誤譯德文版本。例如,他將“中尉轉向城市”[der Unterleutnant wandte sich der Stadt zu(Wasow,“Welko im Kriege,”36.)]譯為“少尉也背向了市人了”(伐佐夫:《戰爭中的威爾珂》,魯迅譯,載《魯迅譯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第401頁)。德文譯文與保加利亞原文一致(Vazov,“Vǔlko na voina,”116.),因此此處應為魯迅誤譯。
58Pu Wang,“The Promethean Translator and Cannibalistic Pains:Lu Xuns ‘Hard Translationas a Political Allegory,”Translation Studies 6,no. 3(2013):328.
59Wasow,“Die Bulgarin,”17.
61Vazov,“Edna bǔlgarka,”10.
63Wasow,“Welko im Kriege,”43.
64Vazov,“Vǔlko na voina,”122.
67瞿秋白:《關于翻譯的通信》,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80、384頁。
68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回信)》,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91-393頁。
69Lawrence Venuti,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8),11.
(馬筱璐,香港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