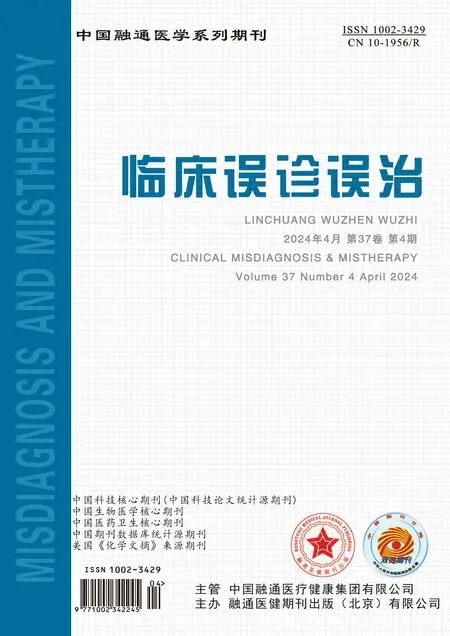以消化道癥狀首發的系統性紅斑狼瘡誤診原因探析
耿獻輝,邊緒強,王雪蓮,常書振,張洋洋,王智鋒,馮海龍,黃 錦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種自身免疫介導的彌漫性結締組織病,常累及全身多個臟器系統,臨床表現復雜多變。我國SLE患病率約為(30~70)/10萬[1-2],男女患病比為1∶10~1∶12[3-5],合并消化道癥狀的SLE患者占所有SLE患者的4%~50%,50%以上是由于患者服用藥物或者合并腸道感染引起的,真正以消化道癥狀為首發的SLE比較少見,其中約10%的患者以消化道癥狀為首發表現[6],且大多數癥狀不典型,臨床常表現為腹痛、腹瀉、惡心、嘔吐等,首診誤診率達72.7%[7]。我院2013年12月—2023年9月共收治并確診SLE 125例,因消化道癥狀首發收入我院消化科或普外科3例,均存在誤診誤治情況,現分析誤診患者臨床資料報告如下。
1 病例資料
【例1】男,35歲。以“腹痛伴惡心、嘔吐2 d”入院。患者入院前2 d出現上腹部疼痛,呈陣發性絞痛,不向他處放射,與體位變動無關,伴食欲減退、乏力、惡心、嘔吐,嘔吐呈非噴射樣,嘔吐物為胃內容物,大便不成形、無黏液膿血。急診以“腹痛待查”收入我院普外科。近1個月內,患者2次因上腹痛伴惡心于我院就診,按“急性胃炎”治療后出院。查體:意識清楚,精神差,急性病容,表情痛苦。腹部膨隆,未見腸型及蠕動波,腹軟,上腹深壓痛,無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觸及。移動性濁音(-),腸鳴音3/min。查血白細胞10.20×109/L,中性粒細胞0.827;總蛋白53.6 g/L,白蛋白32.9 g/L;尿蛋白(+);血淀粉酶正常。腹部CT:腹水、回腸擴張積氣并水腫,考慮腸梗阻。行腹腔穿刺見少量淡黃色滲出,排除腹腔臟器穿孔、壞死可能。考慮“急性胃腸炎”,予抗感染、營養支持、補液等藥物治療3 d,效果欠佳,腹痛、惡心、嘔吐時輕時重,大便呈稀水樣。入院第15天,請消化科醫師會診后,以“急性胃炎,不完全腸梗阻”轉入消化內科繼續治療。查體:顏面部輕度色素沉著。進一步查紅細胞沉降率21 mm/h;抗核抗體IgG(熒光法)(+),抗SS-A(±),抗nRNP/Sm抗體(+)。追問病史發現患者有腎病綜合征病史2年。考慮可能與免疫性疾病相關,請腎內科醫師會診,根據病史、癥狀、實驗室檢查結果,診斷為SLE,腎病綜合征,予甲潑尼龍琥珀酸鈉治療5 d,癥狀明顯好轉。3個月后隨訪,患者癥狀消失,二便正常,因蛋白尿反復到腎內科就診。
【例2】女,33歲。以“間斷腹痛、腹瀉20 d,加重1 d”為主訴入院。患者入院前20 d出現腹痛,疼痛位于臍周,呈間斷性絞痛,排黃色稀水樣便4~5/d,量不詳,伴惡心、嘔吐,嘔吐物為胃容物,在社區醫院按“感染性腹瀉”給予諾氟沙星、蒙脫石散等藥物治療,上述癥狀時輕時重。入院前1 d患者無明顯誘因上述癥狀加重來診。門診以“胃腸功能紊亂”收入我科。既往身體健康。查體:意識清楚,精神差,痛苦面容。腹部平坦,左右對稱;腹軟,全腹部未觸及包塊,臍周壓痛,無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觸及,Murphy征陰性,麥氏點無壓痛;腹部叩診呈鼓音,肝腎區無叩擊痛,無移動性濁音;腸鳴音約6/min。入我科后給予抑酸、護胃、止瀉、解痙等藥物治療3 d。查血白蛋白37.7 g/L,尿酸383 μmol/L,二氧化碳15.5 mmol/L,鈣2.07 mmol/L;血中性粒細胞0.787,超敏C反應蛋白11.01 mg/L;尿蛋白(+);凝血功能、胰酶檢查未見明顯異常。腹部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示腹水。請普外科醫師會診,考慮急性胃腸炎,胃腸道痙攣,腹水。建議給予抗感染治療,補足液體,注意電解質變化;定期復查腹部CT查看腸管擴張及腹水情況;必要時請感染科醫師會診。根據會診意見予注射用頭孢曲松鈉抗感染治療4 d,效果欠佳。進一步查抗核抗體IgG(熒光法)(+),抗nRNP/Sm抗體(+),抗Sm抗體(±),抗SSA抗體(+),抗Ro-52抗體(+),抗核小體抗體(±),抗核糖體P蛋白抗體(+),抗組蛋白抗體(±),類風濕因子193.4 U/mL,免疫球蛋白G 19.79 g/L,補體C3 0.79 g/L,補體C4 0.09 g/L,白細胞介素-6 15.88 pg/mL。多項免疫指標異常,多系統受累,請腎內科醫師會診,查體可見面部輕度色素沉著,診斷SLE,予甲潑尼龍琥珀酸鈉治療4 d,癥狀緩解。3個月后隨訪,患者癥狀消失,腎內科門診隨診。
【例3】女,20歲。因“腹痛、腹瀉1周”入院。患者1周前進食辛辣刺激食物后出現中上腹部疼痛,呈持續性絞痛,伴惡心、嘔吐,嘔吐物為胃內容物,腹瀉,大便稀水樣,2~3/d,無黏液膿血。在當地診所按“急性腸炎”給予諾氟沙星、蒙脫石散等藥物治療,效果不佳,后到當地縣醫院行腹部CT示腸壁增厚、腹水,查體見腹肌緊張,腹部壓痛、反跳痛,行左下腹診斷性穿刺抽出少量血性液體,考慮急腹癥,欲行腹部探查術明確病情,家屬拒絕。為求明確診治來我院,門診以“腹痛待查”收入我科。既往身體健康。查體:意識清楚,精神差,貧血貌,面部見少量痤瘡;腹部平坦,腹肌緊張,臍周壓痛、反跳痛,腸鳴音3/min。查血白細胞2.75×109/L,紅細胞3.35×1012/L,血紅蛋白88 g/L;尿蛋白(++),酮體(++);抗核抗體(+),抗Sm抗體(+),血清IgG4>3.2 g/L,補體C3 0.59 g/L,補體C4 0.08 g/L。腹水有核細胞數310×106/L,單核細胞數280×106/L,總蛋白45 g/L,乳酸脫氫酶208 U/L;鏡下見中等量間皮細胞、吞噬細胞、淋巴細胞。胸腹部CT:雙側胸腔可見積液影,小腸壁節段性增厚,管腔內見積液影,考慮炎癥。請腎內科醫師會診,考慮SLE,予轉科,行腎穿刺病理學檢查符合輕度系膜增生性狼瘡性腎炎(Ⅱ型),給予甲潑尼龍沖擊治療4 d,癥狀緩解。3個月后隨訪,患者腹痛、腹瀉未再出現,因蛋白尿反復腎內科門診就診。
2 討論
2.1 病情分析
SLE是多器官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膚、關節、腎臟、血液系統受累率高,有較高的臨床認知度,但現臨床對其消化道受累認識不足。SLE可侵犯從口腔到直腸的消化道任何部位,以小腸多見[8],病情亦相對較重,治療延誤可能會危及生命。1895年OSLER[9]首次報道了SLE消化道受累,其中空腸和回腸最易受累。KOO等[10]和雷玲等[11]認為SLE消化道受累主要有3種表現形式,為狼瘡性腸系膜血管炎(LMV)、假性腸梗阻(IPO)及蛋白丟失性腸病,成人SLE中LMV占0.2%~5.8%,且85%的患者為女性。SLE消化道受累常見癥狀為腹痛、腹瀉、惡心、嘔吐、腹水、發熱及排氣、排便停止等,容易誤診為急性胃腸炎、急性腸炎、急性胃炎、腸梗阻等消化系統常見疾病,進而行抗感染、抑酸、解痙、止痛等治療,甚至誤診為急腹癥而行手術探查,給患者造成非必要醫療損害。
例1為青年男性,以腹痛、惡心、嘔吐為首發癥狀。該患者1個月內癥狀反復發生2次,首先就診于急診科,均以“腹痛待查”收入普外科,按“急性胃炎”予以處理。第3次入院查血白細胞略有升高,腹部CT示腹水、腸梗阻,結合患者有排便情況,排除腸梗阻診斷,按“急性胃腸炎”給予治療,效果不理想。轉入消化內科,詳細查體見顏面部色素沉著。查紅細胞沉降率增快,免疫指標抗核抗體(+),抗nRNP/Sm抗體(+),追問病史患者訴有腎病綜合征病史2年,考慮免疫性疾病可能。請腎內科醫師會診,并結合病史、癥狀及實驗室檢查,患者消化系統、泌尿系統[尿蛋白(+)]、皮膚受累(顏面部皮疹),免疫指標陽性,考慮SLE。該患者近期消化道癥狀反復發作3次,先后經急診科、普外科、消化科診治,誤診為急性胃炎、急性胃腸炎等疾病,抗感染、止瀉治療效果不佳,經再次仔細查體見面部色素沉著,詳細詢問有腎病綜合征病史,最后結合腎內科醫師會診結果、免疫學指標得以明確診斷。
例2為青年女性,以“腹痛、惡心、嘔吐、腹瀉”為首發癥狀。首先就診于社區醫院考慮“感染性腹瀉”予抗感染、止瀉治療,效果不理想。后我院門診以“胃腸功能紊亂”收入院,給予解痙、鎮痛、抑酸、補液等治療,效果不佳。查血中性粒細胞比例偏高、超敏C反應蛋白11.01 mg/L;尿蛋白(+)。請普外科醫師會診,考慮急性胃腸炎,予抗感染、補液等治療,癥狀仍未改善。進一步查免疫學指標:抗核抗體(+),抗Sm抗體(±),補體C3、C4下降,考慮免疫性疾病。請腎內科醫師會診,結合患者癥狀、實驗室檢查,患者多系統受累,消化系統、泌尿系統受累[尿蛋白(+)],抗核抗體(+),補體下降,考慮SLE。該患者以消化道癥狀為首發表現,先后經社區醫院及我院門診、消化內科、普外科診治,誤診為胃腸功能紊亂、急性胃腸炎等疾病,抗感染、補液、解痙等藥物治療不佳,最后查免疫學指標異常,結合患者多系統受累,明確診斷為SLE。
例3為青年女性,以“腹痛、腹瀉伴惡心、嘔吐”為首發癥狀。首先就診于當地診所,按“急性腸炎”給予抗感染治療,效果不理想;到當地縣醫院查體見腹膜刺激征,查腹部CT見腸壁增厚、腹水,行腹腔診斷性穿刺,抽出少量血性液體,考慮急腹癥,擬行剖腹探查術。查體見面部痤瘡樣皮疹。實驗室檢查:血白細胞、紅細胞、血紅蛋白降低;尿蛋白(+);抗核抗體(+),抗Sm抗體(+),補體C3、C4降低。胸腹部影像學檢查見雙側胸腔少量積液,腸道管壁增厚,管腔可見積液影。考慮免疫性疾病可能,結合患者癥狀及實驗室檢查,消化系統、血液系統(紅、白細胞減少)、泌尿系統[尿蛋白(+)]、皮膚受累(面部皮疹),考慮SLE。該患者以消化道癥狀首發,經當地診所、縣醫院、我院消化內科診治,先后誤診為急性腸炎、急腹癥等,由于腹痛劇烈、腹腔穿刺抽出血性液體,當地醫院考慮急腹癥欲行腹腔探查手術。查血細胞、免疫學指標異常,詳細查體見面部皮疹,腎內科醫師考慮SLE,腎穿刺病理學檢查為狼瘡性腎炎,最后確診。
2.2 發病機制
SLE是一種全身多系統受累的疾病,主要病理改變為炎癥反應和血管異常,累及消化道導致LMV、IPO等[12],進一步出現腹痛、腹脹、腹瀉、惡心、嘔吐等消化道癥狀,腸系膜血管炎和血栓形成是SLE合并消化系統疾病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可導致危及生命的腸缺血、穿孔和梗死[13]。其發病機制主要基于免疫耐受的喪失,導致免疫復合物清除的缺陷和持續的自身抗體產生,且受遺傳、免疫、激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免疫復合物清除缺陷、凋亡細胞碎片和干擾素產生異常進一步導致組織損傷[14-15]。免疫復合物沉積于血管引起的血管炎和抗磷脂抗體直接侵襲管腔導致血栓形成,致腸道缺血[16]。小腸和大腸常表現為節段性或多灶性受累,病變腸段介于正常腸段中間,呈跳躍征象,提示缺血性改變,表明了血管炎存在。YUAN等[17]研究也表明,血管炎(大部分是小血管的受累)會引起SLE腸道病變。在MARUYAMA[18]的研究中,SLE腸道病變主要分為小腸型和大腸型。SLE腸道病變小腸型一般以LMV為主,受累區域為小腸和盲腸(腸系膜上動脈區域);大腸型則一般表現為IPO,其發病機制可能不是單純的血管炎,也包括免疫介導的平滑肌運動障礙。有報道顯示,在SLE所有受累腸段中,空腸和回腸是最常見的受累節段[13]。
2.3 診斷及鑒別診斷
SLE是一種多系統受累、高度異質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應對患者進行全面病史采集、體檢和實驗室檢查評估,診斷結合2010年SLE診斷和治療指南[19]、2019年歐洲風濕病聯盟與美國風濕病學會關于SLE的分類診斷標準[20]及2023年SLE診療規范[21]。其診斷要點:多系統受累臨床表現和免疫學異常[特別是抗核抗體(+)],有2個以上系統受累合并自身免疫證據[自身抗體(+)、補體降低]等。
本文3例主要以腹痛、腹瀉、惡心等消化道癥狀為首發表現,需要與以下疾病進行鑒別。1)過敏性紫癜:過敏性紫癜患者可出現腹痛、腹瀉等消化道癥狀,75%的患者年齡較小,多為<10歲兒童,成年人少見,SLE則是18~40歲人群發病率較高;該病多見于男性,SLE則女性患者較多;該病血IgA型免疫復合物可升高,補體C3、C4可暫時性降低,但下降程度與病情無關,而75%的SLE患者IgG及IgM正常或升高,偶見IgA降低者,75%~95%的SLE患者補體C3、C4亦下降,但下降程度與SLE活動度相關[22]。2)急性胃腸炎:急性胃腸炎可引起腹脹腹瀉、惡心嘔吐、食欲不振、水樣便、低血鉀及發熱,血白細胞計數可正常或升高;病毒性胃腸炎病程一般短于2周,不需抗生素治療,而細菌性胃腸炎則需敏感抗生素治療。3)腸易激綜合征: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可反復出現腹痛、腹瀉、腹脹等不適,部分患者有便秘或腹瀉、便秘交替,通常在排便、排氣后癥狀明顯緩解。血常規、便常規未見明顯異常。與SLE一樣,常見于青年女性患者。但該病免疫學檢查正常、腹部CT檢查腸壁結構正常。4)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該病男女患病率無差別,臨床以腹痛、腹瀉多見,患者常有哮喘等過敏史。血常規檢查可見外周血嗜酸粒細胞增加,內鏡檢查可見黏膜糜爛、發紅、水腫。腹部CT可見腸壁增厚,累及漿膜層患者容易發生腹水,腹水中可見大量嗜酸粒細胞。
2.4 誤診原因分析
1)對SLE缺乏充分認識:該病是涉及多系統、多器官的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常見臨床表現為關節炎、皮疹、發熱、腎臟損害等,臨床較易診斷,但臨床癥狀、體征缺乏特異性,以消化系統表現為首發者,臨床上容易被忽視。以腹痛、腹瀉、惡心、嘔吐等為主要癥狀者,通常就診于消化科、急診科,而不是風濕免疫科,首診醫師因思維慣性和對該病認識的局限性,容易導致誤診。本組病例出現癥狀后就診于基層醫院、急診科、普外科、消化內科,由于接診醫師對該病的認識不足,誤診為“感染性腹瀉、急性胃腸炎、腸梗阻、急性胃炎”等;例3腹痛劇烈,當地醫院考慮“急腹癥”,欲行剖腹探查術。另外,該病多見于青年女性,本文例1為青年男性,也是導致誤診誤治的一個因素。
2)問診及體格檢查不夠仔細:接診醫生病史詢問不詳細,查體不認真,主觀片面,被既往診斷所約束,診斷思維狹隘[23]。SLE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常見于青年女性,面部皮疹可因應用化妝品而遮蓋,易導致延誤診斷。本文例2顏面部應用化妝品,難以觀察皮疹,后經腎內科醫師仔細觀察,發現面部存在輕度色素沉著。例1有免疫性腎病,患者入科未交代,后期追問病史得知患者有腎病綜合征病史2年。例1近期2次因“急性胃炎”入科,第3次入院受前期診斷影響,仍按“急性胃炎”給予處理,1個月內3次發病住院,未引起重視和充分分析病情。
3)缺乏簡便易行特殊檢查手段:SLE早期癥狀不典型,可能以單一癥狀出現,以消化道癥狀為主要表現時容易誤診為單純消化系統疾病。該病診斷需結合臨床癥狀及自身免疫證據,自身抗體和補體等檢查在基層醫療單位難以普及,給臨床一線醫生診斷造成困難。本文例2、例3早期曾在社區醫院、縣醫院等基層醫療單位診療,誤診為“急性胃腸炎”等消化系統疾病,分析其原因包括受診療條件限制,不能開展相關免疫學檢查,客觀上增加了診斷難度。
2.5 防范誤診措施
1)切實加強醫學相關理論知識培訓和學習:各級醫療機構應注重對青年醫師“三基”知識培訓,可采取科室定期舉辦學術課堂、外派人員進修交流等方式提高所屬人員知識儲備,同時專科臨床醫師也應自覺在日常工作中加強理論知識學習,拓寬知識面。SLE是一種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結締組織病,臨床癥狀多樣,發病早期癥狀不典型,可能以單一癥狀或單系統癥狀出現。對于臨床醫生來說,不能僅憑個人經驗,先入為主,要打破思維慣性,全面考慮,充分分析患者的臨床表現及醫技檢查結果,慎重診斷及治療。
2)認真細致病史采集及體格檢查:問診和體格檢查是明確診斷的基礎,全面系統地問診、體格檢查是防范疾病誤診的可靠保證。臨床醫生在接診患者時應耐心、細致詢問發病史、家族史等相關問題,查體時注意患者是否有貧血、面部皮疹等情況。病史遺漏和體征失察可能會直接導致誤診。
3)提高臨床診治警惕性:腹痛、腹瀉、惡心、嘔吐是消化系統疾病常見癥狀,臨床對于按消化系統疾病治療效果不佳的患者要有警惕性,及時行進一步檢查,如血清免疫學檢查、腎穿刺病理學檢查等,必要時進行多學科醫師會診,以盡早明確診治。基層醫師遇到類似情況,要適時建議患者到高級別醫院就診或外請專家會診,以減少或避免誤診誤治的發生。
總之,SLE臨床表現多種多樣,消化道癥狀為常見癥狀,部分患者以消化道癥狀首發,因其早期表現不具典型性,在臨床診治過程中易出現誤漏診,延誤病情,甚至因誤診行剖腹探查術,給患者帶來不可逆醫療損害。臨床醫生平時應加強理論學習,拓寬知識面,日常診療工作要有一定警惕性,必要時進行多學科醫師討論,早期識別以消化道癥狀首發的SLE,盡早給予個體化治療可明顯改善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