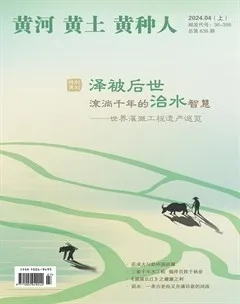《滾滾長江》之灌溉之利
陳松平



滾滾長江水,日夜競東流,萬世資灌溉。
灌溉是農業發展的基礎支撐,中國古代以農立國,修水利、促灌溉、興農事,歷來是治國安民的大事。
生生不息的長江,經過歷代治理開發,龐大的水系盡顯灌溉之利,將流域大地澆灌成平疇沃野,孕育了悠久燦爛的華夏文明,留下了眾多歷久不衰的水利瑰寶。
都江堰、長渠、溇港、槎灘陂等歷經千年風霜,至今依然在發揮作用的灌溉工程,就是這些水利瑰寶中造福一方、澤被后世的光輝典范。
水暢其流,潤澤沃野。
正在不斷拓展的灌溉之利,讓流域上下田園牧歌更嘹亮、大江南北家家糧倉更殷實。
千古一堰
“砍榪槎——放水啰——”隨著放水號令發出,身著古裝的堰工們揮舞著板斧,使勁砍向榪槎。頃刻間,岷江水策馬奔騰,一瀉千里,流向廣袤的成都平原。
每年清明時節,中國·都江堰清明放水節開幕式上,都會再現千年前壯觀的放水景象。都江堰清明放水民俗始于978年。古時,每到冬季,人們便用榪槎筑成臨時圍堰,淘修河床,加固河堤。到清明時節歲修結束,便舉行儀式拆除榪槎,讓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千里沃野。后來,放水儀式演化為灌區人民的一項傳統文化活動,以祭祀李冰父子,祈求五谷豐登。清代詩人山春在《灌陽竹枝詞》中再現了清明放水喜迎春耕的情景:“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開時涌岸邊。喜看榪槎頻撤處,歡聲雷動說耕田。”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干流中游。古時,岷江穿過上游水流湍急的峽谷后,猶如離群的野馬般四處奔竄,致使成都平原水道紊亂,西部洪澇、東部干旱,交替為患。到戰國時期,秦國吞并蜀地后,欲將這塊膏腴之地打造為支撐其統一天下的后方大糧倉,治理岷江水患、發展農業生產就成了當務之急。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51年,蜀郡郡守李冰在借鑒前人治理岷江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當地西北高、東南低的地理條件,根據岷江出山口特殊的地形、水脈、水勢,率眾鑿離堆、穿二江,以石頭、木樁、竹籠為主要材料,建成了都江堰。岷江自此被分為內外兩江,外江仍循原流,內江經人工渠道流入成都平原,灌溉農田,把水害變為水利,使四川盆地成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的天府之國。
這座世界上唯一存留至今的大型無壩引水工程,以最小的工程量,成功解決了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術難題,在200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始終運行不輟、造福一方,是中華民族科學治水的光輝典范。
都江堰三大主體工程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和寶瓶口(引水口)在選址和營構上,巧妙地運用了地形、地勢、河流彎道和水流態勢,利用“凹岸取水”“凸岸排沙”的原理,以“魚嘴”分流分沙,筑“飛沙堰”泄洪排沙,鑿“寶瓶口”限洪引水。具體說來,就是魚嘴分水堤把岷江一分為二,在正常的情況下,60%的水量會被分流進入內江,用來灌溉農田;洪水到來時,這個比例就自然地顛倒了過來,外江正流則發揮排泄洪水的作用。飛沙堰溢洪道在旱季把岷江的水攔住,全部引入內江;在雨洪季節,又把內江容納不了的水溢出,自動流入外江。寶瓶引水口是內江的咽喉,進入內江的水,都是通過這個口子流向各條灌渠的。這三大主體工程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協調運行,共同發揮了引水灌溉、分洪減災、排沙防淤的神奇作用,其技術含量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驚嘆,堪稱全世界最偉大的古代水利工程。
此后,歷代治蜀者均以李冰為標桿和榜樣,擔當治水重任。西漢蜀郡太守文翁主持復修都江堰,率先擴大了都江堰灌區;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認為“此堰農本,國之所資”,遂專門設置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護”,對都江堰進行經常性的管理維護;唐代尚書右仆射高儉在原有渠道和工程整治的基礎上,布置和擴建了許多分支渠道,擴大灌溉面積;元代吉當普、明代施千祥均在渠首分水樞紐魚嘴結構和材料上進行革新嘗試。這些先賢們在治水實踐中,總結出“深淘灘,低作堰”“遇彎截角,逢正抽心”等蘊含著“人水和諧”“道法自然”理念的治水經驗,直至今天依然被世界水利界奉為圭臬。
“歲修”是都江堰每年一次的大事。古代竹籠結構的堰體在岷江急流沖擊之下并不穩固,而且內江河道盡管有排沙機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積。因此,需要定期對都江堰進行整修,以使其有效運作。宋代訂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農閑時斷流歲修的制度,稱為“穿淘”。史書記載,每當隆冬時節,由上萬名民工組成的歲修大軍,從四面八方來到都江堰岸邊安營扎寨。江上大小船只川流不息,岸上鼓聲雷動響徹云霄。根據李冰留下的“深淘灘,低作堰”歲修準則,內江要清淤,堤岸要加固,什么時候看見埋在河床上的三根臥鐵了,就算達到內江歲修的標準了,那是“深淘灘”的標記。淘得過深,寶瓶口進水量大了,會引起澇災;淘得過淺,水量又達不到灌溉的需求。“低作堰”是說飛沙堰的標準,從臥鐵到堰頂不高不矮只能是2.15米。據說有一年,因農田面積的增加,需要加大灌溉水量,歲修時將飛沙堰加高了80厘米,這年春汛時成都北部就超過了警戒水位,人們趕快拆掉加高的水泥圍堰,恢復古制,水位才降了下來。
以現代眼光來看,都江堰工程是一個巨大的灌溉水網。通過寶瓶口進入成都平原的江水,經過仰天窩閘之后分為兩股,再經過蒲柏閘和江安走江閘分為四股,以下又按干渠、支渠、斗渠、農渠、毛渠五級,愈分愈細,成為密如蛛網的灌溉網。余水,一部分流入沱江,一部分回到岷江,即外江。
是故,都江堰的灌溉面積大小,全在于灌溉水網的大小、長度和暢通程度。據水利專家估計,進入寶瓶口的江水如全部利用,可灌溉田地2000萬畝。歷史上關于都江堰的具體灌溉面積,極少見諸文獻記載。《宋史·河渠志五》第一次明確提及了都江堰的灌溉區域,主要為導江、新繁、金堂、成都、華陽等10個縣。清代后期,都江堰灌溉面積曾達300萬畝。其后,由于灌溉渠道年久失修,淤塞垮漏,到民國時期,只能灌溉200萬畝。
從20世紀50年代起,都江堰灌區先后修建了人民渠、東風渠等重要渠系及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的土地全部得到了澆灌。如今的都江堰已成為四川省不可或缺的水利基礎設施,承擔著7市、40縣(市、區)1089萬畝農田灌溉,以及2300多萬城鄉人民生活、生產及生態環境用水任務,在灌溉、城鄉供水、防洪、水產養殖、種植、旅游、環保等多目標綜合服務保障中,煥發出無限生機與活力。
2000年,都江堰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8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著名社會活動家趙樸初先生曾在參觀都江堰后賦詩曰:“長城久失用,徒留古跡在;不如都江堰,萬世資灌溉。”這一贊譽,都江堰完全擔當得起。
與都江堰興建時間大致相同的古巴比倫的納爾—漢穆拉比灌溉渠系、古羅馬的遠距離輸水道,都因滄海變遷和時間的推移,或湮沒,或失效。只有中國的都江堰,雖安處一隅,卻澤被后世、造福千年,且至今運行不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灌溉等綜合效益,成為一個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數千年奇跡。
戰渠灌渠
漢江與其支流蠻河夾交的沖積平原,是一片富饒的土地,一條綿延百里的灌渠縱貫其間,將湖北省南漳縣和宜城市的沃野平疇連在一起。
這條灌渠就是長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的戰國時期,其歷史比都江堰早23年,比鄭國渠早33年,比靈渠早65年,是中國現存古代興建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被《中國水利之最》列為“中國最早的灌溉渠道”。渠道西起襄陽市南漳縣武安鎮謝家臺村,東至宜城市鄭集鎮赤湖村,全長49.3千米,故又有“百里長渠”之稱。
2018年,長渠與都江堰、靈渠、姜席堰一起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這條在常人眼里與普通河渠似無二致的渠道才漸漸進入了公眾的視線。
頗為吊詭的是,長渠的修建初衷,并非用于農業灌溉,而是用于戰爭。
長渠最初的名字叫白起渠,是源于修建它的人——戰國時期秦國著名將領白起。戰國晚期,秦國發起規模空前的統一戰爭,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79年遣大將白起南下攻楚,秦軍乘船走漢江水路,直撲當時楚國的別都鄢城(今湖北省宜城市南鄭集境內)。楚國為了保衛戰略要地,調動主力部隊與秦軍在鄢城決戰。白起率軍進逼鄢城后,遇楚國重兵把守,久攻不下,決定采用水攻,根據鄢城地理位置較低而周圍又河渠密布的條件,在城西百里處的蠻河上壘石筑壩攔水,開溝挖渠,“以水代兵”,待江水漲起后,引水傾灌鄢城,人亡城破。
戰事結束后,秦國在當地設置鄢縣,并對白起渠進行疏浚改造,用來灌溉農田,“戰渠”由此變“灌渠”。
白起渠的功能發生顛覆性的轉變后,長渠便開啟了2000年的灌溉史。歷代統治者中的有識之士,認識到長渠的巨大灌溉效益,不斷加以開發、治理,從唐朝始,直至清朝康熙年間,長渠經歷了5次大修和7次局部修治。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宜城縣令孫永主持的大修,是對長渠灌溉功能最重要的恢復與擴展,他不僅重新修復了工程,還建立了長渠灌區民間自治、政府督導的管理制度。南宋初期,漢江中游襄陽一帶成為南宋與蒙古對峙的重地,出于軍事屯田的需要,朝廷多次組織整修長渠,使灌區工程體系更加完善,渠道與陂塘相連,溝渠密布,襄宜平原成為重要糧倉。
長渠開掘、修治的歷史功勛及其發揮的巨大灌溉效益,歷代皆有詩文辭賦贊頌。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稱“白起渠溉三千頃”;唐代詩人胡曾賦在《詠史詩·故宜城》中云:“武安南伐勒秦兵,疏鑿功將夏禹并;誰謂長渠千載后,水流猶入故宜城。”北宋歐陽修在《書宜城修水渠記后奉呈朱寺丞》詩中有言:“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兇菑。”
與都江堰一樣,長渠同樣浸潤著古人的治水智慧。其“長藤結瓜”的工程布局,和“分時輪灌”的灌溉模式,有效平衡了水資源,極大地提升了灌溉效益,至今仍被許多水利工程借鑒。
何為“長藤結瓜”?長渠啟用之初,沿線就串聯了土門陂、新陂、熨斗陂、臭陂和朱湖陂等水庫和堰塘。經過歷代擴建翻新,在沿線修塘筑堰,又新挖了很多支渠,使得這條百里長渠流經之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灌溉網。這就好比長渠干渠是一條粗壯的瓜藤,大大小小的水庫、堰塘就像藤上結出的“瓜”,于是有了“陂渠相連,長藤結瓜”這個形象的說法。“藤”引水、“瓜”蓄水,互相串聯、互為補充,從而提高了整個渠系的灌溉能力。在非灌溉季節,攔河壩使河水入渠,渠水入陂塘,常年蓄水,不讓水白白流走浪費;到了灌溉季節,長渠供水給陂塘,多者三四次,少者一兩次,循環蓄水,實現了以豐補歉、以大補小、互通有無、平衡水量,最大限度發揮了工程潛力。沿渠水庫、堰塘的有效利用,使得長渠灌區灌溉保證率達85%以上,成為中國南方“長藤結瓜”灌溉工程的典型。
唐宋時期,大規模修治長渠,增加了4個大型節制閘,為實施“分時輪灌”創造了條件。4個大型節制閘把灌區劃分為4個區域,自上而下分時輪灌。以9天(216小時)為一輪,一輪分四個階段,第一段節制閘以上供水48小時,第二段節制閘以上供水56小時,第三段節制閘供水50小時,第四段節制閘供水54小時,再留出8小時機動時間用于維護和檢修。“分時輪灌”實現了高渠高田有水抽、低渠低田能自流,極大地擴展了灌溉面積,還減少了水事糾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襄州宜城縣長渠記》中記述“時其蓄泄而止侵爭,民皆以為宜也”。“分時輪灌”這一用水管理技術上的創新之舉,一直沿用至今并得到了革新發展。
古長渠,歷盡滄桑,穿越20多年,屢廢屢興。經1951年以來多次續建配套,長渠灌區發展成為以三道河大型水庫為主水源,15座水庫及2671口陂塘為補充水源,各級干支渠道為脈絡的“大、中、小”相配套、“蓄、引、提”相結合、“長藤結瓜”式農業灌溉系統。工程擁有規模以上干渠1條、主要支渠38條、閘門499座、渡槽39座、涵洞518座、倒虹吸3座、滾水壩1座,灌溉著30.3萬畝良田。
如今,長渠兩岸林木繁茂,莊稼豐腴,被當地百姓親切地稱為“幸福渠”“致富渠”。
智慧流淌
薄霧輕繞,青山吐翠。
曙光微露之際,湖南省新化縣水車鎮紫鵲界村的村民們就在田間忙活開了。正值夏種時節,層層疊疊的梯田浸滿了水,似一塊塊明晃晃的鏡子,倒映著人們赤腳下田、彎腰插秧的身影。
這片分布在海拔500~1200米的山麓間,共有500多級的梯田,就是2014年首批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的紫鵲界梯田。據考證,紫鵲界梯田起源于先秦,至宋元明時期進一步擴大完善。算起來,這梯田里的水,已連綿不絕地流淌了2000多年。
梯田對灌溉水源依賴度極高。千層疊翠的紫鵲界梯田卻沒有任何山塘、水壩等蓄水系統,但水源又似乎無處不在,從石頭縫里迸出、從土壤中滲出,水量雖不大,卻布滿山坡。憑借巧奪天工的設計,紫鵲界梯田構筑起純天然的自流灌溉系統,實現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堪稱世界灌溉工程的奇跡。這里潺潺流水四季不絕,澆灌著依山勢而建的數萬畝梯田,旱澇保收,至今仍養育著16個村莊1萬多村民。
水繞著田,田依著寨,人居與農耕和諧交融。紫鵲界梯田,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面對水利難題,用智慧書寫的驚艷世界的又一答卷。
像紫鵲界梯田這樣歷經歲月風霜而不朽,流淌著千年治水智慧的古代灌溉體系或工程,在長江流域還有不少,如溇港和槎灘陂,其蘊含的治水智慧,則有別于都江堰無壩引水、長渠“長藤結瓜”和紫鵲界梯田自流灌溉模式。
溇港,是太湖地區獨有的一項古老灌溉與排澇系統。2500年前,吳越兩國正上演跌宕起伏的爭霸大戲。為擴大糧食種植面積,吳國相國伍子胥與越國相國范蠡分別組織各自國家民眾,在太湖南岸的沼澤灘涂上爭相開河筑堤,用圈圩擋水之法,陸續開鑿塘、浦、溇、港,修建渠道,排出疏干濕地水分,將涂泥逐漸改造為沃土。這是開發溇港系統的起源。
經過歷代擴建改良,至北宋時,太湖溇港水利體系臻于完善。在太湖南岸,從東至西每隔1千米左右就有一條河渠,像梳齒一樣排列開來,河道寬的叫作“溇”、窄的叫作“港”,故統稱“溇港”。橫貫其間的一道道東西向河道叫作“橫塘”,縱溇橫塘之間的格子狀田塊,就是“圩田”。這樣,就構筑了“田成于圩內、水行于圩外”的溇港灌溉體系。
每一條溇港與太湖交匯處均建有一道閘門,上游區域遇洪澇時,水閘開啟,泄洪水入太湖;太湖漲水時,水閘關閉,防止湖水內侵害田;旱季開啟水閘,引太湖水流入溇港灌溉圩田……依靠水閘的調節,溇港中始終可以保持較為穩定的水位,正如北宋范仲淹所言“旱澇不及,為農美利”。源源不斷的太湖水,通過眾多溇港,流入萬千圩田中,造就了“魚米鄉,水成網,兩岸青青萬株桑”的盛景,時至今日仍發揮著重要的灌溉作用。
雙向引排的溇港水利系統,奠定了太湖平原魚米之鄉、絲綢之府、財稅之區和文化之邦的重要歷史地位。正因為如此,該系統曾被水利界泰斗鄭肇經先生高度評價,認為這是“古代太湖勞動人民變涂泥為沃土的一項獨特創造”,甚至“可與四川都江堰、關中鄭國渠媲美”。
太湖溇港水利系統中的治水智慧,亦被歷代治水專家推崇與借鑒。明代著名水利學家潘季馴,曾4次總理河務,主持黃河和京杭大運河治理。其間他吸收借鑒家鄉湖州溇港水利系統的經驗,特別是在認真研究溇港“重陽后閉閘、清明后啟閘”這一沖沙減淤、保護河道的先進舉措后,創造性地運用“逼水歸槽,束水攻沙”之策,有效治理了黃河泥沙淤積問題,被譽為“千古治黃第一人”。
槎灘陂位于江西省泰和縣,始建于南唐。937年,躲避戰亂寓居鄉村的南唐金陵監察御史周矩,在贛江水系禾水支流的牛吼江上游槎灘村畔,組織當地民眾將木樁打入河床,再編上長竹條,遏擋水流,然后填筑黏土夯實,最后在主壩上層壘疊堅固的紅條石,形成陂壩,名為槎灘陂。陂成后,周矩父子相繼率眾陸續開挖了36條灌溉渠道,使得當地9000多畝因旱歉收的薄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良田。
槎灘陂有主壩和副壩兩部分,初建時為木質結構,元代末期重修時改為石質結構,此后又經多次維修,直至1983年對壩體進行混凝土包裹加固,一直沿用至今。
科學、因地制宜的設計,是槎灘陂千年不敗的重要因素。其壩址選在河床堅硬、水流較緩的河段,有利于壩體穩定。而經過精心測算的壩高,則限定在略低于河岸,這樣,枯水期時,陂壩可有效將江水聚集后引入下游的灌溉渠網,發揮更大的灌溉作用;洪水期時,陂壩隨著水位上漲沒入水下,洪水從壩上自然溢出泄入河道,從而發揮防洪減災功能。此外,槎灘陂主壩和副壩各設有一孔沖沙閘,有效解決壩前泥沙淤積問題。陂左側還設置了供船只、竹排通行的水道,保證了航運暢通。
千年來,槎灘陂活水長流,還在于實施了“陂長制”這一先進的水利工程管理與運行制度。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周、蔣、胡、李、蕭五姓宗族在官方的支持下制定了《五彩文約》,由五姓宗族輪流擔任陂長,實行陂長負責制,維修和管理槎灘陂,形成了官府與宗族、官與民結合的管理體系,從根本上保障了工程修繕維護所需人力和資金的來源,也減少了用水糾紛。
槎灘陂經過多次維修改造,灌區不斷擴展,灌溉面積現達6萬余畝,滋潤著億萬稼穡,被譽為“江南都江堰”。
中國古代以農業立國,對水利建設尤其重視,在幾千年的農耕歲月中,興建過數以萬計的水利設施,是世界上灌溉工程遺產類型最豐富、分布最廣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國家。從2014年起,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開始在世界范圍內評選灌溉工程遺產。截至2022年,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上,共有30項中國工程。據不完全統計,除上述都江堰、長渠、紫鵲界梯田、溇港、槎灘陂外,長江流域還有靈渠、漢中三堰、千金陂、潦河灌區、東風堰、通濟堰、興化垛田、松古灌區和上堡梯田等古代著名灌溉工程也入選了該名錄。
這些灌溉工程或系統雖然造型多樣,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流淌著古人治水智慧、閃爍著農耕文明之光。
水潤沃野
江南多水澤。
長江流域的灌溉設施源于水稻等親水作物大規模種植和栽培的需要。據考古發掘證明,長江中游地區是世界稻作文明的發祥地,在江西萬年仙人洞、湖南道縣玉蟾巖等遺址中先后發現了距今1萬年到1.2萬年的稻作遺存,表明當時逐步形成了最初的水稻農業。隨著水稻種植面積增長,農業灌溉應運而生。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連續成片的大面積稻田,并有與之配套的蓄水池、放水溝等灌溉系統,大大提升了稻作農業規模化生產水平。
不過,在春秋戰國以前,長江沿岸人口與土地等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一塊土地經常出現水旱災害,人們可易地而居,另覓土地耕作,加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所以當時人們興修較大規模水利灌溉工程的意愿并不強烈、條件也不成熟。
及至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鐵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為興修水利創造了有利的物質條件。由于諸侯割據,互相攻伐稱霸,出于對糧食征集等方面的需要而進行大規模墾殖荒,農田灌溉工程因此有了較大規模的發展。都江堰、長渠、紫鵲界梯田、太湖溇港等,均是這一時期興修完成和開工建造的,后世的各類灌溉工程,幾乎都可以在這些工程里找到模板和影子。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將嶺南的百越之地納入大秦版圖,于公元前219年詔令監御史祿掌管軍需供應,督率士兵、民夫在湘江與漓江之間修建一條運載軍糧的人工河。5年后,這條人工河鑿成,是為靈渠,不久秦國就統一嶺南。靈渠的主要功能是航運,2000多年來一直是嶺南地區與中原交通往來的戰略要道,同時也發揮著灌溉效益,歷代皆有疏浚維護,灌溉湘桂走廊沿線農田,目前灌溉面積約6萬畝。
到了漢代,國家政權相對穩定,在長達400多年的歷史中,除對原有水利工程進行維修取得效益外,在今陜西漢中、河南南陽、四川成都、安徽舒城、江蘇揚州等地區和浙江長興一帶,都新建有相當多的塘堰灌溉工程。在漢江上游大大小小的支流上,西漢立國之初就開始修建引水堰壩,數百年來先后建有100多處引水堰壩,構成了發達的農田灌溉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發揮灌溉效益最大、使用時間最長的是有“漢中三堰”之稱的山河堰、五門堰、楊填堰。東漢初年,南陽太守杜詩在當地“修治陂池,廣拓土田”,并利用水力鼓風,發明“水排”。在江漢支流蠻河上擴建了木里渠,灌溉農田7萬畝。三國時,吳將周泰引涔水灌田數十萬畝,為當時湖南最早的大型引水工程,同時期的蜀漢則經營都江堰和漢中灌區。
西晉永嘉之亂后,北方人口大規模南渡,也在長江流域開墾了更多的農田,興建了大量灌溉工程。長江中下游地區主要是依托比較大的湖泊水系,按照灌溉需要進行人工改造,如位于今江蘇句容的赤山湖、位于今江蘇丹陽的練湖等,都產生了很大的灌溉效益。長江上游則是根據地理條件開發小型蓄水工程,有的利用積水洼地修陂池,有的則利用取土坑積水,如成都千秋池、萬歲池,就是秦國筑城墻時留下的取土坑。在今湖南郴州一帶,當年還曾利用溫泉水灌溉,取得了一年三熟,灌溉面積有幾千畝之多。
隋唐大一統后,中國進入古代極盛時期,經濟社會有了很大發展。對漕糧的需求,使得朝廷更加重視農田水利建設,唐代尚書省工部下設有水部郎中和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堤防、塘堰、舟楫、灌溉等等,一并管理。一方面,對歷代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靈渠等進行維修以充分發揮其灌溉效益;另一方面,則在長江流域新建了相當多的灌溉工程,大小陂塘遍布大江南北。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代水利工程共有236處,其中灌溉排水工程有165處。以755年安史之亂為唐代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地理分界線,則唐代前期的灌排水利工程有107處,其中北方為67處,南方為40處;唐代后期的灌排水利工程有58處,其中北方僅10處,南方48處。長江流域各州府縣志中有不少關于唐代興修堰塘的記載,如唐元和年間(806—820),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發動群眾在南昌(今江西南昌縣附近)“筑堤扦江,長二十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修建灌溉陂塘598處,受益農田達120萬畝,這就是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的潦河灌區之肇始;唐大和年間(827—835),四川青神縣修成灌田2萬余畝的引水工程,即鴻化堰前身。
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在宋代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形成“國家根本,仰給東南”的局面。農田水利建設是農業的基礎工程,兩宋君臣對此一直十分重視,宋神宗說“灌溉之利,農事大本”,這是宋朝歷任皇帝對農田水利建設重要性的普遍認識。朝廷經常發布有關農田水利建設的詔令,將此項工作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北宋一代,太湖地區興修水利的記載不絕于史書,主要是在蘇州、松江、昆山、宜興一帶筑堤、建橋、開塘、置閘,重點解決農田的排灌問題。宋室南遷后,南方人口劇增,沿江地區墾田面積迅猛增加,與之相配套的是大舉興修陂塘灌溉工程。據《宋史》載,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上奏,江東共修治陂塘、溝堰22451處,可灌溉田畝440萬畝。這是南宋重視農田灌溉的一個寫照。當時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形式多樣,數量極多,幾乎每個縣都有,不少工程持續到明清以后,至今仍在使用。
元明清是中國人口增長較快的時期,其中清代的265年間全國人口總數由1億左右增至4億多,促使耕地增加和單產提高,同時也促進了灌溉的發展。各地普遍興修以灌溉為主的農田水利工程,江南地區較為突出,但大型工程較少。元代學者王禎在《王禎農書》中記述:“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堨水蕩,難以數計。”據清代光緒年間的《湖南通志》統計,全省有陂塘8700多處,其中建于清代或始于清代灌田千畝以上的有120多處,灌田10萬畝以上的10處。
近代以來,山河破碎,戰亂不已,民不聊生,水利設施不僅缺乏正常維護,而且遭受破壞的不少,灌溉能力大為下降。據長江水利委員會編著的《長江治理開發保護60年》一書統計,新中國成立前夕,長江流域灌溉面積約為1.0005億畝,僅占耕地面積的23%,灌排能力嚴重不足,糧食生產能力低下,一遇大的旱澇災害,往往赤地千里,糧食絕收,餓殍遍野。
倉廩實而天下安。
糧食安全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壓艙石。長江流域是農業生產的地帶,上游的成都平原,中游的洞庭湖和江漢平原,下游的鄱陽湖和太湖平原都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棉油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興水利,修復和續建了都江堰、長渠等一批古代灌溉工程,新建了湖北漳河水庫灌區、湖南韶山灌區、江西贛撫平原灌區、安徽駟馬山灌區、河南鴨河口灌區等一大批灌區,長江流域內灌溉體系初步形成,已成為中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區。
水到田頭,糧食豐收。
長江流域不斷發展的農田灌溉事業,既充實了國家的糧倉,又鼓起了農民的錢包,為長江流域各地鄉村振興、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