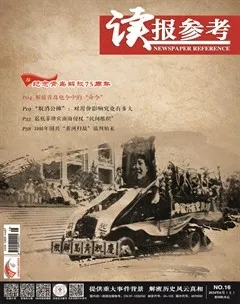魏然:揭開流淌千年的“運河往事”
李祺瑤
5月初,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處建筑工地上,幾棟新樓拔地而起。另一邊,空曠的土地蓋上了綠色苫布,放眼望去,一個個矩形的“深坑”坐落其間。一群考古人拿著手鏟,不斷重復著拉線布方、刮面找遺跡、記錄整理等步驟。
配合城市建設,考古發掘工作正在同步進行。2018年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魏然帶隊“扎根”在這里,試圖拂去層層塵埃,從一處處遺跡、一件件出土文物中,找到這片區域與一座漢代古城的關系。
在墓葬間捕捉歲月變遷
“之前觀察到的現象可能是榫卯結構,有新發現嗎?有沒有發現金屬器?”一座形制較大的墓葬前,魏然三步并作兩步,順著探方里的階梯下到墓室跟前,一邊觀察棺槨的木結構,一邊詢問同事。
一位考古隊員指著一段已經朽掉的棺板前段,示意上面凸起的一角可能就是榫結構。魏然蹲下,仔細觀察。“考古現場,任何一個小細節都可能標注著歷史。”他解釋,腳下的這片區域屬于北京市通州區潞城鎮前北營村。2018年至今,他們已經在這里連續進行了6年的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大量各時期遺跡,類型包括墓葬、灰坑、窯址、水井、房址等,考古發掘面積累計超過3萬平方米。
“我們發現,這些墓葬以兩漢時期為主,反映出自西漢以來完整的文化序列。”魏然指著面前不同形制的墓葬介紹,西漢時期,墓葬的葬具以木制為主,隨著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逐漸演變為磚結構,形制也由簡單發展得更為復雜。“不僅僅是墓葬,任何一處遺跡,我們都要反復確認結構和微細的現象,有針對性地提取每一份樣品標本,小心提取每一件文物,這是為了確保盡可能全面地提取有效信息。”
每一處埋藏在土里的信息,魏然都囑咐考古隊員認真清理、記錄、提取,為考古發掘結束后的整理和實驗室工作作好準備。20多分鐘后,他又急匆匆地前往下一處遺跡——一口水井。站在探方邊上向下望,能看到八角形的水井內部,有一圈木板圍成的井壁。“路縣故城遺址也出土了相似結構的水井,規模和體量更大,兩者時代也不同。在這里,我們也希望找到更多歷史發展演變的信息。”魏然說著,還不忘囑咐工人做好遺跡的保護措施,“前幾天下了場雨,井內的土層還有點潮,提取信息的時候要小心。”
日復一日,魏然和同事就這樣往返于一處處遺跡間,小心翻找歷史信息,探知古人生活,捕捉歲月變遷。
結束了上午的工作,魏然一行人回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工作站,簡單吃口午飯,又一頭鉆進辦公室,對著滿柜子的出土文物,開始了下午的工作。
“有上千件文物等著我們整理,可耽誤不得。”他說,出土文物也是考古人員判斷歷史信息的重要證據,正在整理的這批文物大多為陶器,器型以鼎、罐、壺等為主,也有小型玉器、銅器,“無論居住址還是墓葬,都是當時在這里生活的人留下的歷史印記,我們要做的就是要盡可能全方位提取和還原這些歷史信息,并加以保護”。
為了配合基本建設項目,他和同事都在和時間賽跑。“考古和工程建設一環扣著一環,如何保證城市建設能夠順利進行,又能以符合工作規程要求的方式完成好考古工作,是每個投身于此的考古工作者反復思考的事情。”
細致勘探發現運河故道
2012年,魏然來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他正式開啟考古世界廣闊的大門。
那時,跟著單位的老師們跑田野,是他最開心的事。不論寒暑,總能在考古工地看見他被曬得黝黑的身影。“最開始就是在工地跟著技工學技能,向領隊老師討教考古發掘的經驗。”魏然說,漸漸地,去的工地多了,實踐得多了,自己也能幫著領隊老師在現場分擔一部分工作,“每當遇到重要的遺跡現象,能自己作出正確判斷,得到領隊老師的肯定,這種成就感溢于言表。寫發掘記錄、整理資料、修復文物、考古繪圖……用自己的雙手發掘歷史、證實歷史,心中有無限的驚喜、興奮、滿足”。
對于魏然來說,2018年是他職業生涯里的一個重要節點。那一年,在經過國家文物局的專業考古培訓后,他成功拿到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的資格,自此能夠獨當一面,帶隊開展考古項目。當時,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的各項工作不斷推進,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負責的考古工作也從未停歇,魏然一連接了好幾個考古項目。
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讓魏然與大運河結下了不解之緣,揭開了一段段流淌千年的“運河往事”。
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魏然和同事對通州區永順鎮的小圣廟村、張家灣鎮的上馬頭村等區域進行了細致的考古勘探。“在勘探小圣廟村北時,我們發現了文獻中記載的清嘉慶十三年運河改道前的舊河道。故道經小圣廟向南經過上碼頭村,與文獻中記載的基本一致。”魏然比劃著解釋,根據清光緒《順天府志》記載,嘉慶年間北運河在通州的河道由于常年洪水反復淤塞,發生了較大改變。從嘉慶十三年(1808年)開始,北運河河道不再由小圣廟經上馬頭至皇木廠,再經張家灣與涼水河匯合,而是向東經黎辛莊形成新的運河河道。“結合文獻推測,這條古河道應為北運河故道。”
運河故道廢棄淤淺、湮沒無聞,在考古工作者的細心找尋下,200多年后得以重見天日。魏然介紹,經過考古勘探和后續的局部發掘,他們發現了總長約3000米運河故道,證實了文獻的記載。“這一發現,對北京古代漕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是元、明、清三代大運河漕運興衰的明證。”
隨著運河故道的發現,更多的歷史遺存揭開面紗。魏然和同事還在運河故道岸邊發現了清代小圣廟遺址。根據清乾隆時期《通州志》記載:“小圣廟,一在州北門外,一在張家灣。”這是大運河北京段首次考古發現的祭祀河神的廟宇遺址。
科技考古勾勒生動細節
最近幾年,除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項目考古外,魏然的足跡踏遍大半個北京城,延慶、大興、房山……每到一處遺址,他總是收獲頗豐。
大部分時間,他往返于一個個考古工地,“泡”在探方里找遺跡。
到了冬天,考古工作者就進入了“冬歇期”。因為北方冬天一旦土被凍住,就無法進行考古勘探和發掘了。北京的這個階段要從12月一直持續到來年3月份,考古工作者會利用這段時間,整理平日里積壓的考古資料,編寫考古報告。
“但這幾年,工作多、任務重,在天氣不是特別寒冷、凍土層不是很厚的時候還可以堅持工作一段時間。”魏然說,冬天考古的辦法就是“給土地蓋棉被”——每天在室外溫度低于零攝氏度之前,在工作面上蓋上棉被和厚厚的一層土,第二天太陽出來氣溫回升到零攝氏度以上后,再把棉被與土揭去繼續工作,如此往復。
學科技考古出身的魏然,也不忘自己的“老本行”。他參與了延慶大莊科遼代冶鐵遺址、通州路縣故城遺址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在路縣故城城址外西南部,魏然和同事發現了兩漢地層中出土的煉渣、爐壁殘塊、陶范等冶鑄相關遺物。這是首次在路縣故城遺址周邊發現大規模的冶鑄相關手工業遺存,為研究漢代的手工業發展、經濟分工提供了重要資料。
如今,聚焦冶金考古和科技考古方向,魏然正在整理近年來從各大遺址收獲的相關遺物,作進一步研究。他希望,利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為人們撥開歷史的塵煙,勾勒出更生動的歷史細節。
(摘自《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