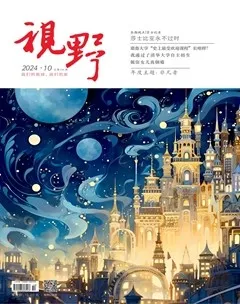莎士比亞與錢
一飲一啄Video

莎士比亞對拜金主義的厭惡和鄙夷,總是借筆下人物之口道出。
“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只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雅典的泰門》)
但他在作品里談錢次數之多,似乎又離不開這個“萬惡之源”——38部劇作里,光“有錢”(rich)就出現過150次,“金子”(gold)被提過200次,“債務”(debt)被提及50次。
盡管市面上不乏莎士比亞的傳記,但其實真實史料不多,關于莎士比亞充滿創造力的生活和思想,是后人猜測和演繹的。已經被公開的文物資料里,大多呈現的是他土財主和商業天才的一面。
賣詩、賣劇、炒房、建劇院……小莎是一個會賺錢的文藝青年。
一個劇本十英鎊:比夏洛克更懂斂財
22歲的莎士比亞從斯特拉特福走出來的時候,正好走進了倫敦的“黃金季節”時代。
從劇院打雜開始入行,莎士比亞做過馬夫、催場員、演員助手。但他的才華并沒有被埋沒多久,僅僅兩年的時間,他所在的劇團就開始演出他改編的劇本。
那時市民看戲,大多是圖一樂呵,大家結束工作后,選擇一個新的地方消遣,順便嗑嗑瓜子、聊聊鄰里瑣事。莎士比亞的戲簡直正中市民的下懷,人們大掏腰包,討論度持續不下,小莎成了市民眼中的紅人。紅人的進賬自然不少。熱愛戲劇的倫敦市民每年看戲不止一次——老劇目翻來覆去地看,希望演員有不一樣的演繹;對于新出的劇目更是有極大的熱情。
莎劇的演出地點和看戲門檻低,又足夠精彩,在場的觀眾不吝夸贊,一定會給予掌聲。這種時代背景,讓好的戲劇能快速脫穎而出,大藝術家在世的時候,不用過著凄苦的日子,也不用等到死了以后才成名成腕。
當時,一部“原創”新劇目的劇本酬金是五到十英鎊左右。最吃香的劇作家,每年起碼能寫五部戲。按當時的物價,一公斤煙草要四英鎊,一匹馬大概一英鎊,而英國一個教師的平均工資是每年20英鎊,熟練工人則只有八英鎊。
以莎士比亞流傳后世的38部“獨立原創”劇作計算,他至少靠寫劇本賺了200英鎊。但遠遠不止這些。當時的劇團,會將從另處得來的劇本交給駐團作家改編,一年下來經莎士比亞之手潤色的劇本也不少。他還和其他人合寫了一些劇本,這些酬金不會是小數目。
莎士比亞是有商業頭腦的。在倫敦的二十多年間,莎士比亞曾跳槽過一兩次。當時駐團作家的劇本通常是屬于老東家的。跳槽后,需要創作新的故事給新東家。莎士比亞不管這些,他奉行自己的一套做法——每次跳槽,他總會帶去一些自己以前的作品,維護自己的版權。他把老劇本加以修改,根據新劇團演員的特性量身定制角色,適應新劇團的需要。就這樣,老劇本給他創造了“二次財富”。
寫詩成了暴發戶:一字抵千金
就算在戲院都被迫禁演的時候,其他演員都斷糧了,莎士比亞也不缺少“錢路”。
1591年至1594年間,倫敦全城瘟疫肆虐,劇場關門歇業。
戲劇業陷入了低谷,人們不能看劇了,但莎士比亞總有辦法用才華讓大家想起他。趁著瘟疫的這段空檔,他找出版界的同鄉幫忙,出版了兩本長篇敘事詩《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和《魯克麗絲受辱記》。一夜之間,倫敦城里無論平民還是貴族都成了他的“小粉絲”,這兩部作品遠比他的任何一部戲都要受追捧。
在莎士比亞去世前,《維納斯與阿都尼》就再版八次,每本詩作定價六便士,每次印刷1300多冊;而在英國歷史上的王政更替時期前,一共再版了14次。另一部戲劇《魯克麗斯受辱記》也再版了八次之多。
盡管受歡迎,但莎士比亞從出版詩集中撈到的油水不多。可以想象,當時的出版業屬于大資本家產業,給到莎士比亞的酬金不多,何況,當年在缺乏市場意識的情況下,出版商可能是一次性買斷付款,而非收益抽成。
但莎士比亞給自己的詩作找了一個買單的恩主——年僅19歲的南安普敦伯爵。彼時,伯爵很受伊麗莎白女王的器重,既英俊,又熟諳文學,還非常有錢。莎士比亞在兩部詩作的開篇都附有給南安普敦伯爵的獻詞。后世對兩人的關系有諸多曖昧的猜測,從獻詞看來,這關系的確非同一般。
“我所寫出的作品屬于您,我將要寫作的作品也同樣屬于您,凡我所有的,也都必定屬于您,您忠誠的莎士比亞。”(《魯克麗斯受辱記》獻詞)
伯爵似乎很受用,惠贈了莎士比亞一千英鎊(也有說法是一百英鎊,無論一千還是一百,這在當時都非小數目)。莎士比亞找到了庇護自己理想的恩主。
寫一首詩都能值這么多錢,放在現在是無法想象的。
得到市民和恩主如此捧場的莎士比亞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個暴發戶,一票難求的戲劇場,成為他表現才華和發財之所。
也難怪,莎士比亞同時期的競爭對手羅伯特·格林,曾含沙射影地諷刺莎士比亞是“一只用我們的羽毛打扮的暴發戶烏鴉”。
炒房+入股劇院:會投資的文藝青年
莎士比亞賺的錢不少,但對自己卻很“小氣”。
他在倫敦初期住在燈紅酒綠的肖迪奇區,租住的房子面積很小,陳設簡單。在一次搬家后,莎士比亞去教區登記,評估冊上顯示,他家的各項物件總估值只有13先令4便士。
他也不喜歡交際。每晚的肖迪奇區,是一個演員和劇作家們扎堆兒的地方,劇團的演員們總是邀約莎士比亞一起去尋歡作樂,但都被小莎以不舒服的理由推脫了。好像沒有什么享樂的事值得他花錢。
但莎士比亞在房地產投資上十分豪氣。
33歲,莎士比亞花了60英鎊購置了斯特拉福鎮上埃文河畔最大的豪宅“新宅”,隨后又買下了花園對面的15英畝地,包括一所茅屋和一個花園。雖然購房契約上寫的成交價是60英鎊,但伊麗莎白時代的房產買賣很復雜,實際成交價也許是這個價格的兩倍。不過,在莎士比亞買下來之前,按照有關材料的描述,這棟房子“年久失修,破敗不堪,而且至今仍未修繕”。換句話說也就是,越來越不值錢了,莎士比亞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投資的好機會。
六年后,他以320英鎊收購了家鄉北部100多英畝耕地。隨后,他用440英鎊的高價買下斯特拉福及附近地區的“谷類、禾葉與草料”的什一稅的一半份額。這筆租稅可使他每年收益60英鎊。
僅僅41歲,莎士比亞陸陸續續投資房產800多英鎊,每年收益達80-90英鎊,投資回報率超過10%,跑贏了當今大多數理財產品。
“不要把錢借給別人,借出去會使你人財兩空;也不要向別人借錢,借進來會使你忘了勤儉。”(《哈姆雷特》)
但有意思的是,莎士比亞雖然勸告他人“不要借錢”,但自己在投資的時候,可都一不做二不休地借現金,只等到資金寬裕后再慢慢補上。1613年3月,他進行了最后一項地產投資,以140英鎊高價購得倫敦黑修士地區一所公寓,其中的60英鎊,就是等把房子租出后,拖了半年才付清的。
要活到現在,莎士比亞必定是資本運作的高手。
在倫敦摸爬滾打一段時間后,莎士比亞和七個朋友各出資50英鎊,成為了內務大臣供奉劇團的創始人和股東之一。這意味著,他將享有劇團票房收益的八分之一分紅。其時,合資公司的模式僅在英國剛剛起步50年,而這在當時的劇作家圈子也并不尋常,這是個“冒險的決定”。
五年后,他和朋友合資,在泰晤士河邊建起了一座環形露天的環球劇場,擁有十分之一的股份。其后,他又分享著黑衣修士劇場的紅利。
按1613年莎士比亞把手上劇團的股份全部賣掉的時價估算,他每年從劇團的分紅能賺到200多英鎊。
小莎到底有多少錢?
給你一條公式自己算:
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300鎊 ≈ 現在的50000英鎊;
50000英鎊 ≈ 44萬元人民幣。
這幾筆被認為冒險的風險投資,一投一個準。
富二代:很努力賺錢,但我爹其實也很有錢
莎士比亞那么努力地圈錢,但其實他是一名隱藏版的富二代。
莎士比亞出身富庶之家,生活安逸。父親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上任斯特拉特福鎮鎮長,母親出身大戶家族,這樣的背景讓他渾身上下都透著那種富家子弟才有的自信勁兒。
但因為宗教信仰與當時的政權相悖,莎士比亞的父親在他13歲之時辭去了公職,一夜之間,家道中落。為了籌集給政府繳納的罰金,父親還將自家的幾套房子抵押給親戚。15歲時的他,還跑去鄰鎮的大戶人家做家教,減輕家里的負擔。
莎士比亞可能經歷過一段比較困苦的童年,但他父親實際上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富有,這可能連莎士比亞自己都沒有料到。在父親1601年去世的時候后,留下了一筆遺產,具體數額不得而知,但繼承了遺產的一年多后,也正是之前提到莎士比亞大手購入家鄉的耕地之時,時間點之巧合,不免讓人聯想,莎士比亞父親到底有多會“藏富”。
莎士比亞還有更多的理財手段,都源于父親,自小耳濡目染:囤糧發災難財,甚至放貸、逃稅,猶如筆下的商人夏洛克一般。但這些手段沒有持續多久,或許,他不想成為自己不恥的人。
(摘自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