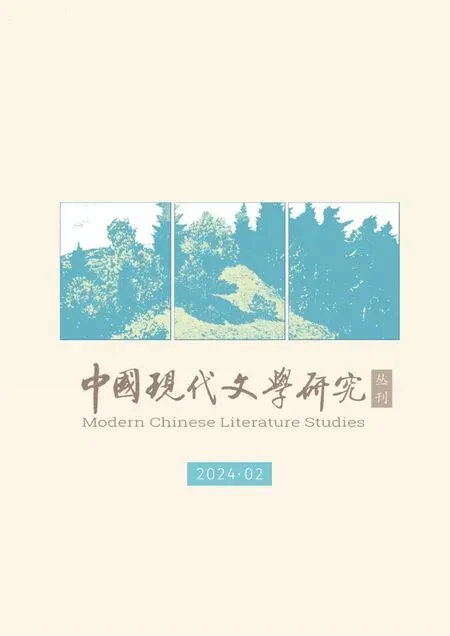“包產(chǎn)到戶”的歷史轉(zhuǎn)折與陳忠實的文學(xué)過渡
李 旺
內(nèi)容提要:在新時期開始反思“農(nóng)業(yè)合作化”表現(xiàn)“包產(chǎn)到戶”的文學(xué)潮流中,作為“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傳統(tǒng)后起之秀的陳忠實顯得猶豫不決。在小說中具體表現(xiàn)為:“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的繼續(xù),農(nóng)村基層干部在包產(chǎn)到戶政策實施時的心理矛盾與悲壯心境,及敘述者對此的體諒與同情。這使得他1980年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顯得“保守”“滯后”。但接近歷史語境,這“保守”“滯后”,留存了農(nóng)業(yè)合作化與包產(chǎn)到戶兩種農(nóng)村政策的基層實施者在歷史轉(zhuǎn)折時期的過渡心境,呈現(xiàn)了在“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農(nóng)村題材作家進行“包產(chǎn)到戶”敘述時的思想轉(zhuǎn)折與敘述轉(zhuǎn)變。
陳忠實的小說《信任》獲得過1979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在整個1980年代他也持續(xù)創(chuàng)作。但與同一年獲獎已經(jīng)成為文學(xué)史名篇的《喬廠長上任記》《剪輯錯了的故事》《李順大造屋》《內(nèi)奸》《記憶》相比,與同時期農(nóng)村題材名篇《鄉(xiāng)場上》《黑娃照相》相比,與因名篇而成為1980年代小說經(jīng)典作家的茹志鵑、蔣子龍、高曉聲、方之、張弦、何士光、張一弓等相比,陳忠實與他1980年代的小說是湮沒于文學(xué)史敘述之中的。在反思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時代氛圍與閱讀視野中,陳忠實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時期基層干部的體諒與同情,顯示出“保守”“滯后”的特質(zhì)。因此,他的這些小說就似乎成了歷史轉(zhuǎn)折時期的懸浮物無處安置。不過,如果我們把他1980年代的小說放置在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nóng)村政策調(diào)整與包產(chǎn)到戶政策實施前后的歷史變遷中,放置在“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向包產(chǎn)到戶敘述轉(zhuǎn)換的文學(xué)環(huán)境中,同時關(guān)注陳忠實10年的公社書記身份,從1960年代到“文革”后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陳忠實與他的1980年代的小說就留存了兩種農(nóng)村政策的基層實施者在歷史轉(zhuǎn)折時期的過渡心境,呈現(xiàn)了在“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傳統(tǒng)中成長的作家敘述包產(chǎn)到戶時的文學(xué)過渡形態(tài)。
“農(nóng)村政策調(diào)整”與陳忠實的新時期“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
張光年在1978年讀了《人民文學(xué)》轉(zhuǎn)載的陳忠實的《信任》,在日記中表示“有深廣的現(xiàn)實意義,看后受到教育”1張光年:《文壇回春紀(jì)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這一年,陳忠實的小說寫作在中斷兩年之后再次開始。
1978年到1980年,陳忠實的十多部短篇小說塑造農(nóng)業(yè)社生產(chǎn)隊長、大隊支書、公社書記的正面形象,突出他們建設(shè)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使命感與崇高感。小說文本的敘述聲音、敘述態(tài)度非常集中統(tǒng)一,敘述者對生產(chǎn)隊長、大隊支書、公社書記的正面形象完全認(rèn)同。生產(chǎn)隊長、大隊支書、公社書記成為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人格象征,小說賦予了他們強烈的英雄氣質(zhì)。如《南北寨》中南寨支書常克儉一心為社、一心為隊的忍辱負(fù)重,《七爺》中老支書七爺對公正終會到來的歷史遠見,《小河邊》中農(nóng)業(yè)社長與大隊支書“老大”面對磨難的云淡風(fēng)輕。到了《石頭記》中的隊長劉廣生與《心事重重》中的模范飼養(yǎng)員,確證了農(nóng)業(yè)集體化精神的持久影響力與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有效性。
陳忠實在塑造生產(chǎn)隊長、大隊支書、公社書記正面形象的同時,表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社社員對農(nóng)業(yè)社的追懷,呈現(xiàn)了物質(zhì)與精神都充分自足的農(nóng)業(yè)社圖景。由于敘述者與農(nóng)業(yè)社員情感、態(tài)度的高度契合,小說又是立足新時期的回顧性敘述,追懷就體現(xiàn)出復(fù)原并再造這一理想農(nóng)村的想象與激情色彩。《七爺》敘述“四十歲左右的男女社員,懷念田莊歷史上這一段欣欣向榮的日子”2陳忠實:《七爺》,《陳忠實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頁。,《心事重重》中的方老三老漢是合作化時期的飼養(yǎng)員,“他對農(nóng)業(yè)社的感情是任何沒有受過凍餓的人無法理解的”1陳忠實:《心事重重》, 《陳忠實文集》第1卷,第96頁。。在追懷的同時,小說強調(diào)農(nóng)業(yè)社的精神感召力,如《徐家園三老漢》中,蔬菜生產(chǎn)專業(yè)隊苗圃組組長徐長林老漢幫助治安老漢從“奸老漢”變成好社員過程中,篤信的是“一個社員對集體的實心”2陳忠實:《徐家園三老漢》,《陳忠實文集》第1卷,第58頁,。小說《豬的喜劇》雖然涉及了“文革”后期農(nóng)村左的政策,但隊長克賢對社員來福老漢的體諒,兩人在推搡中留下的理解的熱淚,彰顯的還是農(nóng)業(yè)社社員之間、社員與隊長之間的深厚情誼。尤其是小說中人物來福老漢與敘述者的口吻合二為一:“農(nóng)業(yè)社好,靈人一個勞動日分八毛,咱笨來福也分倆四毛。”3陳忠實:《豬的喜劇》,《陳忠實文集》第1卷,第105頁。農(nóng)業(yè)社的理想性已經(jīng)完全征服了敘述者。小說《南北寨》中南寨支書常克儉走過場畔時,吃中飯的社員的眼睛流露出對當(dāng)家人的崇敬與仰視。社員對大隊支書的信任,體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社的向心力,倫理滿足與精神自洽。
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單向度的肯定性敘述,與《剪輯錯了的故事》中老壽的不解與敘述者的感慨,《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李銅鐘應(yīng)對饑餓的務(wù)實與敘述者的寫實,《李順大造屋》中李順大屢次蓋房不成的苦惱與敘述者的解嘲形成的敘述態(tài)度的多重性、駁雜性,以及由此發(fā)生的小說對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反思性相比,顯得觀念滯后、敘述封閉、情感單一。這種與眾不同是由陳忠實獨特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與人生經(jīng)歷決定的。
陳忠實1960年代后期在報紙上開始發(fā)表作品,“文革”開始中斷了他的寫作。從1973年開始,到1976年,他以一年一部中篇的穩(wěn)定創(chuàng)作進度,在農(nóng)村題材小說領(lǐng)域形成了符合當(dāng)時時代主題的故事模式,具有了可辨認(rèn)的創(chuàng)作特色,開始發(fā)生全國性影響。1973年的《接班以后》入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選本,并被改編為電影。1974年的《高家兄弟》和1975年的《公社書記》都改編為連環(huán)畫。1976年的《無畏》發(fā)表于《人民文學(xué)》。這些小說著力塑造公社書記形象,在當(dāng)時農(nóng)田水利與辦副業(yè)、上大學(xué)與扎根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集體化與包干到戶的兩條路線之中,凸顯公社書記形象的斗爭性、政治覺悟與英雄品質(zhì)。與政治化的人物糅合在一起的是小說對同宗同族、兄弟叔嫂笑罵之間的鄉(xiāng)村倫理溫情書寫。政治倫理與鄉(xiāng)村倫理的結(jié)合使得陳忠實的小說在當(dāng)時獨樹一幟。兩相比較,陳忠實1978年的小說與他“文革”后期的小說具有明顯的繼承關(guān)系,新時期的重啟是以恢復(fù)自己已有的寫作傳統(tǒng)開始的。但也體現(xiàn)了新時期的特質(zhì),基層干部形象從“文革”后期的現(xiàn)實斗爭性向新時期治愈傷痕重新上路的精神引領(lǐng)方面轉(zhuǎn)變。
現(xiàn)實生活中的陳忠實直到1978年還是毛西公社黨委副書記。自1968年從民辦中學(xué)教師借調(diào),進入毛西公社協(xié)助做專案工作開始,他在人民公社工作10年之久。其間,1972年正式成為國家基層干部,1974年成為毛西公社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擔(dān)任毛西公社黨委副書記,直到1978年。1邢小利:《陳忠實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56、82、86頁。10年間,陳忠實分管公社衛(wèi)生工作、養(yǎng)豬工作、農(nóng)田水利工作。保證了每個村子建立起醫(yī)療站;落實“養(yǎng)豬的一封信”的精神,實現(xiàn)每戶一頭豬的要求;保證了公社所屬城市區(qū)段的蔬菜供應(yīng),駐隊解決派性嚴(yán)重對立的生產(chǎn)隊,化解矛盾恢復(fù)生產(chǎn)。2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4頁。在“文革”結(jié)束后的兩年,為毛西公社辦了幾件大事。1976年冬,被公社委派駐隊,調(diào)查一個在四清運動中被開除的支書的案件,1977年底支書平反,陳忠實的工作受到好評。1977年再次駐隊,提高一個落后生產(chǎn)隊的生產(chǎn),生產(chǎn)隊生產(chǎn)面貌改觀。1977年6月到7月,擔(dān)任毛西公社學(xué)大寨平整土地副指揮,帶領(lǐng)群眾把跑水、跑土、跑肥的800畝“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從1977年冬天到1978年6月,擔(dān)任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會戰(zhàn)工程的主管副總指揮,組織公社人力,完成灞河河堤水利工程,這一段河堤幾十年堅固如初。3邢小利、邢之美:《陳忠實年譜》,陜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7頁。陳忠實一直在以人民公社干部的身份、心態(tài)參與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具體工作,已經(jīng)融入了農(nóng)業(yè)集體化之中。“無論我無論我周圍的干部,議論只局限在某項具體政策的恰當(dāng)與否,誰也不會發(fā)生對集體所有制的絲毫懷疑,甚至可以說,對自50年代中期完成的農(nóng)業(yè)集體化體制的理性信奉,已經(jīng)形成意識里的自然習(xí)慣。”4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4頁。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成長環(huán)境、生活環(huán)境、工作內(nèi)容與基層干部的紀(jì)律自覺,促成了陳忠實篤信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思想慣性,推遲了他的歷史變遷感知。另外,在陳忠實的基層干部經(jīng)歷中,1976年到1978年,歷史轉(zhuǎn)折之際的兩年,陳忠實的實際工作沒有出現(xiàn)停頓、間斷與變化,基層工作的一貫性、連續(xù)性讓他較之于他人更久地在歷史的延宕中置身其間、置身事內(nèi),這再次延緩了他的歷史變遷感知。這種推遲、延緩提供了新時期歷史轉(zhuǎn)折、農(nóng)村政策調(diào)整、農(nóng)村經(jīng)濟落實的層次性、遞進性。
農(nóng)村政策調(diào)整改革的階段性、探索性也是陳忠實的思想慣性、新時期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得以發(fā)生的時代背景。1977年傳達過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的講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也還“不能突破‘三級所有’的集體模式,寫上了‘不許包產(chǎn)到戶’‘不許分田單干’的規(guī)定性語言”1劉湛:《回顧一九七九年七省農(nóng)口座談會》,杜潤生主編:《中國農(nóng)村改革紀(jì)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fā)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黨的工作“破除階級斗爭為綱”轉(zhuǎn)移到“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上來,已經(jīng)開啟了新的歷史時期。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關(guān)于地主、富農(nóng)分子摘帽問題及地主、富農(nóng)子女問題的決定,這意味著自農(nóng)業(yè)合作化開始,農(nóng)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敵對成分已經(jīng)不存在了。1979年9月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加快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的“不許包產(chǎn)到戶,不許分田單干”改成了“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yè)生產(chǎn)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qū)、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chǎn)到戶”。參與了農(nóng)業(yè)政策制定的親歷者立刻就從“‘兩個不許’到‘不許分田單干,也不要包產(chǎn)到戶’的改動中感覺到了包產(chǎn)到戶的突破”。2段應(yīng)碧口述:《1979年〈關(guān)于加快農(nóng)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始末》(下),《農(nóng)村工作通訊》2015年第13期。后來的研究者把1979年看作人民公社制度進入革故鼎新的非均衡狀態(tài)的一年。3劉慶樂:《權(quán)力、利益與信念: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頁。但當(dāng)時身在陜西的公社書記陳忠實聽到“私底下傳說安徽有地方實行了包干到戶,但不敢相信”4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第96頁。。一方面是農(nóng)業(yè)政策調(diào)整的破冰進程,另一方面是邁向改革步伐的探索、實驗。政策制定者與基層實施者的身份差異、中央與地方農(nóng)業(yè)部門的觀念差異、地區(qū)之間的農(nóng)業(yè)水平差異,不同地方落實農(nóng)業(yè)政策、推行包產(chǎn)到戶的先后差異,都造成了政策落實、推行、接受的不同步、不平衡。1978年到1980年的陳忠實與他的小說,呈現(xiàn)了這一不平衡性與差異性,留下了歷史轉(zhuǎn)折之際的過程性。
“包產(chǎn)到戶”的改革與陳忠實的矛盾
1980年4月2日與5月31日,鄧小平兩次談話都肯定了包產(chǎn)到戶、包干到戶。5月31日的談話提到了安徽鳳陽1978年開始的包產(chǎn)到戶。“農(nóng)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chǎn)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chǎn)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chǎn)隊搞了包產(chǎn)到戶,增產(chǎn)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chǎn)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1鄧小平:《關(guān)于農(nóng)村政策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編:《新時期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頁。這兩次談話形成了1980年12月的75號文件。“75號文件傳達貫徹后,‘包產(chǎn)到戶、包干到戶’迅速在各地發(fā)展起來,呈現(xiàn)出強勁的勢頭,實際上突破了文件。”2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jīng)過》 ,杜潤生主編:《中國農(nóng)村改革決策紀(jì)事》,第134、135頁。突破是指文件本來限定包產(chǎn)到戶與包干到戶在“邊遠山區(qū)和貧困落后地區(qū)”可以施行。到1982年元旦,第一個一號文件出臺,說明包產(chǎn)到戶不姓資,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責(zé)任制。全面肯定了包產(chǎn)到戶。3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jīng)過》 ,杜潤生主編:《中國農(nóng)村改革決策紀(jì)事》,第134、135頁。1980年最著名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當(dāng)屬何士光的《鄉(xiāng)場上》。馮幺爸在羅二娘面前、在曹福貴面前直起腰來說了公道話,形象地體現(xiàn)了“責(zé)任田落實到人”照亮了農(nóng)民的尊嚴(yán)。張一弓《黑娃照相》也是名篇,表現(xiàn)“有了責(zé)任田”的黑娃的樂觀與自足。陳忠實也在1980年開始寫作包產(chǎn)到戶題材的小說,但他的小說并沒有寫包產(chǎn)到戶的順理成章,而是寫這一政策在農(nóng)村干部精神世界中激起的波瀾。何士光、張一弓等人是從農(nóng)民的角度寫包產(chǎn)到戶,表現(xiàn)農(nóng)民擁護包產(chǎn)到戶的心境。陳忠實是從農(nóng)村干部的角度寫包產(chǎn)到戶,表現(xiàn)農(nóng)村干部對包產(chǎn)到戶的猶豫不決。這類小說,讓我們增加了一種觀察包產(chǎn)到戶在農(nóng)村引起反響的角度,也可看到包產(chǎn)到戶實施過程的復(fù)雜性與豐富性。
陳忠實小說中的生產(chǎn)隊長、老支書、公社書記等基層干部無法接受包產(chǎn)到戶政策。即使接受,也有保留意見。他的小說不涉及包產(chǎn)到戶實施后給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生活帶來的具體變化,主要集中表現(xiàn)農(nóng)村干部面對包產(chǎn)到戶時的思想觀念斗爭,做了多角度的展現(xiàn)和揭示。
首先,小說展現(xiàn)農(nóng)業(yè)合作化政策中成長的農(nóng)村干部在包產(chǎn)到戶政策實施后的思想障礙與精神負(fù)累。“多年來對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限制和斗爭,是公社黨委書記的神圣職責(zé)。現(xiàn)在要他去鼓吹農(nóng)民上自由市場,甚至叫他逛自由市場,嫑說理論,感情上也難得暢通!”1陳忠實:《反省篇》,《陳忠實文集》第1卷,第193、192頁。“不管感情上是否暢通,他們已經(jīng)向縣委明確表示:保證尊重社員意見,由社員選擇責(zé)任承包的形式。”2陳忠實:《梆子老太》,《陳忠實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頁。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退出,意味著與之相關(guān)的價值觀念、立場態(tài)度的塌毀。包產(chǎn)到戶,不僅是一種農(nóng)業(yè)政策,也包含這一政策背后的價值觀念、立場態(tài)度的建立。在塌毀與建立之間,農(nóng)業(yè)合作化中成長起來的基層干部背負(fù)著由制度慣性、政策慣性與思想慣性構(gòu)成的情感壓力。
其次,小說寫到生產(chǎn)隊長、支書等農(nóng)村干部無法接受終結(jié)農(nóng)業(yè)合作化政策時一并否定他們的精神付出。黃建國不滿于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弊端與基層執(zhí)行者等同的社會輿論。他陳述自己的辛苦:“在河?xùn)|公社,他睡過安穩(wěn)覺嗎?坡陡溝深的塬坡,沙石嶙峋的河灘,跑爛了他多少雙鞋?泥濘狹窄的溝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進道溝,摔得人事不省,我是為了坑害農(nóng)民嗎?”3陳忠實:《反省篇》,《陳忠實文集》第1卷,第193、192頁。馮景藩不理解被時代遺忘的境遇。“真是令人寒心哪!想當(dāng)年,馮景藩在馮家灘辦起河西鄉(xiāng)第一個試點社的時光,鄉(xiāng)上縣上領(lǐng)導(dǎo)們嘴里喊著他名字的聲音,夠多親切!你王書記調(diào)來河西公社才幾年?你知道馮景藩為了農(nóng)業(yè)社熬過多少心血?你知道馮景藩在三年困難時候領(lǐng)著社員大戰(zhàn)小河灘的壯舉嗎?你知道馮景藩從縣里鄉(xiāng)里領(lǐng)回去多少獎旗錦標(biāo)嗎?你知道中共馮家灘支部書記在‘四清’運動中挨打受罵的委屈嗎?”4陳忠實:《初夏》,《陳忠實文集》第2卷,第50頁。黃建國們與馮景藩們的痛苦源自歷史更迭之際,把自己的付出從歷史中抽離,也包括他們奉獻但不被理解的傷感,從農(nóng)業(yè)合作化到包產(chǎn)到戶轉(zhuǎn)變中的心理落差與精神失衡。他們沒有回顧農(nóng)業(yè)合作化給農(nóng)民帶來了怎樣具體的效益,而是不斷突出自我精神的高尚與英雄主義。自我對話的傾訴,反問句式的辯詰,人物語言與敘述者態(tài)度的同一,表現(xiàn)出敘述者的同情。《初夏》里馮景藩自思:“二三十年來,他不僅沒有實現(xiàn)當(dāng)初實行合作化時給社員們展示的生活遠景,而且把自己家庭的日月搞爛包了。無論公私,三十年里,他竟然一事無成啊!”1陳忠實:《初夏》,《陳忠實文集》第2卷,第18、12頁。這是陳忠實小說中生產(chǎn)隊長、支書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唯一的一次具體評價。經(jīng)歷過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生產(chǎn)隊長、支書對包產(chǎn)到戶作出合理評價需要巨大的歷史勇氣,也需要破除沉重的思想重?fù)?dān)。
最后,陳忠實小說呈現(xiàn)了生產(chǎn)隊長、支書包產(chǎn)到戶后的失落、留戀情緒。“地畔上的界石是他倆帶領(lǐng)著社員,一個一個拔掉的;牲畜是他倆一家一戶說服動員集中到大槽上來的。現(xiàn)在,得由他倆再把一條條地畔分開來,把一頭頭牲畜送交社員牽回家里去飼養(yǎng)……”2陳忠實:《梆子老太》,《陳忠實文集》第2卷,第228頁。“等到二隊最后分掉這兩槽牛馬,老漢心里感慨系之:完了!他終于抑制不住心情的傷感,涌出眼淚了……”3陳忠實:《初夏》,《陳忠實文集》第2卷,第18、12頁。小說《霞光燦爛的早晨》中包產(chǎn)到戶后的一匹紅馬因想念飼養(yǎng)院而偷跑回來更是一個象征性細(xì)節(jié)。失落、留戀情緒與當(dāng)時從農(nóng)民角度寫包產(chǎn)到戶的小說形成了強烈反差。同樣的政策在農(nóng)村干部和農(nóng)民之間激發(fā)出完全相反的情緒。
與此同時,陳忠實還塑造了接受包產(chǎn)到戶政策的新一輩隊長,具有農(nóng)業(yè)合作化隊長氣質(zhì),這流露了他對農(nóng)業(yè)集體化隊長精神的歷史期待。農(nóng)業(yè)社隊長馮景藩在包產(chǎn)到戶后退出,兒子馮馬駒走馬上任,這父與子的傳承,包含著父一代倫理的延續(xù),馮馬駒的理想體現(xiàn)出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小說中當(dāng)年第一個支持馮景藩辦農(nóng)業(yè)社的人是馮德寬父親,如今馮德寬父親又督促兒子支持推行包產(chǎn)到戶的馮馬駒,表征了包產(chǎn)到戶中農(nóng)業(yè)社長與社員關(guān)系的重演。小說結(jié)束時,馮馬駒、馮德寬和彩彩在已故生產(chǎn)隊長馮志強墳前立下誓言,凸顯他們向農(nóng)業(yè)合作化精神汲取資源的決心。
陳忠實對農(nóng)村干部在包產(chǎn)到戶到來后的不解、失落的精神情緒的體諒式書寫,對生產(chǎn)隊長、公社書記在農(nóng)業(yè)集體化時期的付出的理解與同情,在推動包產(chǎn)到戶的1980年代顯得“不合時宜”,作為歷史的后來者,我們把這份“不合時宜”放置在歷史的“長時段”中,有可能接近歷史。推動了包產(chǎn)到戶改革的杜潤生在1981年就說:“有的同志說,在包產(chǎn)到戶這個問題上,中央幾個文件前后不連貫,下邊很被動。對于包產(chǎn)到戶,先是說不準(zhǔn),后來說不要,再后來是有條件地要,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變動又恰好證明黨中央是根據(j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biāo)準(zhǔn)這個哲學(xué)論斷來處理問題的,是實事求是的。不足之處是,這些變動事先在干部中醞釀不夠。這是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部門應(yīng)該擔(dān)負(fù)的責(zé)任,和下邊通氣不夠。”1杜潤生:《堅持改革,穩(wěn)步前進》(1981年10月20日,全國農(nóng)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杜潤生文集》(上),山西經(jīng)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也就是說,農(nóng)村基層干部對包產(chǎn)到戶的隔膜、不解是當(dāng)時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農(nóng)村基層干部在包產(chǎn)到戶施行過程中屬于不無被動的中間地帶人群,處于尷尬的位置。此外,農(nóng)業(yè)集體化時期的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所起的農(nóng)村生產(chǎn)條件積累作用,也是歷史存在。“集體化時期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平整了土地,修筑了機耕路和拍灌水渠道,購置了動力機械。”2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362頁。農(nóng)民從三十年的集體化中得到了兩樣?xùn)|西,其中之一是“具有交通排灌系統(tǒng)的平整農(nóng)田”3曹錦清:《當(dāng)代浙北鄉(xiāng)村的社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頁。,50年代,水利措施主要集中于大工程,60年代轉(zhuǎn)向基層的水利,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這些基礎(chǔ)工程的進一步完善和提高。4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nóng)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4、235頁。“集體化也為新的水利建設(shè)提供了實際上免費的勞動力。”5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nóng)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4、235頁。陳忠實一直無法忘懷,自己參與的農(nóng)田水利工程一直造福家鄉(xiāng)。從這一點來看,陳忠實小說中的基層干部強調(diào)自己參與的農(nóng)業(yè)集體化時代的付出,也是歷史的事實。這些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的組織者、貫徹者在包產(chǎn)到戶之后,大部分退出了歷史舞臺。“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鄉(xiāng)鎮(zhèn)黨政主要負(fù)責(zé)人都逐漸為新提拔的干部所取代,曾經(jīng)為農(nóng)業(yè)集體化立下過汗馬功勞的農(nóng)村老干部們先后告老還鄉(xiāng)。”6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362頁。農(nóng)業(yè)集體化時期的基層干部在包產(chǎn)到戶轉(zhuǎn)折之際成為歷史的隱匿者。而由《鄉(xiāng)場上》中的隊長,《桑樹坪紀(jì)事》中的李金斗,《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隊長,“厚土”系列的生產(chǎn)隊長等家長式隊長形象形成了新時期文學(xué)中隊長的“惡名”。陳忠實為歷史的隱匿者,新時期文學(xué)中的被貶抑者,作出了雙重調(diào)整。
《初夏》是陳忠實表現(xiàn)包產(chǎn)到戶題材中用力最多的一篇,寫作過程長達三年。寫作時,“陷入痛苦的深淵”7陳忠實:《創(chuàng)作感受談》,《陳忠實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485頁。,“這是我從事寫作以來二十年間所經(jīng)歷的最嚴(yán)重的一次痛苦”8陳忠實:《創(chuàng)作感受談》,《陳忠實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485頁。。造成痛苦的最重要的緣由就是對馮景藩精神性格的塑造和展現(xiàn)。“我可以輕輕嘲弄一下馮安國,卻無法傷害馮景藩一詞一字。我想真實地寫出他們今天的心理意識,就不能不如實地回顧他們歷史的功績和光榮,有意無意的失誤和自己遭到的挫折。沒有這些歷史,就沒有今天的那種‘失落’情緒。”1陳忠實:《關(guān)于中篇小說〈初夏〉的通信》,《陳忠實文集》第2卷,第491頁。修改的痛苦包含了陳忠實思想的劇烈斗爭。他無法面對馮景藩,其實是無法面對自己。他被自己所逼迫。陳忠實面臨著兩種精神壓迫:一是作為農(nóng)村基層干部的陳忠實,在現(xiàn)實中遭遇著馮景藩式的沖擊;二是作為寫作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的小說家陳忠實,知道自己的寫作傳統(tǒng)面臨改變。
在陳忠實的個人經(jīng)歷中,有兩件事令他難以忘懷。1982年,陳忠實做了實驗。在分到的責(zé)任田里自種自收。收了20袋新麥,2000斤,這算中等收成。但這一料麥子的收成,抵得上生產(chǎn)隊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糧。實驗的結(jié)果讓他在回顧自己擔(dān)任農(nóng)村基層干部歷史時的悖論,也察覺了農(nóng)業(yè)合作化具有的弊病,但他無力回答。最終,他把歷史造就的理解的困境轉(zhuǎn)換為一種個人選擇,“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選擇避開這一悖論性的人生境遇與當(dāng)代農(nóng)村歷史。2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第99、91頁。與此同時,陳忠實在騎著自行車走鄉(xiāng)串戶落實包產(chǎn)到戶的夜路上,突然想到,如果柳青在世,對于他一生文學(xué)事業(yè)中論證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正確性遭遇到現(xiàn)實的推翻,他會怎么辦,想到這一點,陳忠實驚嚇得從自行車上跌落下來。3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第99、91頁。這種痛苦既源自陳忠實的現(xiàn)實處境的悖論,個人經(jīng)驗對包產(chǎn)到戶效率的確證,而他自己10年的工作就是以對人民公社的推行否定包產(chǎn)到戶,也源自陳忠實的寫作處境。他信奉追隨的柳青的寫作方式也是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論證,而包產(chǎn)到戶的施行意味著柳青所論證的農(nóng)村政策即將告別歷史。與之相應(yīng)的寫作方式也需要更新。陳忠實寫出了歷史過渡者與文學(xué)過渡者經(jīng)歷的精神焦慮與痛苦。在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十七年時期與新時期文學(xué)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形成了斷裂的敘述。十七年時期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講述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必然,新時期以來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敘述包產(chǎn)到戶給農(nóng)民帶來的由衷喜悅。陳忠實的小說提供了斷裂的敘述之間的情感銜接,以及情感銜接時的困惑與彷徨。
晚年柳青、農(nóng)村題材小說傳統(tǒng)與新時期陳忠實
柳青是陳忠實文學(xué)道路上至為重要的作家,但陳忠實只聽過柳青的講座,在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直接的交流。但晚年柳青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思考在新時期陳忠實的小說中有很多密切呼應(yīng)。晚年柳青反復(fù)提及農(nóng)村干部在“四清”等運動中所受的冤屈,表示了對他們的理解與同情。柳青問道:“農(nóng)村干部的辛苦,你們知道嗎?他們黑不當(dāng)黑,明不當(dāng)明,難得吃上個正頓飯,睡上個囫圇覺,吃飯時間還是工作時間,難道他們就一無是處?這十幾年的工作沒有一點成績,就漆黑一團嗎?”柳青很氣憤。1劉可風(fēng):《柳青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252、263頁。柳青也提到《創(chuàng)業(yè)史》原型王家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1964年12月,“四清”工作組召開了斗爭王家斌和全體干部的大會。2劉可風(fēng):《柳青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252、263頁。《創(chuàng)業(yè)史》中馮有萬的原型,勝利大隊的董柄漢,情況也令柳青痛心。董柄漢被剝奪了黨員身份,工作組不允許他當(dāng)隊長、組長。但董柄漢工作有辦法,群眾讓他當(dāng)隊長,生產(chǎn)上來之后工作組就又把他拉下來。3劉可風(fēng):《柳青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252、263頁。柳青晚年對農(nóng)村基層干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回憶,在陳忠實的《七爺》《鄉(xiāng)村》《初夏》等多篇小說中都能找到可以對應(yīng)的人物形象。柳青認(rèn)為社教運動極大地破壞了長安縣的干部隊伍,新的干部隊伍在運動以后思想、心理、作風(fēng)都有了較大的轉(zhuǎn)折性變化。4劉可風(fēng):《柳青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252、263頁。陳忠實自《信任》始,屢次敘述“四清”等運動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基層干部的打擊。1980年代后期,小說《地窖》又重寫《信任》故事,并發(fā)生了從和解到和解的困難的變化,同一主題的重新敘述,同一歷史的反復(fù)講述,陳忠實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時期的基層干部曾被歷史誤解但又在農(nóng)村政策轉(zhuǎn)變之后被遺忘無法釋懷。柳青晚年的回憶遲至2016年才公開面世。但兩代作家在體察農(nóng)業(yè)合作化實施過程,思索農(nóng)業(yè)合作化問題時,因相同的生活體驗產(chǎn)生了情感共振與觀念契合。可以說,柳青沒有時間寫出的,陳忠實寫出了。新時期的陳忠實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了柳青在新時期的思考可能,寫出了柳青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傳統(tǒng)在新時期的演變路徑。
柳青之外,歷史也沒有給同樣是“農(nóng)業(yè)合作化”典范作家的周立波、趙樹理留出時間敘述新的歷史時期。作為十七年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代表王汶石與李準(zhǔn)也沒有奉獻新時期農(nóng)村題材新作。唯有“山藥蛋派”作家馬烽的新時期新作留下了難得的思想與文學(xué)參照。獲獎小說《結(jié)婚現(xiàn)場會》突出落實農(nóng)村政策對農(nóng)民的鼓舞,《典型事例》強調(diào)落實農(nóng)村政策中實事求是的重要性。《伍二四十五紀(jì)要》具有全面反思?xì)v史的意愿,對大躍進、浮夸風(fēng)的危害、“文革”時期左的政策都做了揭示。等到1984年發(fā)表《我村有個章小寶》,馬烽通過小說把開放自留地、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家庭副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等新時期以來農(nóng)村政策的演變做了全面的文學(xué)演繹。可以看出,馬烽小說及時地對農(nóng)村政策變化做了小說書寫,不存在如陳忠實的轉(zhuǎn)變的艱難、接受的猶豫。但馬烽小說采用的視察體、訪問體與巧合、反轉(zhuǎn)的情節(jié)形式使得小說接近于演繹政策的故事,缺乏當(dāng)事人的現(xiàn)實感與現(xiàn)場感。這或許是老作家沙汀覺得似曾相識的原因。“馬烽的《結(jié)婚現(xiàn)場會》,才力不減當(dāng)年。較之一般新出現(xiàn)的優(yōu)秀短篇,總像缺少一點新銳之氣。故事,人物安排總覺似曾相識。”1沙汀:《沙汀文集》第九卷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858、824、860頁。沙汀并非十七年時期農(nóng)業(yè)合作化代表作家,但他新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獎評委的身份與對當(dāng)時小說的閱讀與自我反思,也提供了文學(xué)史參照。1978年與1984年沙汀發(fā)表的兩篇農(nóng)村題材小說《青?坡》與《木魚山》,都沒有超越1950年代“農(nóng)業(yè)合作化”敘述框架。他對此反思道:“這是一部我醞釀了三四年的作品,最初九章,也已寫好一年多了。我之?dāng)R下來另寫別的,也就是解放前夕的,主要是因為思想障礙未能克服;不愿損害,或者說擔(dān)心損害黨和毛主席的形象。現(xiàn)在算想通了,盡管我對三年困難,特別是大躍進的失誤,同《黑旗》的作者仍然存在很大差距。”2沙汀:《沙汀文集》第九卷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858、824、860頁。同時談及,“《鄉(xiāng)場上》那樣的短篇,我也有不可企及之感”3沙汀:《沙汀文集》第九卷下,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858、824、860頁。。同反思小說存在很大差距與對包產(chǎn)到戶小說的不可企及,“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對老作家沙汀而言,不僅是突破一種農(nóng)業(yè)政策與敘述方式,還包括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時代的評價,因此產(chǎn)生了沉重的思想顧慮,并最終也不可能走出認(rèn)識突破但寫作踟躕的錯位。較之于沙汀,陳忠實對農(nóng)業(yè)集體化精神的期待與公正評價的信心,包含著農(nóng)業(yè)集體化環(huán)境中成長的作家的篤定,其間,有著當(dāng)代作家與老作家的區(qū)別。陳忠實與馬烽、沙汀新時期寫作的比較,為觀察“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傳統(tǒng)的新時期演變提供了又一種可能。
1984年之后,陳忠實小說開始表現(xiàn)包產(chǎn)到戶后農(nóng)村的變化,包括農(nóng)村干部與農(nóng)村世風(fēng)的變化。不論是干部的變化還是世風(fēng)的變化,有一部分是以農(nóng)業(yè)社的倫理自足為遠景的。如《拐子馬》中的支書馬成龍,《最后一次收獲》中的支書趙濟生在包產(chǎn)到戶后成為既得利益者。《害羞》《兩個伙伴》描摹金錢名利對農(nóng)村風(fēng)氣的影響,《山洪》中村民對干部吃要之風(fēng)的痛恨,《兔老漢》中姚善民老漢的善心反得惡報。有的是對農(nóng)業(yè)社干部的再發(fā)現(xiàn),如《轱轆子客》中的支書劉耀明一直都是利益獨占,《綠地》中的公社書記也經(jīng)歷過誘惑的困擾,《十八歲的哥哥》中的村長從農(nóng)業(yè)合作化到包產(chǎn)到戶都以精明著稱。面對農(nóng)村的變化,《最后一次收獲》中已經(jīng)在城市工作的趙鵬在包產(chǎn)到戶后第一次收獲后舉家離開了,《十八歲的哥哥》中的曹潤生在興辦村鎮(zhèn)企業(yè)受到壓制后懷著氣憤離開了,這表現(xiàn)了陳忠實面對農(nóng)村變化的思想情感困惑。此后的《四妹子》是陳忠實表現(xiàn)包產(chǎn)到戶后農(nóng)村變化最為深入的小說,敘寫妯娌由于四妹子的先行致富引發(fā)貧富不均引起的嫉妒心理,涉及了生產(chǎn)隊與封建道德觀念的雙重束縛,這意味著陳忠實從當(dāng)代農(nóng)業(yè)政策敘述接通了鄉(xiāng)村文化書寫的文化血脈。他從當(dāng)代中國農(nóng)村的講述轉(zhuǎn)向?qū)ΜF(xiàn)代中國鄉(xiāng)土的講述,從《藍袍先生》,到《四妹子》,再到《舔碗》,具有自身的演變邏輯。
《白鹿原》于1990年代出版后的巨大且持久的影響,陳忠實自己關(guān)于1980年代的剝離說,研究者以“蝶變”1李建軍:《陳忠實的蝶變》,二十一世紀(jì)出版社2017年版。概括陳忠實1990年代創(chuàng)作的自我超越,都不斷加深了1980年代陳忠實創(chuàng)作的湮沒。這造成了陳忠實創(chuàng)作歷程的割裂,也忽略了一個貫穿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的當(dāng)代農(nóng)村題材小說家攜帶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密碼。“作為一個農(nóng)村題材寫作的作者,你將怎樣面對30年前‘合作’30年后又分開的中國鄉(xiāng)村的歷史和現(xiàn)實?”2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第96、96頁。“在作為一個基層干部的時候,我毫不含糊地執(zhí)行‘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切實按照區(qū)委區(qū)政府的具體實施方案辦事,保證按照限定的時間,把集體所有的土地,耕畜和較大型的農(nóng)具分配到一家一戶;在我轉(zhuǎn)換出寫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時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軟弱和輕,這是面對這個正在發(fā)生著的生活大命題時的真實感受。”3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第96、96頁。這是困擾陳忠實精神與寫作的最大難題。在他的生活與寫作中,表現(xiàn)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合法性與正確性是難解難分的,已經(jīng)成為他生命認(rèn)知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視角的一部分。但時代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農(nóng)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被包產(chǎn)到戶取代。他對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看法與觀點沒有隨著新時期的政策與時俱進。這種遲疑在某種程度上是難能可貴的。當(dāng)代農(nóng)村政策論證了“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正確性,同時也論證了“農(nóng)業(yè)合作化”解體的必要性。但既經(jīng)歷“農(nóng)業(yè)合作化”施行又經(jīng)歷告別“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歷史見證人的形象是缺乏的。這一退出歷史的群體的生命體驗在新時期是被遮蔽的,陳忠實寫出了這份被遮蔽的退出者體驗。“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與時代完全一致,也不讓自己適應(yīng)時代要求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就是不相關(guān)的。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狀況,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位,他們比其他人更能夠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1吉奧喬·阿甘本:《何為同時代人》,《裸體》,黃曉武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頁。陳忠實以一種同時代人的“斷裂”“錯位”感知、把握了從“農(nóng)業(yè)合作化”到“包產(chǎn)到戶”的歷史轉(zhuǎn)折與敘述轉(zhuǎn)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