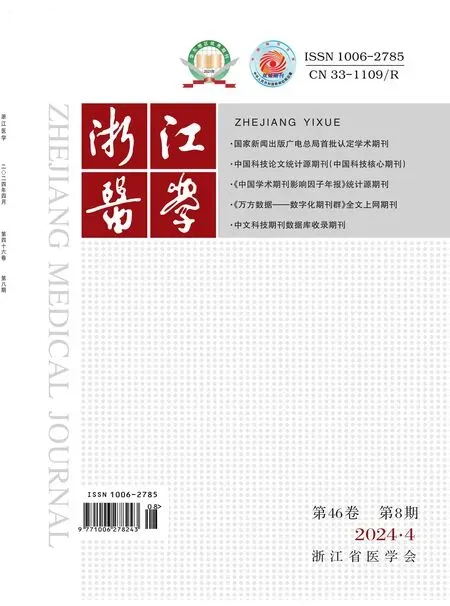飛蚊癥的治療與YAG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指征的把握
沈麗君 林鐵柱
飛蚊癥實際是玻璃體混濁在視網膜上的投影所形成的點狀、線狀、環狀或塊狀視覺感知[1]。嚴格來說,玻璃體混濁不等同于飛蚊癥,“有癥狀的玻璃體混濁”似乎更為恰當[2]。廣義來說,飛蚊癥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原發性飛蚊癥一般是由于與年齡或近視相關的玻璃體液化、塌陷導致玻璃體膠原聚集甚至后玻璃體脫離(posterior vitreous detachment,PVD)所形成的混濁;繼發性飛蚊癥一般由一些眼病或眼部手術引起,如眼內炎癥、玻璃體變性、玻璃體積血、淋巴瘤、玻璃體腔注藥/氣等。臨床上的飛蚊癥一般是指原發性飛蚊癥。
飛蚊癥是個臨床普遍存在的問題。10 年前一份調查研究顯示,76%受訪者表示眼前有混濁物漂動,33%受訪者表示這些混濁物對其視力有明顯影響[3]。飛蚊癥對患者的影響個體間差異較大,與“飛蚊”位置、大小、致密程度、病程的急緩程度以及患者年齡和心理素質等多種因素相關。例如,年輕患者可能會抱怨“飛蚊”會影響手機等電子產品使用和駕駛汽車。對于飛蚊癥的治療目前尚無臨床共識或指南,本述評旨在闡述飛蚊癥治療的必要性及各種治療方法的利弊,重點介紹近年來較為流行的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適應證把握。
1 飛蚊癥是否需要治療
飛蚊癥是一種主觀不適感覺。有調查研究顯示一部分飛蚊癥患者確實存在明顯的煩惱體驗,“飛蚊”會對視覺質量產生負面影響[4]。Kim 等[5]發現飛蚊癥患者存在心理困擾,且與癥狀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另外,基于時間權衡法和標準博弈法的飛蚊癥患者效用值測量研究顯示,飛蚊癥患者的平均效用值與之前報道的一些存在眼底疾病(如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或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的平均效用值相當。患者愿意冒11%壽命損失風險和7%失明風險來擺脫飛蚊癥的困擾,年輕患者的治療意愿比年長者更強[4]。盡管大家普遍認為絕大多數患者會逐漸適應飛蚊癥,亦或玻璃體混濁會逐漸吸收,但一些患者在長期隨訪中仍表示很難對其適應[4]。
盡管飛蚊癥可引起視覺障礙,但臨床上多數時候仍以保守觀察為主[6]。當飛蚊癥持續存在并對患者的視覺、生命質量和心理健康產生嚴重影響時應給予治療。
2 治療方法的利弊
包括含碘類藥物在內的飛蚊癥藥物治療因療效不確切而意義不大,目前針對飛蚊癥的主要治療方法是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或玻璃體切除術(pars plana vitrectomy,PPV)。PPV 是通過手術將玻璃體全部或部分切除,可有效地切除玻璃體混濁,療效確切,患者滿意度基本在90%以上[7]。而激光玻璃體消融術則是利用納秒級激光電離作用將玻璃體混濁汽化或從視軸區移除,具有簡單易行、無痛、無創口的優勢。既往研究報道顯示,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玻璃體飛蚊癥的有效率達50%~77%[8-12]。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報道主要研究的是激光治療最具優勢的Weiss 環型“飛蚊”。
在安全性方面,飛蚊癥PPV 術后并發白內障、醫源性裂孔和視網膜脫離均有報道,其他術后并發癥如青光眼、黃斑囊樣水腫、視網膜前膜、玻璃體積血、黃斑裂孔等發生率極低,眼內炎也有個例報道[7]。白內障是飛蚊癥PPV 術后最常見并發癥,發生率高達30%以上[7],前部玻璃體切除后晶狀體周圍環境改變可能是白內障發生的重要原因[13]。僅行核心玻璃體切除對前部玻璃體進行保留可使術后白內障發生率顯著下降[14]。醫源性裂孔和視網膜脫離是嚴重的并發癥,在玻璃體手術中有一定發生率,相關因素包括疾病種類(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易發生)、術式(常規比微創)、是否伴有PVD 以及是否有晶狀體眼等。微創手術中使用微套管可減輕器械進出時對玻璃體直接牽拉,25G玻切頭抽吸口距末端近不易發生醫源性裂孔。有學者認為,飛蚊癥手術中發生醫源性裂孔與PVD 制作相關,僅切除核心玻璃體可消除這一危險因素,但殘余玻璃體可能使飛蚊癥復發[15]。目前,僅針對飛蚊癥而采取PPV 治療在歐美國家流行,在我國并非常態。
盡管目前已證實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隨訪時間通常未超過1 年,術后眼底檢查中未結合鞏膜頂壓來排除周邊部裂孔,也未做眼底熒光血管造影或光學相干斷層成像來排除后極部視網膜損傷;另外,入選的患者也存在類型單一、樣本數少等不足。有報道飛蚊癥激光治療中可發生晶狀體后囊損傷、視網膜少量出血、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脫離,其他并發癥包括開角型青光眼,原因可能與玻璃體混濁物碎屑、巨噬細胞和炎癥細胞阻塞小梁網有關,也不排除小梁網內皮細胞在激光治療時受到沖擊受損[16]。但總的來說,目前報道上述并發癥的總體發生率不到1%[17]。同時,無痛、無創口、門診可行和治療成本低符合大部分患者的訴求,于是近年來在我國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由于臨床醫師對于激光治療的適應證標準把握不一,臨床治療效果差異較大。因此,行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前,需對玻璃體“飛蚊”的特點及干預時機進行嚴格把握。
3 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的治療要點
3.1 適合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的玻璃體“飛蚊”類型 Weiss 環的出現提示完全PVD,常位于視盤周圍。一些研究認為,部分患者的Weiss 環之所以易在視網膜上投影,是因為發生過程中伴有盤周組織的撕脫[18]。Weiss 環型“飛蚊”是既往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研究最多的飛蚊癥類型,有效性得到了一定的證實[8-12]。
玻璃體后界膜抬起是PVD 的又一特征。有研究在脫離的玻璃體后界膜中發現了Ⅳ型膠原,其最可能的來源是視網膜內界膜[19]。所以,有學者認為伴隨玻璃體后界膜脫離的板層內界膜引起了入眼光線散射[20];此外,脫離的玻璃體后界膜會向眼球前方移動,因面積縮窄發生折疊,也可能形成視網膜投影[21]。此種類型“飛蚊”多呈“云霧狀”或“窗簾狀”,面積較大,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效果欠佳[12]。
玻璃體膠原纖維發生聚集是玻璃體液化所致,老化和近視是最常見的因素。此種類型的“飛蚊”多呈“網狀”或“線團”狀,分布廣泛,臨床中即使行多次激光治療也難以將其完全汽化消融[21]。根據飛蚊癥的數學模型可以知道,越貼近視網膜的“飛蚊”所形成的投影顏色越深[22]。臨床中,正是這些位置靠后的“飛蚊”造成了患者視覺的主要干擾,所以可以有針對性的對中軸、位置稍后的玻璃體混濁進行激光消融治療。根據效果進行分次激光治療是一個不錯的選擇[23]。
對于在年輕人中常見單個可顯影的小“飛蚊”,激光治療需謹慎。此種較小的膠原纖維聚合物之所以能在視網膜上投影,是因為其距離視網膜表面足夠近,又多位于后極部,因此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的風險較高。此類“飛蚊”行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的臨床研究較少,臨床激光干預需要仔細認真評估。
高度近視眼的“飛蚊”經常同時含有PVD 相關混濁物和玻璃體膠原聚合物。“飛蚊”常常較粗大、致密且數量較多,汽化所需的激光能量通常較高。此類眼的另一個特點是眼軸較長,常伴有后鞏膜葡萄腫,操作時存在即使激光機幾乎貼到接觸鏡表面仍無法對后部混濁物聚焦的情況[21]。此類患者的激光治療效果一般較差[9,12]。對于執意要求激光治療的患者,可以有針對性的對中段中軸部玻璃體混濁進行治療。
3.2 適合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的玻璃體“飛蚊”空間位置 玻璃體混濁可位于玻璃體腔的前段、中段和后端,也可位于中軸部和周邊。雖然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對于前中后段的玻璃體混濁均可實現汽化消融,但位置靠前的玻璃體混濁在視網膜上的投影一般面積彌散且灰度偏淡[22],所以其一般不是飛蚊癥的元兇;此外,在既往文獻報道中,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誤傷晶狀體后囊并不罕見[24-28]。所以,建議將激光的靶目標聚焦于中后段的玻璃體混濁。對于位置貼近視網膜的“飛蚊”,要格外小心,尤其是背景位置為黃斑區或視網膜大血管時。筆者會診中發現,有患者因視網膜大血管的YAG 激光誤傷發生了大量玻璃體積血。既往多個研究對于玻璃體混濁治療距離的要求只是簡單描述需離視網膜3 mm、離晶狀體后囊膜5 mm 以上[8-12],但在激光的實際操作中,準確把握“飛蚊”的空間位置是較難的,視網膜背景成像虛化和參考自然晶狀體厚度是一個很實用的方法[21]。或許,未來開發一款可實時測量玻璃體“飛蚊”空間位置的軟件可大大提高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飛蚊癥的安全性。
對于“飛蚊”位置周邊的玻璃體混濁,在激光操作中通過患者的眼位配合是可觀察到的,但不推薦對其進行激光治療,主要由于:(1)位置周邊的玻璃體混濁通常不是患者“飛蚊”視覺困擾的主體;(2)行周邊玻璃體混濁激光消融時,存在焦點與激光爆點不一致的現象;(3)周邊玻璃體混濁物的空間位置評估較中軸部更加困難,治療風險增加。
3.3 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的時機 PVD 相關的玻璃體飛蚊癥一般都是突發起病的,患者通常可以明確告知臨床醫師患病時間。隨著PVD 脫離范圍的擴大,“飛蚊”會逐漸向前方和下方移動。所以,此類飛蚊癥有一定的癥狀自發緩解概率。既往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臨床評估研究中,通常選擇3~6 個月癥狀無法緩解的飛蚊癥患者[8-12]。在筆者前期平均約24個月的觀察研究中發現,約40%PVD 型飛蚊癥可自發緩解,平均時間約18 個月[29]。因此,筆者認為“飛蚊”癥狀持續3~6 個月以上并非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的嚴格適應證;對于無法耐受飛蚊癥要求癥狀快速緩解的患者,如果“飛蚊”特征符合激光治療要求,可在詳細排查視網膜不穩定變性、裂孔、脫離后提早治療。
膠原纖維聚集物相關飛蚊癥的患者一般很難準確描述發病時間,通常是不經意間發現眼前“飛蚊”。此類飛蚊癥的特點是癥狀長期穩定,難于自發緩解。所以,治療與否主要取決于患者的訴求及“飛蚊”的特征。3.4 單脈沖模式或多脈沖模式 在筆者前期的YAG激光玻璃體消融術能效研究中,發現相同脈沖總能量下,單脈沖模式的激光能效范圍最小,所以筆者推薦常規用單脈沖模式進行玻璃體消融治療,可以提高治療安全性[30]。對于游走的移動靶“飛蚊”,可以選擇多脈沖模式以提高治療效率。此外,在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過程中,經常有快速連續的激光激發操作,頻繁的多脈沖模式操作可能會使激光機溫度升高而出現“卡殼”現象。
3.5 特殊晶狀體狀態的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 有晶狀體眼人工晶狀體植入手術是當下頗為流行的一種近視矯正方法,尤其對于具有準分子激光手術禁忌的高度近視眼患者。但眼內植入一枚“凹透鏡”會讓裂隙燈下視網膜成像放大,玻璃體可觀察空間縮窄,讓本就存有難度的高度近視眼“飛蚊”激光消融治療變得難上加難[19]。
白內障術后的視力提高可以讓術前不明顯的“飛蚊”變得“嚴重”起來。同時,白內障術后的玻璃體前移會加速PVD 的發生,引起飛蚊癥[31]。因此,飛蚊癥在很多人工晶狀體眼患者中存在。因為無需擔心自然晶狀體的損傷,很多激光醫師偏愛對此類玻璃體“飛蚊”進行消融治療。囊袋攣縮和后發性白內障會影響玻璃體“飛蚊”的觀察,可能需先行處理,多焦點人工晶狀體對激光的操作影響不大。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晶狀體眼視網膜脫離的發生危險系數是自然晶狀體眼的4 倍[32],所以治療前需仔細檢查周邊視網膜,尤其是上方象限。
4 總結
不會有患者因單純的玻璃體飛蚊癥而喪失視功能,所以筆者認為飛蚊癥的治療在多數情況屬于“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治療安全永遠都要放在第一位。治療主要面對的應是受飛蚊癥困擾的患者,而非針對存在玻璃體混濁的征象。因此,在對飛蚊癥采取干預前要詳細進行臨床評估,制定治療方案。若選擇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需嚴格把握臨床適應證。行YAG 激光玻璃體消融術治療前需要判斷哪些玻璃體混濁是患者癥狀的主要元兇,同時評估哪些“飛蚊”是可通過激光處理的。最后,關于飛蚊癥治療的相關共識及指南也亟待制訂和推出。
(本文由浙江省醫學會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