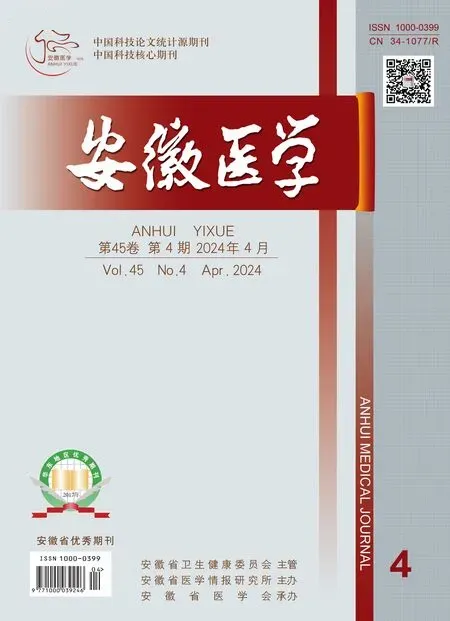乳腺癌乳房切除術后即刻重建的研究進展
黃 毅 程 騰 吳曉東 胡 勇
乳腺癌是目前全球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2020年全球新發乳腺癌230 萬例[1]。預計2022年中國新發乳腺癌人數超過42 萬例,美國新發乳腺癌人數超過25 萬例[2]。當前乳腺癌的治療是以手術為基礎的綜合治療,乳房原發病灶的切除無法豁免,由此帶來外觀的毀損伴隨患者終生[3]。隨著乳腺癌分子機制的研究進展,乳腺癌患者生存時間不斷延長,對生存質量的要求也不斷提高。
患者自身的心理負擔、腫瘤安全性是很多患者選擇全乳切除的原因[4]。乳房重建的創新為患者提供了美學和腫瘤安全的治療選擇,外科干預向重建方法的過度,可以確保美學滿意度與腫瘤安全性相結合[5]。修秉虬等對中國110 家醫院研究發現87.3% 已開展乳房重建手術,2017年已開展重建手術醫院中,全乳切除術后總重建比例為10.7%(6 534/61 099),所有重建方式中即刻重建占67.6%(4 417/6 534),延時重建占32.4%(2 097/6 534)[6]。同期美國乳腺癌術后即刻乳房重建率已達54%[7]。即刻重建首選最多的為假體一步法,占36.5%,其次為假體一步法乳房重建(聯合補片),為27.1%;第三為擴張器-假體兩步法假體乳房重建19.8%,背闊肌重建占15.6%,腹部皮瓣等其他皮瓣占比1.0%[6]。臨床中乳房重建按重建手術時機分為即刻乳房重建(immediate breast reconstruction,IBR)、延期乳房重建(delayed breast reconstruction,DBR)和延期-即刻乳房重建。本文對乳腺癌術后即刻乳房重建作一綜述。
1 術前計劃
與乳房切除術相比,IBR 可以提供更好的美容效果和更高的生活質量,而不會影響腫瘤學安全性。法國140 904例乳腺癌乳房切除術的觀察項研究發現IBR 率平均為16.1%,并且在研究期間逐年增加[8]。影響IBR 的重要乳腺外科醫生相關因素是預期的放射治療、較大的年齡和較高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9]。因此應在初次會診時評估患者的期望和整體健康情況,健康、不吸煙的中小型乳房以及重建后具有相似的乳房大小,是IBR 的理想人選。IBR 的禁忌癥包括既往接受過乳房放療或已有瘢痕對乳房切除術后皮瓣灌注產生不利影響的患者,病態肥胖、未控制的糖尿病、灌注不良或薄的乳房切除皮瓣或晚期腫瘤疾病的患者[10]。需要仔細考慮的變量包括患者的年齡、身體質量指數、既往病史(如吸煙、高血壓病、糖尿病)、既往手術史(例如活檢、乳房部分切除術、隆胸手術)、腫瘤的范圍、腋窩淋巴結的受累、乳房切除術的重量和所需乳房的大小。體格檢查應重點評估乳房的大小、下垂度、對稱性、既往瘢痕、皮膚變化、乳頭-乳暈復合體的位置和胸壁形態[11]。
2 即刻乳房重建方法
2.1 自體組織重建 基于皮瓣的乳房重建是使用微血管游離皮瓣移植或帶蒂皮瓣移植進行的。皮瓣重建與假體重建對比具有一定優勢,輔助放療期間并發癥發生幾率較低,并具有更好的長期美學效果[12]。自體組織重建由于其美容效果佳、可避免植入物相關并發癥的優勢,成為乳房重建的主要方式之一。自體組織重建使用皮瓣,取自供體區域組織,在適當成型后用于重建乳房區域,這種技術可以獲得與原始乳房相似特征的自然乳房外觀,并適用于放療區域。自體組織重建相比于植入物重建早期并發癥發生率較高,主要包括皮瓣壞死、脂肪壞死、創面感染、血清腫等[13]。
目前臨床中使用的自體組織皮瓣根據皮瓣組織是否帶有原供血血管分為帶蒂組織皮瓣和自體組織皮瓣。帶蒂組織皮瓣以背闊肌肌皮瓣(latissimus dorsi myocutaneous flap,LDMF)、單蒂或雙蒂的腹直肌肌皮瓣為主(transverse recuts abdominis myocutaneous flap,TRAM)。游離組織皮瓣包括游離腹壁下深動脈穿支皮瓣(deep inferior epigastric perforator flap,DIEP)、腹壁淺動脈皮瓣(superficial inferior epigastric artery flap,SIEAF)等。
2.1.1 背闊肌皮瓣 LDMF 是最早應用于乳房重建的肌皮瓣組織,血供主要來源于胸背動脈和肋間血管,血管蒂解剖位置相對恒定,由背部皮膚、皮下脂肪組織和背闊肌組成,LDMF 的血供豐富,皮瓣成活率高,游離皮瓣后將LDMF 從胸廓后方轉移至胸廓前方進行乳房重建,背部供區切口皮膚直接關閉。胸背血管的解剖是不必須的,但胸背神經需要被識別和分割以防止潛在的術后不自主肌肉收縮,如果皮瓣旋轉受到限制,可分開前鋸肌的血管分支,皮瓣通過腋窩隧道下至乳房缺損區域[14]。由于LDMF 相對組織量較少,存在一定局限性,適用于背部皮膚肌肉組織豐富和乳房較小的患者,在DBR 中也常與植入物聯合使用。因為腹部手術、腹部疾病等問題,不能采用腹直肌肌皮瓣進行乳房重建的患者,首選背闊肌肌皮瓣重建乳房。LDMF 乳房重建手術相對簡單,供區損傷不大,手術操作簡單方便,恢復時間較快,可以有效降低供區并發癥的發生率[15]。
2.1.2 單蒂或雙蒂的腹直肌肌皮瓣 TRAM 是最常見的帶蒂肌皮瓣,血供來源于腹壁上下動脈,由腹直肌表面皮膚、皮下脂肪組織和腹直肌組成,游離后通過腹部到乳房缺損處的皮下隧道轉移至胸部進行乳房重建,腹部供區進行關閉并重新固定臍部位置。TRAM 體積相對LDMF 更大,適用于乳房較大患者,特別適用于不適合保乳又不希望失去乳房有美容需求的患者,或者乳房切除術后無法直接縫合的大面積缺損的修復(局部晚期患者)。尤其適合腹部脂肪組織比較多,要求自體組織重建乳房的患者。手術禁忌為體型過瘦或過胖、腹部瘢痕、術后腹壁功能無法代償[16]。
2.1.3 游離腹壁下深動脈穿支皮瓣 DIEP 僅游離皮膚和皮下組織,將腹壁下動靜脈與內乳動靜脈行血管吻合重建皮瓣血供,DIEP 保留腹直肌前鞘膜、腹直肌和大部分肌間神經,避免了TRAM 損傷大,術后并發癥多的缺點[17]。但術式耗時較長,需要顯微外科技術進行血管吻合,術式成本相對較高。適用患者包括乳房較大需提供大量皮瓣組織,供受區血管條件良好不能接受乳房假體重建;假體或背闊肌肌皮瓣等方式乳房重建失敗,腹部皮膚松弛,皮下脂肪組織豐富以及有生育需求或對腹壁功能要求較高。
2.1.4 腹壁淺動脈皮瓣 SIEAF 切取腹壁淺層血管作為皮瓣的血管蒂,不需切開腹壁深層組織,完全保留了腹壁的完整性,因此術后幾乎沒有腹壁不對稱、腹壁薄弱和腹壁疝發生。但SIEA 血管的變異較多,血管走行不恒定,對皮瓣切取操作的要求較高;同時SIEA 血管的管徑通常較細,容易出現吻合血管管徑不匹配的情況,對于顯微血管吻合技術的要求也更高;另外,SIEA 血管蒂通常較短,皮瓣擺放的選擇余地較小,乳房塑形的難度也較大。因此腹壁淺動脈檢測、SIEA 皮瓣評估是目前選擇患者的主要因素[18]。
2.2 植入物重建 基于植入物的乳房再造是一種安全的方法,具有良好的結果、較低的發病率和較短的手術時間[19]。植入物重建既往多用于延期-即刻重建,隨著保留乳頭乳暈組織皮下腺體切除手術(nipple-sparing mastectomy,NSM)的普及,即刻植入物重建適用群體越來越多。一般適用于皮膚缺損較小、皮下組織厚度足夠,乳房尺寸較小的患者,具有足夠皮下層的血管化良好的乳房切除術皮瓣被一致認為是實現成功的關鍵,腫瘤累及皮膚或保留乳房皮膚不足是相對禁忌[20],外科醫生的術中判斷皮瓣血供情況對植入物重建成功的至關重要,以最大程度減少乳房切除皮瓣壞死的機會。根據假體植入的層次可以將其分為胸肌前乳房重建和胸肌后乳房重建。
2.2.1 胸肌后乳房重建 胸肌后乳房重建是目前最常使用的即刻重建方法,將假體放置于胸大小肌間,通過胸大肌進行假體覆蓋,并可利用周圍肌肉或筋膜協助增加假體表面的覆蓋,形成肌下袋,避免假體直接暴露于切口下方,減少包膜攣縮、假體外漏、切口感染的風險,常使用的覆蓋皮瓣包括胸大肌、前鋸肌筋膜瓣、腹直肌筋膜瓣和背闊肌等。因胸大肌后方間隙空間有限,傳統手術將假體置入胸大肌后方存在較大限制,雖然周圍肌肉筋膜瓣聯合成型固定可以有效避免假體移位,但是假體下極無法充分擴展,很難呈現自然的乳房下皺襞形態。現今的補片技術使用對假體使用帶來巨大拓展,將補片與離斷的胸大肌下緣縫合,合理使用補片可以起到延展胸大肌的作用,減少對自體組織的損傷,保證假體的完整覆蓋包裹,對假體具有支撐效果,減少并發癥的發生。臨床常用補片包括脫細胞真皮基質(acellular dermal matrix,ADM)、鈦涂層聚丙烯網狀補片(TiLOOP Bra,德國科隆)。TiLOOP 補片具有良好的生物組織相容性,使用時下緣需反折并完全包裹假體,優勢在于價格較低,不增加并發癥,臨床上目前應用廣泛。ADM 補片下緣需要與胸壁縫合固定,ADM在增加符合條件的患者數量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在使用肌下植入物的即刻直接置入(Immediate direct-to-implant,DTI)乳房重建中,ADM 提供了對植入物下部和外側部分的覆蓋以及皮膚和植入物之間的初始強化。據報道,ADM 的好處包括降低植入物暴露和遷移風險、更令人滿意的乳房下皺襞形態、通過增加植入物口袋體積和消除對周圍肌肉(前鋸肌、腹直肌)或筋膜覆蓋的需要來減少術后疼痛[21],同時包膜攣縮的風險降低[22]。但是目前對TiLOOP 補片和ADM 補片在TDI 中的益處和風險仍缺少廣泛共識。
2.2.2 胸肌前乳房重建 胸肌前乳房重建是近年來乳房植入物重建探索方向,對比胸肌后組手術時間明顯縮短,主要并發癥減少,而亞組分析中,種植體移位、包膜攣縮和皮瓣壞死對比無差異[23]。植入物部分或者全部放置于胸大肌后方都不可避免出現因為胸大肌或其他覆蓋肌肉筋膜收縮造成乳房外觀變形,肌肉剝離也會帶來額外損傷。同時胸肌后植入假體,重建的乳房內側邊界受胸大肌內側邊界限制,并非正常乳房內側邊界,重建乳房的美學外形受到影響,胸肌前乳房重建在假體放置上不受固有肌肉的限制,因此胸肌前乳房重建更符合解剖生理,也不會增加周圍組織的損傷。既往胸肌前乳房重建因乳房切除術后殘留皮膚較薄并發癥較高難以開展,補片的應用可以最大可能減少相關并發癥,主要方法包括提前將ADM 或TiLOOP 補片植入皮下和胸肌表面,并在四周將其固定,與胸大肌共同形成袋裝,將假體置入后進行關閉。也可以在體外將補片與假體完全包裹后置入胸肌前,固定假體-補片復合體的上緣和外側緣于胸壁。補片使用可以增加皮瓣強度,減少包膜攣縮風險。
3 修復手術
乳頭乳暈復合體(nipple-areola complex,NAC)重建至少在術后第3~6 個月通過局部皮瓣進行,紋身推遲到NAC 重建術后6 周[24]。自體脂肪移植是即刻重建后安全有效的二次修復[25]。自體脂肪移植可以通過矯正可見的植入物邊緣、與對側乳房的不對稱性以及腋前皺襞下方的上部外部缺陷來改善任何殘留的輪廓畸形。此外,由于存在所謂的脂肪源性干細胞,脂肪移植物顯示出超越簡單填充能力的再審潛力和治療效果。脂肪來源的干細胞可以分化成多個細胞譜系并分泌旁分泌因子,因此血管生成和傷口愈合能力大大增強,導致更高的脂肪移植存活率以及真皮和皮下組織再生[26]。此外自體脂肪移植已經被證明對重建乳房放療輻射中引起的軟組織損傷具有積極作用,脂肪移植物可以通過增強其血管供應來增厚皮下組織并改善受照射皮膚的質地[27]。但是英國一項單中心數據顯示IBR 術后二次修復手術對患者來說是一項較大的負擔,可能增加27.1%~74.1%的醫療費用[28]。
4 術后并發癥
每種重建方式都有其固有的不良事件風險,雖然IBR 和DBR 這兩種手術某些并發癥發生率不同,但都有類似的并發癥包括感染、血清腫、血腫、皮瓣壞死、包膜攣縮等。乳房手術后出現術后并發癥的患者的腫瘤學結果產生次要的不利影響,從而導致癌癥的復發風險增加[29]。繼發于術后并發癥釋放的生長因子可以在局部有絲分裂,并刺激遠離手術區域的部位的轉移擴散。研究報道術后腹膜感染患者腹膜液中細胞遷移和侵襲的能力增強,表明術后感染并發癥可以增加殘留腫瘤細胞的侵襲和遷移能力[30]。因此立即重建并發癥的發展會影響腫瘤學結果,從而可能導致乳腺癌的發生。但是也有研究發現手術區域發生的感染等并發癥對乳腺癌復發沒有顯著影響[31]。一項薈萃分析納入1 418 名患者,指出雖然并發癥組的復發率有所增加(n=66/382,17.3% 比n=92/1 032,8.9%),但并發癥和乳腺癌復發(breast cancer recurrence,BCR)之間無明顯相關性(17.3%比 8.9%,P=0.18),死亡率也無明顯差異(3.6% 比 2.3%,P=0.15)。IBR 組的傷口并發癥發生率更高,輔助治療時間顯著增加,但是這些并未轉化為接受IBR 的乳腺癌患者的不良腫瘤學結果[32]。可能支持原來的假設,即在原發腫瘤部位局部釋放的生長因子或炎性細胞因子,而不是全身循環的,可能相互作用并激活局部殘余或休眠腫瘤細胞,促進腫瘤的再生和轉移。
但是術后并發癥的發展可能會阻止患者接受額外的腫瘤治療,從而導致更嚴重的腫瘤學結果。即刻乳房重建本身不會推遲輔助治療,術后并發癥可能會導致開始治療的顯著延遲,這也可以作為一個強大的混雜因素。鑒于傷口裂開和乳房切除皮瓣壞死可能與復發相關,因此有必要通過丟棄灌注欠佳的組織來預防這些傷口并發癥[33]。
5 綜合治療的影響
5.1 新輔助治療 新輔助放化療可以僅行早期評估治療反應,指導輔助治療的進行如TDM1。新輔助放化療后接受即刻乳房重建手術并不常見,但是這種逆向序列治療侵襲性、非轉移性乳腺癌患者在近年來也逐漸增多。目前擔心的新輔助治療后會增加IBR 的手術相關并發癥如感染、血清腫等。一項3 249 名IBR患者的薈萃分析顯示,NAC 并未增加IBR 術后并發癥的風險(RR:0.91,95%CI:0.74~1.11,P=0.34),包括血腫、血清腫或傷口并發癥的發生率[34]。韓國一項回顧性研究納入609例接受新輔助化療后接受IBR 的乳腺癌患者,分析局部區域復發(local recurrence,LRR)在中位隨訪時間63 個月下累積發生率為10.8%,多因素分析顯示NAC 后高Ki67、組織學分級高和淋巴血管侵犯是LRR 的危險因素[35]。新輔助放療一度被認為可能是IBR 的相對禁忌,但一項基于傾向性匹配評分分析指出接受新輔助放化療的患者接受IBR 的比例更高,而并發癥發生率沒有增加,新輔助在改善病理完全緩解和生存的趨勢,同時有助于改善IBR 的使用[36]。日本593例接受IBR 的研究顯示NAC 組的手術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AE)顯著高于非NAC 組(35%比22%,P<0.05),而腋窩淋巴結清掃是最有影響的危險因素,NAC 并未確定為IBR 患者手術AE 的危險因素,兩組患者分期存在差異,因此NAC 雖然可能導致患者術后AE 增加,但是它不影響術后治療,IBR 仍適用于接受NAC 的患者[37]。
5.2 輔助化療 重建術后輔助化療目前探討的重點在于重建是否會影響輔助化療的開始時間,從而對患者復發率造成影響。645 名患者中的研究發現186 名IBR 患者和459 名非IBR 患者在化療開始時間存在差異,與單純乳房切除術相比,IBR 顯著增加了術后并發癥的風險,術后并發癥是延遲開始化療的重要危險因素[38]。國內天津腫瘤醫院研究發現即刻乳房重建組和改良根治組患者的總并發癥發生率無明顯差異,但即刻乳房重建組患者二次手術的發生率高于改良根治術組,尤其是化療開時候,即刻乳房重建延長患者術后輔助化療開始時間(the time to adjuvant chemotherapy,TTC)[39]。但是美國一項458 名Ⅰ~Ⅲ期接受IBR 的乳腺癌患者研究在中位隨訪時間7.6年結果雖然顯示出現并發癥組患者的輔助治療時間延遲(52 天 比 41 天,P<0.001),但兩組患者的復發率無明顯差異[40]。更高質量的Ibra-2 研究在76 個中心招募2 540 名患者,結論指出IBR 不會導致臨床上顯著延遲輔助治療,但術后并發癥與治療延遲有關。需要采取盡量減少并發癥的策略,包括仔細選擇患者,以改善患者的預后[41]。同時化療時機也并未增加接受IBR 患者手術部位感染的幾率[42]。荷蘭一項6 300 名患者的傾向性匹配評分結果顯示乳房切除術后IBR 在6 周內略微降低了接受輔助化療的可能性,但在9~12 周內沒有,因此乳房切除術后需要輔助化療不是患者接受IBR 的禁忌癥[43]。
5.3 輔助放療 在一項回顧性匹配隊列研究中對1 247 名患者進行回顧性匹配隊列研究,確定20 名IBR 患者和40 名DBR患者,接受PMR 后兩組患者早期并發癥無明顯差異,晚期并發癥中IBR 組的脂肪壞死率(60% 比12.5%,P<0.001)和皮膚攣縮率(60%比2.5%,P<0.001)高于DBR 組,指出放療可能會導致IBR 后長期的皮瓣相關不良后果[44]。而一項匯聚3473例患者的薈萃分析顯示,IBR 組相對DBR 組患者術后輔助放療包括脂肪壞死(14.91% 比8.12%,P=0.076),皮瓣丟失(0.99% 比1.80%,P=0.295),血腫(1.91% 比1.14%,P=0.247),感染(11.66%比4.68%,P=0.155)和血栓形成(1.51% 比 3.36%,P=0.150)并發癥的發生率無顯著增加,而血清腫(2.69% 比10.57%,P=0.042)并發風險明顯改善[45]。
6 總結
2022年癌癥統計數據顯示歐美國家約60% 的新診斷患者接受保留乳房手術,20%~40% 的患者選擇全乳切除,國內保乳患者比例相對較低[46]。重建手術可以幫助這些失去乳房的患者。與傳統的延期、即刻-延期重建相比,IBR 具有幾個潛在優勢,包括操作簡單、避免第二次手術和不需要組織擴展。事實上,由于術后相關治療措施的影響,延期重建平均在放療6~12個月進行[47]。獲得最終結果所需要的這段時間對于許多患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IBR 意味著達到最終重建的時間更短,這減少了臨床就診次數和感知的殘缺感,有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然后IBR 有相當多的術后并發癥,例如乳房切除術后皮瓣壞死,其范圍可能從輕微的表皮松解到全層壞死,而嚴重的術后并發癥可能會損害最終的美學效果,延長恢復時間,降低患者的生存質量,并延遲輔助治療的實施,同時增加患者的經濟成本和醫療保健系統[48]。
鑒于良好的美學效果、與常規兩階段重建的共同優勢以及達到的患者滿意度,IBR 具有更多的吸引力。隨著皮瓣手術技巧的進步和ADM 補片的發展,已經看到從傳統的兩期乳房重建到即刻乳房重建的術式改變。雖然存在一定缺點,我們認為可以通過仔細選擇患者和嚴格遵守手術技術來克服這些缺點,同時,需要更大規模的比較研究、更明確的選擇標準和結果報告來制定合適的適應癥,以成功施行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