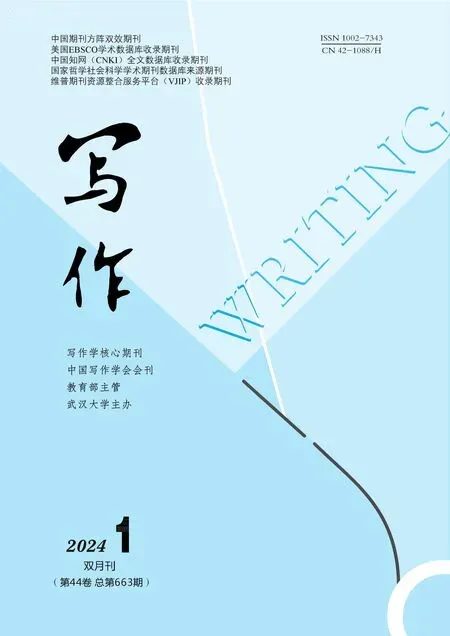顧城愛情詩的隱秘表達及成因探析
賴靜怡 謝君蘭
顧城是朦朧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其詩歌因空靈純凈、天真自然而又不失哲思的語言,曾引起巨大反響,也贏得了“童話詩人”的贊譽。為守護其童話世界的純真,顧城堅持用孩童視角進行寫作,將成人世界劃分為“你們”,詩歌中也極少出現成人世界的內容——例如愛情。學者張捷鴻認為:“在他留下的700 多首詩中,幾乎沒有愛情的內容……即使詩中出現女性形象,那也是抽象、隔膜的女性的幻想,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們的出現,只是作為童話詩中不可或缺的風景,比如小女巫之類的童話人物。”①張捷鴻:《童話的天真——論顧城的詩歌創作》,《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實際上,縱觀顧城創作的詩歌,其童話詩主要出現在創作早期(“自然的我”),而這部分只在顧城作品中占很小的比例;當褪去朦朧詩的歷史語境和對顧城先入為主的“童話”濾鏡后,筆者發現顧城的詩歌中有大量“非童話”的因素,其中不乏關于“愛情”的表達。對顧城的愛情詩進行細分,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較為直接地表達愛情,如《我好像……》《祭》《我是一座小城》《就在那個小村里》《是樹木游泳的力量》等。若僅計算這一類愛情詩,那么誠如前文所言,“愛情”在顧城詩歌中確實是罕見的題材。然而,顧城還有很大一部分詩作,是由其愛情經歷激發、影響創作而成的。此類較為隱秘——或是和常見愛情詩的表達不大相同,或只有詩中小部分內容提及了愛情,但同樣值得討論,不應忽視。典型的詩作有《別》《雪人》《遠和近》《泡影》《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門前》等,這一類愛情詩的特征為:情感表達不明顯,通常被歸為童話詩、寓言詩,需要通過文本細讀并結合創作背景進行闡釋。
目前學界對顧城這一部分愛情詩歌的研究仍有較大空間。研究者關注較多的是顧城早期的童話詩(如《生命幻想曲》),以及寫于20世紀80年代帶有政治意味的朦朧詩(如《一代人》),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多角度探討顧城“童話詩人”的創作特點;在激流島事件后,“詩人之死”引發了人們對顧城“童話”釋義的質疑,不少研究者發現了顧城詩歌童話外衣內部的矛盾和殘忍,認為文學史把80年代啟蒙的光明希望寄托在顧城身上,有意識地塑造其童話詩人的形象,并企圖借其詩歌中的童話特質治愈時代創傷,忽略和弱化了顧城詩歌的死亡、恐懼意識①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許永寧、粟芳:《文學史編撰與顧城童話詩人形象建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22 年第4 期;周思:《啟蒙的歧路——“童話詩人”之殤與1980 年代的“童話”話語》,《現代中文學刊》2022 年第1 期;張厚剛:《論顧城詩歌的“恐懼情結”》,《文藝爭鳴》2016年第8期。。虹影、趙毅衡總結說,在顧城的詩歌中,“死是一個貫穿主題,而且‘死’與‘童心’互相滲合”②虹影、趙毅衡編:《墓床——顧城謝燁海外代表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頁。,顧城的童心只是其擺脫恐懼的一種方式。值得肯定的是,進入新時期以來,學界的討論逐漸從顧城其人回歸到其詩,以更客觀全面的態度進行審視;同時也開始重視顧城后期的創作,出現了對顧城詩歌的整體性研究。然而,有關顧城愛情詩的研究熱度依然不高,學界主要從顧城的小說《英兒》去分析其愛情觀和感情心理③有關《英兒》的研究,參見謝冕、祁述裕、伊昌龍等:《絕筆的反思——關于顧城和他的〈英兒〉》,《小說評論》1994 年第3期;吳思敬:《〈英兒〉與顧城之死》,《文藝爭鳴》1994年第1期。,以顧城“詩歌”為基點去挖掘其愛情表達的文章非常少,也缺乏顧城愛情詩與同時期朦朧詩人愛情詩的比較分析。本文嘗試將顧城愛情詩與其創作風格、生命經歷進行聯系,對顧城的愛情詩作深入探討。
一、隱而幽現:顧城“愛情詩”文本表現形式與特點
顧城的詩歌語言純美而夢幻,他在詩中創造了一個浪漫的童話王國,里面的場景多是童心的港口、幻夢的湖泊、溫暖的花園;而這個王國的主角,往往是顧城所代表的“我”,或者是他所推崇的一切“自然”。大多數時候這個王國是封閉的,沒有現實的來客,也沒有黑暗和污穢,只偶爾會有孩童思考生命時多愁善感的情緒,這種封閉的源頭和顧城一再強調的自己的童年經歷有關。1967 年,12 歲的顧城隨父親顧工下放到山東廣北一個部隊農場,并在那里度過了五年。在顧城的回憶里,“那里的天地是完美的,是完美的正圓形……當我在走我想象的路時,天地間只有我”和“一種淡紫色的草”④顧城:《學詩筆記》,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895-898頁。。可以發現,顧城作詩強調忠于內心,他的詩歌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其生命體驗的復雜性,即使這段記憶很大程度上存在人為美化的嫌疑。顧城認為:“詩和生命是一體的……詩一步步由生活的過程趨向生命。”⑤顧城:《從自我到自然——演講錄之一》,《顧城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86頁。當研究者談起顧城,恐怕無法做到繞過其人而單論其詩,因為顧城部分詩作的形成無疑和他與妻子謝燁、情人英兒這兩段濃墨重彩的感情生活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即便顧城基于他的價值觀和詩歌追求,努力在作品中回避有關“愛情”“欲望”的描寫,但他“詩即生命”的詩學理念,使其詩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近乎等同于詩人本身。有了此前提,本文嘗試將詩人的人生經歷作為對其朦朧詩的理解基礎方可成立。張清華認為顧城是精神現象學意義上的詩人,寫詩屬于一種精神性的自傳⑥張清華:《朦朧詩:重新認知的必要和理由》,《當代文壇》2008年第5期。;那么,顧城源于生命的寫詩沖動便一定會使他記錄對愛情的感受。
(一)表現形式:從稱謂“你”窺察起
顧城愛情詩最明顯的痕跡是“你”的出現。上文提到顧城的童話世界很少有外界的介入,“你”的到來讓這個看似平靜的王國有了新的景象。“你”是誰?筆者總結有三種情況。在一些詩歌中,“你”有具體所指,如《給我的尊師安徒生》《給我逝去的老祖母》里,“你”特指安徒生和祖母;而在《小巷》《我們去尋找一盞燈》等詩歌里,“你”的指稱往往是象征性的。如《小巷》:
你拿把舊鑰匙/敲著厚厚的墻①顧城:《小巷》,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91頁。
此處的“你”可以泛指所有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人。本詩的最初版本為:“我用一把鑰匙敲著厚厚的墻”②顧城:《小巷》,《文匯月刊》1981年第6期。,可見此詩中的“我”和“你”可以相互替換而不影響詩歌主旨。
《我們去尋找一盞燈》中,“我”和“你”是一種對話關系。“我”要去尋找一盞燈,“你”說“它在窗簾后面”。“它在一個小站上”。“它就在大海旁邊”,并點出“所有喜歡它的孩子都將在早晨長大”③顧城:《我們去尋找一盞燈》,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63頁。。從詩歌充滿童趣的語言和內容看,這個“你”的身份極有可能是個孩子,亦或是顧城內心人格的表現,借虛化的“你”之口表達對生活的理想化追求。
然而有一種“你”,明顯和前面這兩種表達有所不同。如《雪人》:
在你的門前/我堆起一個雪人/代表笨拙的我/把你久等/你拿出一顆棒糖/一顆甜甜的心/埋進雪里/說這樣就會高興④顧城:《雪人》,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13、314頁。
這首詩的語言并不晦澀,與其將其牽強附會為“寓言故事詩”,不如遵循最直接的閱讀感受——這是一首愛情詩。“雪人”代表了“我”,“笨拙”體現了“我”久等“你”的癡情和期待。和前文的兩種“你”相比較,我們會發現此處的“你”并不是詩人預設好的角色,不是詩人內心的傳話筒,也并非理想、自由等符號的化身。“你”是脫離詩人主觀意識行動的,其一言一行影響著“我”的情緒:
雪人沒有笑/ 一直沒作聲/ 直到春天的驕陽/ 把它融化干凈/ 人在哪呢?/ 心在哪呢?/小小的淚潭邊/只有蜜蜂。⑤顧城:《雪人》,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13、314頁。
“你”給了雪人一顆甜甜的心,但雪人卻沒有笑,因為“我”不想做靜默守護的雪人,而是渴望與“你”相擁相伴。“春天的驕陽”喻指兩人間的阻礙,雪人的堅持最終被“融化干凈”,但那顆甜甜的心已融入他的身體,化為淚潭后引來了蜜蜂。這首詩寫于1980 年2 月,顧城是在1979 年7 月,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車上與謝燁相識,隨后便對其展開了猛烈的追求。“雪人”融化自我的戀愛模式,也可以視為顧城后來行為的預示:因謝燁家人不同意顧城的求婚,顧城索性在謝燁家門口一個棺材樣子的箱子里連睡了幾天。不管是從詩歌的創作時間背景,還是基于詩歌文本的分析,不難聯想到詩人在這首詩里流露出對愛情的執著。
在與謝燁戀愛期間(1979—1983),顧城還創作了很多表達自己癡情守望、愛而不得、戀情受阻的苦悶詩句,如1980年6月《小詩六首》的《遠和近》:“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①顧城:《小詩六首(六首)》,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70、171頁。;《泡影》:“我像孩子一樣,/緊拉住漸漸模糊的你。/徒勞地要把泡影,/帶回現實的陸地”②顧城:《小詩六首(六首)》,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70、171頁。。如1981 年1 月創作的《土地是彎曲的》:“土地是彎曲的/我看不見你/我只能遠遠看見/你心上的藍天”③顧城:《土地是彎曲的》,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95頁。,此時顧城和謝燁相隔兩地,顧城患得患失,“彎曲的土地”既指兩人距離上的遙遠,也形容戀愛之路的曲折。除開這一時期,1985年創作的《是樹木游泳的力量》更是直接談到了愛情:“我們看不見最初的日子最初,只有愛情”④顧城:《是樹木游泳的力量》,《顧城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頁。。綜上所述,“顧城的詩歌里幾乎沒有愛情”的說法恐怕是不恰當的,其詩中出現的“第三者”“女性形象”也并不全是為其童話詩服務的背景板;相反,有相當一部分詩歌是以“我”愛慕的“你”為主角,隱秘地表達詩人的愛情觀和相戀中的情感。
(二)表現特點:愛情與專制的潛在對話
顧城的愛情詩帶著初戀般的悸動和美好的童話色彩,語言空靈純凈,有意的克制,過分的含蓄。在愛情話語的表達上,顧城總是憂郁頹廢,甚至孱弱。當面對“自然”時,他寫出的是如《生命幻想曲》般開闊的詩句:
我行走著,/赤著雙腳。/我把我的足跡/像圖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進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類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鳴。⑤顧城:《生命幻想曲》,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3頁。
顧城少年時代在山東的河灘沙地上寫下這首詩,他曾說:“我確信了我的使命,我應走的道路——我要用我的生命,自己和未來的微笑,去為孩子鋪一片草地,筑一座詩和童話的花園,使人們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存儲東方會像太陽般光輝,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終都會實現”⑥顧城:《少年時代的陽光》,《卷一:別有天地》,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頁。。可見顧城在自己的童話王國里充滿自信:他有確定的目標、積極的態度、認為自己有能力控制這個世界。雖然有關自然題材的創作偶爾也會流露輕微的虛無情緒,但通常只是就“生命”“死亡”等宏大命題進行思考;顧城對生死向來報以坦然接受的態度,并不回避這類主題,而是深入探討其本質。然而對于愛情,顧城總是將“情欲”的一面摘得干干凈凈,極力避免在詩中描寫愛情的過程;他筆下的愛情也是簡單而理想化的,不涉及愛情本身,只捕捉那點游絲般的憧憬。
當我們將顧城詩中隱秘的愛情表達集中觀照時,顧城的另一個形象也隨之呈現——一面是夢幻童話里的“小王子”,另一面卻是封閉自我世界里專制獨裁的“暴君”。其愛情詩里,顧城的“凝視”無處不在,話語中透露出他對另一半專橫的占有欲望。《遠和近》中,“我”十分在意“你”的一舉一動,在“你”漫不經心看云的瞬間,“我”便敏感地認為這是一種分心,覺得“你”離我很遠了。這一“覺得”完全是“我”內心武斷的主觀感受,無關事實,也不容“你”去辯解。顧城不止一次在詩中強調“我”需要“你”的絕對關注,如《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里對愛人的想象:
我的愛人/她沒有見過陰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顏色/她永遠看著我/永遠,看著/絕不會忽然掉過頭去。⑦顧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顧工編:《顧城文選》卷1,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09頁。
詩里兩次強調“永遠”,還用了非常堅定的“絕”字,這種強硬的態度在顧城詩歌中較為罕見。向來追求夢幻和諧、內在人格孱弱的童話詩人,在談及想象中的愛人時卻表現強烈的控制欲,甚至帶有不服從便自毀的傾向。顧城的愛情詩,純潔卻并不純粹:看似唯美浪漫的示愛詩句,背后是專制懦弱的心靈。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以愛之名搭建的童話王國,實則是一種自私的牢籠。
二、內在特質:顧城人格與其愛情詩之關聯
顧城愛情詩之所以呈現上述特點,與顧城的人格特質相關。其人格的孱弱在很早便有所顯現,它表現為一種自我封閉的狀態,極力回避成人世界。顧城一直強調自己是個孩子,拒絕長大,即使婚后也不愿承擔責任。他不愿面對生活的壓力,一味沉溺于其理想的童話王國,“童話詩人”這一稱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這位天才詩人理所當然的保護傘。習慣性的逃避讓顧城的愛情詩缺少“進攻”的銳利,大多時候,他是以隱藏的“被守護者”身份出現的,如《南國之秋(二)》:
我要像果仁一樣潔凈/在你的心中安睡……/我要匯入你的湖泊/在水底靜靜地長成大樹①顧城:《南國之秋(二)》,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49頁。
單看這段文字,與其說兩人是戀人關系,不如說是一個孩子對母親的撒嬌。這種愛情觀畸同顧城的女性觀有很大聯系。在顧城的觀念里,世界分為兩類,一類是充滿了潔凈、自由的女兒性世界,一類是充斥強力哲學的男性世界。近乎于偏執的女性崇拜,令顧城始終厭惡自己的男性身份,他認為男性污濁、渣孽,要“用自己的混亂和黯淡來反襯女兒性的光輝”②顧城:《浮士德·紅樓夢·女兒性》,《你是前所未有的,又是久已存在的》,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頁。。對男性陽剛一面敬而遠之的顧城,自然不愿在詩中流露“我”強勢的男性氣質。在顧城的理解中,這樣的愛無甚問題,因為他對所有的女性都懷著“博愛”的態度。他將女性分為“女人性”“女孩性”“女兒性”,妻子謝燁“像湖泊一樣”寬容、溫和的性子,完美符合其對女人性的期待。顧城將女子天然的“母性”歸于他愛情的一部分,心安理得地享受,不去區分“丈夫”和“兒子”兩者身份權利和義務的不同,也就不用面臨自身角色的轉型陣痛。然而不管顧城如何模糊二者的界限,他自身是個成年男子的事實不會改變。男子所固有的欲望,與他對女性純潔的崇拜有所沖突,這種沖突使他在寫愛情詩時難以保持全然不諳世事的天真。顧城本人盡力在詩歌中隱藏、融合這一沖突,因此其對愛情的描寫總是表現得十分節制。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顧城性格中的“早熟性”。顧城常以自己是“任性的孩子”為由,希望博得對方永遠的關注,雖然有學者認為這是顧城對童年母愛缺失的心理補償,但筆者認為這種心理比“補償”更為復雜。顧城何其早慧敏感,他的詩之所以特別,正是因為很好地平衡了天真與深刻,看似簡單童稚的語言背后有著“沉默的深處”。顧城對“童心”是刻意維持的,并非其的像孩子般隨意寫就。通過《顧城哲思錄》和顧城的相關訪談,我們發現顧城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大眾意義上“天真爛漫”的詩人;相反他有相當理性、抽象、智慧的成熟一面。他在大眾媒體面前不厭其煩地解釋那頂奇特的帽子,且每次說法并不一致(比如有時說帽子是自己和外界的邊界,有時又說帽子是煙囪,不高興了可以用來出氣);在參加詩歌交流會時故意遲到,為了享受壓軸出場時所有人的掌聲;總是眨著懵懂雙眼,不善言辭的他,當年竟“躲在樹上,畫了一些神奇的解釋,哄得贊成或反對者都以為那幾句詩大有思想隱藏”①轉引自畢光明、樊洛平:《顧城:一種唯靈的浪漫主義》,《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原文《遠帆》,見老木編:《青年詩人談詩》,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1985年版。。我們有理由認為,顧城通過謝燁治療童年創傷,享受謝燁無微不至的照顧,并利用文學的創作,讓自己能心安理得地做生活上的巨嬰。然而,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做到無條件的、永遠專注地望著他,哪怕他是孩子、是天才詩人、是童話世界的王。如果“我的愛人”忽然掉過頭去,離開了“我”的注視范圍,等待她的是什么呢?激流島的慘案似乎已經給出答案,謝燁在那一刻看到了顧城世界里的“陰云”。
其三,顧城有著近乎偏執病態的“情感潔癖”。他對女性“純潔”的理解便很能說明:自顧自地將女性抬上圣潔的神壇,將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標簽化為女人性、女孩性、女兒性。女人性代表大度的慈母,女孩性代表活潑的情人,女兒性則是接近無欲無求的仙子。這種女性崇拜看似尊重女性,實則是對女性的一種“捧殺”:通過放大女性奉獻犧牲的一面,削弱女性的獨立人格,使其成為“理想女性”的刻板想象。顧城在《門前》描繪過一副和諧的畫面:
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②顧城:《門前》,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506頁。
這個場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舒婷的《致橡樹》:
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每一陣風過,/我們都互相致意,/但沒有人/聽懂我們的言語。③舒婷:《致橡樹》,《舒婷詩精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92-93頁。
舒婷在這首詩中抒寫了獨立女性理想的愛情觀,即兩人各自獨立而又共同成長。然而在顧城的愛情詩中,美好只存在于表面,內在卻對另一半的“純潔”作出極高的要求。顧城詩中出現過很多次“眼睛”,以這一意象為窗口,我們可以窺探到顧城眼里的理想愛人。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愛人的眼睛“是晴空的顏色”④顧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顧工編:《顧誠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09頁。;在《就在那個小村里》里,“你眼睛的湖水中沒有水草”⑤顧城:《就在那個小村里》,《顧城的詩顧城的畫》,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9頁。。可見,顧城心中的愛人美好到沒有一絲瑕疵。他對女性的潔癖在《島》中已然明顯:
有人愛花/有人愛人/有人愛雪/而我/卻愛灰燼的純潔⑥顧城:《島》,《顧城的詩顧城的畫》,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203頁。
顧城愛的是抽象的人,而非具體的人。凡是具體的人都有七情六欲、愛恨嗔癡,可顧城寧愿毀滅一切,留下灰燼,也要保存其理想中的“純潔”。舒婷身為女性,更能體會到女性處境的不易,她在《神女峰》中直言:“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⑦舒婷:《神女峰》,《舒婷詩精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頁。,充分表達了對女性欲望的正視。通過對比,不難發現顧城對女性、對愛情的偏激。到了后期,顧城認為女兒性是一種由女兒體現出來的精神,和性別本無關系,并非女人即有女兒性。可以想見,顧城痛恨男性而喜愛女性,不過是痛恨男性需要承擔的義務,更愿意用他臆想的女兒性“精神”來逃避現實世界的壓力。諷刺的是,他從未放棄過自己身為男性的權利。1988 年7 月,顧城和謝燁移居激流島,在《字典》一詩中寫到:
在有花的地方坐下/一切將從這里開始/我的妻子要為我生育部族①顧城:《字典》,《顧城的詩顧城的畫》,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頁。
詩歌中流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以“我”為尊,要求妻子為他生育。回顧顧城詩中的“你”,“我”的愛人,從未擁有過“我”平等的對視。顧城實際上并不理解女性,更遑論給予女性真正想要的“愛”。更為遺憾的是,或許顧城終其一生也并未學會如何愛人。仿佛是預言般的,顧城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中已經想到了自己的結局,沒有家、沒有同行者、只有虛幻的夢:
最后,在紙角上/我還想畫下自己/畫下一只樹熊/他坐在維多利亞深色的叢林里/坐在安安靜靜的樹枝上/發愣/他沒有家/沒有一顆留在遠處的心/他只有,許許多多/漿果一樣的夢/和很大很大的眼睛②顧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10頁。
三、外在機制:“童話詩人”的生成與陰影
顧城的愛情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為“童話詩”“寓言詩”所掩蓋,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由三點造成:朦朧詩時期特殊的閱讀機制、同時期詩人愛情詩的突出以及童話詩人的形塑。以顧城的《遠和近》被推上朦朧詩神壇這一事件為例,可以探尋該時期特殊的閱讀機制如何將這首詩的意義“朦朧化”,如何成功定格了顧城“童話詩人”這一身份,最后又如何反過來,形成遮蔽其愛情詩的龐大陰影。
傅元峰對朦朧詩的定義為:“‘朦朧詩’的‘朦朧’并非是詩學效應,而是歷史事件。”③傅元峰:《孱弱的抒情者——對“朦朧詩”抒情骨架與肌質的考察》,《文藝爭鳴》2013年第2期。從時代背景來看,朦朧詩誕生于非常時期結束后的空白期,其“朦朧”形成于歷史語境造成的閱讀障礙上。《遠和近》的主旨一直以來眾說紛紜,艾青認為“評論家也各人在做各人的文章”:從階級論出發認為這首詩用“遠和近的象征表現了物理距離和感情距離的對立,表現了對長期階級斗爭擴大化所造成的人與人關系異化的聲討,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向往”④艾青:《從“朦朧詩”談起》,李建立編:《朦朧詩研究資料》,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頁。;從英美新批評理論出發則認為這首詩的主題可以理解為靈與肉的對立和沖突,遠和近可以象征為現實/理想、實在/欲望、精神/物質等等⑤魏天無:《怎樣細讀現代詩歌——以顧城的〈遠和近〉為例》,《名作欣賞》2007年第1期。。詩人自己的解釋也頗有意思,稱“《遠和近》很像攝影中的推拉鏡頭,利用‘你’、‘我’、‘云’主觀距離的變換,來顯示人與人之間習慣的戒懼心理和人與自然原始的親切感。這組對比并不是毫無傾向的,它隱含著‘我’對人性復歸自然的愿望”⑥顧城:《關于〈小詩六首〉的信》,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900頁。。
有趣的是,這首詩很容易讀出“你”與“我”之間的曖昧意味。把《遠和近》放回到《小詩六首》組詩中去看,會發現組詩中有五首涉及“你”和“我”。在這些詩中,“你”是和“我”相互慰藉、相互依偎的對象;在《在夕光里》中,基本可以明確“你”就是“我”的戀愛對象。在眾多主流解讀中,卻并無人提及這是一首“情詩”。雖然解釋成“人與人的關系”可自圓其說,但從詩中讀出“階級斗爭”“共產主義理想”,則明顯帶上時代烙印。完全沉浸在自我夢幻中的愛情詩,這種解讀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里,還是太格格不入。情感體驗層面的愛情和個人意識曾經是非常前衛的詩歌,超越政治話語的修辭也一度蒙蔽了讀者。然而事實證明,許多朦朧詩的“朦朧感”在之后消失了,它們的蘊意遠沒有曾經想象的那般復雜。
可以進一步追問:時代背景固然是顧城愛情詩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可同時期其他朦朧詩人愛情詩的井噴現象又該如何解釋?從客觀上看,顧城的愛情詩本身表達不明朗,創作數量占比較小的情況下,與同期擅長寫愛情詩的詩人相比,并不具有突出的競爭優勢:舒婷的《致橡樹》《日光巖下的三角梅》《神女峰》,融合了偉大的女性意識和平等的愛情理想;北島的《雨夜》《你說》《愛情故事》,借助愛情撫慰現實的靈魂,拯救淪落的人性。顧城“朦朧”的寫法,注定會犧牲一部分愛情詩所必需的原始直接的沖擊,再加上同期詩人創作愛情詩的突出,顧城的愛情詩自然處于被無意忽略的狀態。
那么,為何顧城堅持“朦朧隱秘”地寫愛情詩?不難發現,對于《遠和近》的解釋,顧城也有意將其往“童話”“自然”的主旨靠攏。雖說創作者自身的闡述是解讀詩歌不容忽視的參考材料,但并不代表必須要對其全盤接受和信任。一方面,創作者的解讀同樣會受思想背景和當時輿論的干擾;另一方面,很多時候創作者的說法也會模棱兩可。顧城不只一次出現過創作內容與創作理念表達上的矛盾:例如顧城雖與眾人反復講述“詩意童年”,但實際上他并不喜歡勞作的生活,這與他想象中玻璃一樣的世界有很大的距離,而這種距離讓他感到痛苦。在這些“矛盾”的說辭中,顧城始終有一個不變的意圖,那便是維持其“童話詩人”形象。
可以說,顧城成為“童話詩人”,原是無心,后是順勢;既是偶然,也是必然。1980年《遠和近》問世時,舒婷曾在4月贈給顧城一首《童話詩人——給G.C》,“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蟈蟈的隊伍,向著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出發”①舒婷:《童話詩人——給G.C》,《舒婷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這句詩奠定了其“童話詩人”的稱號;彼時剛憑借《一代人》一舉成名的顧城,確實以天真的“黑眼睛”形象在大眾面前亮相。《小詩六首》發表在《詩刊》1980年10月號時,顧城添加了一段序言:“我生活,我寫作,我尋找美并發現美,這就是我的目的。”②顧誠:《小詩六首(六首)》,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69頁。這一段闡述其對美、童話、自然追求的宣言,使得當時有關這組朦朧詩的論爭更加激烈,主題更為撲朔迷離。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序言實際上是顧城在《詩刊》編輯的要求下臨時加上的,然而正是這段序言進一步加深了顧城在大眾心中“童話詩人”的形象。作為1980年代詩壇的頂級刊物,《詩刊》在朦朧詩的發現和推廣上功不可沒。1980年4月,顧城在《詩刊》“新人新作小輯”中發表詩作《眨眼》,同年參加《詩刊》于7月20日至8月21日舉辦的第一屆“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參與者共17人,他們的作品以“青春詩會”為總標題統一發表于《詩刊》10月號,《小詩六首》便是在第一屆“青春詩會”誕生的作品。這場活動的舉辦目的主要是培養扶植青年詩人,據青春詩會作品組副組長王燕生回憶:當時《詩刊》的領導,嚴辰、鄒荻帆、柯巖、邵燕祥四人,“每個人負責三四個學生,除了講大課之外,平時還要單獨輔導……輔導以后,他們也要花時間修改,然后還創作新作品”③田志凌、汪乾:《青春詩會:這里能看到中國詩歌發展的縮影——王燕生訪談》,《變遷: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文化生態備記錄》,廣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頁。。然而,顧城在自我介紹時便“惹怒”了老師們,他認為政治口號只是一陣風,大自然要長久得多,稱“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國徽跟瓢蟲身上的花紋沒什么兩樣,甚至還沒瓢蟲好看”④劉春:《海子、顧城——兩個詩人的羅生門》,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頁。。語罷好幾人當場拂袖而去,唯一留下的柯巖很嚴肅地說:“你要是我兒子,我現在就給你兩耳光,你知道國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鮮血嗎!”①劉春:《海子、顧城——兩個詩人的羅生門》,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頁。雖然未有顧城分組情況的確切記錄,但舒婷在回憶顧城的文章《燈光轉暗,你在何方?》中曾說,江河曾在排隊打飯菜時告訴她顧城被“安排的輔導老師嚴詞厲色訓了”②舒婷:《燈光轉暗,你在何方?》,《2014中國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頁。,舒婷和其他成員跑去央求邵燕祥收留顧城,顧城這才“轉班獲釋”。在青春詩會中最引人矚目的《小詩六首》,實際上是“差生”顧城的“意外之作”。在《和顧城談他的詩》一文中,顧城稱“他的幾批習作幾乎都不適用。當時詩刊的領導很關心他,找他談話,希望他寫一些現實感強、光明的詩,但由于他當時頭腦淤塞,就是沒寫出來。最后要定稿了,他便摘了一些筆記性的東西交上去”③余之:《歲月留情》,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頁。。顧城曾明確表示:“詩刊的領導并不贊成這種寫法。”直到1982年顧城給王燕生寫信,還署名為“留級生”,信中表示自己“終于積極了,找到了光明,于是朦朧化為了彩虹”④王燕生:《我所認識的顧城和李英》,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頁。。
可以看出,青春詩會的編輯理念是確保大方向的前提下,充分給予青年詩人機會。這首使顧城家喻戶曉的《小詩六首》,實際竟是詩人與刊物之間互相妥協的一次“意外”。由此可看出這個組序言和《小詩六首》的內容相關性并不是太大;臨時加上的“序”主要是為了“符合刊物主題”,“為了能達到‘積極、向上’的要求”⑤顧城:《顧城文選》卷1,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頁。。縱觀顧城的一生,他對“童話詩人”這一稱號欣然接受,并在詩歌創作中一以貫之。這既是出于其本人的創作理念及審美追求,也有一部分是緣自他逃避成人世界的私心。作為童話詩人”,顧城的詩歌成就與“童話”密不可分,該形象在詩壇、讀者心目中根深蒂固,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詩中的“愛情”。
結 語
顧城的愛情詩長期被讀者所忽視,或者說,讀者很少有從顧城的詩中去發現愛情。在大眾印象里,顧城是寫朦朧詩的童話詩人,人們習慣性只關注詩中明麗純凈的童話,把其中具體的感情抽象化。另一方面,顧城的一生充滿爭議,他的詩歌某種程度上已論為其私人八卦的附屬品,喜愛者借其詩歌“美化”他的殺人行為,厭惡者因蔑視他的行為而貶低其創作成就。顧城的愛情詩數量雖在其詩歌創作總量上不算多,但為我們還原其愛情體驗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也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顧城其人提供了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