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身份重構(gòu)的晚明士人:主體覺(jué)醒與美學(xué)轉(zhuǎn)向①
丁以涵(東南大學(xué) 藝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96)
一、引論
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層面,晚明是一個(g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藝術(shù)、工藝等方面都發(fā)生著劇烈變化的時(shí)代。政治上以“大禮議”事件為開(kāi)端,士人傳統(tǒng)“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政治道路變得異常艱難。商業(yè)經(jīng)濟(jì)的繁榮促進(jìn)了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動(dòng)、士商互動(dòng)和士匠牽手日益增多。同時(shí),伴隨著陽(yáng)明心學(xué)文化及后繼者思想的廣泛傳播與接受,士人在時(shí)代變化的浪潮下探索著新的日常化美學(xué)精神歸宿。在晚明日常化及“非主流”思想的影響下,士大夫群體也不再將入仕作為實(shí)現(xiàn)自身價(jià)值的唯一途徑,轉(zhuǎn)而尋找新的“非士”身份認(rèn)同,開(kāi)始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文化商品的創(chuàng)造、品鑒與交易。士人身上同時(shí)存在閑適與奢侈、雅與俗的共同特征,在日常審美活動(dòng)中為欲望的滿(mǎn)足賦予了合理性,以至于在物質(zhì)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共同建構(gòu)下實(shí)現(xiàn)了自我主體美學(xué)身份的新轉(zhuǎn)向。
為此,基于晚明社會(huì)背景,本文擬從士人被重構(gòu)的身份出發(fā),通過(guò)對(duì)晚明士人現(xiàn)實(shí)困境與精神世界的雙向探究,試圖探尋晚明士人是如何在自我發(fā)展中尋找新的“非主流”日常化社會(huì)定位,又是如何用自身主體審美思想建構(gòu)理想的日常化美好生活,聚焦闡釋他們?cè)谒囆g(shù)活動(dòng)、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背后所蘊(yùn)含的審美傾向與精神訴求,從而更好地認(rèn)識(shí)與理解晚明時(shí)代浪潮中晚明士人的主體覺(jué)醒與美學(xué)轉(zhuǎn)向,以增益于建構(gòu)當(dāng)代文藝的主體美學(xué)及其生活系統(tǒng),進(jìn)而發(fā)揮傳統(tǒng)文化的新時(shí)代傳承價(jià)值。
二、社會(huì)發(fā)展與士人身份的重構(gòu)
明代早期社會(huì)狀態(tài)與之前的朝代具有一定相似性,但隨之而來(lái)的是政治與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諸多變革,直至中后期,各階層的生活模式及其審美風(fēng)尚都發(fā)生巨大變化,讓后世看到了一個(gè)政治腐朽、經(jīng)濟(jì)繁榮與文藝發(fā)展共存的特殊時(shí)代。伴隨晚明的政治權(quán)利紛爭(zhēng)與經(jīng)濟(jì)興盛,作為知識(shí)群體的文人士大夫經(jīng)受著雙重沖擊,朝廷的腐敗令部分士人選擇遠(yuǎn)離朝堂,而同時(shí)自身文化權(quán)力也受到來(lái)自商人階級(jí)的挑戰(zhàn)。可以說(shuō)從明代中后期開(kāi)始,士人的思想觀念與價(jià)值理想發(fā)生了傾斜,身為社會(huì)精英及上層知識(shí)分子的士人群體呈現(xiàn)出分裂與異動(dòng),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構(gòu)成了自身身份的轉(zhuǎn)型,也奠定了晚明審美與藝術(shù)觀念轉(zhuǎn)向的基石。
(一)政治身份重構(gòu)
面對(duì)政治混亂、宦官專(zhuān)權(quán)、君臣離心的晚明社會(huì),士人投身仕途似乎不僅無(wú)法完成自身儒學(xué)理想,還更容易將自己的人生推向生活困境。明代統(tǒng)治者對(duì)待文人士大夫的態(tài)度極為嚴(yán)苛,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如此形容明代士人的處境:“身為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xí)于訶斥,歷于桎梏,褫衣以受隸校之淩踐。”[1]對(duì)士人的折辱必然導(dǎo)致不滿(mǎn)與怨憤,也因此形成了“君臣對(duì)立”的政治景象。而嘉靖時(shí)期的“大禮議”(1521—1538)事件,士人立足于前朝歷史與傳統(tǒng)制度的禮法,試圖挽回自身尊嚴(yán)并維系不斷被收回的政治權(quán)力,但在這次長(zhǎng)達(dá)二十余年“帝王之勢(shì)與儒者之道的又一次較量”[2]中,皇權(quán)取得了徹底勝利,確立了相對(duì)于士人的“絕對(duì)優(yōu)勢(shì)地位”,[3]最終導(dǎo)致重臣離開(kāi)朝堂,君臣間對(duì)立愈發(fā)嚴(yán)重,士人階級(jí)權(quán)力喪失的同時(shí)宦官地位則在不斷上升。
在如此政治背景下,諸多文人不再執(zhí)著于廟堂之學(xué),并逐漸脫離過(guò)去單一政治倫理的束縛,轉(zhuǎn)而尋找新的文藝生存空間,譬如民間漆工黃成本來(lái)可以走入仕之路,卻投身到髹漆美學(xué)及《髹飾錄》的創(chuàng)作中,進(jìn)而在工藝領(lǐng)域?qū)崿F(xiàn)自己的士人理想。晚明的政治亂象給予了士人沉重打擊,但政治情勢(shì)的嚴(yán)酷確實(shí)成了他們調(diào)整心態(tài)的主要原因,[4]而這些文人士大夫所做出的不同選擇,讓處于同一階級(jí)的上層知識(shí)群體在實(shí)際行動(dòng)中出現(xiàn)了分裂,也揭示了晚明士人必然要在如此困境中尋求一條新的日常化出路。
(二)倫理身份重構(gòu)
在晚明士人追求多樣化的生活時(shí),高度發(fā)達(dá)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給予了他們找尋自我或是奢靡享樂(lè)的溫床。從明嘉靖開(kāi)始,“商品經(jīng)濟(jì)空前繁榮,人們的私有觀念迅速膨脹,商品意識(shí)大為增強(qiáng),全國(guó)各地去農(nóng)經(jīng)商成風(fēng)”。[5]直到晚明這股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浪潮走向了最高峰,以江南地區(qū)尤甚,工商業(yè)與服務(wù)業(yè)普遍繁榮,形成了百賈交會(huì)、萬(wàn)商云集的景象,[6]對(duì)士大夫的倫理身份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在商業(yè)文化沖擊下,明初以國(guó)家權(quán)力與儒家倫理為核心建立的“士農(nóng)工商”等級(jí)制度發(fā)生動(dòng)搖,其中顯著的特征便是商人倫理地位的上升。對(duì)于擁有大量財(cái)富的商人而言,他們影響力逐步擴(kuò)大,不僅引導(dǎo)著平民階級(jí),對(duì)士人階級(jí)也產(chǎn)生了相當(dāng)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商人擁有了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與社會(huì)地位后,對(duì)文化權(quán)力的渴望也在不斷攀升。因而在這一時(shí)期,士紳與商人兩個(gè)階級(jí)進(jìn)行了大量互動(dòng),士人進(jìn)入商業(yè)尋求發(fā)展或是商人躋身士紳之流時(shí)常發(fā)生。士人群體中如李卓吾以評(píng)書(shū)、著書(shū)為業(yè);陳洪綬、唐寅、文徵明以賣(mài)畫(huà)為生;陳繼儒廣結(jié)人脈、販賣(mài)詩(shī)文以及相當(dāng)一部分士人進(jìn)入書(shū)坊業(yè)等。換言之,晚明士人不論選擇何種生活方式,均有意識(shí)地將自身所學(xué)融入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需求,以獲取最大程度上社會(huì)倫理身份的重構(gòu)。晚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后社會(huì)各個(gè)階層對(duì)文化倫理消費(fèi)的需求增大,從而促進(jìn)了相關(guān)文化藝術(shù)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這樣的“士商互動(dòng)”和“士工對(duì)話(huà)”則意味著晚明社會(huì)各階層成員在互相流動(dòng),在融合中實(shí)現(xiàn)彼此的身份倫理重構(gòu)。
(三)文化身份重構(gòu)
在晚明,統(tǒng)治者放松了對(duì)文化的掣肘,客觀上促進(jìn)了藝術(shù)和工藝的發(fā)展。統(tǒng)治階層的腐朽奢侈也影響了其他階層“靡然向奢”,甚至“以?xún)€為鄙”,[7]整個(gè)社會(huì)在當(dāng)時(shí)高度發(fā)達(dá)的經(jīng)濟(jì)條件下呈現(xiàn)一種悠然享樂(lè)的生活狀態(tài)。晚明時(shí)期士人心態(tài)逐漸由“外顯”轉(zhuǎn)向“內(nèi)隱”,文人逸士在遠(yuǎn)離廟堂后更加沉浸于聲色享受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將自身文化實(shí)力轉(zhuǎn)變?yōu)樵谏虡I(yè)經(jīng)濟(jì)中發(fā)展的資本。譬如蘇州工匠陸子岡在豁達(dá)開(kāi)放的藝術(shù)秉性中逐漸走上了“動(dòng)刀必落款”的個(gè)性追求,在外顯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展示出晚明士大夫獨(dú)有的“內(nèi)隱”化的玉德情懷追求。晚明文化已然具備了商業(yè)化與世俗化的特征,晚明士人作為“文化”的權(quán)威代表,被市民階層爭(zhēng)相模仿的同時(shí),出于自身的追求文化階層也會(huì)做出一定妥協(xié)。而追求其文化品位、審美趣味的商人階級(jí)也獲得了所謂的“雅”。盡管文化修養(yǎng)需要長(zhǎng)時(shí)間的積累與浸潤(rùn),這種雅致的生活藝術(shù)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依然使其獲得了美學(xué)品位與主體精神的提升。
簡(jiǎn)言之,晚明士人在社會(huì)活動(dòng)中除了與文人士大夫之間的平等交流,也與工匠、商賈、平民往來(lái),并實(shí)現(xiàn)個(gè)性化的日常美學(xué)對(duì)話(huà)與交往。或者說(shuō),晚明社會(huì)中人與人的社會(huì)交流活動(dòng)密切頻繁且呈現(xiàn)出“美學(xué)下移”傾向,同時(shí)也帶來(lái)了晚明文化“自上而下”的學(xué)術(shù)思潮轉(zhuǎn)向和主體意識(shí)覺(jué)醒,以至于“非主流思想”成為晚明士大夫的追求。
三、學(xué)術(shù)思潮與主體意識(shí)的覺(jué)醒
思想的轉(zhuǎn)變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在晚明特殊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的背景下,晚明興起的學(xué)術(shù)思想為文化發(fā)展構(gòu)建出一個(gè)相對(duì)寬松的人文環(huán)境,其變化對(duì)作為知識(shí)群體的士人產(chǎn)生巨大影響,也對(duì)藝術(shù)觀念的形成起到引導(dǎo)作用。晚明時(shí)期士人從思想上便有反對(duì)封建束縛的傾向,他們崇尚真情且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個(gè)體、個(gè)性的尊重,肯定對(duì)自我欲望的追求與滿(mǎn)足,開(kāi)始關(guān)注下層人民的生活空間,這極大地改變了知識(shí)階層的審美價(jià)值觀與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響著士人對(duì)藝術(shù)、工藝的理解與創(chuàng)作。
(一)心學(xué)思潮與個(gè)體自覺(jué)
自士人階層在政治層面遭受挫折后,原本作為明代正統(tǒng)的程朱理學(xué)無(wú)法推陳出新為其提供指引。同時(shí),伴隨經(jīng)濟(jì)的迅速發(fā)展,奢靡的物質(zhì)消費(fèi)意識(shí)自上而下輻射至整個(gè)社會(huì),心學(xué)在這個(gè)時(shí)期興起,“嘉靖以后,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間”。[8]心學(xué)的核心主張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與“致良知”,并提倡天理在于人心,不必外求天理,“人者,天地萬(wàn)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wàn)物之主也”,[9]對(duì)程朱理學(xué)“存天理,滅人欲”給予了徹底否定。在心學(xué)影響下,士人可以跳脫出傳統(tǒng)倫理綱常的封建政治領(lǐng)域,試圖開(kāi)拓文化、審美、經(jīng)濟(jì)等領(lǐng)域的新成就。陽(yáng)明心學(xué)后又發(fā)展出不同流派,以泰州學(xué)派影響最大,王艮為首的一眾哲學(xué)家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觀點(diǎn),將對(duì)“心”的關(guān)注轉(zhuǎn)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因而在社會(huì)普通民眾中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令士人更多地開(kāi)始關(guān)注下層人民的生活,同時(shí)也肯定了人們對(duì)物質(zhì)的需求。這種追求以李贄最為激進(jìn),“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wú)倫物矣”等理論更加深了功利欲望的合理性。并提出“絕假純真”的“童心說(shuō)”,李贄的思想體系中最為倡導(dǎo)“真心”,如果說(shuō)王艮學(xué)說(shuō)有重視個(gè)體的傾向,那么李贄的思想則真正做到了重視個(gè)體。[2]431之后王門(mén)心學(xué)又發(fā)展出言情思潮,其中以湯顯祖與馮夢(mèng)龍最為突出,他們將“情”的價(jià)值推向極致,對(duì)晚明士人影響巨大,可以“說(shuō)‘言情’是晚明士人的一大人生追求,從哲學(xué)到政治再到文學(xué),無(wú)不顯示出言情的蹤跡”。[2]453除此以外也有受到王門(mén)左派的影響的學(xué)說(shuō),如以袁宏道為首推崇本然情性的“性靈說(shuō)”,其主張“獨(dú)抒性靈,不拘格套”,[10]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一種不受拘束地進(jìn)行表達(dá)情感欲望的態(tài)度。
(二)人本主義思潮與個(gè)性解放
陽(yáng)明心學(xué)與王門(mén)后人各種學(xué)說(shuō)的發(fā)展與傳播,其影響力在晚明各個(gè)階層與地域中不斷擴(kuò)大,晚明士人的心態(tài)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這種思想領(lǐng)域變化,其趨勢(shì)與晚明社會(huì)的發(fā)展始終相契合,士人意識(shí)到評(píng)判人生的標(biāo)準(zhǔn)可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我與內(nèi)心,自我意識(shí)覺(jué)醒并得到空前的張揚(yáng)。理學(xué)式微后的系列學(xué)說(shuō),為晚明帶來(lái)的是一場(chǎng)不斷變革的人本主義思想潮流,士人大膽反對(duì)傳統(tǒng)的束縛而重視自我價(jià)值,在繁復(fù)的世俗生活中進(jìn)行美的經(jīng)營(yíng),創(chuàng)造雅化的日常生活,同時(shí)以此作為對(duì)當(dāng)時(shí)政治困境的一種突破。這種主體意識(shí)為藝術(shù)發(fā)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想空間,也改變了整個(gè)社會(huì)的審美傾向,“李贄的童心說(shuō),湯顯祖的唯情說(shuō),公安派的性靈說(shuō),它們所包含的個(gè)性解放的傾向,對(duì)于儒家傳統(tǒng)的‘溫柔敦厚’美學(xué)思想是嚴(yán)重的沖擊”。[11]這些思維都是“率性而行”“純?nèi)巫匀弧钡牡浞丁?/p>
(三)主體意識(shí)覺(jué)醒下的文藝創(chuàng)作
晚明士人既有偏重世俗享樂(lè)、縱情肆意的一面,也有追求內(nèi)心安寧、超塵脫俗的一面,這種態(tài)度融入士人生活與藝術(shù)活動(dòng)的方方面面,晚明時(shí)期文學(xué)、戲曲、繪畫(huà)、工藝等文藝領(lǐng)域都有相應(yīng)的發(fā)展,尤其是戲曲與小說(shuō)等大眾藝術(shù)最能體現(xiàn)對(duì)個(gè)體生命的尊重與追求以及對(duì)真摯情感的贊頌。
晚明文學(xué)與戲曲領(lǐng)域發(fā)展受泰州學(xué)派影響極大,尤其是“人欲是合理的,百姓日用即是天理”,沖擊著封建禮教對(duì)人性的束縛,對(duì)晚明文學(xué)重視自我展現(xiàn)與至情至性的觀念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因此晚明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一改正統(tǒng)詩(shī)文的面貌,走向自由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方向,也令晚明文學(xué)掀起了一股肯定個(gè)人欲望、推崇真情的主情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贄、湯顯祖、袁宏道等。李贄主張“童心說(shuō)”,認(rèn)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在詩(shī)文創(chuàng)作層面應(yīng)當(dāng)注重對(duì)情感的表達(dá),而非拘泥于創(chuàng)作技巧與形式。因此在《焚書(shū)·讀律膚說(shuō)》中提出“自然發(fā)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fù)有禮義可止也”,公開(kāi)反對(duì)“以禮節(jié)情”的傳統(tǒng)規(guī)范,寫(xiě)作時(shí)不要限制人的天性,以自然為美,對(duì)晚明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李贄在繼承泰州學(xué)派思想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抨擊封建禮教對(duì)人的束縛,為晚明興起主情思潮提供了理論的雛形,而提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湯顯祖則可以稱(chēng)為主情思潮的集大成者。在湯顯祖看來(lái)“情”才是創(chuàng)作的源泉,而他的“至情論”不僅認(rèn)為創(chuàng)作者需要自由地抒發(fā)所感,也應(yīng)兼具教化作用,在作品中挽救社會(huì)的落敗風(fēng)氣、批判政治的腐敗不公。而在此之后的公安派則將主情思想理論應(yīng)用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革新之中,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提出“獨(dú)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理論核心,主張?jiān)谠?shī)歌創(chuàng)作中不受陳腐之規(guī)的拘束,是一種自由表現(xiàn)性情與心靈的創(chuàng)作觀念,在大量詩(shī)歌散文中呈現(xiàn)出無(wú)拘無(wú)束的情感表達(dá),直面人性物欲以及享樂(lè)的人生態(tài)度。總體來(lái)說(shuō),晚明通俗文學(xué)與戲曲發(fā)展極為繁盛,這種重情重性的思想主張產(chǎn)生于特定的時(shí)代背景,在陽(yáng)明心學(xué)沖擊程朱理學(xué)的基礎(chǔ)上,泰州學(xué)派進(jìn)一步釋放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對(duì)人性的壓制。也正因?yàn)閯?chuàng)作極度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濫情、真情、自我交織的狀態(tài),繁盛發(fā)展的表象下隱含著人性解放與傳統(tǒng)倫理間的矛盾。但以歷史發(fā)展的眼光來(lái)看,晚明文學(xué)與戲曲以強(qiáng)烈的創(chuàng)作主體意識(shí)開(kāi)啟了一場(chǎng)文學(xué)領(lǐng)域的情感解放運(yùn)動(dòng),具備著思想解放的重要意義。
同時(shí)主情思潮的出現(xiàn)使晚明藝術(shù)審美發(fā)生根本性變化,與明代早期用于教化功能的圖像不同,繪畫(huà)創(chuàng)作的理念逐漸回歸藝術(shù)本身,也逐漸擺脫倫理教化的約束走向自由書(shū)寫(xiě)的道路。晚明時(shí)期繪畫(huà)藝術(shù)同樣體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主體創(chuàng)作精神,與早前的宮廷畫(huà)派、吳門(mén)畫(huà)派、浙派等畫(huà)壇主流審美背道而馳,打破了傳統(tǒng)繪畫(huà)和諧優(yōu)雅、清淡平和的古典審美,以一種個(gè)性張揚(yáng)甚至離經(jīng)叛道的姿態(tài)深化了美的概念,并且能做到“化丑為美”“以丑為美”。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將晚明描述為一個(gè)“天崩地解”的時(shí)代,而中和之美通常出現(xiàn)在安定繁榮的太平盛世,晚明藝術(shù)中的“丑”并不是直白感官意義上的丑陋,而是不拒絕怪異,在繪畫(huà)藝術(shù)上推崇獨(dú)立有特色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幫助創(chuàng)作者在抒情達(dá)意時(shí)拓寬藝術(shù)張力。就繪畫(huà)本身而言,文人畫(huà)的發(fā)展自唐宋元至晚明,早已形成一套具體的繪畫(huà)體系與范式,不論是山水花鳥(niǎo)人物的用筆用墨都有一定規(guī)程。明代早期繪畫(huà)依然遵循傳統(tǒng),所謂“守古人之法”“師古人之跡”。然而從徐渭、陳洪綬、傅山、吳彬、崔子忠、金農(nóng)、羅聘、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中,不難看出從明代中期開(kāi)始繪畫(huà)的題材、構(gòu)圖、筆墨、意境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開(kāi)創(chuàng)晚明潑墨大寫(xiě)意風(fēng)格的徐渭受陽(yáng)明心學(xué)影響,認(rèn)同自然真實(shí)之美,畫(huà)作中充滿(mǎn)變異與豪放。徐渭在傳統(tǒng)題材中開(kāi)發(fā)新的藝術(shù)生命力、找尋獨(dú)特的繪畫(huà)視角,大寫(xiě)意風(fēng)格逸筆草草、墨色淋漓,直白地展現(xiàn)了他的狂狷與放縱,沒(méi)有規(guī)范的形式美,在筆墨流淌中肆意揮灑、追求自由。追求“入畫(huà)也不得安寧”變形怪誕的丑拙人物畫(huà)風(fēng)的陳洪綬以及明確提出“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12]的傅山等人,大多也具有類(lèi)似的審美,所體現(xiàn)的是晚明畫(huà)家反對(duì)庸俗媚俗、秩序統(tǒng)一,且擁有批判精神的強(qiáng)大藝術(shù)生命力。
時(shí)代精神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藝術(shù)觀念的形成,學(xué)術(shù)思潮最先影響的就是文化階層。文人士大夫、藝術(shù)家、思想家往往是最為敏感、細(xì)膩的群體,不甘被束縛、追求自由的本性被激發(fā),從而孕育出極具影響力的藝術(shù)活動(dòng)與文藝作品。這些藝術(shù)形式蘊(yùn)含著晚明士人的精神訴求與審美追求,其反對(duì)傳統(tǒng)禮教、封建束縛、強(qiáng)調(diào)個(gè)性自由的理念,推動(dòng)了明清文藝思潮的發(fā)展,在中國(guó)哲學(xué)思想史與美術(shù)史的發(fā)展歷程中都具有重要意義。
四、士人心態(tài)與審美趣味的轉(zhuǎn)向
士人階層藝術(shù)觀念的形成不僅僅是一個(gè)美學(xué)維度的事件,還涉及士人對(duì)自身的身份認(rèn)同,體現(xiàn)了晚明士人生存狀態(tài)的變化。譬如朱元忠對(duì)晚明士人群體心態(tài)變化的概述:“由于朝政腐敗,皇帝怠政,內(nèi)擅權(quán),黨爭(zhēng)不斷,國(guó)事日非,內(nèi)憂(yōu)外患,危機(jī)四伏,政治情勢(shì)的嚴(yán)酷成為文人調(diào)整心態(tài)的主要原因;社會(huì)觀念的變化也使得文人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方面都受到嚴(yán)重?cái)D壓,社會(huì)生態(tài)、價(jià)值觀念的變化,加之對(duì)性靈等的提倡,促使明代士人積極調(diào)整自己的心態(tài),積極調(diào)整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開(kāi)始尋找新的人生寄托。”[4]360-361這種心態(tài)變化受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與學(xué)術(shù)思想的雙重影響,如上文所言“大禮議”事件使士人階層意識(shí)到自身的行為準(zhǔn)則與當(dāng)時(shí)的政治場(chǎng)域相悖,不得不將對(duì)政治活動(dòng)的注意轉(zhuǎn)向?qū)θ粘I畹臉?gòu)建,士人的關(guān)注重心也在自上而下地轉(zhuǎn)移。
(一)崇尚奢靡之風(fēng)
晚明時(shí)期“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fēng)以侈靡相高”,[13]人們普遍追求奢華、享樂(lè)和舒適的生活,重商逐利、縱欲浮華之風(fēng)盛行,也常有違禮逾制的行為。所謂“奢靡”,集中表現(xiàn)為明代中后期日常生活中的非必要花費(fèi),一種為用度數(shù)量上的揮霍,另一種為用物的精細(xì)奢侈。明朝范濂編著的《云間據(jù)目抄》便記錄了嘉靖、萬(wàn)歷年間的社會(huì)風(fēng)俗,尤其在《紀(jì)風(fēng)俗》一卷中,記載了如衣飾、頭飾、鞋襪、綾絹花樣、婦人頭髻等衣著方面的變化,如“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圓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鬢,后用滿(mǎn)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環(huán)。年少者用頭箍,綴以團(tuán)花方塊。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圓領(lǐng)。裙有銷(xiāo)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頂髻。”[14]詳細(xì)描寫(xiě)了婦人頭髻簪花的樣式,稱(chēng)前人裝飾清雅,而如今崇尚華麗。又比如晚明士人熱衷梨園戲曲,范濂對(duì)演劇人員的描寫(xiě)則是“至萬(wàn)歷庚寅,各鎮(zhèn)賃馬二三百匹,演劇者皆穿鮮明蟒衣靴草,而幞頭紗帽,滿(mǎn)綴金珠翠花,如扮狀元游街。用珠鞭三條,價(jià)值百金有余。又增妓女三四十人,扮為寡婦征西、昭君出塞,色名華麗尤甚。……日費(fèi)千金,且當(dāng)歷年饑饉。而爭(zhēng)舉孟浪不經(jīng),皆予所不解也。”[15]有研究表明,晚明的奢靡之風(fēng)并不僅是在相對(duì)發(fā)達(dá)的江浙及兩都(北京、南京)地區(qū)獨(dú)有的社會(huì)風(fēng)氣,而是蔓延至大江南北與社會(huì)各個(gè)階層,因此在晚明的地方志中,也常有對(duì)“世風(fēng)趨奢”的批判。
晚明的奢侈已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基于物質(zhì)水平的極大提升,物質(zhì)欲望不僅影響了基本的日常生活,也促進(jìn)晚明文學(xué)、手工藝的快速發(fā)展,并延伸至審美領(lǐng)域與精神需求的各個(gè)方面。同時(shí)晚明商人階層的社會(huì)地位不斷上升,憑借經(jīng)濟(jì)資本進(jìn)入文化市場(chǎng),在士商互動(dòng)和士工對(duì)話(huà)的過(guò)程中士人不僅需要通過(guò)更為獨(dú)特的藝術(shù)審美維持自身的聲望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人崇奢審美的影響。因而晚明時(shí)期雅致與奢華在藝術(shù)活動(dòng)中共同存在并相互影響,當(dāng)士人介入平民空間,各種藝術(shù)活動(dòng)可以脫離政治存在并顯示出新的審美情趣。
(二)閑適與欲望并存
這一時(shí)期,士人階層的審美趣味展現(xiàn)出閑適與欲望共存的特征,既追求舒適自然的生活,又縱情縱欲地追求奢侈的體驗(yàn)。這種生活風(fēng)氣主要體現(xiàn)在晚明士人日常生活的審美情趣,士人主動(dòng)地構(gòu)建一種藝術(shù)化的生活情境,西方漢學(xué)家柯律格認(rèn)為:“正是在16世紀(jì)(主要是后半葉),傳統(tǒng)的社會(huì)精英感到其社會(huì)地位受到威脅,轉(zhuǎn)向‘發(fā)明趣味’,以此為手段來(lái)強(qiáng)調(diào),要緊的不僅是對(duì)美學(xué)奢侈品的占有,而且是占有它們的方式。”[16]可以看出對(duì)士人而言不僅需要占有諸如漆器、瓷器、玉器等奢華“物”,更重要的是如何審美化地加以占有,而他們藝術(shù)審美態(tài)度的變化也離不開(kāi)對(duì)“物”的迷戀與重視。基于這種日常化審美追求,士人的藝術(shù)能力、鑒賞能力從傳統(tǒng)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流向生活,因此晚明時(shí)代士人生活呈現(xiàn)出特有的藝術(shù)化、審美化特征,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寫(xiě)道:“能于此等處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戶(hù)登其堂,見(jiàn)物物皆非茍?jiān)O(shè),事事俱有深情,非特泉石勛猷于此足征全豹,即論廟堂經(jīng)濟(jì),亦可微見(jiàn)一斑。”[17]從日常生活、陳設(shè)用品延伸到了廟堂經(jīng)略,士人對(duì)生活的經(jīng)營(yíng)已然成為施展自身才華的方式,是一種藝術(shù)的生活化和日常化延伸。
以晚明的園林營(yíng)造為例,園林作為晚明士人居住并玩樂(lè)的場(chǎng)所,也是他們怡情養(yǎng)性、展現(xiàn)自身審美情趣的精神后花園,即“一個(gè)賞心悅目、怡情騁懷的生活空間”。[18]中國(guó)臺(tái)灣學(xué)者王鴻泰對(duì)明代中期以后士人熱衷修建園林這一現(xiàn)象有著這樣的解讀:“與前述政權(quán)控制下最素樸的住宅相比,園林修建蔚然成風(fēng)反映出個(gè)人生活空間觀念的拓展。他們已不再將‘住宅’界定為只是日常食宿的場(chǎng)所,而想要進(jìn)一步延伸‘住宅’的意涵,將休閑性質(zhì)納入房屋的領(lǐng)域內(nèi)。”[19]顯然,明代初期朱元璋倡導(dǎo)儉樸的生活方式已無(wú)法滿(mǎn)足士人的需求。晚明結(jié)社集會(huì)、游謁的交往方式十分盛行,文人士大夫通過(guò)這種交往拜訪(fǎng)名家、切磋學(xué)問(wèn)或談?wù)撛?shī)文,構(gòu)建出一個(gè)士人群體的活動(dòng)空間。
對(duì)晚明士人而言,園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隱居山林替代性選擇,園林不但在審美上可以使他們模仿居于山林的體驗(yàn),也表達(dá)出他們放棄仕途追求隱逸的意愿,因此這是一個(gè)“去政治化”空間。但與真正的隱居不同的是,居于園林的士人并沒(méi)有完全放棄社會(huì)生活,而是代表士人退出仕途名利的追求轉(zhuǎn)而更加關(guān)注自身的生活體驗(yàn)與精神享受。晚明著名園林藝術(shù)著作《園冶》中所提供的造園技術(shù)或是理論依據(jù),被總結(jié)為“因水構(gòu)園”“因地成形”“因地造屋”“因地取材”“因時(shí)制宜”,[20]因此可以說(shuō)“因地制宜”是一種貫穿始終的理論方法,士人順應(yīng)內(nèi)心并借景打造一方模仿山林的自然景致,根據(jù)地勢(shì)自然地挖掘池塘、建造亭臺(tái)樓閣,建造體驗(yàn)涵蓋了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觸覺(jué)等多個(gè)方面,為士人階層在園林中的生活與交往活動(dòng)提供場(chǎng)景。景觀與建筑順勢(shì)而為相互配合以達(dá)成士人的審美需求,因此晚明園林蘊(yùn)含的意境受到士人推崇,能否擁有這樣閑適、自然且具有雅致趣味的生活也成了影響士人文化聲望的重要尺度。
(三)物戀與日常化審美趣味
在這種審美觀念的影響下,生活中的物與藝術(shù)品間的邊界不再清晰,從而產(chǎn)生出在日常生活中實(shí)現(xiàn)自身藝術(shù)審美的生活方式,即當(dāng)下所說(shuō)的“生活美學(xué)”。日常用物被要求“適用美觀均收其利而后可”,[16]214無(wú)關(guān)日用的“長(zhǎng)物”“玩物”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晚明誕生出一批“物”為主題的美學(xué)著作,“僅《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所著錄的就多達(dá)二十余部,其中為后世所熟知的包括高濂的《遵生八箋》,袁宏道的《瓶史》,文震亨的《長(zhǎng)物志》,計(jì)成的《園冶》,屠隆的《考槃?dòng)嗍隆贰镀鹁悠鞣{》《山齋清供箋》《文房器具箋》,衛(wèi)泳的 《枕中秘》,陳繼儒的《妮古錄》,谷應(yīng)泰的《博物要覽》等等。”[21]其中文震亨所著《長(zhǎng)物志》包含了“室廬”“花木”“水石”“禽魚(yú)”“書(shū)畫(huà)”“幾榻”“器具”“衣飾”“舟車(chē)”“位置”“蔬果”“香茗”共十二大類(lèi),涉及衣食住行各個(gè)方面,對(duì)“物”的審美范圍在大幅擴(kuò)展。文震亨的論述中,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成了士人階層品味鑒賞的對(duì)象,也成為士人踐行文雅生活的載體與身份象征。可以看出晚明時(shí)期被納入審美對(duì)象的范圍十分廣闊,在繼承了前人常見(jiàn)審美事物的基礎(chǔ)上,日常生活中任何事物如剪刀、飼養(yǎng)器具等日用工具均可以作為審美對(duì)象。一方面是因?yàn)槭艿酵砻魃菝抑L(fēng)的影響,器物被開(kāi)發(fā)出實(shí)用性以外的審美價(jià)值,另一方面士人也在通過(guò)對(duì)物品的精神“消費(fèi)”超越世俗的物質(zhì)消費(fèi),借“物”營(yíng)造出一種藝術(shù)化、審美化的日常情境,從中獲得審美的趣味體驗(yàn)并彰顯自身才情。如晚明沈春澤在給《長(zhǎng)物志》所作的序中說(shuō)道:“夫標(biāo)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杯鐺之屬,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zhǎng)物。而品人者,于此觀韻焉、才與情焉。”[22]晚明士人在“造物”中追求“玩物”,但在“玩物”中并非純粹的“戀物”,而在其中走向了“情物”的主體美學(xué)消費(fèi),實(shí)現(xiàn)了自我的物戀與日常化審美趣味。
(四)附庸風(fēng)雅和意趣之適
藝術(shù)審美對(duì)象范圍不斷擴(kuò)大,士人的價(jià)值觀念也在發(fā)生轉(zhuǎn)變。晚明時(shí)期,由于商人階級(jí)的崛起,在擁有了相應(yīng)的社會(huì)地位后,商人選擇主動(dòng)向士人階層的審美靠攏,通過(guò)奢靡的消費(fèi)與效仿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希望以此感受知識(shí)階層的審美趣味。文震亨將其稱(chēng)為“好事者”,“吳中菊盛時(shí),好事家必取數(shù)百本……若真能賞花者,必覓異種,用古盆盎植一株兩株,莖挺而秀,葉密而肥,至花發(fā)時(shí),置幾榻間,坐臥把玩,乃為得花之性情。”[22]78商賈富戶(hù)雖有足夠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參與或模仿士人階級(jí)的審美活動(dòng),但依舊是一種“附庸風(fēng)雅”,缺乏對(duì)“物”真正的品位與格調(diào)。可以看出文人雅士們依然以雅致的精神性體驗(yàn)作為審美的最高境界,其藝術(shù)追求建立在自身豐厚的文化積累上,士人“通過(guò)傳承經(jīng)典、區(qū)分雅俗、厘定正統(tǒng)、品藻人物等方式,行使著知識(shí)話(huà)語(yǔ)權(quán)力”,[23]維護(hù)著士人階層在文化場(chǎng)域中的優(yōu)勢(shì)地位。然而,在實(shí)際的藝術(shù)活動(dòng)推動(dòng)中,士人始終無(wú)法置身于士商高度互動(dòng)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之外,即便文震亨在“賞菊”活動(dòng)中認(rèn)為商人行為庸俗且士人階層擁有更高的審美,但最符合賞玩標(biāo)準(zhǔn)的還是條件苛刻的“異種”,其培育、運(yùn)輸?shù)某杀疽餐瑯痈甙骸M砻魃鐣?huì)商業(yè)化程度高,對(duì)物欲的追求與對(duì)“物”的占有成為士人審美中重要的一環(huán),士人的需求也同樣進(jìn)入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文化商品的交流之中。因此士人在對(duì)物的賞玩過(guò)程中也會(huì)陷入一種物化的境地,在《長(zhǎng)物志》中,既能看到士人對(duì)商人審美品位的鄙視,也能看到如何甄別挑選名貴之物的指導(dǎo)與對(duì)占有名貴物品的渴望。余英時(shí)指出“如果從商人的立場(chǎng)出發(fā),我們毋寧說(shuō),他們打破了兩千年來(lái)士大夫?qū)τ诰耦I(lǐng)域的獨(dú)霸之局。即使我們一定要堅(jiān)持‘附庸風(fēng)雅’之說(shuō),我們也無(wú)法否認(rèn)下面這個(gè)事實(shí):即由于商人的‘附庸’,士大夫的‘風(fēng)雅’已開(kāi)始改變了。”[24]但是相較于商人權(quán)貴的極盡奢華,晚明士人對(duì)欲望的追逐則不會(huì)直接呈現(xiàn)出來(lái),往往隱匿于閑適雅致的趣味之中,“明代士人尚物,所取者不是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于其德。”[25]
概言之,晚明士人對(duì)“物”的審美概念進(jìn)行了大幅擴(kuò)充,其審美對(duì)象也主要圍繞“物”而展開(kāi),士人的審美活動(dòng)中包含了對(duì)奢侈生活的追求、個(gè)體欲望的滿(mǎn)足以及聲色感官的體驗(yàn),對(duì)美的感受與標(biāo)準(zhǔn)都有了一定變化。從晚明藝術(shù)的整體發(fā)展來(lái)看,“雅”與“俗”之間的交融與互動(dòng),是晚明藝術(shù)觀念的一大特征,對(duì)晚明士人而言,欲望與閑適共同構(gòu)建出屬于晚明士人雅致的奢華生活,所追求的是“欲望和審美的交融”,[4]429在“長(zhǎng)物”中實(shí)現(xiàn)了美好生活的多重身份建構(gòu)。
五、結(jié)語(yǔ)
晚明士人藝術(shù)觀念的形成與發(fā)展不僅是物質(zhì)層面的問(wèn)題,還是美學(xué)層面的問(wèn)題,也應(yīng)對(duì)了士人所面對(duì)的身份焦慮和內(nèi)在矛盾,更體現(xiàn)了在傳統(tǒng)士人道路坍塌時(shí),晚明士人如何沖破綱常禮教,尋求和重建自我價(jià)值,探尋自身作為獨(dú)立個(gè)體生命的意義。
從整個(gè)時(shí)代背景來(lái)看,晚明士人內(nèi)心無(wú)疑是矛盾的,在鐘情心學(xué)思潮的影響下極具浪漫主義精神、渴望自由精神的滿(mǎn)足,將生活及其物質(zhì)享受作為一種日常化藝術(shù)美學(xué)而對(duì)待,同時(shí)又無(wú)法回避掌握雄厚財(cái)力的商人所帶來(lái)的威脅。因此對(duì)“物”的審美態(tài)度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變,士人利用自身卓越的藝術(shù)品位、文學(xué)修養(yǎng),借“物”或藝術(shù)活動(dòng)這一媒介在晚明的時(shí)代變化中積極尋找士人階層的新出路,以至于將美學(xué)的目光走出了書(shū)齋,走向了底層,并為晚明的文藝發(fā)展帶來(lái)新轉(zhuǎn)向。晚明士人構(gòu)建了一個(gè)游離于政治場(chǎng)域之外的“非主流”美學(xué)空間,進(jìn)而形成一種以藝術(shù)的視角統(tǒng)一看待日常生活、文化藝術(shù)、社會(huì)交際的美學(xué)觀念,并將生活營(yíng)造成藝術(shù)品。認(rèn)清晚明士人精致藝術(shù)化的生活體驗(yàn),尤其是日用器物、家居用品、居園林所、服飾飲食、工藝美術(shù)均成為被審美的對(duì)象,而原本高懸于上層文化階層的文學(xué)書(shū)畫(huà)、古董清玩、戲曲娛樂(lè)等形式反而逐漸下移具有日常化趨勢(shì)。這樣的生活體驗(yàn)在晚明的繁榮經(jīng)濟(jì)下得以進(jìn)行,但是追求縱欲抵消對(duì)現(xiàn)實(shí)不公的無(wú)奈,也不可避免生發(fā)出虛情泛濫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同時(shí)也應(yīng)該看到,晚明擁有極為寬松的人文環(huán)境,足以包容新的哲學(xué)思想、文藝作品、生活潮流,而當(dāng)這一切沒(méi)有可以相抗衡的制度時(shí),也無(wú)法避免地陷入“極敝”的危機(jī)之中。晚明時(shí)代的歷史局限也正在于此,士人追逐自由并滿(mǎn)足個(gè)體欲望,享受“清福”“閑適”的生活,其中沉淀的是無(wú)數(shù)的政治失意、人生挫敗。晚明文人士大夫在后世時(shí)常遭到非議,其主要原因便是人欲膨脹后導(dǎo)致欲望肆意蔓延,令推崇自由、真性情的實(shí)踐者們逐漸標(biāo)新立異、玩物喪志,最終甚至行為追求怪異、荒誕不經(jīng),這不僅體現(xiàn)在晚明士人的生活行徑中,也反映在晚明文藝作品中,盛大繁榮的表象下是社會(huì)與個(gè)人的矛盾糾葛。
毋庸置疑,晚明藝術(shù)與生活美學(xué)所帶來(lái)的精華與糟粕都需要仔細(xì)甄別,極度的放縱對(duì)創(chuàng)作者而言或許有益,但在晚明政治衰微的環(huán)境下,文人士大夫階級(jí)責(zé)任意識(shí)的消解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huì)風(fēng)氣的沒(méi)落,甚至預(yù)示著國(guó)家命運(yùn)的走向。對(duì)晚明士人身份覺(jué)醒與美學(xué)思想轉(zhuǎn)向的研究,也是在明晰晚明時(shí)代各方面的發(fā)展脈絡(luò),如何在創(chuàng)造中探尋物欲與情感的尺度、找尋自由與世俗生活的平衡依然值得思考,同時(shí)也為當(dāng)代文藝發(fā)展提供一定的啟發(fā)與借鑒意義,有助于為當(dāng)代奢華的美學(xué)消費(fèi)主體思潮帶來(lái)反思,并為美好生活系統(tǒng)的建構(gòu)展示出傳統(tǒng)文藝的主體力量及其獨(dú)特貢獻(xi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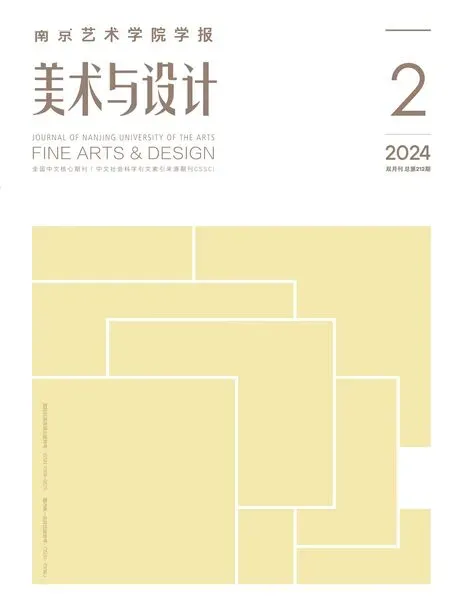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的其它文章
- 春 天
- 語(yǔ)言之思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的雙重變奏
- 張杰創(chuàng)作中的社會(huì)學(xué)敘事與觀看之道
- 宗旨、體制與革命:高等美術(shù)教育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美術(shù)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三重維度①
- “以竹代塑”的審美倫理意蘊(yùn)
- 布格爾法則的啟示:邁克爾·巴克桑德?tīng)柕恼Z(yǔ)境性藝術(shù)史闡釋策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