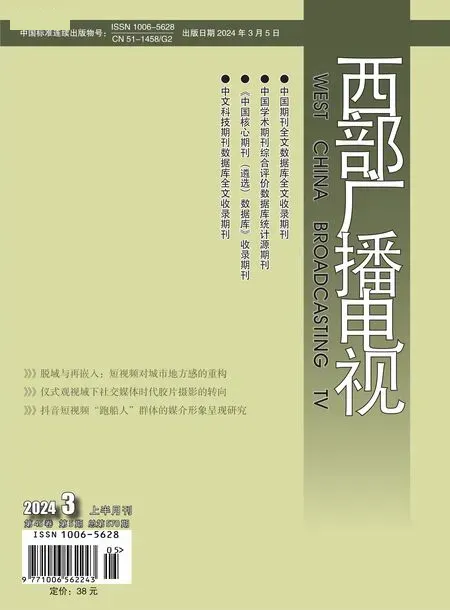人工智能浪潮下新聞傳播領域的風險及治理思考
張匯典
(作者單位:天津中醫藥大學文化與健康傳播學院)
1 新聞傳播領域人工智能的應用狀況
1.1 新聞采集智能化
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信息的采集僅僅依靠人力來進行。需要依靠記者本人去挖掘新聞線索或者接受大眾的投稿,以此來確定社會熱點并且需要深入走訪,進行實地考察,最終完成信息的采集。而在大數據時代,社會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集合體。身處于大數據時代中的事物都將會被數據化,一些細微的舉動也會被記錄下來。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加速了信息爆炸時代的到來。這就造成了傳統媒體時代的記者面對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時應接不暇,大大增加了對于有效的新聞線索進行搜集與分析的難度。在新聞傳播領域,采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海量信息進行搜集,即為“數據挖掘”[1]。媒體從業者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可以更好地獲得新聞線索,追溯事件的起源與經過;分析數據,優化報道策略以及擴大選題范圍。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線索主要靠記者搜集,但是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數量爆炸式增長,記者很難顧及所有的信息,導致對于關鍵的新聞線索有所遺漏。但是,記者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就可以將視野放眼到整個社會,在海量的信息中心精準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線索,大大減少了遺漏的可能性。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可以構建多時空的信息采集渠道,使得新聞信息的采集突破了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大大方便了記者獲取新聞線索,使得信息采集更加準確與快速,節省了采集過程中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目前,多家主流媒體將采集到的海量信息借助大數據技術進行快速整理、分析,提高了新聞的時效性[2]。
1.2 新聞生產高效化
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參與新聞生產的本質是將新聞記者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相聯結,新聞記者通過對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創作的內容進行把關,形成“把關人+人工智能”的人機協作的生產模式。人工智能參與新聞寫作的創作模式早已有之,早期的寫作機器人多進行的是一些簡單且重復的寫作,較為呆板與單一。但這時人工智能已經作為傳播者的身份而存在了。隨著G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利用自然語言技術以及基于神經網絡算法的深度學習技術的“把關人+人工智能”人機協作模式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人-機共創的模式標志著人機協同成為新型傳播者。利用自然語言技術以及基于神經網絡算法的深度學習技術,新聞記者只需要把標準化、結構化的關鍵詞輸入,并予以精準的指令,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可以從海量的數據以及大量的知識中學習,并且根據指令完成相應的內容創作,形成新聞初稿。新聞記者再根據一定的標準和規范對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創作的新聞初稿進行檢驗、核查、修改、潤色,最終形成能夠發布的新聞成品。這樣的“把關人+人工智能”的人機協作模式精簡了新聞采寫的流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在精準指令下生產內容,形成一篇新聞初稿的時間大大縮短,解放了新聞記者的雙手,記者不用進行重復單一的工作,而是將這項工作交給更適宜的人工智能,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進行全天候的工作,突破了人體的生理極限,解決了不同時間段記者效率不同的問題,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現階段“把關人+人工智能”的人機協作的生產模式多應用于體育新聞和財經新聞這類有固定格式的新聞,或者基于數據抓取、挖掘、統計、分析和可視化呈現的數據新聞,大大提高了新聞生產的效率。
1.3 新聞分發個性化
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在新聞信息采集與生產領域發揮著巨大作用,在新聞分發領域也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人工智能技術借助其算法,將新聞內容、特點與用戶喜好精準對應,實現新聞分發的個性化。個性化推送是指依據用戶自身行為和需求屬性建立不同標簽,進行精準消息推送的過程[3]。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術推動新聞分發領域發生了巨大變革。在傳統媒體時代,人們獲得的信息往往是被動接收與主動選擇相結合的結果。受眾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但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不想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受眾就只能被動地接收傳播者所傳播的內容。而在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收集用戶在每個內容的停留時間、互動頻率來判斷受眾的喜好,精準地構建用戶畫像,進而通過算法將傳播內容與受眾喜好精準匹配。即使一些小眾的、冷門的信息,也能夠得到精準的推送,減少了信息浪費。雖說將內容集中推送給了部分受眾群體,但觸達率更高。在新聞傳播領域,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對受眾的心理狀態、個人需求和行為模式進行深入分析,能夠精準預測用戶的瀏覽傾向和偏好,進而有針對性地為受眾提供更加貼合實際需求的新聞報道,使報道實際作用得到有效發揮[4]。
2 新聞傳播領域應用人工智能面臨的困境
2.1 新聞內容同質化和淺薄化,虛假信息滋生
人工智能應用于新聞的采集、生產與分發過程帶來了許多便利,但同時一些問題也不可忽視。人工智能技術只通過模式化的程序將采集到的信息嵌套在一個模板之中,進而形成新聞。這樣就極易導致同質化現象的出現。針對某種特定類型的新聞,可供選擇的模板較少,雖然生成的新聞有所不同,但相似度過高。而且,人工智能不是人腦,不具備意識,也并不能夠代替人腦進行思考,不具有主觀能動性,因此只能生成特定類型的新聞,例如財經新聞和體育新聞。這樣就導致了人工智能技術生成的新聞內容淺薄化。此外,人工智能技術不能應用于新聞評論和深度新聞報道。一是人工智能不具備思考的能力,二是人工智能技術相較于人類來說缺少人文關懷,因此也就難以實現與用戶的共鳴。
人工智能技術為新聞傳播領域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為虛假信息的滋生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技術面對大量的信息時,如何精準地捕捉線索且精準地轉化為新聞仍是一個技術難題。面對的信息數量眾多,一旦產生細微的誤差就會使整個新聞生產的過程產生偏離,最終導致虛假信息的滋生。此外,由于人工智能不具備人類的思考能力,因此在生產新聞時只能進行篩選匹配,而無法進行精密的邏輯化思考。人工智能面對自己無法思考的問題時,為了完成下達的指令,就會出現“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現象。這也是虛假信息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2.2 算法分發導致“信息繭房”
算法通過與受眾的“互動”,將符合受眾需求的內容精準推送給受眾,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們篩選信息的壓力,使得小眾冷門的信息也可以推送到相應的受眾的界面。但是,算法將用戶喜好與新聞內容精準匹配實現個性化傳播的同時也導致了“信息繭房”的出現。桑斯坦提出人類對信息具有選擇性認知的傾向,公眾只注意到那些包含自己選擇的東西以及使自己愉悅的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束縛于蠶繭一般的“繭房”中[5]。算法根據用戶的興趣與和內容的關聯度篩選內容,用戶只能接收到自己感興趣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受眾選擇信息的權利,久而久之受眾的思維就會固化。而受眾的思維越是固化就越是不愿意接觸自己不感興趣和不認同的信息,進而加固“信息繭房”。
“信息繭房”現象的出現使得用戶可選擇接收的信息范圍變小,思維逐漸固化,一直處于一個自身獨立的固有認知世界里面。這樣就極易導致用戶一旦接收到與自己不相符的觀點就會變得偏激,認為與自己相悖的觀點才是個例。現如今,“信息繭房”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內容推送方面,就連評論也是被算法篩選過后才向用戶呈現的與自己看法相同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新媒體平臺上的評論區中,一旦有用戶看到與自己相悖的觀點,就會在評論區互相攻擊。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這一現象極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來操縱輿論,危害網絡空間的健康與清朗。
2.3 難以保障他人的隱私權與知識產權
人工智能技術背靠海量數據庫,依賴數據分析和構建模型來實現新聞的采集、生產與分發。但這種模式面臨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和隱私權的風險。第一,人工智能技術背后的海量數據是通過搜集他人現有的知識與信息構成的,所生產的新聞和數據有著緊密的聯系。這樣一來就極易造成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現象。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生成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加工他人的知識與信息,經過特定的程序而產生的,這樣一來,對于原有信息的來源與擁有知識產權的作者就難以追蹤,無形中增加了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風險。第二,人工智能的數據庫中收集到的他人的個人信息是否經過本人的同意,如果沒有經過他人的同意便私自收集那么就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在新聞分發方面,一些不良機構為了增加作品的閱讀量與瀏覽量,會利用人工智能進行“竊聽”,人們經常發現自己剛說過想要獲得什么內容,該內容就出現在了手機上。毫無疑問,這種做法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盡管我國已經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相關法律,但是不法分子仍頂風作案,游走在法律的邊緣,侵犯他人隱私權的事件時有發生。
2.4 壓縮新聞從業者的就業空間
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應用再次引發了從業人員關于“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的討論。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技術參與新聞傳播,使得新聞生產的效率提高,新聞分發也不需要記者過多地介入,人工智能代替了記者的部分工作,許多新聞媒體開始裁員,新聞從業者的就業空間被壓縮。人工智能技術使得部分簡單重復的腦力勞動被取代,也沖擊了原有的新聞生產流程,勞動力市場對于新聞從業人員的需求也就大大下降。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術相較于人類來說具有無限的精力,更能適應新聞生產的全時性,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滿足了受眾對于新聞時效性的要求。
誠然,人類的思考與判斷能力以及人文關懷不能夠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人工智能的出現大大沖擊了新聞從業者的就業結構,一些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新聞從業人員更多地扮演了把關人的角色。在人工智能的沖擊下,正確熟練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是未來新聞從業者必備素養,這對于相關人員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個提升個人能力的機遇。
3 新聞傳播領域合理合法應用人工智能的路徑
3.1 堅持新聞從業者的主體地位,強化人機合作交流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出現了很多關于“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的討論。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新聞行業結構,壓縮了新聞從業者的就業空間,但作為有思想的人類,是不能完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雖然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媒體在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新聞生產時也要明確與堅持新聞從業者的主體地位。
人工智能的產生是為了服務人類,因此也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新聞從業者應該做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實現更好的新聞生產,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技術操縱,最終淪為技術的奴隸。相較于人工智能能對海量數據進行采集、分析與處理,能高效地生產新聞,新聞從業者也有自己的優勢。面對人工智能沖擊帶來的就業壓力與失業風險,新聞從業者應該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一是提高自己的專業素養,運用自身的新聞敏感性,精準把控最能引起受眾共鳴的最有價值的新聞線索,深入挖掘新聞內容,最終產出高質量、有思想的新聞。二是學習掌控人工智能技術,強化人機的交流與合作,讓人工智能為人所用,彌補人類自身的生理局限,強化自身能力,最終強調自身的主體地位。
3.2 優化分發機制,打破“信息繭房”
人工智能基于用戶搜索的關鍵詞,為用戶提供其感興趣的新聞內容,減輕了受眾在信息爆炸時代篩選信息的壓力,實現精準傳播。但是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信息繭房”現象悄然出現。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進行新聞分發的同時,也需要時刻警惕“信息繭房”,優化分發機制,保證受眾能夠接觸到不同領域的信息。
一方面,可以豐富個性化推薦算法所依據的數據記錄,擴大分析范圍,不將判斷標準局限于某一范圍。人工智能的算法推薦一般是基于用戶搜索的關鍵詞、頁面停留時間、瀏覽內容等數據。因此,新聞工作者可豐富人工智能算法所依據的數據記錄,擴大分析范圍,并考慮到用戶的整體行為習慣和社會信息環境的變化[6],讓用戶能夠接觸到更為廣泛的信息。
另一方面,要保障用戶的知情權。向受眾公開人工智能的算法推薦機制,讓受眾知道什么是“信息繭房”,怎樣盡可能地避免“信息繭房”。新聞工作者要加強關于人工智能的科普宣傳,讓受眾明白自己所看到的內容并非與其他人的一致。新聞工作者要有意引導受眾瀏覽其他領域的內容,擊破“信息繭房”,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
3.3 健全法律法規,合法利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把“雙刃劍”在新聞傳播領域中廣泛應用,其為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和隱私權的問題也時有發生。為了盡可能地規避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就要健全法律法規。
一方面,國家要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人工智能數據的采集范圍作出明確的規定,細化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和隱私權的懲罰條款,并明確新聞機構和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
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也要加強自身的法律意識,承擔好把關人的責任與義務。在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新聞生產時,要加大審核力度,盡可能地規避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隱患,避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情況。要嚴格遵守審核流程,每一環節都要做到認真核查,最終在新聞里標明由算法生成的字樣以及各級審核人員,將責任落實到每一環節。總之,要合理合法利用人工智能,最終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傳播領域作用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