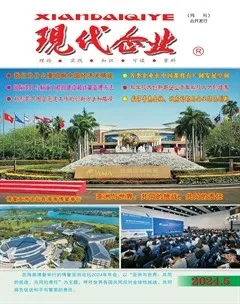關于國家出資企業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
杜庭赫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關于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職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后,對于國家出資企業中工作人員的范圍,理論和實務皆存在爭議。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以及規范性文件的有關規定,采用體系解釋的方法,認為《意見》所稱的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應為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黨委或黨政聯席會議,以及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其批準或者研究決定應等同于《刑法》所稱的委派;在各種條件的限制下,《意見》并沒有擴大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其所做的規定具有合理性,能夠起到保護國有資產的目的。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出資企業是國家為了更高質量發展市場經濟、刺激經濟主體的能動性,從早先的國有企業改制而成。這種改制不可避免地帶來企業性質以及從業人員主體身份的變化,即企業不斷脫離行政化,企業中的從業人員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因此,對于國家出資企業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其涉嫌職務犯罪時就不能僅以其是否從事公務作為其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為判斷標準,還要考慮到是否接受過行政性質的任命。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下發的《關于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職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6條規定:“經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提名、推薦、任命、批準等,在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具體的任命機構和程序,不影響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經國家出資企業中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批準或者研究決定,代表其在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經營、管理工作的人員,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從規定來看,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不具備國有公司、企業的性質,單純在其從事公務的人員并非是《刑法》所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如果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就應當同時具備程序性要件,這種程序性要件分為兩種情形:或受到“國有單位委派”,或受到“監督組織任命”,只有當行為人同時具備程序要件和實體要件時,才可以被評價為《刑法》所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否則,只能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進行刑事處遇。
這里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當不同的行為人在同樣性質的國家出資企業中承擔著相同、相似的職責,主觀上具備著同樣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同種的不法行為、造成了近似的危害結果,最終卻以不同的罪名論處。對此,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是否合理?另外,從法律條文、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頒布的其他司法文件的規定來看,我國法律條文本身是以“委派”和“公務”作為判斷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中的工作人員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標準,而《意見》則額外規定了以出資企業中特定組織的批準和決定作為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要件,其是否超出了《刑法》條文的文義?或是以國家出資企業中特定組織的任命作為“委派”的一種形式?若是,這樣的解釋能否符合法教義學的要求?
在解決上述問題之前,首先要厘清《意見》所帶來的幾個問題。一則是如何理解《意見》所稱的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二則是《意見》第2款所規定的內容是否與《刑法》所規定的“受委派”互相排斥;本文將對這幾個問題分別進行探討,以便能從教義學的角度上驗證司法解釋的規定的合理性。
二、明確《意見》所述的“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
關于何為《意見》所稱的“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理論與實踐一直都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意見》所稱的“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即是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以及上級或本級國家出資企業黨委、黨政聯席會,司法實務也基本采取這種觀點,但該觀點存在諸多瑕疵之處。第一種觀點認為,《意見》第6條第2款的規范表達是“國家出資企業中”,從文義的角度進行理解,“負有管理、監督職責的組織”應為該國家出資企業內部的組織,而上訴單位顯然不是出資企業中的組織。此外,若將上述單位等同于《意見》所稱的“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便會與第1款的規定別無二致。申言之,該觀點的內容值得商榷;第二種觀點認為,“負有管理、監督職責的組織”僅為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黨委和黨政聯席會議,不應包括國家出資企業中的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其認為,將黨委認為是《意見》所述的特定組織符合我國國家出資企業的實際情況,而董事會、監事會等是對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全部資產承擔職責,而不僅是對國有資產承擔職責,若將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認為是《意見》所稱的特定組織,就會導致國家出資企業中工作人員認定范圍的不當擴大。該觀點的理論有待商討,因為《意見》第6條第2款不僅規定了特定組織任命的形式要件,還規定了從事公務活動的實質要件,即便大多管理人員會由上述會議任命,但其未必會從事《意見》所規定的組織、領導、監督、經營、管理的工作,故而將股東會、董事會等排除于特定組織之外也不盡合理;第三種觀點認為,這種特定組織應為企業中的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而不包括出資企業中的黨委和黨政聯席會議。該觀點主要是從系統解釋的角度,將《意見》與《企業國有資產法》的規定相結合,其認為《企業國有資產法》尚未規定出資企業中黨委的權責,而在現代公司治理模式下,黨委并不必然對公司重大事務進行管理和監督,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將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認為是黨委或黨政聯席會是不恰當的。該說以《企業國有資產法》并無對黨委權責的規定來否認黨委不具有監督、管理國有資產職責是不周延的,且其未對黨委并不必然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給予理由;另有觀點認為,《意見》第2款的規定不當擴大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在國家出資企業中,根本不存在“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同樣也不存在代表其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經營、管理工作的人員,其認為,首先,出資企業中的黨委不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的職責,而黨政聯席會議也不屬于《意見》所稱的“組織”;其次,國家出資企業的資產屬于公司所有而非國家所有,國家只是作為股東享有出資者的權利,并沒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的權力,照此邏輯,也不會有任何人能夠代表國家從事所謂的組織、領導、監督、經營、管理工作。該觀點同樣存在著幾點不妥之處,其一,為何出資企業中的黨委不負有管理、監督國家資產的職責,該觀點并無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其二,該觀點立足文義解釋,闡述黨政聯席會議僅是黨組織與行政組織的會議,并非《意見》所規定的“組織”,可問題是,“組織”一詞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僅從文義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并得出否定性結論,是否符合教義學的標準?其三,該觀點認為,國家出資企業不歸屬于國家,國家只有出資人的權利而無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權力,若如此,國家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意義何在?此種觀念能否符合國企改制的初衷以及能否與其他司法文件相銜接皆存在疑問。
本文借對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檢討之機,認為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應為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黨委或黨政聯席會議以及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具體原因如下。
(一)國家出資企業中存在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的組織
反對國家出資企業中存在特定組織的觀點認為,改制之后的國家出資企業,其產權歸屬于企業所有而非國家所有,國家僅僅享有出資者的權利,并不具備監督、管理的權利。從國企改制、國務院設立國資委的初衷來看,國務院在設立國資委時,就曾設想將國資委作為一個單純履行出資人的機構,學界也多有闡述國資委應做“干凈的出資人”的理念。故而該觀點在理論上并無錯誤,但卻忽略了中國國企改制后的現實情況,正如有學者指出,“從應然狀態看,國資委應是純粹的出資人,不行使公權力,但轉型時期的特殊國情還需要國資委承擔一定的公共職責”。這一點,從《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相關規定也能體現出來。
誠然,從最為理想的角度出發,對于國企改制之后的國家出資企業,國資委應當僅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其所包含的監督、管理權,也不過為出資人權中當然蘊含的權利,這是一種私法意義的權利,不應是公法意義的權力。否則,便又會重蹈改制之前“政企不分”的覆轍。可改革絕非是一蹴而就的,從現實角度分析,當改制后對國企監管“五龍治水”的情形消失后,確需國資委承擔對國家出資企業中國有資產監管的職責,以保證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在法律法規已經規定出資企業中的董事、監事、股東代表可以由國資委委派并向國資委匯報工作的情況下,一味地否定國資委具有該種職責,進而論證出資企業中不存在“負有管理、監督職責的組織”是不客觀、不現實的。
(二)特定組織應為黨委或黨政聯席會議及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
同“國家”一樣,“組織”一詞的概念具有抽象性,究竟何種機構是《意見》中所稱的“組織”,引發了實務與理論的爭議。從歷史沿革來看,“組織”一詞的大量適用,與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不無關系,繼而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沿用至今,這種意義上的“組織”,可以概括為是“黨與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一種政治實體”,而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解釋,“組織”即為若干人或群體所組成的、有共同目標和一定邊界的社會實體。以這兩種概念為依據,“組織”一詞可以包括企業、機關單位,也當然能包括黨組織。
由于國有資產的存在,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黨委成員多為上級機關、國資委以及政府組織部任命的,同時享有相關職級待遇。黨委對出資企業的控制,體現為黨委對出資企業中擔任領導職務人員的任命上,正如有觀點指出,根據黨管干部原則,改制后企業一般設有黨委,并有本級或上級黨委決定人事任免,而黨委成員又為上級人民政府黨委、組織部、國資委等機關任命,從這一點上看,被黨委任命的人員,在出資企業內從事監督、管理等活動時,具備相應的代表性,可以認定為是從事公務,進而以國家工作人員論。而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重大事項需要黨委的提前介入,也表明了黨委在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重要地位,佐證了大型國企改制后管理運營模式尚未發生大的轉變的事實,因此,將黨委或黨政聯席會議認定為是《意見》所稱的組織是合理的,能夠符合現階段懲治職務犯罪的需要。
除了國家出資企業內部的黨委和黨政聯席會議,股東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也應當成為《意見》所稱的特定組織。如上文所述,根據《暫行條例》的規定,國資委可以向出資企業中委派監事、股東代表、董事等高層管理人員參加股東會、董事會,并依國資委的指示發表意見、行使表決權,將履職情況及時向國資委匯報。相應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等也有類似規定,故而,國家出資企業中的股東會等高層管理機構也應當成為《意見》第6條第2款所稱的“組織”。
反對意見大多認為,國家出資企業中的高層管理機構不是僅對企業中的國有資產負有管理、監督職責,其輻射范圍是全部企業資產,故其更傾向于企業的盈利性,不負有監督、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參見唐亞南:《貪污賄賂案件裁判規則》,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頁。]況且除了上級機關任命以外,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是經過高層管理機構任命的,若依上述理解,便會導致國家出資企業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范圍不當擴大。[ 參見陳興良:《國家出資企業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及其認定》,載《法學評論》2015年第4期,第13-14頁。]從邏輯上分析,在國家出資企業中,國有資產和公司資產處于混同的情形時,出資企業中的高層管理機構在對企業全部資產進行監督、管理時,必然也會對其中的國有資產進行監督,更何況還會有上級機關委派的股東代表列席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情況。從現實狀況來分析,以中鐵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其在上市擴股之后,僅國資委投資的中國鐵建持股就達51.13%,加上中央匯金等財政部投資的國有金融類公司的持股,國家在中鐵股份有限公司中居于絕對控股地位,此時若仍以公司中的股東會等高層管理機構僅負責公司的盈利而不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的職責,難免會脫離我國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的實際情況。
三、特定組織批準或者研究決定應等同于《刑法》所稱的“委派”
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并不屬于《刑法》所稱的國有公司、企業。依照《刑法》第93條的規定,對于非國有單位的工作人員,只有在國有單位委派其到非國有單位從事公務時,才可將其認定為是“國家工作人員”。故而,是否接受委派才是認定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國家工作人員的標準。而《意見》第6條第2款并未直接援引“委派”一詞,而是以特定組織“批準或者研究決定”的形式來確認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一種理解認為,“委派”的本義,應是由外向內的委派,而在行為人未受到國有單位的委派以及“批準或者研究決定”的對象是企業內部的人員時,《意見》的規定便不完全符合“委派”的要件,從而擴大“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范圍。另一種意見則提出“間接委派”的概念,即認為區分是否“委派”的關鍵不在于形式來源,而在于其職位與相關國有單位是否具有延續性。基于此,即便是行為人的任職是由非國有單位選舉產生,也應當將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關于這個問題,不僅要從經驗層面進行分析,更重要的是應從規范的層面去探討。這里的規范層面,即包含了法律規范,也包括了文義規范。從《紀要》的規定而言,“所謂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種多樣,如任命、指派、提名、批準等。”從“委派”一詞本來的含義而言,其多表達上級對下級的職務安排,并無必然包括行為人需從一機關到另一機關的位置變化之意,相反,即便是企業內部之間的人員任命,也可用“委派”一詞,這與漢語語言本身的文義并不沖突。之所以會引發“內部委派”與“外部委派”的聚訟,緣由主要是法律規范長期以來的規定帶來的經驗層面的慣性思維,如《刑法》、《紀要》以及《批復》的規定皆重點描述的是“外部委派”,由此帶來了經驗上的慣性,誤以為“委派”必須是從外部進行委任派遣才是適當的。實際上,從分層授權的邏輯進行推導,當國資委等上級監督機關授予出資企業中特定組織監督、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和權力,特定組織具備“代表性”時,其任命、建議、指派、提名等任免行為體現的便是上級國家機關的意志,現實中,特定組織的任免行為往往還需匯報至上級機關并獲得批準或同意,任命方才生效。由此,特定組織便是代表上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行為人擔任某職務,這理應包含在“委派”一詞的語義中。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