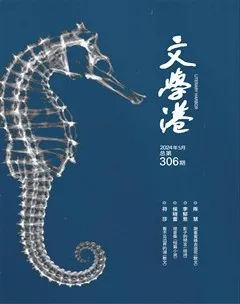那大串大串的螃蟹鉗子
王蘭飛
張根頭掄起斧子,使勁地劈下去,每使一下力,墊在他屁股底下的小板凳都會跟著震顫一下。木柴在斧下一劈兩半,張根頭垂了斧子,左手拾了劈開的柴火,隨手扔到傻子婆腳邊,傻子婆動作遲鈍,緩慢地拾起一塊木柴,走到院角的柴堆旁,把它放上去,再走過來拾起一塊,多一塊都沒有。
來人朝院子里張望了一下,又咳嗽了一聲,張根頭抬起頭來,見來人朝自己招手,便站起身,走出去。這時候,來人又朝傻子婆看了一眼。張根頭問:“啥事體?”來人將身子朝院墻邊縮了縮,輕聲說:“李英要接她娘過去住,李英娘不肯去,正在哭呢,你曉得嗎?”張根頭說:“她跟我說起過,我想年紀大了,還是跟女兒一起住的好。”“可是,李英娘不肯去,大家都說是因為你,她女兒說,如果是這樣,就要把她娘送到你家來。”
張根頭沉默了一會,一句話沒有,轉(zhuǎn)身進了院子,徑直在板凳上一屁股坐下,左手拿了一塊柴,右手高高掄起斧頭。來人的目光訕訕地收了回去,不知啥時沒影了。
張根頭站起身來的時候,傻子婆也不拾劈開了滿地的柴了,等張根頭又坐下,將劈成兩半的柴扔過去,傻子婆遂又彎下腰去。她只拾剛?cè)舆^來兩塊木柴中的一塊,所以,地上劈開的柴禾,總是比她拾起的多了許多。傻子婆不是又瘋又鬧,要讓人提防著的那種傻,她傻得出奇地沉默,在張根頭的感覺中,那是一種異常的冷漠。她神情凝滯,好像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目光茫然虛幻,使得她沉重的表情仿佛遨游在虛渺的太空里。這時,張根頭似有若無地瞟了瞟傻子婆,她毫無反應(yīng)地彎腰拾柴。
李英娘對女兒說:“張根頭在我們家進出也有十來年了,你沒嫁的時候也是阿伯、阿伯叫過了的,現(xiàn)在就不要去為難他了,我不愿離開這里,總是不想離開世世代代住的地方啊,人家臺灣人還要到這里來尋祖尋根,我老了卻要拔根離鄉(xiāng)。”李英娘忍不住又掉下了淚。這樣說了,心里想著,該到丈夫的墳頭去一趟,再去她爺爺奶奶的墳頭拜拜,想到這里,又撲簌簌滑下一串淚。這一天,她不知落了多少說不清是甜是苦是酸的淚。
從丈夫的墳頭望下去,整個西村像被一只手捏碎了的瓷碗,房屋碎片般零零落落地灑在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海的山谷盆里。村道上不見個人影,年紀輕的都喜歡往外搬,年紀大的就像燒完了油脂的木炭,沉默地蹲在灶窩里,再不愿挪動一步。李英娘在心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數(shù)著山下房子里還蜇伏著多少塊灶窩里的木炭,他們一動不動地伏著,保持著最后一點余溫,而自己卻要從溫暖的灶火洞里被抽出來,落到外面清涼陌生的世界里去了。
點上了香和蠟燭,李英朝著墓碑拜了三拜,父親離開她們二十多年了。小時候看到別人家的爸爸每次出海回來,都拎著大串大串的螃蟹鉗子、魚鲞干和許多烤熟曬干了的海鮮。李英就跑回家向母親要,有時要螃蟹鉗子,有時就要爸爸,結(jié)果常常只要得母親的一包眼淚和幾個巴掌。
嫁到東村去的海芬回娘家經(jīng)過她家門口時,都會從袋里掏出一串海鮮,送給李英。她帶著好看靦腆的笑容說:“每次船來,我都會給你留一串螃蟹鉗子的,你等著我好了。”但是沒等幾年,海芬就不再回娘家來了,聽說她一夜里吹著了歪風(fēng),成了傻子。以后倒是李英娘常常提著自家種的蔬菜瓜果去看她。后來,海芬的丈夫張根頭替海芬送螃蟹鉗子來給李英,但這時候李英已經(jīng)成了姑娘家,不再稀罕這些了。
李英盯著墓碑上父親的名字,但是父親的容貌卻想不出個依稀來。李英娘摸著丈夫身旁一墓空穴上的黃土說:“等我死了,你還要乘車乘船的把我運過來,要多麻煩了啊。”
張根頭年輕時,名字后面沒有多出一個“頭”字來。張根結(jié)婚上七個年頭時,漁船在出海回航的途中遇上了風(fēng)暴,船員們在狂風(fēng)惡浪里日夜拼搏、顛簸,大伙筋疲力盡,快要癱瘓了。有人說,誰來講個笑話,給大伙提提神,平時最喜插科打諢、綽號“鐵拐李”的眼睛頓時亮了。他說,我給你們講一個老輩子西村里發(fā)生的事,聽說老輩上頭,西村里嫁過來一個媳婦,長得要臉兒有臉兒,要段兒有段兒,要多俊有多俊。“到底是啥樣的臉兒段兒啊?”大伙來勁了。“鐵拐李”巡視了一遍,最后朝張根一呶嘴,說長得跟張根媳婦差不離。張根媳婦在東村是出了名的美人兒,大家都滿意地笑了,催“鐵拐李”快點講下去。那媳婦不但俊俏,而且聰明,可惜男人年年月月出海在外,在家日夜守著空房的即使是貞潔女也終難敵天長日久糾纏的多情郎。有一個長得像西門慶一樣的男人,天天在她家門口轉(zhuǎn)悠,挑誘,最后終于鉆進了她的巢臼。有一天夜里,倆人正在歡愉之時,忽聽房門咚咚咚地敲響,那西門慶也是個冒牌貨,竟然嚇直了腿,任那媳婦越是拖他快出來,他卻越要扯了被子往頭上蒙。媳婦沒法子,只好去開門。原來是丈夫夜半回船來,丈夫性急地要往內(nèi)房奔,媳婦硬是拖他上灶房去,說他在海上打魚有多苦多累,回家來,一定要好好吃頓半夜餐,補補身體。那憨牛丈夫被妻子的甜言蜜語哄得合不攏嘴,自家釀的又香又甜的米酒不知灌了多少碗,喝得兩眼昏花,四肢無力。
媳婦以為那西門慶該鉆到床底下去了,就扶著丈夫進房。哪想那人還直直躺在床上哆嗦著呢,媳婦又氣又嚇,一松手,丈夫就一骨碌翻進床里了,那媳婦急中生智,跳進床,夾在他們中間。丈夫雖然喝醉了酒,但是心里想,良宵一刻值千金,一定要挺住。可是他發(fā)現(xiàn),床尾上怎么伸著六只腳?他想兩個人合起來只有四只腳啊,他奇怪得很,就爬到床尾去數(shù),數(shù)過來又數(shù)過去,明明只有四只腳。他想可能是自己喝多了,看花了眼,就美滋滋地爬到媳婦身上去了……大伙聽了笑得合不攏嘴,張根也笑著,但是心里卻不是什么滋味,他的媳婦就是從西村嫁過來的,而且也是美麗聰慧。“鐵拐李”怎么拿她跟自己的媳婦比呢?他越想越不是味,就暗自氣呼呼地睡覺去了。
深夜時分,船漸漸靠攏碼頭,張根早已立在船頭,還未待船靠穩(wěn),就一個箭步跳上岸去,飛也似的朝家里趕去。進了院子,剛要喊,卻見窗戶里映著的燈光忽地滅了。張根想起“鐵拐李”講的事,便一腳踹開了門,扯亮了電燈,一把掀了床被,果然,看見自己的媳婦和一個男人赤裸裸地糾纏在一起,他媳婦還媚笑著對張根說:“你回來了。”張根見此情景,腦門忽地一熱,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知覺。
恍惚中有人喊:“起來,起來,船進港了,回家再睡個痛快覺去。”張根睜開眼,這才發(fā)覺自己剛才做了個噩夢。張根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涌起一股比在風(fēng)暴中生死難料更加強烈的恐懼,想想夢中發(fā)生的事,整個人禁不住顫抖起來,他無比煩悶地打開一瓶酒。
船穩(wěn)穩(wěn)地靠上了碼頭,張根已喝得兩腿有點輕飄,他提著心,一步一步地走過跳板,站在了水泥碼頭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腥味的海風(fēng),抬頭望見一彎明亮的刀月懸在天空,就不顧一切地朝家里奔去。
以前,張根夜半回家,總是剛進院子就扯開了嗓門喊:“海芬——海芬——”今夜,他卻鬼使神差般,躡手躡腳地走到門口,在門上咚咚咚地敲。屋里沒人答應(yīng)。張根的血液順著酒氣突突地冒上來,他用腳踢著門,大聲叫著:“快開門!快開門!”海芬慌里慌張地打開了門,驚魂未定地問:“你回來了,出什么事了?”張根不答話,徑直朝房里奔去,一把掀開被子,什么也沒有。但是被酒精浸透的血液已浸入他的頭腦,占領(lǐng)了他的意識,他轉(zhuǎn)身朝她凸出憤怒的帶血的瞳仁,厲聲問:“你把人藏哪去了?”海芬茫然地說:“你說什么呀?”張根驀然性起,一把揪住她的頭發(fā),順手就朝房柱上狠狠地撞了過去,只聽見嫩葫蘆開瓢似的“卟”的一聲,眼見著媳婦一聲沒吭,就軟癱癱地倒在了地上。張根這才回過神來,急忙捧起她的頭,看看沒有血,就抱起媳婦小心地放到床上。
那天夜里,李英娘已經(jīng)睡下了,張根頭來喊她開門。他說,早上傻子婆又犯傻了,把一痰盂糞便倒在了屋門口,又坐在糞便上想“心事”了。張根頭費了好大勁,才把她弄進屋里,洗了身子,換了衣服,又做飯燒菜,好不容易喂了她幾口,忙了整整一天,直到伺候她睡著。張根頭這才默默點上了一根煙,想到李英娘清爽、利索的身影,遂帶上了門,摸黑到李英娘家里來。
李英娘說:“我不是跟你說過,趁我現(xiàn)在身體還硬朗,你家不是空著幾間房,給我一間住住,我就當(dāng)鄰居一樣照顧你們,等我老得不會干活了,我就搬到女兒家去,你還有什么不放心的?”張根頭低下頭說:“我老了,海芬的事在心里窩了二十多年了,別人都說她有福氣,嫁了我這么好的老公。老天爺曉得啊,老天爺懲罰我,我心甘情愿受罰,這輩子還不了,下輩子還要還她。我知道你的心跟她一樣好,可是我不能在她面前再對著你,良心不安啊!”
李英娘聽了張根頭的話,心里想起死了二十多年的丈夫,一股酸酸的咸水,暗暗吞進了肚里。她嘆了口氣說:“如果不是惦著海芬妹那些年常常送給我家英兒螃蟹鉗子吃,我也不會三天兩頭地去看她,我們兩家人也不會當(dāng)一家人來往,這么多年過去了,她對我的情,我也算還過了。你還耿耿記著你欠她的,我也不為難你了,今后,我做人做鬼都不會進你張家一步了,唉!都是罪孽啊!”
李英借來一輛木板車,把一些衣服和娘舍不得落下的什物,一并放到車上。李英娘整理好了一切,就坐到床榻上,低頭默想了一會,干枯的眼眶漸漸潤汪起來,不一會兒,李英娘的哭聲就像村里早起的炊煙,悠悠裊裊地飄蕩開來。幾乎每個老人離開這個已成荒落的村莊時,都會抑揚頓挫地哭一場,這好像成了一個不約而定的告別儀式。這哭調(diào)跟送親人上山一樣悲戚,而李英娘的哭聲里又多了一種說不出的哀怨。
李英叫娘也坐到板車上去,木板車載著李英娘,抽泣著走出了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安棲的家園。
路過東村的時候,李英娘原本嘻在喉嚨里的哭聲又放開來,李英張了張口,沒出聲。張根頭的家離村口只隔了一條巷,哭聲恍恍惚惚地飄了進來,張根頭提著心的手不由自主地抖起來,他拿了一塊木柴,怎么也立不住。這時,彎著腰撿柴火的傻子婆,突然抬起頭,怔怔地盯住張根頭,驀然問了一句:“是誰在哭啊?”張根頭心驚地低下頭,暗啞地說:“大白天的,誰會哭啊,你聽岔了吧?”傻子婆聚精會神地呆了一會,繼而,目光又渙散開去,李英娘的哭聲漸遠漸逝。
原載于《群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