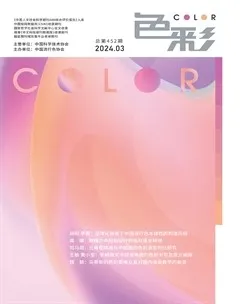李娟散文中綠洲地理的色彩書寫及意義闡釋
王敏 黃小瑩

摘 要:縱觀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中的色彩書寫,極大地擴展了文本寫作的情感表現(xiàn)與敘述內(nèi)涵。作為一名新疆作家,李娟在其散文中呈現(xiàn)出了親和新疆綠洲地理色彩書寫,綠、藍、金三色是其寫作的主色調(diào)。本文通過對其描寫空間中色彩的交融碰撞、單一色彩渲染情感氛圍、多重色彩營造意境空間這三種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分析,意在闡明揭示出了李娟散文書寫的生命蘊含以及審美召喚在文本中的呈現(xiàn)特點。總體而言,李娟色彩的書寫呈現(xiàn)出了一種從感覺精神層次的色彩反映到感情精神層次的色彩表現(xiàn),以及人的全面精神在色彩藝術(shù)中的升華的三階段,展現(xiàn)出了其色彩書寫的藝術(shù)道路。
關(guān)鍵詞:李娟;散文;色彩書寫;綠洲地理;審美召喚
Abstract: Color writ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narrative connotation of text writing. As a writer from Xinjiang, Li Juan presents the geographical colors of Xinjiang oasis in her prose. Green, blue and gold are the main colors of her writ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ree artistic expression modes, namely, the blending and collision of colors in the description space, the rendering of emotional atmosphere by single colors, and the cre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space by multiple colors,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and reveal the life implication of Li Juans prose writing and the pres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call in the text. In general, Li Juans color writing presents three stages from the color reflection of feeling spirit level to the color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spirit level, as well as the sublimation of peoples overall spirit in color art, showing her artistic path of color writing.
Keywords: Li Juan;prose;color writing;oasis geography;aesthetic calling
0 引言
在現(xiàn)當代文學寫作中,色彩書寫屢見不鮮。張愛玲的小說中將色彩與感官意象交織,暗示隱秘情感的壓抑扭曲;艾青詩歌中將色彩賦予土地及太陽意象,展現(xiàn)出了極具象征意義的色彩書寫;莫言的小說中通過反復(fù)運用紅色描寫,展現(xiàn)出高密東北鄉(xiāng)澎湃原始的生命力;蘇童的小說以色彩意象取勝,賦予小說極富隱喻意義的情感表達。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中色彩的書寫極大地擴展了文本寫作的情感表現(xiàn)與敘述內(nèi)涵。在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中,對綠洲地理的較高頻次的色彩書寫展現(xiàn)出了極具地域性與景觀性的審美意蘊。北疆大地上的森林草原、河流天空、日光沙丘、白樺林與向日葵地都是可被顏色附著意義的審美對象,并以極具視覺沖擊的色彩表現(xiàn)呈現(xiàn)于接受者的視野之中,召喚著讀者們進入綠洲地理的色彩空間場域。總體而言,李娟散文中的色彩書寫呈現(xiàn)出了新疆綠洲地理的色彩風貌,以親和自然的原色書寫展現(xiàn)出了色彩之美,并重新喚起了我們對自然色彩的感官體驗與美學認知。在這一過程中,李娟的色彩書寫呈現(xiàn)出了一種從感覺精神層次的色彩反映到感情精神層次的色彩表現(xiàn),以及人的全面精神在色彩藝術(shù)中的升華的三階段,展現(xiàn)出了其色彩書寫的藝術(shù)道路。
1 李娟散文中綠洲自然色彩的書寫
李娟的色彩書寫以綠洲地理為背景,書寫自然色彩的原始風貌,并通過色彩書寫構(gòu)建起了一幅北疆大地的多彩畫卷。在李娟散文的書寫中,其以個人的情感體驗與視覺經(jīng)驗構(gòu)建起了綠洲地理風貌的色彩書寫以及其間的牧民轉(zhuǎn)場遷徙、農(nóng)人耕作勞動的綠洲生活圖景。李娟在書寫色彩時,著力突出了色彩的自然屬性以及區(qū)域色彩文化符號,以綠色深染森林草原之色,以藍色潑墨天空河流之色,以金色點染白樺林、向日葵之色彩,由此突出了綠洲地理自然色彩的書寫。
1.1 自然綠色的書寫
李娟以綠色書寫勾畫出了草原、森林、沼澤、戈壁等綠洲自然的地理面貌。李娟的色彩書寫以遷徙行走作為觀看視角的遷移,進行地理空間色彩的感知與書寫,就此來看,行戈壁、進草原、穿森林構(gòu)成了其獨特的行走與觀看視角。當李娟身處高處,俯瞰整個荒野戈壁,綠色是最顯著的顏色。烏倫古河拖曳出了荒野中最濃烈的一抹綠痕,緊緊依附在河流兩邊的綠色林帶和田野也宛如一條綠色的生命之河。這條綠色的生命之河滋養(yǎng)出了戈壁中人們賴以生存的綠洲環(huán)境。當李娟進入戈壁,綠色是生長在周圍的大面積耕地農(nóng)作物,綠色就在前方,而兩邊的綠色則漂浮而起,如夢幻一般。隨著戈壁上向日葵的蓬勃生長,一片綠色海洋也拔地而起,綠洲戈壁也發(fā)生了變化。當李娟隨著牧民由荒野戈壁進入前山夏牧場繼而轉(zhuǎn)入深山夏牧場,草原森林的顏色也發(fā)生變化。進山處先是淺綠而后是深綠,進入深山則是一個均勻的綠色世界,由此到達水草豐茂的深山夏牧場。跟隨牧民的轉(zhuǎn)場遷徙,戈壁、草原、森林、前山夏牧場、深山夏牧場中的綠色由淺變深,由點染到鋪陳,其色彩變化也逐一在我們的眼中展現(xiàn),與此同時,我們也在閱讀中也建構(gòu)起了以綠色作為底色背景的綠洲地理空間。
1.2 潑墨藍色的書寫
李娟以潑墨藍色勾畫出了天空河流的形態(tài)變化,并在跟隨牧民轉(zhuǎn)場遷徙的過程中,展現(xiàn)了不同狀態(tài)、不同季節(jié),天空河流顏色中純度與明度的變化。行走在荒山,藍天凜冽,藍色的飽和度極高,似要滴下一滴“藍”;進入森林深處,抬頭看天,藍天則如燃燒一般,藍得灼人;身處深山夏牧場中則在白色雪山、墨綠森林的映襯下,“天空藍得響當當”[1]223。這三處地點關(guān)于藍天的描寫中,根據(jù)周圍遮擋物、陽光透射率的不同而呈現(xiàn)出了程度不一的飽和度與透明度的藍色,同時,其色彩書寫也展現(xiàn)出了感覺精神層面的色彩反映。在游牧遷徙的過程中,雨天不可避免,下雨前后天空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藍色。下雨前的藍天,“一汪巨大的圓形藍天停止在那處,像是立刻會有湛藍冰冷的液體傾潑下來。”[1]252雨后的天空,有白云出現(xiàn)在藍天中,天色為湛藍。在牧民遷徙的過程中也偶有深夜舞會,深夜行走在去舞會的路上,天空色彩的呈現(xiàn)也別具特色。傍晚的藍天,“藍幽幽的,只有幾團薄薄的絮狀云霧”[2]147;深夜的藍天,“天空光潔,因鍍滿月色而呈現(xiàn)迷人的淺藍。”[3]李娟在形容冬天河流的色彩呈現(xiàn)時也多用藍色,冬天的大河是寶石藍色,是寒氣逼人的,如一川碧玉;結(jié)著冰的小河則是幽幽發(fā)藍。天空與河流作為李娟參與遷徙轉(zhuǎn)場生活中的日常所見,在其極為豐富的視覺體驗中,通過其感覺精神層面色彩反映的不同,展現(xiàn)出了不同程度飽和度與透明度的藍色。
1.3 燦爛金色的書寫
最后,李娟以向日葵、白樺林、麥田、蘆葦?shù)壬食尸F(xiàn)的鋪排書寫展現(xiàn)了金秋大地的絢爛。《遙遠的向日葵地》中專寫《金色》一篇著力鋪排金秋時節(jié)的色彩呈現(xiàn)。萬畝葵花的金色是亮堂堂的金色;白樺樹的金色是光芒四射的黃金;麥田的金色則富于深沉的安撫力量;飼草的金色是高處的光明;蘆葦之金,水氣充沛,它最脆弱,最纏綿,最無助;月亮的金色是黑暗的金色,孤獨而自由;蜜蜂是最微小的金色;蜂蜜的金色則蘊含著億萬公里的金色飛翔——面對這全部的金色,葵花緩升寶座,端坐一切金色的頂端。秋天的金色成為了李娟散文中最溫暖、最安心、最沉穩(wěn)力量的色彩書寫。
在李娟的散文書寫中,其色彩多取自草原、森林、河流、天空、金秋萬物,并在以綠色、藍色、金色為主的色彩書寫呈現(xiàn)出了一種親和自然的色彩形象。在綠洲自然地理風貌的展示下,李娟的散文以綠洲地理色彩的原色、純色勾畫出了綠洲多彩風貌的自然景觀。
2 李娟散文中綠洲地理的色彩表現(xiàn)形式
在李娟的散文中以綠、藍、金三種色彩書寫為主,展現(xiàn)出了親和自然的綠洲地理的自然色彩書寫。深入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李娟散文的色彩書寫主要呈現(xiàn)為三種表現(xiàn)方式,其一為空間中色彩的交融碰撞進而展現(xiàn)出綠洲地理空間的顏色與形體;其二,表現(xiàn)為以單色著力渲染散文的情感氛圍;其三,表現(xiàn)為以多重色彩營造散文的意境空間。
2.1 空間中色彩的交融碰撞
趙樹勤在《當代女性書寫與現(xiàn)代繪畫色彩美學》中說道:“從繪畫的發(fā)生意義上看,對視覺印象的表現(xiàn),作為形式構(gòu)成的基本原素,色與形當然是共生的。”[4]在綠洲地理空間的自然布局下,色彩呈現(xiàn)出了延伸、蔓延、擴展,進而構(gòu)成了空間中色彩的交融碰撞,并在視覺范圍內(nèi)形成局部關(guān)系感。
李娟在《坐班車到橋頭去》中寫坐班車從橋頭到富蘊縣的經(jīng)歷以及從富蘊縣回橋頭的記憶,她詳細記錄了班車從高原到丘陵再到盤山道烏恰溝進入平原戈壁的景觀。班車經(jīng)過可可蘇之后,翻越達坂,在半山腰的視野中,只有色塊與色塊之間的碰撞,充斥在山間的腹地。“從半山腰往下看,眼前又是一處平坦開闊的山間腹地,金色的向日葵鋪滿了左邊的視野,而右邊是苜蓿的海洋。中間的道路平直、漆黑,被兩排高大整齊的樹木夾簇著。更遠的地方是青白色的伊雷木湖一角。”[5]153車行高處,目之所及,大自然如調(diào)色板一般展現(xiàn)出了巨大的色塊之間的碰撞,遠處有青白色,近處則有金色與綠色的視覺碰撞,其間漆黑道路構(gòu)成色塊之間的分割,三種色彩,三種空間上的分布,在視覺的控制下構(gòu)成了色彩與造型的整體感,展現(xiàn)出了新疆自然地理的廣闊性與遼闊感。
《遙遠的向日葵地》(圖1)中則是寫北疆遼闊的荒漠戈壁的赭黃色與向日葵地蓬勃生長的綠色之間的碰撞。在遼闊的戈壁荒漠上,向日葵蓬勃生長,綠色波浪層層卷來,綠色的延伸、蔓延、擴展帶著一種震撼人心的綠色。這種震撼人心的綠色形成戈壁上的一片綠色,并與荒野戈壁的赭黃色形成了一種碰撞。而當向日葵收割之后戈壁的赭黃色再次顯現(xiàn),僅剩一條綠色林帶成為了唯一可以勾畫綠洲地貌的標識物。這部散文是以李娟對北疆綠洲中耕地變化深刻、精細、具體的感知為基礎(chǔ)而展開的寫作,并通過色彩與線條的勾勒呈現(xiàn)出了空間環(huán)境的變化。在李娟全面的感覺與感知中,色彩變化成為展現(xiàn)這片土地過去與現(xiàn)在的可視運動,并揭露出了土地地貌與生態(tài)的變化。
2.2 單一色彩渲染散文的情感氛圍
李廣元在《東方色彩研究》一書中談到,大量原始時期的遺跡向我們顯示,古人在開始發(fā)現(xiàn)色彩的長時期用色的單一性造成了視覺上色彩傾向,這種由單色所造成的傾向性從視覺感染力看更單純、更直接并進而可以形成某種具有傾向性的情感。[6]53,54綠色作為荒漠戈壁中最具視覺沖擊力的色彩,構(gòu)成了李娟散文中對綠洲自然地理最深切的色彩傾向以及情感投射。李娟散文中對單色的運用合乎色彩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基本的自然規(guī)律,因此其寫作也可以獲得游牧民族自然空間場域的審美感受與審美體驗。
李娟通過“綠色”營造出了一個原生態(tài)自然舒展的空間環(huán)境色調(diào)。其中“羊道三部曲”主要寫李娟跟隨哈薩克牧民的轉(zhuǎn)場,從南面的戈壁一路向北面的阿爾泰山脈遷徙流動的過程。從春牧場到前山夏牧場再到深山夏牧場,從春天到夏天的季節(jié)變動,從山腳到深山的景觀變化,在這其中“綠色”無疑是可以體現(xiàn)其地理景觀的漸變過程。當李娟遷徙到夏牧場后,描寫出了綠色所帶來的沖擊感受。“剛才一路上全是巨大的頑石與蒼翠的林木相交雜,去年的枯枝與先發(fā)芽的新綠斑駁輝映,而眼下卻是一個均勻的綠色世界,像鋪天蓋地披了條綠毯子似的。……全是綠地,全是沼澤。只有高一點兒的綠和低一點兒的綠,沒有深一點兒的綠和淺一點兒的綠之分。”[2]269完全到達深山草場時綠色則令人驚嘆。“這樣大面積的深綠和下面沼澤地清亮歡欣的淺綠撞合到一起,令整條寂靜的山谷充滿了驚嘆。”[1]185在李娟對綠色的書寫中,伴隨著從春到夏,從荒漠戈壁進入到森林草原的遷徙轉(zhuǎn)場之途,其色彩的變化也從新綠的斑駁輝映到勻綠的鋪天蓋地再到完全綠色的碰撞驚嘆。在這一場遷徙之途中,不同季節(jié)、不同牧場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色彩感覺,進而通過色彩的書寫凸顯出了感覺在處理色彩連續(xù)對比中互相協(xié)調(diào)的作用。正如李廣元所說:“這種由視覺為主自動建立的連續(xù)對比和同時對比,使色彩感覺建立了豐富的層次。”[6]137在李娟對綠色牧場的書寫下,強烈的感情推動和引導,使其表現(xiàn)出了牧民轉(zhuǎn)場遷徙過程中的自然空間空間場域所帶來的審美感受。
從李娟對色彩的書寫來看,色彩不僅在于反映事物的內(nèi)容,更在于喚醒著情緒與情感。李娟對“綠色”強烈的抒情,表達出了李娟在自然中強烈的情感沖動與情感指向。李娟在《通往一家人去的路》中寫道:“站在山頂上往下看,整條河谷開闊通達,河流一束一束地閃著光,在河谷最深處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綠的,沼澤是更綠一些的綠,高處的森林則是藍一樣的綠。我愛綠色。為什么我就不能是綠色的呢?我有淺色的皮膚和黑色的頭發(fā),我穿著鮮艷的衣服。當我呈現(xiàn)在世界上時,為什么卻不能像綠那樣……不能像綠那樣綠呢?我會跑,會跳,會唱出歌來,會流出眼淚,可我就是不能比綠更自由一些,不能去向比綠所能去向的更遠的地方。”[5]192在這一段李娟對“綠色”的自白中,“綠色”代表著草原、沼澤、森林等一切綠色的事物,同時也象征著生命的綿延不絕與蓬勃生機,更象征著自由、澎湃、奔騰、熱烈以及原初的生命沖動。這一段關(guān)于“綠色”的書寫可以說是李娟散文的注解,從對綠色的書寫到對綠色的情感表露,是李娟對自然空間色調(diào)進行審美活動的結(jié)果,是對客觀色彩進行視覺的純化與心靈多重體驗的結(jié)果,在這一過程中,李娟借由綠色的書寫實現(xiàn)了感情在主體內(nèi)外的和諧。
2.3 多重色彩營造散文的意境空間
色彩之間的對比涉及色彩的飽和度、滲透性、映襯以及擴散的對比。在李娟的散文書寫中主要表現(xiàn)為不同色相的對比以及不同事物之間的色彩映襯,并在色彩的書寫中構(gòu)建起了其散文寫作的意境空間。
首先,李娟通過金色與藍色不同色相的純度對比突出秋天意境的遼闊感。“色相對比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設(shè)色的主要方法。這種色彩結(jié)構(gòu)比較典型的特征是視覺效果莊重穩(wěn)定。各種純正的飽和色相在整個色彩結(jié)構(gòu)中,仍然各自放射著自身的本質(zhì)色性。”[6]96李娟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寫道:“面對這全部的金色,葵花緩升寶座,端坐一切金色的頂端。這初秋的大地,過于隆重了。以致天地欲將失衡,天地快要翻轉(zhuǎn)。天空便只好越來越藍,越來越藍,越來越藍。”[7]初秋的大地布滿金色,而頭頂?shù)奶炜諈s是越來越藍,大地之金與天空之藍的對比,純粹的色彩碰撞潑墨出自然之顏色的澎湃與傾覆,也在色彩的對比中渲染出了濃烈的情感。在李娟的色彩描寫中,藍色的色相清晰,明度與清晰相對適中,呈現(xiàn)出了一種秋高氣爽的審美感受;金色的色相明麗燦爛,明度與清晰度較高,呈現(xiàn)出了一種大地沉穩(wěn)有力的審美感受。在金色與藍色兩種強烈的色彩對比中,逐漸拉開了天和地的距離,著力營造出了一種秋天“天高氣爽”的意境空間。
其次,李娟通過不同植物之間色彩的映襯書寫展現(xiàn)出了森林之中花草的豐富靈韻。在“羊道三部曲”中森林深處的各色小花競相綻放,色澤濃艷、黃到發(fā)橙的蒲公英;巖石峭壁上隨風飄揚不知名的白色的花;深山處開在木屋頂上又深又濃的白色、藍色以及黃色的虞美人;對岸森林中齊腰的白色花海;山谷里艷艷開著的紅色和粉紅的花;河邊幽幽生長的藍紫的鳶尾;森林邊陰涼之處的簇擁在枝頭深紅的野牡丹等等都與天空的藍、森林的綠、幽暗墨綠的河流構(gòu)成了一種色彩的映襯。森林幽谷之中的野花在李娟的注視中,被賦予色彩、被投射情感,雖無名盛開但自在嬌艷。花朵的色彩的附著靈韻,似乎遠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卻是如此貼近,由此,獨特的審美感受產(chǎn)生,自然的靈韻光輝也顯現(xiàn)了出來。
最后,李娟通過冷暖色彩的對比凸顯出了游牧民族在森林生活的孤獨感。《林海孤島》一篇寫到達深山夏牧場之后的孤獨體驗,穿紅衣的加依娜獨自蕩起秋千,面對大山的綠意蒼茫;而“我”和卡西則孤獨地穿梭在吾賽的森林中,此時的卡西則穿紅雨鞋輕快地走在前面,“我”卻感覺到一絲的孤寂與失落之感。[1]4+9紅雨鞋的鮮艷亮麗與森林的深沉墨綠構(gòu)成了一種強烈的色彩對比,反而映襯出一種身處森林無人問津的孤獨感與寂寞感。正如出現(xiàn)在森林的紅雨鞋象征著外來的沖擊力量,似乎暗示著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的逐漸消亡。李娟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消亡過程中的撼動力量,鮮艷的紅雨鞋作為一個視覺意象所帶來的情緒體驗聯(lián)結(jié)著過去與未來的生存模式的衰亡與轉(zhuǎn)換,揭露出了一個游牧民族生活轉(zhuǎn)型中新世界的一方面,暗示了一個新的時代與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記得韓子勇先生在《文學的風土》一書中寫到:“文學的形式感,是以現(xiàn)實的形式感為基礎(chǔ)的,文學家面對的是一個與人們的經(jīng)驗世界相符合的幻覺世界,在這瑰麗的幻覺世界當中,一定有一條通過實證的隱秘道路”[8]在李娟的散文中,其以北疆綠洲地理中的色彩感覺為基礎(chǔ),構(gòu)造出了綠洲地理自然的色彩表現(xiàn)形式,并由此顯現(xiàn)出了李娟散文中自然色彩與人的情感感覺異質(zhì)同構(gòu)的特征。
3 李娟散文中綠洲地理色彩書寫的意義闡釋
在李娟散文的書寫中,色彩具有區(qū)域地理文化的特征,并成為綠洲地理風貌的展現(xiàn)。其中,在李娟的散文中綠色的書寫占據(jù)絕對的地位,一方面,在新疆干旱與半干旱的沙漠地帶,偏重綠色,將綠色視為生命的顏色;另一方面,對綠色的書寫也成為了一種具有人文色彩與審美偏向的美學表達與美學感受。在李娟的散文書寫中,“綠色”,是生命書寫的內(nèi)蘊表達、是審美情感的召喚共鳴。“綠色”作為自然萬物之生機的原色,在李娟的散文書寫中得到了還原,并重新構(gòu)筑起了自然、生命、情感之間的深層內(nèi)蘊與審美召喚,這也是人的全面精神在李娟色彩書寫中的升華。
3.1 綠洲生命書寫的內(nèi)蘊表達
趙樹勤在《當代女性書寫與現(xiàn)代繪畫色彩美學》一文中表示:“色彩實在就是人類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轉(zhuǎn)述和體現(xiàn),它與人類生命同構(gòu)對應(yīng),色彩即生命。”[9]在李娟的色彩書寫中,綠色寄予著綠洲書寫的生命內(nèi)蘊的表達。從森林到沼澤再從草原到耕地,河流的綠色運動綿延出一條生命之河。森林中的苔蘚馬匹、游牧的牧民牛羊、耕地上的向日葵、勞動的農(nóng)人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與生活形式都構(gòu)成了以“綠色”作為生機與活力的生命書寫。李娟散文中將“綠”之生機著墨于“綠”之自然萬物,并經(jīng)由“綠色”建構(gòu)起了李娟散文中對生命書寫的內(nèi)蘊表達。
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一書中通過向日葵的綠色生長以及我母親旺盛的金色力量展現(xiàn)了北疆戈壁上最強勁的生命力。向日葵地中綠色的蓬勃生長來之不易,經(jīng)過三次被毀,三次重種,終于長出了綠芽。隨著整個向日葵的生長,整片大地由空無一物,逐漸旺壯,一片綠色的海洋也在荒野中拔地而起,隨著葵花越來越繁茂,整片地也呈現(xiàn)出一片金色。而我的母親赤身扛鐵鍬穿行在葵花地里,葉隙間陽光跳躍,腳下泥土暗涌。向日葵綠色的枝葉,形成綠色的海洋,花盤金光四射,行走在萬物生長的土地上的母親,赤身裸體仿佛也是帶著金光的地母。母親茁壯、健康、蓬勃的生命與這片蓬勃生長的金色的向日葵地相互輝映,呈現(xiàn)出了土地、植物、人類廣大的生命力,而綠色、金色作為色彩的描寫,也構(gòu)建起了這最打動人心的生命力量的呈現(xiàn)。李娟在這部散文中選擇綠色與金色作為書寫的主色調(diào)展現(xiàn)出了其對色彩書寫的升華呈現(xiàn),達到了寫作主體自身的全面感覺,感情想象、意志表現(xiàn)等精神因素的高度協(xié)調(diào),實現(xiàn)了自己作為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意義。
在《我的阿勒泰》(圖2、圖3)一書中深入草原牧場,從牧民到馬匹再到苔蘚,從人類到動物、到植物其以噴薄的綠色為主的生命力,都給人以巨大的感染力。《我的阿勒泰》中寫森林中的綠色,“那些幽暗寂靜的密林——里面深深地綠著,綠著……那樣的綠,是瞳孔凝聚得細小精銳的綠。無論移動其中,還是靜止下來,那綠的目光的焦距總是準確地投在我們身體上的精確一點——我們呼吸的正中心……那綠,綠得有著最最濃烈的生命一般,綠得有著液體才有的質(zhì)地。”[5]196森林中的綠色是如此的攝人心魄,投射在我們的呼吸中,仿佛我們的呼吸也是同森林的呼吸一般,正是這綠色使李娟感慨,“綠得有最最最濃烈的生命一般”,綠色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基于森林中的一切存在,構(gòu)成了這蓬勃而有力的綠色脈動。在羊道三部曲中,李娟在一個寧靜悠長的下午走進森林,她看到了沼澤邊的綠色植物有著巨大的葉片;樺樹林的干爽明亮與深綠色的暗林形成對比;楊樹林的青翠似少女般驕傲;一個極微小的綠點竟是一條小小青色肉蟲。在李娟散文中對綠色的大量書寫不會讓人感到疲乏,這是因為森林中的動植物都有著生命的綠色,并表現(xiàn)出了不同狀態(tài)、情致下的綠色,呈現(xiàn)出了生命的自在自由、旺盛蓬勃。
3.2 綠洲審美情感的召喚共鳴
在李娟的散文中由色彩所帶來的情感召喚與情感共鳴,呼吁著人們回到自然,回到純粹。在李娟的書寫中呈現(xiàn)出的自然的廣闊與自由,生命的蓬勃與力量都成為一種審美情感的召喚。在李娟的散文書寫中可以看出其將色彩之自由感揮灑在自己的散文中,并著力呈現(xiàn)出這種自由,這種自由經(jīng)由生命書寫,而揮灑到自然萬物之中,并充分讓自然顯現(xiàn)。這種將自然萬物凝聚為色彩原色的書寫,指向的是一種主客體相互交融,相互建構(gòu)的美學沖動,同時也指向的是文學作品對讀者審美情感的召喚共鳴。李娟在對“綠色”的寫作中,試圖從觀看角度、視覺體驗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調(diào)動讀者的感受方式,使讀者在審美閱讀中達到一種全身心的體驗感和融入感,在對一棵樹、一棵草的慨嘆與書寫中使讀者充分感受到自然的自由與遼闊、蓬勃與生機。
正如《阿勒泰的角落》(圖4)一書中寫道:“還有那些沒什么花開的植物們,深藏自己美麗的名字,卻以平凡的模樣在大地上生長。其實它們中的哪一株都是不平凡的。它們能向四周抽出枝條,我卻不能;它們能結(jié)出種子,我卻不能;它們的根深入大地,它們的葉子是綠色的,并且能生成各種無可挑剔的輪廓,它們不停地向上生長……所有這些,我都不能……植物的自由讓長著雙腿的任何一人都自愧不如。首先,綠色就是大地上最廣闊、最感人的自由呀!當我們看到綠色,總是會想:一切都不會結(jié)束吧?”[10]從對植物的感性認知到對植物綠色的情感抒發(fā),李娟對色彩的運用也從客觀認知過渡到了主觀感受,由此進入色彩全面感覺的后期階段,即“藝術(shù)家可以通過直覺不斷發(fā)現(xiàn)色彩感覺的本質(zhì)特征”[6]139。在主體和客體、人類和自然一體性的交流中,色彩感覺全面升華,成為一種穿透內(nèi)外存在的力量。“對外,它有一種直趨自然本質(zhì)的發(fā)現(xiàn)力量,對內(nèi),它認識到自己作為自己特有的感覺豐富性。內(nèi)外感覺充實使人全面實現(xiàn)感覺的自由。”[6]139在這種狀態(tài)下,色彩藝術(shù)達到了獨立表現(xiàn)人的精神的階段,人與植物之間進行了聯(lián)結(jié),綠色成為了表現(xiàn)生命力的純粹色彩形式,展現(xiàn)了其全部精神的活力與覺醒。
4 結(jié)語
縱觀李娟散文中綠洲地理的色彩書寫,綠、藍、金三色是其寫作的主色調(diào)。本文通過對其描寫空間中色彩的交融碰撞、單一色彩渲染情感氛圍、多重色彩營造意境空間這三種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分析,闡明揭示出了李娟散文書寫的生命蘊含以及審美召喚在文本中的呈現(xiàn)特點。總體而言,李娟散文中的色彩書寫呈現(xiàn)出了新疆綠洲地理的色彩風貌,以親和自然的原色書寫展現(xiàn)出了色彩之美,并重新喚起了我們對自然色彩的感官體驗與美學認知。在這一過程中,李娟散文的色彩書寫呈現(xiàn)出了一種從感覺精神層面的色彩反映到感情精神層次的色彩表現(xiàn),以及人的全面精神在色彩藝術(shù)中的升華的三階段,展現(xiàn)出了其色彩書寫的藝術(shù)道路。
5 參考文獻
[1]李娟.深山夏牧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李娟.春牧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3]李娟.前山夏牧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81.
[4][9]趙樹勤.當代女性書寫與現(xiàn)代繪畫色彩美學[J].東方論壇(青島大學學報),2000(03):56-60.
[5]李娟.我的阿勒泰[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
[6]李廣元.東方色彩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美術(shù)藝術(shù)出版社,1986.
[7]李娟.遙遠的向日葵地[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175.
[8]韓子勇.文學的風土[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5.
[10]李娟.阿勒泰角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