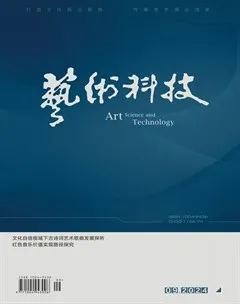箏曲《箜篌引》的詩意表達(dá)探析


摘要:目的:古箏藝術(shù)有著悠久的歷史,在長(zhǎng)期的歷史發(fā)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演奏經(jīng)驗(yàn)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奏技法,隨著近現(xiàn)代中西音樂文化的融合,古箏演奏和創(chuàng)作有了新的思路。《箜篌引》是一首從唐代“詩鬼”李賀所作古詩《李憑箜篌引》中汲取樂思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古箏曲。該曲由四部分組成,與詩歌聯(lián)系,并突破傳統(tǒng)五聲調(diào)式,采用非傳統(tǒng)五聲音階定弦,以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技法展現(xiàn)出《李憑箜篌引》的浪漫意蘊(yùn)。文章側(cè)重分析箏曲作品、箏曲的藝術(shù)表達(dá)與詩意表達(dá),以深入剖析箏曲《箜篌引》,為同領(lǐng)域的演奏者和學(xué)習(xí)者提供參考,促進(jìn)古箏藝術(shù)的傳承與發(fā)展。方法:第一,文獻(xiàn)研究法:通過對(duì)大量文獻(xiàn)資料的閱讀、整理、分類,系統(tǒng)梳理和分析現(xiàn)有關(guān)于箏曲《箜篌引》的學(xué)術(shù)文獻(xiàn),以及《李憑箜篌引》的歷史資料,旨在構(gòu)建研究的理論基礎(chǔ)。第二,比較研究法:利用音視頻軟件觀看和聆聽各演奏家的版本,分析力度、速度、情感,以揭示不同演奏家在音樂處理和情感表達(dá)上的具體差異。第三,實(shí)踐研究法:通過自身的演奏實(shí)踐,結(jié)合文獻(xiàn)研究和專業(yè)交流,提煉出主觀感受與客觀分析相結(jié)合的綜合性結(jié)論,以期對(duì)《箜篌引》的演奏藝術(shù)和詩意表達(dá)進(jìn)行深入探討。結(jié)果:箏曲《箜篌引》是一首大量運(yùn)用西方創(chuàng)作技法,體現(xiàn)中國(guó)詩詞美學(xué)的作品。得益于古詩《李憑箜篌引》,箏曲《箜篌引》也具有浪漫且唯美的氣息,體現(xiàn)出詩樂融合之美。結(jié)論:箏曲《箜篌引》具有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達(dá)與浪漫氣韻,深刻理解此箏曲的文化內(nèi)涵,可在探索和追求美的過程中提高自身演奏技巧,掌握古箏藝術(shù)的真諦,使作品得到真正的藝術(shù)升華。
關(guān)鍵詞:箏曲;? 《箜篌引》;? 《李憑箜篌引》;詩意表達(dá)
中圖分類號(hào):J632.32;J61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4)09-000-03
1 概述
1.1 箏曲《箜篌引》簡(jiǎn)介
《箜篌引》是作曲家莊曜創(chuàng)作的一首現(xiàn)代箏曲[1]。莊曜是國(guó)內(nèi)較早使用計(jì)算機(jī)創(chuàng)作音樂作品的人,其擅長(zhǎng)打破均衡變化的節(jié)奏型,運(yùn)用豐富的織體并結(jié)合管弦樂進(jìn)行創(chuàng)作,作品曾兩度獲得金鐘獎(jiǎng)[2]。莊曜采取西方的作曲手法來體現(xiàn)東方魅力,憑借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思維和作曲技法,譜寫了眾多聞名于世的現(xiàn)代古箏曲,在業(yè)內(nèi)有巨大的影響力。
箏曲《箜篌引》改編自唐代“詩鬼”李賀的《李憑箜篌引》,體現(xiàn)了世紀(jì)末繁花綻放之后凋零頹廢的美學(xué)狀態(tài)[3]。該樂曲突破了傳統(tǒng)的民族五聲調(diào)式,采用非傳統(tǒng)的五聲音階定弦,使風(fēng)格和體裁更具特色。該樂曲由“較自由的散板”段落、“聯(lián)想般的慢板”段落、“活潑的快板”段落、“遼闊的廣板”段落四個(gè)部分組成,與詩歌內(nèi)容相聯(lián)系,并突破傳統(tǒng)的民族五聲調(diào)式,引入非傳統(tǒng)五聲音階定弦,更能夠體現(xiàn)音樂主題與現(xiàn)代創(chuàng)作的特點(diǎn)。李賀的詩歌光怪陸離、獨(dú)具特色。一方面有著意氣風(fēng)發(fā)之氣勢(shì),另一方面又有低落消沉之傷感;一方面展露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另一方面彰顯活在當(dāng)下的頹廢之美。
《箜篌引》被選為第9屆及第11屆中國(guó)音樂金鐘獎(jiǎng)古箏比賽復(fù)賽指定曲目,以及2003年和2005年全國(guó)民族器樂獨(dú)奏比賽中古箏專業(yè)組的指定參賽曲目[4]。
過去,古箏演奏中左手基本發(fā)揮潤(rùn)飾作用,右手演奏技術(shù)也相對(duì)單一。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古箏創(chuàng)作百花齊放。莊曜加大了創(chuàng)新力度,打破傳統(tǒng)五聲調(diào)式的局限,設(shè)計(jì)出全新的調(diào)式,使箏曲定弦時(shí)就為轉(zhuǎn)調(diào)做好了準(zhǔn)備,對(duì)傳統(tǒng)調(diào)式色彩有一定程度的偏離。其在傳統(tǒng)素材的基礎(chǔ)上嘗試創(chuàng)新,促進(jìn)演奏技法的變革,使演奏新作品的選手走上了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道路。
1.2 箜篌簡(jiǎn)介
箏曲再現(xiàn)的樂器是古老的漢樂器箜篌。箜篌作為一種有著悠久歷史的樂器現(xiàn)已失傳[5]。在唐代,箜篌分為豎箜篌、臥箜篌、鳳首箜篌(見圖1),臥箜篌的樣式更像古箏。箜篌有著歷史的厚重感、悲涼感。由于沒有人知道唐朝時(shí)期的箜篌會(huì)發(fā)出什么樣的聲音,也沒有辦法真正聽到當(dāng)年的箜篌聲,所以唯有根據(jù)詩句“芙蓉泣露香蘭笑”“石破天驚逗秋雨”等展開想象。
2 《箜篌引》的藝術(shù)表達(dá)
2.1 動(dòng)機(jī)變奏
樂曲的快板部分,在一個(gè)動(dòng)機(jī)之上進(jìn)行四次變奏,織體變化的同時(shí)帶來多層次的聽覺感受。第一次變奏由一句由輕到重、由弱漸強(qiáng)的拍板開始,拍板之后的一句變得非常厚重,滑音也突然加重,富有節(jié)奏感,給人靈動(dòng)的感覺,右手集中在中低音區(qū)彈奏,塑造雄偉深沉的音樂形象,節(jié)拍則在四拍與二拍之間來回轉(zhuǎn)換。第二次變奏通過一個(gè)刮奏轉(zhuǎn)向中音區(qū),速度也稍稍加快,右手由單音變?yōu)殡p音甚至三音,立體感增強(qiáng)。左手伴有較為密集的掃弦,使音樂情緒更為高漲[6]。第三次變奏將音區(qū)又拔高一個(gè)八度,右手在高音區(qū)演奏旋律部分,左手則在低音區(qū)伴奏并輔以刮奏點(diǎn)綴,增強(qiáng)音樂的多樣性、層次感。第四次變奏左右手互換,由左手擔(dān)任旋律聲部,右手擔(dān)任伴奏聲部,充滿交替感,有線條、有起伏。四次變奏增強(qiáng)了聽覺上的層次感、立體感,這種動(dòng)機(jī)變奏的手法典型當(dāng)數(shù)貝多芬的《命運(yùn)交響曲》,即用一個(gè)極小的動(dòng)機(jī)不斷變奏、不停發(fā)展。
箏曲《箜篌引》運(yùn)用動(dòng)機(jī)變奏的手法,加之變化多端的拍號(hào),由4/4拍轉(zhuǎn)到2/4拍,再轉(zhuǎn)回4/4拍,再到3/4拍,最終回到4/4拍,以及富有動(dòng)感的拍擊手法,如用右手指腹拍擊琴碼右側(cè)低音區(qū)琴弦,用左手手掌拍擊琴碼左側(cè)中高音區(qū)琴弦,均帶有舞蹈的律動(dòng)性,引人遐想。結(jié)尾處為規(guī)律的掃弦,在力度與速度的共同推動(dòng)下,音樂情緒達(dá)到頂峰,最終整首箏曲在左右手強(qiáng)而有力的花指中以恢宏的氣勢(shì)完美結(jié)束。箏曲《箜篌引》將西式變奏手法與古箏巧妙結(jié)合,“洋為中用”,體現(xiàn)了中國(guó)音樂的獨(dú)特韻味[7]。
2.2 虛實(shí)結(jié)合
箏曲《箜篌引》的節(jié)奏和速度是多變的,旋律則采用虛實(shí)結(jié)合、若有若無的線條,契合詩句“空山凝云頹不流”[8]。箏曲采用了多個(gè)六連音,連續(xù)而不激進(jìn),似乎在流動(dòng)又似乎逐漸放慢,賦予了云彩生命力,展現(xiàn)出“頹不流”的狀態(tài)。
“女媧煉石補(bǔ)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mèng)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此兩句描繪了如夢(mèng)如幻的場(chǎng)景,作者通過富有生機(jī)的律動(dòng)、輕快靈動(dòng)的韻律,加之現(xiàn)代作曲技法將其體現(xiàn)出來。左右手分別在琴碼兩側(cè)交替拍擊琴弦,左手掃弦后迅速用手掌側(cè)面止音以營(yíng)造戛然而止的感覺,右手八度大撮加上左手低音區(qū)掃弦增強(qiáng)音樂立體感,右手富有線條感的遙指旋律配以左手跌宕起伏的刮奏以及恢宏果斷的掃弦,旋律基本上為幾小節(jié)的旋律音型重復(fù)、拓展以及變奏,體現(xiàn)多樣的旋律線條,營(yíng)造出“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情景[9],充分表現(xiàn)了音樂的華麗。
樂曲后半部分以左右手虛實(shí)融合的演奏為技術(shù)基礎(chǔ),李賀內(nèi)心跌宕起伏的情感也通過別具一格的作曲手法體現(xiàn)出來。在右手旋律線清晰的基礎(chǔ)上,輔以左手虛幻縹緲、若有似無的單音,讓人覺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10]。
2.3 小二度音程使用
箏曲《箜篌引》在調(diào)式設(shè)置上采用半音音階[11],以變化多端的節(jié)奏與技法來表現(xiàn)光怪陸離的音樂形象,尤其用小二度設(shè)置定弦(見圖2),設(shè)定每個(gè)八度都有兩個(gè)小二度的音階,雖然增加了調(diào)弦的難度,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音色效果。這樣的定弦設(shè)置,體現(xiàn)了唐朝音樂中與西域有關(guān)的元素,也讓人聯(lián)想到箏曲《西域隨想》中的定弦,體現(xiàn)出了異域風(fēng)情[12]。
魏晉南北朝時(shí)音樂大融合,多部樂在唐代較為盛行。唐朝是燕樂、雅樂和胡樂三樂鼎立的朝代,而胡樂在唐朝特別盛行[13]。箏曲《箜篌引》最大的特點(diǎn)是大量使用小二度音程,營(yíng)造出的和聲效果與漢樂的中正平和形成了鮮明反差,展現(xiàn)出異域風(fēng)情。《箜篌引》運(yùn)用創(chuàng)新型的人工定弦而非傳統(tǒng)民族五聲音階,在巧妙傳達(dá)中國(guó)樂器神韻的同時(shí),彰顯了作曲家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的精神,引發(fā)聽者的無限聯(lián)想。
3 《箜篌引》的詩意表達(dá)
3.1 李賀“物思神游”的創(chuàng)作思維
李賀被譽(yù)為“詩鬼”,他的詩不按常理出牌,充滿了靈動(dòng)的意象。李賀辭藻華麗、充滿想象的詩風(fēng)源于其嚴(yán)謹(jǐn)認(rèn)真、一絲不茍的作詩態(tài)度[14]。
李賀的性格非常矛盾,其在極度自信和極度自卑的切換中度過了短暫的一生。李賀既有意氣風(fēng)發(fā)之面貌,又有悲傷消沉之思緒;既有樂觀豁達(dá)的雄志,又有壯志未酬的慘境;既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又有活在當(dāng)下的人生態(tài)度。李賀描述音樂的方式獨(dú)具特色,他用想象力豐富的比擬和聯(lián)想呈現(xiàn)音樂的浪漫主義色彩,令人驚嘆不已[15]。
“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描寫了箜篌眾弦齊鳴的審美體驗(yàn),它的聲音清脆悅耳,仿佛昆山之玉相互擊打碎裂,樂聲舒緩柔美,直入人心[16]。聲音極具畫面感,緊接連音的彈撥,仿佛清雅的蘭花在爭(zhēng)相綻放,向人們展示了《箜篌引》的音樂意境。
3.2 詩與樂的情感體驗(yàn)融合
“石破天驚逗秋雨”中“秋雨”的絲絲寒意使李賀聯(lián)想到了自身遭遇,是詩人聽到箜篌演奏后的內(nèi)心獨(dú)白。箏曲運(yùn)用緊湊嚴(yán)謹(jǐn)?shù)目焖冱c(diǎn)彈技巧,右手清晰的單音點(diǎn)狀旋律音與左手食指的同音重復(fù)相結(jié)合,后又加入左右手交替小撮的技法,增強(qiáng)了音樂的和聲效果與立體感,隨著音樂的進(jìn)行時(shí)起時(shí)落。
樂曲也對(duì)“吳質(zhì)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一句作了處理,尤其在主旋律再現(xiàn)的部分表達(dá)了李賀內(nèi)心不屈的精神[17]。箏曲《箜篌引》中,右手強(qiáng)而有力的高密度遙指伴隨左手將刮奏和掃弦相結(jié)合,將音樂情緒推向高潮。
4 詩樂氣韻
4.1 詩樂結(jié)合
箏樂在漢魏六朝時(shí)已趨于成熟[18],它是雅俗文化的融合,到了唐朝,這種融合便成為社會(huì)現(xiàn)象,成為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詩中有樂、樂中有詩的審美體驗(yàn)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如《長(zhǎng)相思》《定風(fēng)波》《如是》《楓橋夜泊》等都是以古代詩詞為素材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箏曲[19]。
4.2 左手做韻
中國(guó)音樂以五聲性為主,宮音長(zhǎng)且韻律感強(qiáng),體現(xiàn)了中國(guó)人戀家的情結(jié)。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古詩于古箏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做韻最能引起強(qiáng)烈共鳴。
左手做韻在古箏藝術(shù)中是極具生命力的體現(xiàn),這需要在彰顯情感的基礎(chǔ)上設(shè)定每一處指法的“韻點(diǎn)”[20]。左手做韻的韻味在箏曲《箜篌引》尤其是慢板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慢板中多次運(yùn)用到左手押韻的技法,但每次的韻不盡相同:有時(shí)需要左手輕盈活躍地輕壓琴弦;有時(shí)則只需要在余音即將消逝時(shí)輕揉琴弦以點(diǎn)綴修飾;有時(shí)又需要左手快速有力地上滑,果斷迅速地回起,以豪氣的姿態(tài)表現(xiàn)出電閃雷鳴的意境。在箏樂作品中,韻是樂曲的風(fēng)貌、氣質(zhì),韻聲雖然會(huì)消失,但利于演奏者和聽眾超越自我,最終達(dá)到心靈的審美愉悅[21]。
5 結(jié)語
器樂演奏的最高境界便是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音樂意境,但音樂是一種抽象藝術(shù),看不見也摸不著。因此,演奏者需要調(diào)動(dòng)想象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yǎng),深刻理解作品的文化內(nèi)涵,在探索和追求美的過程中提高自身實(shí)力,以努力塑造出栩栩如生的音樂形象,使箏曲作品得到真正的藝術(shù)升華。
參考文獻(xiàn):
[1] 吳思瑤,翟慶玲.箏曲《箜篌引》創(chuàng)演特色與美學(xué)價(jià)值探究[J].參花,2023(5):107-109.
[2] 魏俊琪.古箏特殊定弦與樂曲調(diào)式調(diào)性探究[D].西安:西安音樂學(xué)院,2019:43.
[3] 王春鳴.由技入道:試論古箏演奏家任潔的音樂美學(xué)風(fēng)格[J].黃河之聲,2016(20):114-116.
[4] 雷蕾.意象中的舞者[D].南京: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2005:21.
[5] 楊媛.新時(shí)代高校古箏教學(xué)改革的新思路:評(píng)《文史談古箏》[J].中國(guó)教育學(xué)刊,2022(6):154.
[6] 曾瑞雯.淺析箏曲《箜篌引》的演奏風(fēng)格與詩情意境[J].黃河之聲,2023(8):66-69.
[7] 涂永梅.箏樂創(chuàng)作中調(diào)式的傳統(tǒng)與(下轉(zhuǎn)第頁)
(上接第頁)創(chuàng)新問題[J].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音樂及表演版),1996(2):42-47.
[8] 丁國(guó)鋒.李賀《李憑箜篌引》的藝術(shù)想象魅力[J].語文教學(xué)與研究,2021(20):74-75.
[9] 何玉.李賀《李憑箜篌引》的音樂美學(xué)思想探析[J].中國(guó)音樂,2006(4):191-193.
[10] 吳姿嫻,趙星.從箏曲《箜篌引》看中國(guó)音樂審美趨向[J].樂器,2022(10):33-35.
[11] 趙文婷.建國(guó)后古箏教材的構(gòu)建與發(fā)展沿革研究[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2012:39.
[12] 張麗娜.現(xiàn)代創(chuàng)作箏曲中古箏與少數(shù)民族音樂融合現(xiàn)象之研究[D].貴陽:貴州師范大學(xué),2017:76.
[13] 薛蓮.新時(shí)期古箏表演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探究:評(píng)《文史談古箏》[J].中國(guó)教育學(xué)刊,2020(2):127.
[14] 劉明.《李憑箜篌引》“鬼神之辭”的風(fēng)采與張力[J].中學(xué)語文教學(xué)參考,2022(30):89-90.
[15] 任動(dòng).對(duì)小說藝術(shù)持續(xù)探索的努力:谫論李清源長(zhǎng)篇小說《箜篌引》[J].新疆藝術(shù)(漢文),2023(6):4-11.
[16] 高宏雨.古箏曲《箜篌引》的詩樂融合研究[D].貴陽:貴州師范大學(xué),2017(5):58.
[17] 李冰.箏曲《箜篌引》中的詩意表達(dá)[J].黃河之聲,2019(4):13-14.
[18] 徐天祥.思?xì)v史論功過 重評(píng)往事話得失:讀居其宏新著《新中國(guó)音樂史》[J].中國(guó)音樂,2005(1):160-162.
[19] 馮長(zhǎng)春.在批評(píng)中構(gòu)筑歷史:居其宏著《新中國(guó)音樂史》讀后感[J].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音樂與表演版),2004(2):107-109.
[20] 牛春雨,李皖.“音樂復(fù)現(xiàn)法”教《李憑箜篌引》[J].語文建設(shè),2023(5):69-72.
[21] 王安國(guó).《新中國(guó)音樂史》居其宏著[J].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3):108-110.
作者簡(jiǎn)介:唐歆慧 (1999—),女,研究方向:音樂(古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