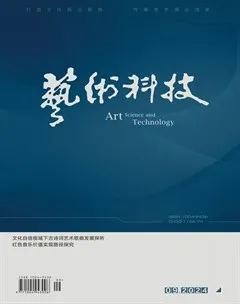“六要論”的內涵與山水畫創作
摘要:目的:在《筆法記》中,荊浩提出備受矚目的“圖真說”,這一理論的核心正是他提出的“六要”原則。文章聚焦荊浩的山水畫理論——“六要論”,深入探討其內涵與對山水畫創作的影響。方法:文章深入剖析《筆法記》中的“六要論”,對其核心思想進行全面細致的解讀。在結合個人閱讀體驗的基礎上,文章系統梳理其中關于山水畫理論的主要觀點,發現其具有深厚的藝術內涵和獨特的審美價值。重視筆勢的流暢與變化、主張筆墨技巧的精湛與獨特、追求真實表達的理念,已經深深烙印在中國歷代畫者的實踐中,對后世的藝術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結果:《筆法記》一書精準提煉了荊浩的創作精髓,深入全面地探討了中國山水畫創作的一系列核心理論問題,為后世山水畫的發展及理論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礎。結論:荊浩長期隱居洪谷山,以自然為靈感之源,他通過深入觀察和深思熟慮,總結出北方山水畫的獨特創作方法,并將其巧妙融入自己的畫作之中。
關鍵詞:? 《筆法記》;? “六要論”;荊浩;創作
中圖分類號:J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9-00-03
0 引言
中國山水畫于唐代萌芽,至五代時期取得長足發展,達到了新的藝術高度。被譽為南宗之祖的王維,以其卓越的才情開創了水墨山水畫的先河,這種以水墨為表現媒介的藝術形式迅速贏得文人墨客的青睞。強調繪畫應致力于追求物象的真實,不僅要精準描繪物體的外在形態,還要深入捕捉其內在的精神實質,使畫面充滿生機與活力。為了實現“圖真”的藝術效果,荊浩認為畫家必須熟練掌握“六要”技法,即氣、韻、思、景、筆、墨六個方面。這些技法相互關聯、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荊浩繪畫理論的核心。如果畫家未能充分掌握這些技法,那么他們所創作的山水畫只能停留在形似的層面,無法達到神似的境界,更難以實現“圖真”的理想。“六要”技法不僅是荊浩“圖真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他經過長期實踐總結出的寶貴經驗。
1 “六要論”形成的背景與內涵
在唐代之前,山水畫創作雖已初見端倪,但人物畫依然穩坐繪畫藝術的頭把交椅。南朝謝赫總結出了一套針對人物畫的“六法”理論,這一理論在后世受到極高的贊譽[1]。直至五代時期,杰出畫家荊浩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藝術造詣,撰寫了《筆法記》這一山水畫論的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荊浩提出畫水墨山水畫的“六要”技法,并對此“六要”進行了深入獨到的闡釋——氣,即心隨筆運,取象精準而不惑;韻,即形神合一,既隱跡又立形,超凡脫俗;思,即提煉精髓,凝想成物,刪繁就簡;景,即因時而畫,搜妙創真,不拘一格;筆,即依循法則,運轉變通,既不拘泥又形神兼備;墨,即深淺相宜,自然成文,品物淺深,文采斐然[2]。
荊浩的“六要”技法與謝赫的“六法”有一定的聯系,其對“氣”和“韻”進行了更為具體的界定,有新的創新與突破。對比二者可以明顯看出,荊浩對氣韻特別重視,他將原本用于人物畫的氣韻概念巧妙引入山水畫創作中,將“六法”中的“氣韻”細化為“氣”與“韻”,其中“思”與“經營位置”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景”則與謝赫“六法”中的“應物象形”和“隨類賦彩”相呼應,至于“骨”則是由“骨法用筆”這一理念演變而來[3]。此外,“六要”還獨具匠心地提出“墨”這一新概念,并將其與其他“五要”并列,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水墨山水畫的發展。這一創新觀點,無疑是荊浩畫論中最能體現其時代特色的地方[4]。
在中國繪畫史上,氣韻始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被視為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對于一幅山水畫而言,其優劣首先取決于其是否具備氣韻。雖然謝赫的“六法”也提及了氣韻,但并未給出具體的解釋。而荊浩則對“氣韻”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闡釋,使其變得更為具體和明確[5]。
在荊浩看來,“氣韻”包含兩層深刻的含義。第一層是指在山水畫中如何巧妙地運用筆墨來展現氣韻;第二層則是關于如何營造出整幅山水畫特有的氣韻。荊浩“六要”中提及的氣和韻,正是對第一層含義的深入闡述,即如何通過筆墨來展現氣韻。對于“氣”的理解,他認為“氣”是畫家作畫時,將自身的氣息融入創作之中,通過手腕的靈活運動表現出來,將自己對客觀物象的真實感受呈現于畫面之上,而不是被物象的外表所迷惑。采用這樣的作畫方式能使畫面氣勢連貫,一氣呵成。至于“韻”,荊浩則解釋為“隱跡立形,備儀不俗”,即在畫面中巧妙隱去痕跡,呈現出自然生動的形態,同時又不失其高雅的儀態。這樣的畫作才能真正達到荊浩所追求的“圖真”境界,實現自然之美與藝術之韻的完美結合[6]。
2 “六要論”在山水畫創作中的應用
“氣韻”不僅是繪畫中不可或缺的技巧,還是構成繪畫作品整體基調的靈魂所在。在繪畫的起始階段,精準把握氣韻尤為關鍵。在中國哲學與美學中,“氣”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韻”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展,其內涵也愈發豐富。到了魏晉時期,“韻”更是被創造性地用于人物品藻中,用以形容一個人的風神、風韻,即內在個性與情調。謝赫提出人物繪畫的首要追求便是“氣韻生動”,將“氣”與“韻”的完美結合視為繪畫藝術的最高境界[7]。荊浩在《筆法記》中明確指出,“思者,刪撥大要,凝想形物”,這里的“凝想”寓意著畫家須全身心投入所繪物象之中,恰如莊子所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8]。這種“凝想”狀態是藝術創作中的關鍵精神層次,它要求畫家通過聯想,篩選并提煉素材,剔除冗余,以精準捕捉最能彰顯物象審美特質的元素。在此過程中,畫家必須摒棄雜念,全神貫注,以揭示物象的本質,進而將其升華為富有審美意蘊的意象[9]。
至于“景”,景的創造須遵循自然的法則,體現四季晨暮的流轉變化。畫家須深入觀察不同季節和時間的山川景物,精準把握其真實面貌,以表現山水的“真”。宋代畫論家郭熙亦強調,山水畫的創作須順應自然節律,展現不同季節的山水風情。要創造出超越畫面本身的藝術世界,蘊含山水的生命力,并彰顯出畫家的精神風貌與境界[10]。“筆”與“墨”作為中國畫之精髓,不僅是構成中國畫藝術特色的核心要素,還是畫家們展現精湛技藝的重要工具。東晉時期的顧愷之以其敏銳的洞察力率先深入探索繪畫用筆,他深刻認識到用筆在表達物象中的關鍵作用,并強調摹象用筆的復雜性與精妙之處,為后世畫家提供了寶貴的啟示,進一步凸顯了用筆在繪畫藝術中的核心地位。這一理論不僅豐富了繪畫技法的內涵,還為畫家們提供了更為明確的創作指導[11]。
荊浩對“筆”的探討則更為深入且全面。在《筆法記》中,他詳細闡述了用筆的法則與變通之道,強調畫家既要熟練掌握用筆的基本技法,又要靈活變通,不被成法所束縛。他提出的“四勢”——筋、肉、骨、氣,不僅是對用筆技法的細化和深化,更賦予了繪畫用筆更豐富的表現力。這一理論框架的提出,無疑拓展了后世畫家們的創作空間[12]。
與謝赫相比,荊浩的探討更為全面和深入。他不僅繼承了謝赫的“骨法用筆”理念,還進一步拓展了用筆技法的內涵和外延,為中國畫用筆技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理論不僅注重筆法的內在精神,還強調筆法與墨色的相互配合,使畫面更加和諧統一[13]。
至于“墨”,中國畫用墨的獨特性堪稱一絕。自唐代王維開創水墨山水畫以來,墨色便成為畫家們推崇備至的表現媒介。荊浩對水墨山水更是情有獨鐘,他認為水墨能夠最大限度表現山水景物的精神本質。他對之前用墨入山水的畫家評價甚高,并在自己的山水畫論中賦予“墨”獨立而崇高的地位。
綜上所述,中國畫中的“筆”與“墨”既是基礎技法,又是藝術特色的重要體現。畫家們通過熟練運用這兩種技法,不僅能夠精準表現出物象的外在形態,還能深入揭示其內在精神和氣韻。荊浩等歷代畫家對“筆”與“墨”的深入探討和實踐,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力,還為后世的繪畫創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啟示。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成果,將永遠閃耀在中國繪畫史上。
3 “六要論”的影響
本文以《筆法記》及其核心——“六要論”為基石,深入挖掘并梳理當時的相關畫論與史料,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討《筆法記》的內涵及其對山水畫創作的深遠影響。這部論著不僅是對繪畫技法的詳盡總結,還是對畫家情感表達的精準提煉與升華。其中,畫筆的輕重、落墨的肆意、行筆的轉折以及運筆的起伏等細微之處,無不成為畫家情感宣泄的關鍵點[14]。
現有的研究資料中對于《筆法記》及“六要論”的探討頗為豐富,以期刊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相對較少。這些研究多從畫作實例出發,以某一畫派或特定作品為例,深入剖析《筆法記》的理論內涵。這種引用闡釋的研究方式,不僅涵蓋了我國古代山水畫的經典之作,如趙伯駒的《江山秋色圖》、南宋梁楷的《潑墨仙人圖》等,還延伸到了近現代山水畫大師的作品,如李可染的《萬山紅遍層林盡染》、吳湖帆的《云表奇峰》等[15]。
盡管《筆法記》篇幅短小,但其美學思想卻深刻影響了中國山水畫理論的發展軌跡。其不僅是畫家們創作實踐的寶貴指南,還是中國繪畫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為人們深入理解和欣賞山水畫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4 結語
荊浩的《筆法記》中,“六要論”詳盡剖析了中國山水畫的繪畫認知過程,并創新性地提出與“寫生”理念相契合的“圖真”概念。這一理論不僅為古典山水畫的藝術精神奠定了基石,還為山水畫審美和品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指導,深刻凸顯了“氣、韻”在東方傳統繪畫中的核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六要”的排列順序并非隨意為之,而是根據繪畫標準的重要性精心安排的。其中,“氣、韻”作為根本,構成畫作的靈魂;“思、景”則要求畫家靈活適應所描繪的對象,創造出具有鮮明繪畫性的形態;而“筆、墨”則通過充滿情感的筆觸和墨法,賦予線條以生命和靈魂。
通過深入對比“寫生”與“六法論”,得以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寫生”在東方美學體系中的地位及其評價標準。東方傳統審美觀念的核心在于通過“寫生”的方式,構建審美內外之間的和諧意境。在這一過程中,“六要論”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荊浩在《筆法記》中所闡述的繪畫美學觀與“寫生”理念密切相關,共同熔鑄成東方傳統繪畫的獨特魅力。
參考文獻:
[1] 張秀秀.“六要”研究[J].藝術家,2024(2):114-116.
[2] 李彥霖.荊浩《筆法記》畫論的理論價值[J].中國美術研究,2023(4):112-117.
[3] 畢峣德.淺析荊浩《筆法記》“六要”在山水畫中的表現與影響:以趙伯駒《江山秋色圖》為例[J].美與時代,2021(12):71-74.
[4] 衛穎.荊浩繪畫美學思想研究[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20.
[5] 張晶.“度象取真”與“畫有六要”:五代荊浩《筆法記》解析(上)[J].名作欣賞,2020(7):122-126.
[6] 武素璞.北派水墨山水鼻祖:讀荊浩《筆法記》有感[J].大眾文藝,2019(23):92-93.
[7] 司淑婷.“寫生”與《筆法記》研究[J].中國文藝家,2018(12):73.
[8] 孫方金.試論《筆法記》在我的山水畫寫生中的指導作用[D].徐州:江蘇師范大學,2018.
[9] 計王菁.論唐宋時期筆墨語言的發展與山水畫的興盛[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18.
[10] 陳鈺膳.淺談謝赫的“六法”與荊浩的“六要”之間的聯系[J].藝術品鑒,2018(5):33-34.
[11] 李樹鋒.荊浩《筆法記》中“六要”的美學意蘊[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6):105-108.
[12] 韓洪展.《筆法記》里的繪畫思想在山水畫寫生中的應用價值研究[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17.
[13] 溫瑋,孫學巧.從自然到創作:荊浩山水畫理論研究[J].統計與管理,2015(10):182-183.
[14] 趙雅坤.荊浩“六要論”與謝赫“六法論”的比較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師范大學,2015.
[15] 牛孝杰.荊浩《筆法記》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2015.
作者簡介:劉豐源 (1997—),男,研究方向:山水畫。